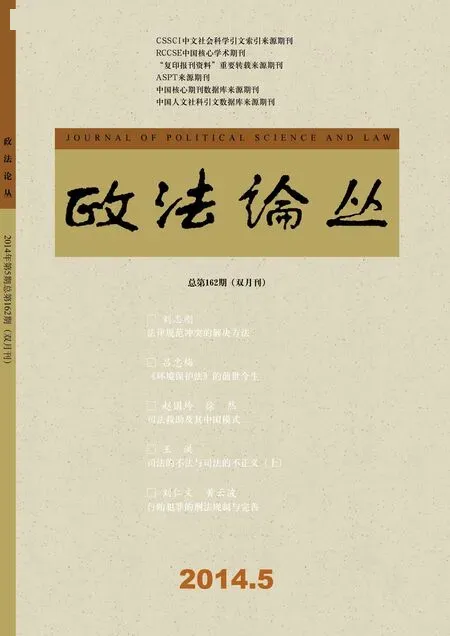限定继承的悖理与我国《继承法》的修正
冯乐坤
(甘肃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源自于古罗马法的限定继承制度是继承人以遗产为限清偿被继承人债务的制度。自古罗马法正式规定了限定继承制度以后,继受古罗马法的近世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继承立法均采纳了此种继承理念,我国1985年制定的《继承法》第33条也同样予以采纳。然而,我国现行《继承法》所规定的限定继承制度在对继承人利益进行保护的同时,却忽视了对被继承人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在借鉴近世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继承立法所设计的财产分离、遗产管理制度、官方清算以及制作遗产清册等不同制度的基础上,继承法学界又提出了若干完善建议[1]P305-314,已经拟定的部分继承法建议稿也进行了相应设计①。其实,古罗马法的限定继承制度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与古罗马继承立法的各种制度理念相互影响的结果。但目前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继承立法已经对古罗马继承立法的各类理念进行了修正,径直规定限定继承制度往往与立法现实相悖。因此,本文特以追溯限定继承制度的生成逻辑为前提,通过诠释限定继承制度的法理悖论,最终为限定继承制度在我国未来的《继承法》修改提供有益的立法建议。
一、限定继承的生成逻辑分析
(一)古罗马法限定继承制度的缘起:概括继承的逻辑演绎
基于维护古罗马时期的家长奴隶制经济,死亡后的家长人格往往由继承人继承,即除了与被继承人的人身相联系的债权、债务或其他权利义务外,继承人要承受被继承人的所有法律关系,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均由继承人概括继承,由此,古罗马早期的继承制度其实就是维护宗法社会的身份继承。随着古罗马后期的奴隶制大庄园经济逐步替代原有的家长奴隶制经济,以往的宗法社会逐渐被商业社会所替代,这就促使人们逐渐将继承客体从身份逐渐转向了财产,身份继承逐步演变为财产继承。但以身份继承为基础的古罗马早期的被继承人人格均由继承人予以概括继承的立法规定却损害了继承人利益,古罗马时期的大法官法通过创设继承人以遗产为限清偿被继承人债务的财产清册制度而予以应对,限定继承制度开始形成[2]P435-436。
就古罗马法创设的限定继承制度的生成逻辑而言,无非是受概括继承逻辑演绎结果的影响所致。一方面,当时的罗马继承制度经历了从身份继承到财产继承的转变,继承对象发生了从被继承人人格到财产的转变,将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一并转移予继承人的概括继承却没有变化,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之和应为遗产[3]P248,遗产范围其实被限定为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另一方面,继承人成为了被继承人的遗产所有人,共同继承人就各自的应继份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所有人,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就成为继承人的债权债务,被继承人的他物权就由继承人享有,被继承人与继承人间存有的债权债务以及他物权也就因混同而消灭。如此,古罗马法的遗产范围就限定为被继承人的权利义务,遗产自继承开始也就归属予继承人所有,被继承人的财产事务的处理就由继承人承担。若存有遗嘱,继承人充当遗嘱执行人,履行被继承人的遗嘱和遗产信托[2]P526-532,即使后来的身份继承演变为财产继承,此种遗产范围以及遗产归属的理念并没有发生变化。
为了避免概括继承对继承人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古罗马后期开始依据继承人的不同而决定是否赋予其接受或放弃继承的选择权。具体言之,自家继承人(家内继承人)是在家长权下而自家长死亡后成为自权人的家属,此类继承人视为继受被继承人之人格,不得拒绝继承;必要继承人是被奴隶主遗嘱解放而负有清偿奴隶主债务的奴隶,作为继承人的奴隶被遗嘱解放附加了清偿奴隶主债务的条件,此类继承人也不得拒绝继承;而家外继承人则可以对是否接受继承进行选择。此外,古罗马后期大法官法也允许自家继承人可以享有放弃继承的权利,只要其在一定期限内发表弃权声明,就不再对被继承人债务负责[4]P469,由此,古罗马后期的继承立法就在一定限度范围之内赋予了继承人享有接受或放弃继承的选择权。既然继承立法已经逐渐允许各类继承人可以拒绝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并没有由继承人予以继承,继承人人格与被继承人人格并没有混同为同一人格,继承人人格与被继承人人格分别独立的立法已经彰显了继承人并不必然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此种立法其实已经将限定继承制度的适用范围加以了限制。但受古罗马法身份继承的影响,除继承人明确予以放弃继承以外,接受继承的继承人势必要承受被继承人的人格。据此,尽管限定继承制度所依存的遗产范围以及遗产归属的理念在古罗马法后期已经逐渐开始动摇,但因当时的继承立法中没有其他制度可以替代限定继承制度,为了对继承人的利益予以保护,限定继承制度也就继续存在。
显然,此种遗产范围以及遗产归属的理念无疑使继承人承担了应由被继承人承担的财产义务,继承人在取得遗产所有权的同时,也负有清偿遗产债务的义务,继承人对遗产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也就在所非问,这极易产生将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两个独立人格视为同一人格的后果。实际上,既然被继承人的遗产归属于继承人所有,被继承人的债务也就理应由继承人承担,但被继承人的债务与继承人的主观状态以及客观行为均无任何关系,由继承人承担被继承人的债务势必损害继承人的利益,故此,古罗马法创设了限定继承制度予以应对。但是,此种立法现实却忽视对被继承人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为此,古罗马法遂又规定了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可以申请将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财产予以分别的制度[2]P527-529。只不过,受遗产范围为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以及遗产归属于继承人所有的理念影响,被继承人债权人的利益仍然无法达到周全保护。
(二)近世大陆法系继承立法的继受与演变
受古罗马法的影响,近世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继承立法纷纷继受了限定继承制度,限定继承制度的前述生成逻辑必然会被继受。具体言之,近世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继承立法在参照古罗马法的遗产范围以及遗产归属理念的前提下,不仅将遗产范围明定为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德国民法典》第1922条、《瑞士民法典》第560条、《日本民法典》第896条之规定②),且又明确规定遗产归属于继承人所有(《法国民法典》第274条、《德国民法典》第1942条、《瑞士民法典》第560条、《意大利民法典》第459条、《日本民法典》第896条)。据此,近世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规定的限定继承制度是以继承人概括承受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为基础,继承人在取得遗产所有权的同时,应负有清偿遗产债务的义务。既然继承人成为了遗产的所有者,遗产所负担的义务理应由继承人承担,继承人对遗产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也就理所当然,只不过,基于继承人的利益保护,继承人以继受的遗产为限而予以清偿遗产债务。进而言之,近世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继承立法均继受了古罗马法中的以身份继承为核心的概括继承,继受基于概括继承而形成的遗产范围以及遗产归属的理念实属必然,此种立法现实也就为设计限定继承制度提供了基础。
为了对继承人的利益进行有效的保护,近世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继承立法又继受了古罗马后期赋予的继承人享有接受或放弃继承的选择权理念,如此,以继承开始后的继承人是否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为标准而形成了当然继承与承认继承的两种立法例。当然继承是指继承人对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无须为接受继承的意思表示,放弃继承则需要明确的意思表示;承认继承是指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须经继承人明确的接受或者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③。因两种立法例对继承人利益保护力度不尽一致,继承立法遂赋予继承人依据自己利益而选择对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是否接受继承或者放弃继承;且接受继承又分为无限继承与限定继承,无限继承是指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债务承担全部责任,限定继承是指继承人以被继承人遗产为限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不过,为了更加周全地对继承人的利益进行保护,继承立法中又出现了接受继受的继承人应承担限定继承的趋势。比如《法国民法典》第782条规定的“数个继承人对接受或者放弃继承达不成一致意见而以有限继承的形式接受”、1994年实施的《魁北克民法典》第625条规定的“继承人承担被继承人债务范围不得超过他们现实取得的遗产价值”就是此种立法趋势的典型代表。
与此同时,古罗马的继承立法创设的限定继承制度虽然达到了避免将继承人与遗产管理人的身份混同为同一人而出现的损害继承人、遗产债权人利益的弊端,但继承开始后至遗产分割期间的遗产容易被私分、转移或隐匿的事实却无法对继承人、遗产债权人利益真正地进行保护。对此,近世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又依据不同情形而设计了负责清理继承开始后的遗产相关诸事务的遗产管理制度。当然,因遗嘱最能充分体现被继承人真实意思,近世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继承立法不可避免地又明确规定了被继承人通过遗嘱所设立的负责处理相关遗产事务的遗嘱执行人制度,最初的遗产管理制度适用范围就仅限定在接受继承与无人继承的类型之中。基于避免此种立法分散规定所容易出现的立法重复弊端,瑞士、埃及、葡萄牙以及我国澳门民法法典开始采纳设立统一的遗产管理制度而将不同继承方式所涉及的遗产处理事务均予以纳入的立法模式,此种遗产管理制度适用范围就包括了遗嘱执行人(遗嘱执行人其实就是遗产管理的特殊方式)。显然,为了达到对继承人以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保护,无论继承立法采纳何种遗产管理制度的立法模式,立法设计遗产管理制度的现实就已经说明立法者已经意识到了限定继承存有制度缺陷;而此种立法态度转变也已经说明限定继承制度无法周全地对继承人以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进行保护,毕竟限定继承仅适用继承人接受继承的情形。当然,大陆法系的继承立法纷纷予以设计遗产管理制度的现实其实已经说明了遗产管理制度可以替代限定继承制度,且两种制度必然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性,对此有必要予以澄清。
二、遗产管理制度与限定继承制度的差异
依前述,近世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继承立法在规定限定继承制度的同时,又规定了遗产管理制度,究其原因,无非是限定继承制度与遗产管理制度的不同立法目的所致。大陆法系立法设计限定继承制度初衷在于纠正概括继承对遗产债权人的过度保护,但限定继承制度又造成了对继承人的过度保护,如何对继承人、遗产债权人的同等保护也就成为了立法设计首先必须要考量的问题。尽管继承立法又设计了将继承人与被继承人财产予以相分离的制度以及继承人负有制作遗产清单义务的遗产清册制度,但仍然无法实现对遗产债权人利益的有效保护,为此,部分国家或地区又采纳了放弃限定继承制度而径直设计了遗产管理制度的立法模式(如魁北克、埃及民法典)。尽管此种制度设计其实与限定继承制度的法律后果具有相似性[5]P271,但却达到了对继承人、遗产债权人的双重保护目的,立法实有必要予以重视。不过,遗产管理制度与限定继承制度仍有差异,理解此点须从遗产管理的制度构造具有的以下两点进行诠释:
其一,继承立法构建的遗产管理制度是以遗产为基础而设计。遗产管理组织并不对遗产享有所有权,仅依据继承立法的规定而享有处理遗产事务的管理权,遗产管理组织也并非继承人、遗产债权人的代理人。此立法基础就在于将遗产视为了独立的主体即财团,遗产管理制度构造中的遗产管理人以及继承人也就对遗产享有管理权[6]。就遗产的法律地位而言,为了避免遗产在继承人未表示接受前处于无主物状态,古罗马法遂将待继承遗产视为了一个独立的团体,使其具有主体地位而承担权利义务。尽管对当时的古罗马法是否赋予待继承遗产具有法人资格存有争议,但赋予待继承遗产具有独立地位却毋庸置疑。受古罗马法对接受继承前的遗产赋予了独立人格的立法理念影响,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均赋予“继承人不明的遗产”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即除接受继承的继承人取得遗产所有权之外,接受继承之前以及拒绝继承乃至继承人不明的遗产均赋予了独立的主体地位④。此种以继承人是否接受继承为标准而对遗产赋予不同地位的立法现实无疑使遗产地位处于复杂化的状态,从古罗马法到目前大陆法系的继承立法并没有对遗产的法律地位达到统一的认识。与此同时,限定继承制度是以继承人接受继承为前提,作为限定继承制度立法基础之一的遗产归属予继承人所有的法律后果必然与丧失继承权、转继承、继承权回复请求权等相关继承制度的法律后果相悖,毕竟诸种相关继承制度均以遗产不归属继承人所有为基本前提;且既然自继承开始的遗产已经归属于继承人所有,遗产归属就已经确定,立法再论及继承遗产也就无任何意义。需要注意的是,接受继承的继承人是以遗产为基础而处理相关的遗产事务,理论与实务中出现的“遗产债务”、“遗产债权”等概念其实就是此种现实的真实反映,遗产其实是被视为了具有独立地位的主体,此种现实必然使以遗产归属予继承人所有为基础的限定继承处于尴尬境地。由此,不论继承人是否接受继承,遗产均具有主体地位,此种现实与遗产管理的制度设计基础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毕竟遗产管理的制度设计是在对遗产地位达到统一认识后所形成的结果。显然,遗产管理制度的立法基础已经包括限定继承制度的立法基础,既然遗产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遗产也就不归属任何人所有,继承立法摒弃限定继承制度固守的遗产归属予继承人所有的理念也就理所当然,限定继承制度的立法基础必然会受到动摇,质疑限定继承制度也就成为必然。
其二,担当遗产管理制度职责的遗产管理人要依次经过清理遗产、清偿遗产债务和遗产分割等程序。就遗产管理人清理遗产的职能范围而言,不仅要整理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也要整理被继承人的财产义务,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均属于遗产管理人所要清理的对象;并且只有在清偿完遗产债务后且有遗产剩余的情形下,继承人才能分割遗产,若遗产不足以清偿债务,遗产就会处于破产境地,继承人也就不会承担任何责任。如此,遗产管理人所面对的遗产范围为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继承人所面对的遗产范围为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不同的遗产范围其实就是以不同继承法律关系主体的角度而进行观察的结果[6]。因现实生活中遗产的多寡并不一致,不加区别地予以构建遗产管理制度只会对继承人、遗产债权人徒增负担,所以,继承立法也就允许继承人担任遗产管理人⑤。但在继承人为遗产管理人的情形下,继承人是以遗产管理人身份出现,继承人与被继承人财产相互混淆的事实容易损害遗产债权人的利益,有必要将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财产分别予以独立⑥。不过,古罗马继承立法并没有明确规定遗产管理制度,继承开始后的遗产归属予继承人所有且由继承人处理所有遗产事务的立法理念其实就是将继承人视为遗产管理人。而继承人担当遗产管理职责势必会损害遗产债权人的利益,因此立法就创设了限定继承制度予以应对,欠缺独立的遗产管理制度就是立法创设限定继承制度的直接原因。所以,古罗马法将遗产范围视为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实属正当,继承人承受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的概括继承也就具有了继续存在的正当理由。当然,遗产管理制度不仅将作为限定继承制度立法基础的遗产范围予以纳入,而且又将继承人在处理诸多遗产事务中所具有的遗产管理人的身份予以明确,清偿遗产债务是遗产的责任,而非遗产管理人以及继承人的责任,这成为遗产管理制度被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继承立法所采纳的理由之一。
总之,古罗马法欠缺独立的遗产管理制度致使出现了继承人在多数情形下处理遗产事务的事实,而这种事实必然使继承人与遗产管理人混同为一人,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必然会同时处理,作为遗产管理人的继承人承受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也就理所当然。尽管古罗马法创设的限定继承制度达到了继承人利益保护的目的,但却忽视了对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遂通过构建独立的遗产管理制度予以修正,但并没有禁止继承人担任遗产管理人,继承人与遗产管理人的身份混同的事实依然使限定继承制度继续存在。须注意的是,遗产管理制度的制度构造其实已经将限定继承制度的立法基础予以纳入,且对继承人在处理遗产事务中所有的不同身份也就进行了相应区别,继承人与遗产管理人其实负有不同的责任。如未履行遗产管理职责的遗产管理人所承担的责任是以遗产管理人身份而承担的侵权责任,至于继承人隐匿遗产、虚假编造等危害其他遗产债权人行为所承担的责任是继承人作为侵权者所承担的责任⑦。进而,遗产管理人是以所管理的遗产为限清偿遗产债务,在遗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形下,遗产管理人并不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所谓对遗产债务承担限定责任或者无限责任也就无从论及,不论继承人或者非继承人担任遗产管理人均不影响此种法律效力。在继承立法已经规定遗产管理制度的情形下,再规定限定继承制度也就欠缺合理,只会徒增立法重复以及不必要的歧义。
三、我国《继承法》对限定继承:选择与修正
我国清末以前的继承立法历经了从身份继承、祭祀继承与财产继承三者合一的宗祧继承到单纯财产继承的转变,不同朝代的统治者基于维护社会稳定,立法均规定了同籍或者同居共财而禁止别籍异财,此种情形无疑会形成由同一家庭成员共同所有的家产或者同一家族成员共有的族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实中出现的别籍异财的分家析产现象致使立法不再禁止别籍异财,只不过,为了达到维护宗族秩序的目的,统治者仍然褒扬世代同居的大家庭[7]P240-251,现实中遂形成了因同一家庭成员共同生活而形成的共同所有且由家长进行管理的家产的事实,但家长死亡后的家产必然会面临如何在家庭成员之间进行分割。然而,作为家庭成员的继承人既要分割家产,又要分割作为家长的被继承人遗产,此两种财产往往混为一体,分割家产也就对被继承人的遗产进行了分割。因作为家产管理者的家长生前所欠的债务就是所有家庭成员所欠的债务,此债务在家长死亡后理应由作为家庭成员的继承人承担,被继承人死亡后的家产及债务也就继续存在,继承人继承家产的同时也应负担其债务,实务中则形成了被继承人债务由继承人予以清偿的事实⑧。既然现实生活中存有因同居共财而形成的由家长管理的家产制度,家长死亡后的家产则由则由继承人分割家产,父债子还的继承习惯也就形成。
因体现家族主义的归属家长所有的家产制度一直被历代立法者所遵循,现实生活中的父债子还的继承习惯也就被民众视为圭皋,加之,受继受古罗马法的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继承立法的影响,我国清末所制定的《大清民律草案》乃至《民国民法典》将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视为遗产范围也就理所当然⑨。同时,除《大清民律草案》第1472条以及《民国民法典》第1151条通过规定“数个继承人对分割前的遗产享有共有权”而确定遗产归属以外,其他均通过规定继承人承受被继承人财产权利义务而予以确定遗产归属予继承人所有[5]P150,只不过,为了保护继承人的利益,我国《大清民律草案》以及《民国民法典》均设计了限定继承制度,《民国民法典》又设计了继承人享有对无限继承、限定继承或者放弃继承的选择权⑩。因实务中出现的继承人不知被继承人死亡而无法办理限定继承以及法定继承人的疏忽而没有替其未成年子女办理限定继承或者放弃继承的事实已经屡见不鲜,台湾地区遂于2009年5月对《民国民法典》第1148条又增加了第2款“继承人以因继承所得之遗产为限对于继承开始后的始发生代负履行责任之保证契约债务负清偿责任”,即除继承人承认无限继承和放弃继承外,不论继承人是否予以承认限定继承制度均应对继承的遗产债务以遗产为限承担清偿责任,其实。此立法例仍然将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视为遗产范围,仅是在继承债务后限定其清偿责任而已。当然,我国清末所制定的《大清民律草案》以及《民国民法典》也采纳了在接受继承、无人继承、遗嘱中分别规定遗产管理制度的立法模式,继承立法也就形成了限定继承制度与遗产管理制度并存的现实。令人遗憾的是,《民国民法典》并没有遗产地位的相关规定,仅有学者认为无人承认继承的遗产应为无权利能力的财团或为一种目的财产[8]P370,对此,有必要予以借鉴遗产管理制度中所确定的遗产具有统一法律地位的理念进行研究。显然,立法采纳的设计遗产管理制度理念已经表明,试图通过限定继承制度其实无法达到继承人、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但遗产管理制度已经将限定继承制度的立法基础进行了修正,在立法规定遗产管理制度的前提下,有必要予以检讨限定继承制度继续存在的合理性。
王树林无意中发现了它,显然是属于车内的某个配置,凹字型的一个塑料物件,烟壳大小,遗落在座位与档位的狭窄空隙里。纯属偶然,王树林移动座椅的时候发现了它。是座椅下面的螺栓扣件。他拿起来看了一眼,这东西怎么掉下来了?
反观1949年以后的我国大陆地区,因传统的宗法制度被摒弃,继承立法无从规定家长制度,家产也就无从谈及,但现实中存在的父债子还的继承习惯却损害了继承人的利益,在借鉴《苏俄民法典》的继承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大陆地区继承立法理念中出现了限定继承制度[9]P52,且1958年的《继承法(草稿)》与1980年至1982年的历次民法草案均予以继受,1985年制定的《继承法》第33条遂明确地予以了规定。就作为限定继承制度立法基础的遗产范围和遗产归属而言,1979年2月2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1980年8月到1982年5月数次所起草的《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及1985年的《继承法》将被继承人的债务排除在遗产范围以外,此种立法理念就是将遗产范围视为了财产权利而非财产义务,且仅以现实社会中的部分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为限[9]P93-107。同时,现行《继承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继承开始后的遗产归属,但从1985年9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9条所规定的“继承人在遗产分割前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应当是继承权而不是所有权”的精神推知:继承人只有在遗产分割后才能取得所有权。相反,因共同继承人在被继承人去世后的首要任务是处理丧葬事宜,径直分割遗产与我国风俗习惯不符,即父母亲一方去世后的遗产一般由生存一方管理,子女待父母都去世后才能予以分割遗产,最高人民法院依次在1987年6月的《关于父母的房屋遗产由兄弟姐妹中一人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并视为已有产生纠纷应如何处理的批复》、1987年10月的《关于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1988年的《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均将“未分割遗产解释为共有”。据此,现行司法解释对遗产归属的定性其实处于矛盾状态,我国继承法学界对继承开始后的遗产归属定性形成继承人取得的死亡说和继承人只有在遗产分割后才能取得遗产所有权的遗产分割说也就理所当然。如此,我国现行继承立法虽然已经规定了限定继承制度,但继承立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所采纳的遗产范围以及遗产归属的立法理念并没有继受古罗马法创设限定继承制度所依赖的将被继承人生前的财产权利义务一并继承的概括继承理念,限定继承制度在我国继承立法中是否存也就尚有疑问[10]。
就我国现行继承立法关于遗产管理制度的立法现状而言,历次的继承立法并没有明确规定遗产管理制度,仅设计了简单的遗产保管制度。尽管遗产保护制度已经具有遗产管理的雏形,但遗产保管制度不等同于遗产管理制度,仅具有遗产管理制度的诸多功能之一的遗产保护功能,遗产保护人也就无法充分履行遗产管理人职责。同时,1985年的《继承法》不仅没有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后的遗产于无人保管情形下的遗产管理制度,又欠缺在法定继承及遗产无人继承情形下而进行遗产管理制度的明确规定,且立法所规定遗嘱执行人仅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遗产管理人职责,遗嘱执行人其实也无法涵盖遗产管理人的内涵,诸种现状也使我国继承立法实有必要予以设计遗产管理制度。当然,既然前述的遗产管理制度构造已将设计限定继承制度所要应对的问题均予以了纳入,我国未来继承立法中的遗产管理制度设计就应当对遗产范围以及遗产归属进行准确定位。具体言之,遗产管理制度是以遗产为基础而进行设计,遗产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分割前的遗产不归属于任何人所有,遗产管理人仅对遗产享有管理权,继承人只有在对遗产进行分割后才能取得遗产所有权,进而避免上述我国的遗产归属的司法解释冲突。另外,无论继承人或者非继承人担当遗产管理人,均以遗产管理人身份清理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遗产管理人所面对的遗产范围也就包括被继承人的权利义务,继承人所面对的遗产范围就是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我国现行继承立法所采纳的遗产范围就是以继承人为视角而分析的结果,继承人继受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就是将继承人视为遗产管理人而分析的结果,继承人只有在清偿完遗产债务后且有剩余的前提下才可以取得遗产。此种理念必然导致我国继承立法中根本不存在限定继承制度,论及限定继承制度理念纯属多余,我国继承立法以及实务中所面临的诸多限定继承的困惑就能够予以解决。
四、结语
任何法律制度的形成均受到当时特殊社会背景影响。源于古罗马法的限定继承制度是与相关继承制度理念互相影响的结果,即将遗产范围视为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与遗产归属于继承人所有所逻辑演绎的结果;近世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继承立法是在立法理念的影响之下而规定了限定继承制度。基于达到对继承人、遗产债权人利益的同等保护,近世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或地区又以遗产为基础而构建了遗产管理制度。就遗产管理人处理遗产事务的先后顺序而言,首先要清理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其次要收取被继承人债权、清偿被继承人债务,最后才将剩余财产分配给继承人。由此,从遗产管理人角度观察,遗产范围应为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从继承人角度观察,遗产范围则为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同时,遗产并不归属继承人所有或者遗产管理人所有,清偿完遗产债务后的剩余遗产才可以由继承人取得所有权;遗产管理人并非继承人、遗产债权人的代理人,而是以遗产为基础所形成的财团的管理人,不论继承人或者非继承人担任遗产管理人均不影响遗产管理制度所具有的此种立法理念。进而言之,以遗产为基础而形成的遗产管理制度立法理念已经动摇了限定继承制度的立法基础,立法再予以规定限定继承制度也就欠缺合理,未来修改《继承法》应当予以修正。当然,现实中绝大多数的人们所拥有的财产数量有限,均依法成立遗产管理组织而处理遗产事务也不太现实,大量的遗产事务其实仍由继承人自己直接担当遗产管理人予以处理,而此种情形势必将继承人的财产与遗产相混同而损害了遗产债权人的利益,继承立法可通过规定将继承人与被继承人财产予以相分离的制度以及继承人负有制作遗产清单义务的遗产清册制度予以避免,未来《继承法》的修改应当注意此点。
注释:
① 目前的继承法学界共有六部继承法专家建议稿,依次为徐国栋主持的《绿色民法典》中的第4分编继承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298页)、梁慧星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 侵权行为编·继承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270页)、何丽新主持的《民法典草案继承编修改建议稿》(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7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1-301页)、王利明主持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 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57-637页)、张玉敏主持的《中国继承法立法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陈苇主持的《〈继承法〉修正案建议稿》,2012年6月16日至6月17日西南政法大学主办的“中国继承法修改热点难点问题研讨会”论文,第313-336页)。其中徐国栋主持的《绿色民法典》中的继承编第342条、梁慧星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1909条、王利明主持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第658条、张玉敏主持的《中国继承法立法建议稿》第16条、陈苇主持的《〈继承法〉修正案建议稿》第70-71条均设计了限定继承制度。
② 法国民法虽然没有明确予以规定遗产范围,但从《法国民法典》第793条至第810条中规定的相关“有限责任继承”的内容可以看出,法国民法的继承立法其实是将遗产范围限制为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义务。
③ 德国、法国、日本等国民法采纳了当然继承立法例,俄罗斯民法则采纳了承认继承立法例。
④ 参见陈棋炎:《民法继承》,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194页;【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页;周枏:《罗马法原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71页;陈朝璧:《罗马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9-70页。
⑥ 《德国民法典》第1959条【拒绝前的事务管理】第1款与第1978条【继承人对原管理的责任、费用的偿还】第1款将担当遗产管理人的继承人与继承人、遗产债权人之间的关系视为无因管理的规定就是此法理的明证。
⑦ 《日本民法典》第926条规定的“限定继承制度人应以对自己固有财产一样的注意继续管理继承财产”就说明了继承人担当了遗产管理人,第934条【不当清偿的责任】第1款所规定的“限定继承制度人怠为行使公告或催告或于公告或催告期间内向债权人或受遗赠人清偿,致使不能对其他债权人或受遗赠人清偿时,对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其实就是继承人以遗产管理人身份所承担的责任;《葡萄牙民法典》第2096条第1款规定“如继承人隐匿遗产中之财产,因而故意隐瞒有关财产之存在,则不论其是否为待分割财产管理人,均丧失其对所隐匿财产之任何部分会拥有之权利,而惠及其他共同继承人,并须接受对其适用之其他制裁”,此种情形下的继承人对外承担责任其实具有两种身份,即为遗产管理人或者为继承人,只不过承担的责任形式相同而矣。
⑧ 参见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4页,第886页。
⑨ 参见1911年的《大清民律草案》第1470条、1926年的《民国民律草案》第1346条、1930年的《民国民法典》第1148条之规定。
⑩ 参见1911年的《大清民律草案》第1470条、1462条之规定,1926年的《民国民律草案》第1346条、第1361条之规定,1930年的《民国民法典》第1148条、第1154条、第1174之规定。
参考文献:
[1] 张玉敏.继承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 周枏.罗马法原论(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 [英]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M].黄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 陈朝璧.罗马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5] 史尚宽.继承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6] 谭启平,冯乐坤.遗产处理制度的反思与重构[J].法学家,2013,4.
[7] 程维荣.中国继承制度史[M].东方出版中心,2006.
[8] 史怀璧.略论我国继承的几个基本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
[9] 刘春茂主编.中国民法学·财产继承[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10] 苏号朋.我国继承法有“限定继承制度”原则吗?[J],法治论丛,19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