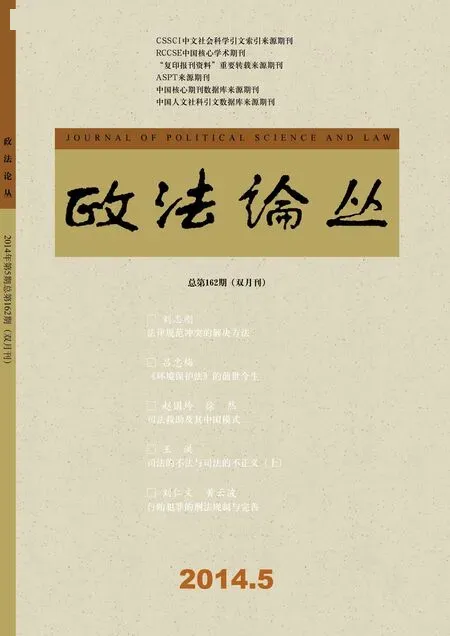国际组织管辖豁免:从绝对豁免走向限制豁免*
谢海霞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70)
2013年10月9日,海地霍乱受害者的代理律师在纽约地方法院起诉联合国,要求联合国赔偿海地霍乱受害者,索赔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海地霍乱受害者的代理律师声称,海地百余年来并无霍乱疫情,2010年10月在当地爆发的霍乱是由联合国尼泊尔籍维和士兵带入。这起霍乱疫情导致海地至少8300人死亡,约68万人染病。海地霍乱受害者方面要求联合国赔偿每位死难者家庭10万美元,每位染病者5万美元。联合国拒绝就赔偿金额与霍乱受害者达成庭外和解。联合国发言人指出,根据《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联合国享有豁免权,不受当地法院管辖。该案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核心问题在于,在当前国际法背景下,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已经从绝对豁免发展为限制豁免,国家的“管理权行为”(jure gestionis)不再享有管辖豁免。与此相对照,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际组织享有的豁免权是否也在从绝对豁免走向限制豁免,尤其是在涉及人权保护问题时,是否存在相应的制衡机制,以限制国际组织享有豁免。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联合国豁免与人权保护具有别样意义。“海地索赔案”的意义在于该案并不涉及维和人员的刑事责任,而仅仅是关涉到如果联合国因为享有管辖豁免而使当事人无法获得救济,这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法的要求。这再一次检测了联合国豁免的实质,当事人“诉诸法院之权利”是否已经成为联合国管辖豁免的制衡器,或者说是国际组织豁免的制衡器,国际组织豁免是否到了从绝对豁免走向限制豁免的历史时刻。
一、国际组织管辖豁免的实质
国际组织豁免被联合国视为一个全球性的议题,二战后,为了防止国际组织豁免问题碎片化,《联合国宪章》中专门规定了联合国的法律地位。其中第104条规定:“本组织于每一会员国之领土内,应享受于执行其职务及达成其宗旨所必需之法律行为能力。”第105条则专门规定了“(1)本组织于每一会员国之领土内,应享受于达成其宗旨所必须之特权与豁免。(2)联合国会员国之代表及本组织之职员,亦应同样享受于其独立行使关于本组织之职务所必需之特权与豁免。(3)为明定本条第1项和第2项之施行细则起见,大会得作成建议,或为此目的向联合国会员国提议协约。”为了实现《联合国宪章》的目标,联合国还专门制定了两个重要的条约,即1946年的《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和1947年的《各专门机构特权与豁免公约》,具体规定了联合国享有的特权与豁免的范围。《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2条第2项的规定:“联合国,其财产和资产,不论其位置何处,亦不论由何人持有,对于各种方式的法律程序应享有豁免,但在特定情况下,经联合国明示抛弃其豁免时,不在此限。惟缔约各国了解抛弃豁免不适用于任何强制执行措施。”联合国关于联合国豁免的规定被认为确立了国际组织豁免的“标准条款”,即国际组织原则上享有管辖豁免,除非其明示放弃豁免。这种“规范涟漪”(normative ripples)对于其他国际组织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为以后的国际组织基础文件或者东道国协议所效仿。
与国家不同,国际组织没有领土也没有主权,因此,国际组织豁免必然不是如国家豁免一样建立在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国际法学界普遍承认,国际组织的豁免权建立在职能必要理论基础上,也就是给予国际组织豁免的初衷是为了防止东道国通过司法审查干涉国际组织执行其职能。为了方便国际组织执行其职能,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承认国际组织享有的是绝对豁免,除非其放弃豁免。英国、美国、瑞士等,也通过专门的国内立法确立了国际组织享有特权与豁免,并且多数国家的国内法院根据一般习惯国际法也将此视为绝对豁免。[1]P62因为只有给予国际组织管辖绝对豁免或者接近绝对豁免才能保证有关国家的司法审查不会妨碍国际组织执行其职能。正如瑞士劳工法庭在“ZM诉阿拉伯国家联盟驻联合国常驻代表团”(ZM v. Permanent Delegation of the League of Arab Statues to the UN)一案中所认定的,习惯国际法承认国际组织,无论普遍性的还是区域性的,享有绝对的管辖豁免……国际组织的这种特权与豁免来自于其宗旨和职能。只有不受其成员国或者东道国法院干扰,它们才可以执行其职能。在具体操作上,各国国内法院一般都会积极寻求运用“避免技巧”,拒绝对以国际组织为被告的案件行使管辖权,即当国内法院在处理具体问题时,经常将管辖权问题视为一个程序问题,因为国际组织享有管辖豁免,法院有权拒绝审理该案件,其实质是法院承认国际组织享有绝对豁免。
但是,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国际组织管辖豁免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总结近年来的理论与实践,这种挑战的核心在于是时候“解构”国际组织的豁免权了,国际组织管辖豁免应当从绝对豁免转向限制豁免,理由可以归纳为三点:国家管辖豁免理论的发展;人权保护的需要;国际强行法效力的凸显。那么,这三种理由是否充分呢?
二、国家管辖豁免与国际组织管辖豁免:不具有类比性
国家及其财产享有豁免权是国际法的一项原则。但是,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国家管辖豁免理论已经开始从绝对豁免走向限制豁免。自美国于1976年率先制定《国家主权豁免法》以来,英国、新加坡等国家也陆续制定了相应的国内立法,这些国家的立法中都毫无例外地采用了限制豁免的原则,对国家的统治权行为给予豁免,管理权行为不再给予豁免,并具体规定了不给予豁免的例外情形。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也在国内司法实践中陆续承认了限制豁免原则。2004年联合国通过的《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虽然公约第5条规定一国本身及其财产遵照本公约的规定在另一国法院享有管辖豁免,但是公约中也明确规定了国家及其财产不享有管辖豁免的例外情形,从而确立了限制豁免的地位。
面对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权的发展路径,一些国际法学者,尤其以美国学者为代表,开始重新思考国际组织的管辖豁免问题。他们认为,既然给予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以管辖豁免也发生在限制豁免理论产生前,那么当国家及其财产享有限制豁免权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趋势时,是时候“解构”国际组织的豁免权了。这些学者指出,美国《国际组织法》(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mmunity Acts,以下简称“IOIA”)制定于1945年,当时国家管辖豁免理论尚处于绝对豁免阶段,因此,当时国会制定的《国际组织法》,以及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签订的协议等,其立法原意也是给予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以绝对管辖豁免。但是自“泰特公函”提出后,尤其是当美国制定了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之后,整个情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逆转。美国在1976年的《主权豁免法》中明确放弃了绝对管辖豁免的主张,转向了限制豁免,即对外国国家的管理权行为(jure gestionis) 不再给予豁免权。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的内容应当对国际组织具有溯及力,应当将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的内容并入到《国际组织豁免法》的适用中,对国际组织的商业行为等将不再给予管辖豁免。[2]P532尽管从《外国主权豁免法》的立法意图看还存在一定疑问,但是从立法相关的参考文件看,当《外国主权豁免法》对外国豁免的态度发生变化时,对国际组织的豁免的程度也相应变化。因此,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最初享有的绝对管辖豁免就不再适用了,而是由限制豁免原则取代。[3]P638
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美国国内法院传统上给予国际组织以绝对豁免。但是在2010年“The OSS Nokalva Inc. v. European Space Agency Case ”案中,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开始寻求改变传统做法。在该案中,OSS Nokalva公司和欧洲航天局签订了四份商业合同,其中都包含替代争议解决条款。第一份合同包括仲裁条款,另外三份合同中约定将争议提交新泽西州法院解决。后双方发生争议,OSS Nokalva公司在新泽西州法院起诉欧洲航空局,欧洲航空局抗辩法院管辖权,一审法院以被告已经明示放弃豁免以及从事商业活动为由驳回。案件被上诉到上诉法院。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通过对《国际组织法》的狭义解释,认为美国1976年《主权豁免法》中有关限制豁免的内容应当被并入到对《国际组织法》的解释中,对于国际组织商业行为和侵权行为都不再给予豁免。第三巡回上诉法院的做法已经逐步偏离了华盛顿特区法院确立的国际组织享有绝对豁免的规则。“这些案例表明,从整体上看,国际组织依据《国际组织法》享有的豁免似乎已经到了尽头,国际组织应当对其员工,对无辜第三方的损害承担责任。”[4]P451无独有偶,欧洲的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5],认为应当对国际组织的豁免权予以一定的限制。意大利的国内法院在“FAO v.INPDAI”案中曾试图运用“职能必要理论”来限制国际组织的豁免权。奥地利最高法院 在“E GmbH v. European Patent Organization”案中也指出,国际组织豁免在职能限制的框架内原则上是绝对的,也就是说,绝对是职能范围的绝对。
但是,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限制管辖豁免都尚未发展成为习惯法,也没有被写入成文法,无论是FISA的立法历史还是后续的修法建议都没有改变国会拒绝限制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的做法。也就是说,关于限制国际组织管辖豁免的各种主张还处于讨论层面,目前尚未发展出限制国际组织豁免权的习惯性做法,也缺乏统一的国际立法和实践。即使在理论层面,许多国际法学者认为这种以国家管辖豁免理论来类比国际组织豁免的主张是片面的,不成立的。且不说在国家豁免上的这种国家双重行为理论是否是一种圆满无漏的理论,但目前将国际组织司法管辖豁免的主体的行为范围类推适用国家豁免的“统治权行为”和“管理权行为”是明显不合适的。[6]P134因为国际组织不是国家,并不行使主权权力,仅是为履行特定职能而创设的主体,因此无法区分国际组织的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
对于联合国而言,几乎所有国家,即使那些曾经对国际组织采用限制豁免原则的国家也都认为联合国不同于其他国际组织,联合国享有的仍然是绝对豁免。在“Manderliner v. Organization des Nations Unies et I’Etat Belge”案中,以及在以后的一系列以联合国为被告的雇佣协议以及因维和行动造成损害的赔偿诉讼中,都给予了联合国以绝对豁免。即使美国国内个别法院主张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适用于国际组织,但是在对待联合国的问题上,仍然小心翼翼,在操作中还是给予了联合国以绝对豁免。例如在“Askir v. Boutros-Ghali &Others”案中,一个索马里公民起诉联合国1992年4月索马里维和行动中非法占有其财产,该案被法院驳回,理由是联合国享有豁免,本案情形不属于豁免例外情形。在“Brazk v. UN”案中涉及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是否适用,法院认为原则上应当适用,但是法院特别指出,联合国仍然享有绝对豁免,除非属于该法案中仅有的几个例外情形。实践表明,相较于其他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地位更具有特殊意义,国内法院不会对联合国轻易适用限制豁免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地索赔案”就具有特别意义。如果纽约法院在本案中不遵从以往的做法,转而适用限制豁免原则,不再给予联合国以管辖豁免,这将对国际组织管辖豁免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产生重大影响。
三、诉诸法院之权利:形成中的管辖豁免制衡器
国际组织豁免毕竟不同于国家主权豁免,因此不能将国家主权豁免理论简单推定适用于国际组织。但是,当国际组织豁免涉及人权保护时,如果国际组织无法保障当事人“诉诸法院之权利”的实现,无法给予受害人以公平救济时,就应当对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在内,采取限制豁免的立场,不再给予豁免。正如国际法学者指出的,这种给予国际组织绝对豁免的做法,事实上使得当事人个人的权利无法得到救济,违反了国际法和国内法中的正当程序条款,否定了受害人提起诉讼的权利,侵犯了当事人寻求陪审团审判的权利等。这一主张从保障当事人诉诸法律救济的权利出发,当国际组织无法提供替代争议解决机制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实现时,就应当限制国际组织的豁免权,由国际组织对有关当事人承担法律责任。“海地赔偿案”就被认为属于这种情形[7]。
当事人“诉诸法院之权利”属于国际人权法的内容,主要体现在《联合国人权宣言》、《公民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等多个人权条约中。“诉诸法院之权利”被认为是国际习惯法的内容,只要受到损害,当事人就应有寻求公平救济的机会,无论对方是私人、国家还是国际组织。相比较而言,国际组织更有义务提供争端解决机制,因为理论上当事人可以通过本国法院寻求法律救济,而国际组织因为没有类似的国内法院,因此需要建立类似的救济机构。在实践中,一些国际法庭或者国内法院处理的案例中已经开始讨论当事人诉诸法院权利,并以此作为决定是否给予国际组织管辖豁免的前提条件。
在“Beer and Regan v. Germany” 案和“Wendy and Kennedy v. Germany”案中,德国法院拒绝受理以欧洲空间局(Europe Space Agency,简称“ESA”)为被告的案件,当事人不服德国法院判决,诉讼到欧洲人权法院, 指控德国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 6条第1 款规定。法院认为,虽然国际组织豁免权是保障国际组织不受成员国影响独立行使其职能的首要条件,但是给予国际组织管辖豁免的前提条件是该国际组织提供了合理的替代争议解决机制,能保障当事人权利的有效实现。欧洲人权法院认为ESA已经提供了替代争议解决机制,因此给予ESA管辖豁免。在“Siegler v. Western European Union”案中,欧洲人权法院进一步指出,给予管辖豁免的前提不仅仅是替代争议解决机制的存在,该机制还要符合欧洲人权条约第6条的正当程序标准。也就是说,欧洲人权法院不仅将国际组织提供替代争议解决机制作为是否给予管辖豁免的首要条件,还将符合正当程序条款作为衡量标准。
在国内法院审理的以国际组织为被告的实践中,一些国家的国内法院也指出,给予国际组织以管辖豁免应当保障当事人诉诸法院之权利。法国法院在“UNESCO v. Boulois”案中直接援引《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驳回了UNESCO的豁免申请,在2005年审理的“Banque africaine de de?veloppement v. M.A. Degboe”案中则拒绝给被告非洲发展银行为以管辖豁免,理由是损害了当事人诉诸法院之权利。比利时法院在2009年审理的三个案件中都采用了欧洲人权法院的标准,在2011年审理的“Energies nouvelles et environnement v. Agence spatiale Europeenne” 案中,比利时上诉法院再次重审了欧洲人权法院在“Wendy and Kennedy” 案中的观点,指出,当存在其他国内法院或者国际组织内部解决机制时,就给予国际组织管辖豁免。在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Consortium X. v. Swiss Federal Government (Conseil federal)”案中,瑞士联邦最高法院解决了国际组织管辖豁免和执行豁免,以及当事人根据人权法有权诉诸正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平等诉权的冲突。法院认为,当事人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合同中预设的仲裁条款符合欧洲人权法院在“Wenndy and Kennedy” 案中确立的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公平审判的标准。
在“Stichting Mothers of Srebrenica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案中涉及是否给予联合国管辖豁免的问题。该案原告是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荷兰起诉联合国。原告认为,联合国和荷兰应当共同对波黑战争中,1995年7月发生在波黑东部的斯雷布雷尼察联合国保护区内的惨案负责,该惨案造成了8000多名手无寸铁的波斯尼亚穆斯林被波斯尼亚塞族武装杀害。原告认为,根据荷兰国内民法,联合国和荷兰未能遵守与塞尔维亚人达成的解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护区协议,并且,荷兰在联合国的默许下,也未能向波黑派遣有武装的部队保护他们,因此构成了侵权行为。根据《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和《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中的规定,一个国家和一个国际组织对此行为都应承担责任。但是,荷兰上诉法院驳回了维和部队当时受联合国控制这一主张,而是认为荷兰派遣的维和部队仍然在荷兰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因此,只有荷兰政府应当对难民的死亡负责。由于《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都赋予联合国以管辖豁免,因此荷兰上诉法院以此为由驳回案件。
有些国家还将“诉诸法院之权利”上升到了宪法权利范畴,例如在“Urban v. United Nations ”案中,美国法院认为,不得不适当地损害当事人拥有的宪法上的诉诸法院的权利。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Hetzel v.EUROCONTROL”案中也指出,如果国际组织已经提供了充分的替代解决机制,则法院就给予国际组织以管辖豁免,这并不违反德国宪法中所规定的法律原则的最低要求。
虽然每个案件案情不同,但是上述的相关实践表明,如果国际组织侵害了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则当事人基于人权保护挑战豁免权有可能获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就放弃传统的国际组织豁免而言,国内法院的实践有了显著的发展,基于人权保护法上的“诉诸法律之权利”、或者习惯国际法或者国内宪法上“诉诸法院之权利”来决定是否国际组织管辖豁免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8]P303,这些案例表明,基于人权保护来挑战联合国豁免的大门已经开启。但是,上述实践,无论是从地域上还是内容上都具有局限性,与国际组织享有的绝对管辖豁免相比,“外国法院和国际法庭不同的实践表明尚未形成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的习惯国家法。”[9]P364因此,认为“要求国际组织提供司法救济或准司法救济已经被认为是一种一般法律原则或习惯规则”的观点还需要更多的国际国内实践支持。事实上,任何以人权保护为由简单地否定一个传统规则的做法都被认为是不可取的,在新的规则到来之前,还是要认真地研究旧轮子的功能。[10]P1140
也有学者指出,豁免权与人权保护的问题不是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冲突,而是国际法规则之间的冲突,因为国内法院如果不给予联合国管辖豁免就违反了其承担的国际法义务。但是,如果能将“人权保护”或者将当事人“诉诸法院之权利”上升为强行法,国内法院就可以以此为由不再给予国际组织管辖豁免。这似乎也是解决海地索赔案的途径,但是,强行法真的是国际组织豁免权的克星吗?
四、强行法和豁免权:互不冲突的领域
要讨论能否以强行法理论来制约豁免权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强行法?当事人“诉诸法院之权利”是否属于强行法的范畴?违反强行法是否必然导致豁免权的丧失?强行性规范来源于国内法, 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国内法中,都可以找到强行法规则。在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条约法公约”)缔结之前,对于一般国际法中是否存在强行法是存在争议的,但是在1969年《条约法公约》缔结后,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国际强行法的存在。一般都认为,强行法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条约法公约》第53条规定中: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者无效。就适用本公约而言,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指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第53条的规定被认为是不溯及既往的,如果以后产生了新的强行法,根据第64条的规定,任何现有条约之与该项规律抵触者即成为无效而终止。
《条约法公约》中仅仅规定了强行法,但是并未明确强行法的范围,为此,国际法理论界和实务界曾就强行法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2001《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评注中,国际法委员会曾在题为“严重违背依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承担的义务”的评注中指出,强行法包括实行侵略、种族灭绝、奴役、种族歧视、反人类罪和酷刑以及民族自决权。在“Furundzija 案”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也把禁止酷刑定义为一种强行法和一项普遍义务,并指出:由于这一原则(禁止酷刑原则)所保护的价值观点很重要,它已经演变成了一项强制性规范或强制法,即在国际等级中享有高于条约法,甚至高于普遍习惯规则的等级规范。其显著后果是国家不能通过国际条约、地方或特殊习惯甚至是没有被赋予同样规范效力的一般习惯规则减损这一原则。国际法中的强制法被认为与普遍义务不同,强行法的特点是具有规范权力——废除冲突规范的能力,而普遍义务则指定了有关法律的适用范围以及由此而来的程序性后果。创设普遍义务的规范应属于“整个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然而,一项义务的普遍性并不表明该项义务明显高于其他义务。也就是说,强行法一定是普遍性义务,但是普遍性义务并不都是强行法。条约中所列举的关于国际强行法规范的例子,与国际法院提出的“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这一概念所列举的例子是大体相同的。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关于适用于武装冲突的人道主义法,包括日内瓦四公约和两个附加议定书中包含的基本规则都被国际法院称之为具有“不可侵犯性”,因此,应将这些规则都视为强制性规范。但是个人严重违反它们引起刑事责任这项规则还处在一般的习惯国际法地位,尚未取得强行法的地位。[11]P325
国际法院在1995年的“东帝汶案”中曾指出,尊重民族权属于对一切的义务。在2004年的“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中,国际法院再次重申了民族自决权是对世义务。在1996年“适用《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初步反对)案”中,国际法院曾指出,“本公约的基本原则是文明国家承认的即使没有规定任何契约性义务也对各国具有约束力的原则。” 1996 年在“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的咨询意见中,国际法院也提到了“国际习惯法不可侵犯的原则。”在“巴塞罗那电力公司案”中国际法院指出,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在现代国际法中是从宣布侵略和灭种行为为非法,以及宣布个人基本权利的基本原则和规则,包括免受奴役和种族歧视而得来的。”尽管国际条约、国际人权法案例、一些学者的著作中都确认国际强行法的存在,但是直到2006年,在“Armed Activities案”中,国际法院才在判决中首次明确使用了“强行法”这个概念。国际法已有的理论和实践表明,“诉诸法院的权利”现在还不属于强行法范畴。
至于强行法和豁免权的关系,直到2012年,在“德国诉意大利案”中,国际法院才在判决中明确了强行法和国家豁免的关系。法院认为,这一争议取决于强行法和一国给予另一国豁免的习惯法规则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在法院看来,二者之间是不存在任何冲突的,强行法与国家豁免规范两个不同范围。国家豁免规则是程序事项规则,决定的是一国法院能否对另一国国家行使管辖权,而不决定提起诉讼的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说,当针对德国1943-1945年的行为适用当代有关国家豁免的法律时,并不能违反这一原则,即不能决定行为的合法性和责任。反之,承认一国根据习惯国际法享有的豁免权时也不等同于承认违反强行法行为的合法性。在该案中,国际法院指出,即使德国的行为违反国际法,但是,国家能否享有豁免权是个程序性问题,只有在确定一国法院拥有管辖权之后,才能判断导致诉讼的行为是否严重违反国际法。从习惯国际法看,习惯国际法赋予了一国在军事战争中因军队或其他部门在另一国领域内导致侵权的行为享有豁免权,习惯国际法未发展到一国因其违反国际人权法或者军事法时就不享有国家豁免权。国家享有的豁免权不因行为的严重性或者行为所违反的规则的强制性质而改变。尽管国际法院的法官们在国家豁免与强行法的关系问题上分歧很大,但是国际法院在“德国诉意大利案”的判决中采用的“程序——实体”区分法被认为是确立了国家主权豁免与强行法关系的新标准,即强行法与国家豁免权之间不存在任何冲突。
早在“德国诉意大利案”之前,在“Princz v. Germany”案之后,强行法和豁免权关系问题就已经被提出来了。尽管各国承认国家及其财产享有管辖豁免是一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国际法学界对于强行法的范围、性质均存在着争议,因此关于强行法的认定标准和效力,强行法和豁免权的关系却充满疑义。多数学者,或者被认为是“传统”、“正统”的学派都承认国际法中确实存在强行法,但是强行法并不必然高于豁免权。因为二者并不会发生冲突,而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规范,强行法规范的是实体行为,而豁免权属于程序性规范。强行法规范并不必然给国内法院赋予强行性义务,对于外国国家在外国实施的行为给予受害人以民事救济。[12]豁免权也不是要取消或者违反强行法,而只是反对在国内法院的程序中违反豁免权,强行法的优先效力并没有受到影响。 “程序——实体”区分法在实践中已经被许多国家法院的实践所采用,如英国、美国、加拿大、荷兰等。欧洲人权法院也倾向于支持给予国家管辖豁免,其中“Al-Adsani v. United Kingdom” 案、“McElhinney v. Ireland” 案和“Fogarty v. United Kingdom” 案被认为是欧洲人权法院审结的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在这三个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都认为给予国家管辖豁免并不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
尽管如此,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实体——程序”区分法是为了加强和巩固国家主权豁免的传统或者主流观点,这种严格区分方法仅仅在绝对豁免的情形下才起作用,仅仅根据被告的身份而不考察案件的实质就终止诉讼是有问题的,并不是解决当前国际法稳定性的理想方法。“国际法院反复强调了德国二战中暴行的非法性,承认其违反了国际法,认为其有赔偿义务,但又认为其有权援引国家豁免,这种态度不仅是矛盾的,而且会导致人民质疑强行法的实际效力,强行法的不得背离的拘束力不应当被限定于仅仅宣布某些国家行为的非法,也应及于此种非法行为的法律后果,”[13]这被认为是不利于人权保护的。还有些学者从规范等级理论出发,认为强行法是对世义务,国家豁免权仅仅是一般原则,从规范的效力等级看,豁免权低于人权保护等强项法义务,因此当二者发展冲突时,应当剥夺相关国家的管辖豁免权,国家应当承担国家责任。“国际法院坚持的国家豁免的程序性性质无疑影响了诉讼参与人的重大实质利益,对于国家主权的过度保护导致了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 尤其是基本人权方面的利益) 严重失衡。”[14]另有学者认为规范等级理论有缺陷,因为其混淆了国家豁免权的基本内容。他们从限制豁免理论出发,认为限制豁免是国家豁免权的根本,因此,违反强行法的行为应当归属于豁免例外条款,即当国家的行为违反了国际义务时,国家就不再享有豁免。
尽管众说纷纭,一些国际法学者从更深层面分析了国际法院判决的理由,即从国际法院设立目的和国家豁免存在的必要性角度来分析,考虑到国家豁免对国家间关系以及国家责任的重大影响,维护传统的国家豁免权理论更有利于当今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国际法院做出的判决虽然保守,在保护人权方面未起到更大的作用,但国际法院的最初设立并非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更多的在于维护国家间的公平正义。这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阿塔什·巴维特在《权利的神话:宪法权利的目的与限制》中分析美国权利法案与结构性条款的功能的方法并无二致,即探寻其存在的目的——首先是用来限制政府权力的目的和范围,以使公民和国家保持平衡,它也的确促进个人利益,但那并非首要目的[15]。
就国际组织豁免权与强行法的关系而言,2012年欧洲人权法院审理的“Stichting Mothers of Srebrenica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案”与国际法院判决的“德国诉意大利案”殊途同归。在该案中,原告于 2012年10月8日在欧洲人权法院起诉荷兰,认为荷兰法院给予联合国管辖豁免的行为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联合国对于发生在塞尔维亚的灭种行为负有责任,并违反了国际强行法,对这种行为荷兰法院不应再给予管辖豁免。原告还认为,由于缺乏替代管辖权,如果欧洲人权法院不予审理,这等于剥夺了原告享有的“诉诸法院之权利”。在该案中,欧洲人权法院需要裁定,荷兰国内法院给予联合国管辖豁免是否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此外,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13条的规定,法院还要考虑给予联合国管辖豁免是否逃避了荷兰对原告的的责任。2013年6月27日,欧洲人权法院以缺乏事实根据为由驳回原告起诉。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国际组织享有豁免权是保证其在实践中实现组织职能的重要条件,这是国际社会也已广泛承认的实践,欧洲人权法院具有驳回起诉的合法理由。接着,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当事人起诉到法院的权利是有限制的,尤其是国际法尚未确立这样一条规则,即国际组织由于严重违反国际法而被剥夺其享有的管辖豁免,即使违反的是强行法。也就是说,欧洲人权法院在国际组织豁免权和强行法的关系上,得出了与国际法院在“德国诉意大利案”中同样的结论。欧洲人权委员会也认为,国际组织或外国使团或领馆的管辖豁免不能被视为根据国内法划定实质性权利之内容的范围。委员会还说,把民事责任豁免赋予人数众多的群体或类别,将会违背《欧洲人权公约》的第6条第1款。在所涉案件中,没有发生类似违反公约第6条第1款的情况,因为,可以说在国际豁免规则与欧洲空间机构作为一个国际组织追求的合法目标之间,存在着一种合理的相称关系。欧洲人权法院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如果缔约国被免除根据公约承担的豁免领域的责任,就不符合该公约的宗旨与目标。对国际组织的豁免不能被视为欧洲人权法院适用范围的一种一般性的不成文例外。
在欧洲人权法院看来,虽然给予国际组织管辖豁免以该国际组织提供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为前提,但是违反强行法并不是不给予豁免的理由。无论“诉诸法院之权利”是否是强行法在此时就已经不重要了。就“海地索赔案”而言,显然困难重重。因为姑且不论当事人诉诸法院之权利是否已经发展为国际强行法,就是其已经是国际强行法了,现有国际实践表明,国际社会更倾向于将强行法和豁免权问题视为两个不同的问题,二者没有冲突,因此无法将强行法作为豁免权的制衡机制。尽管国内法院不受国际法院和其他国际法庭的判决的拘束,但是,该判决仍然会对国内法院的司法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寻求其他机制或者途径解决国际组织的责任问题。
五、替代争议解决机制:亟需完善
从替代争议解决机制出发,以当事人“诉诸法院之权利”作为限制国际组织豁免权的制衡器,尽管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尤其是在欧洲地区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但是尚未得到国内法院和国际法庭的广泛认可,尚未形成习惯国际法,因此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并具有渐进的特征。但是,建立并完善现有的替代争议解决机制确实应该成为未来国际组织责任中需要重点研究的内容,也是未来的发展思路,这既符合人权保护的要求,也符合国际组织因为职能必要而享有管辖豁免的需要。
国际法院在1954年就“联合国行政法庭所作赔偿裁决的有效性问题”发表的咨询意见中就指出,联合国如果不能为解决其与职员之间发生的任何争端提供司法或仲裁救济,则很难说与宪章中促进个人自由和公正的明确目标相符[16]。虽然《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等公约中规定的义务对于联合国并非具有直接效力,但是作为特权豁免的受益者,其被认为具有“默示义务”。在“Curamaswamy”案中,国际法院指出联合国有义务在享有豁免权时提供替代争议解决机制。这种机制排除了国内法院管辖,要符合《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中所指的适当方式。在“Effect of Awards”案中,国际法院又指出为员工提供争议解决机制是联合国宪章促进个人自由和正义的要求。事实上,《联合国管辖豁免公约》第29条就规定, 联合国应对下列争端提供适当的解决方式:(甲)由于联合国为当事人的契约所生的争端或联合国为当事人的其他私法性质的争端;(乙)牵涉联合国任何职员的争端,他们因公务地位而享有豁免,而这项豁免并未经秘书长抛弃时。在实践中,联合国内部已经建立了替代争议解决机制,包括行政法庭,主要处理与雇员之间的纠纷;仲裁机制,主要解决与合同事项有关的争议;此外,联合国还针对个案,分别采取协商、仲裁等方式解决问题,例如针对维和事项给平民造成的人身或者财产损害,联合国都倾向于采取协商的方式解决。此外,在联合国发展项目的履行过程中,受益国和联合国在协议中会约定由受益国承诺负责解决与第三方的争议,除非联合国人权存在重大过失或者有恶意行为。“海地索赔案”就涉及《联合国管辖豁免公约》第29条所包含的联合国与第三人因为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私法争端,如果联合国未能提供其他争议解决方法,联合国在该争端中又享有豁免权,则海地受害者就无法从其他途径获得救济。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协商解决问题也许是最好的方法。
虽然一些国际法庭和国内法院认为提供替代争议解决机制是国际组织享有管辖豁免的前提,但是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接踵而上,即在多大程度上国内法院能挑战这些替代争端解决机制?事实上,国际法庭和国内法院并不具体考量替代争议解决机制是否符合保障当事人“诉诸法院权利”实现的“标准”,如欧洲人权法院在“Waite and Kennedy”案中就指出,在确定是否给予国际组织豁免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原告是否能有效实现公约规定的“诉诸法院之权利”,但是在具体考察是否存在这样的机制时,法院认为ESA内部的上诉机制就足够符合标准了,也符合有效保障当事人诉诸法院权利实现的要求。就联合国而言,联合国现有的替代争议解决机制也是符合替代争议解决机制的标准,但是否能实现当事人,尤其是第三方受害人诉诸法院之权利则充满争议。
此外,其他多数国际组织内部也都设立了类似的争议解决机制,如行政法庭或雇员管理咨询联合机构等。这些争议解决机制处理的问题相当广泛,从劳工纠纷到个人损害,甚至性骚扰等案件。尽管从这些争议解决机制的实际运作情况看,无论是机构的独立性、法官的遴选,还是工作程序、决定公开性等都无法完全满足法律上的正当程序条款的要求,但是可以通过成立独立的仲裁机构,或者在这些机构进行改革,增强纠纷解决机制的独立性、透明度,加强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同时有学者提出将职能豁免作为有效抗辩的依据,而不是法律上绝对不受理案件的依据也具有一定合理性[17]P452,这样就能给予原告在法庭上充分申诉的机会。
六、结论
在国际组织豁免问题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国际法庭和国内法院的实践上,都还充满着疑虑和矛盾。但是,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借鉴国家管辖豁免的发展历程和国家有关豁免权的立法,将限制豁免类推适用于国际组织管辖豁免,包括联合国的管辖豁免,显然还为时尚早,目前尚未形成这样的习惯国际法;第二,将当事人“诉诸法院之权利”上升到强行法范畴是缺乏法律依据的,认为强行法的效力“高于”豁免权的做法还未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当事人寻求正义的权利与国家和国际组织享有管辖豁免的权利二者并不存在必然矛盾;第三,从人权保护出发,积极利用替代争议解决机制作为解决有关争议的做法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尽管这种“制衡器”还不能达到制衡的标准,还不够完美,需要逐步完善。在某些时候,当替代争议解决机制不存在时,国际组织主动放弃管辖豁免也不失为良性选择。
参考文献:
[1] August Reinisch and Ulf Andreas Weber, In the Shadow of Waite and Kennedy: The Jurisdictional Immun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Individual’s Right of Access to the Courts and Administrative Tribunals as Alternative Means of Dispute Settlement[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aw Review ,Vol.1,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4.
[2] Stecen Herz,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U.S. Courts: Reconsidering the Anachronism of Absolute Immunity [J]. 31 Suffolk Transnational Law Review, 2008.
[3] Kevin M. Whiteley, Hold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ccountable Under the 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 Civil Actions Against the United Nations for Non-Commercial Torts [J].7 Washington University Global Studies Law Review, Vol.7:619,2008.
[4] Greta L. Rios and Edward Patrick Flaherty,Mr. Ban-Tears down the U.N.’s Wall of Immunity / Impunity ( Before a National Court does)[J].ILS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Vol. 18:2012.
[5] Emmanuel Gaillard and Isabelle Pingel-Lenuzz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mmunity from jurisdiction: To Restrict or to Bypass [J].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ly, Vol. 51, January 2002.
[6] 李赞.国际组织的司法管辖豁免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7] Rosa Freedman, UN Immunity or Impunity? A Human Rights Based Challeng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5 (2014) No. 1.
[8] August Reinisch,The Immun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Jurisdiction of their Alternative Tribunals[J].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8), Vol. 7, No. 2.
[9] Aaron I. Young, De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mmunity [J].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44, 2012.
[10] Christian Tomuschat,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State Immunity and Its Development by National Institutions [J].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n Law, Vol. 44, 2011.
[11] 朱利江.对国内战争罪的普遍管辖与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2] Zimmermann, Sovereign Immunity and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Jus Cogens - Some Critical Remarks[J].16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5.See also Caplan, State Immunity, Human Rights and Jus Cogens[J]. 97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3.
[13] 张辉.国际法效力等级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13.
[14] 郭玉军,刘元元.国际强行法与国家豁免权的冲突与解决——以德国诉意大利案为视角[J].河北法学,2013,1.
[15] 姜峰.宪法权利:保护个人还是控制国家?[J].读书,2014,4.
[16] Effect of Awards of Compensation Made by the United Nations Administration Tribunal, ICJ Reports, 1954.
[17] Greta L. Rios and Edward P. Flaherty, Legal Accoun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Challenges and Refor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Reform or Immunity? Immunity is the Problem [J].16 ILS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winter,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