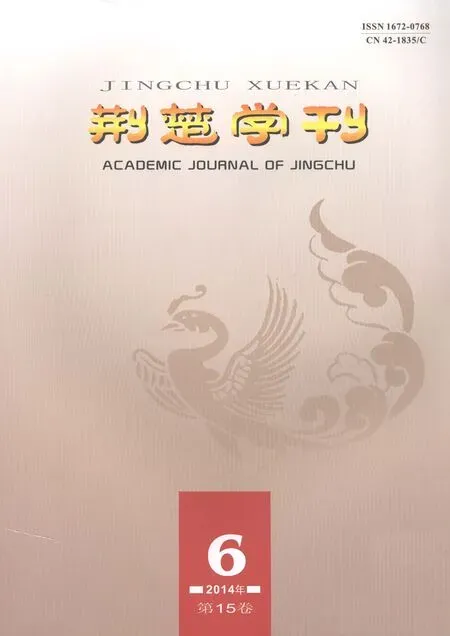明显陵《皇考恭穆献皇帝睿功圣德碑》碑文考异
胡家全
(荆楚理工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荆门 448000)
《皇考恭穆献皇帝睿功圣德碑》碑文,是嘉靖皇帝在嘉靖六年(1527)时为怀念父亲而亲笔撰写的一篇纪念性文章,后制成碑安置于显陵之中。碑文中因有明史上著名的“大礼议”之争和与兴献帝逝世有关的皇室活动的记述,从而使其具有了一定的文献意义,又因其用语典雅,说理透彻,情感真挚,从而也具有较强的文学价值。明显陵在历史上曾经历过两次大的浩劫,使得此碑遭到毁坏,只剩下近80字的残片,这对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明显陵来说无疑是一大损失,今人不能目睹《圣德碑》全貌,不能欣赏一代帝王——嘉靖皇帝的文采,更是一大缺憾。所幸的是在不少的典籍与方志中都收录了这篇碑文,如嘉靖时期成书的《兴都志》[1]和《承天大志》[2]等,这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碑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不足的是,文献在流传的过程中因重抄和重刊等原因而出现了不同版本,各个版本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差别,又因现代人对文意的理解问题,断句方面也出现了错误,这些对传播古代文化和开展文物恢复工作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对碑文的勘误工作就很有必要。
确定权威版本是我们勘误的前提。记载此文最早的文献有明朝嘉靖时期成书的《兴都志》和《承天大志》,两书都应是权威的参考文献,但通过考证,钟祥档案馆珍藏的嘉靖时期刻印的《承天大志》复印本比《兴都志》更权威,更准确。理由如下:
首先,从成书过程和命运看。《兴都志》成书于嘉靖二十一年,写作班子是由顾璘为首的志修专家组成,因没很好领会嘉靖皇帝纂修帝乡之志的意图,写完后嘉靖皇帝以“体例不合”“纪事实多误”而不予刊行。《承天大志》成书于嘉靖四十五年,写作班子是以徐阶、李春芳等为主的阁臣组成,他们揣摩透了帝王的心事,汲取《兴都志》失败的教训,在《兴都志》基础上重新修订,书成后嘉靖帝大加赞赏,并命礼部精审,大量刊发。两部书都是嘉靖在世时编成,晚于碑文写作时间,都收录了这篇碑文。因碑文是嘉靖亲自撰写,具有圣谕的性质,且两部书都是经过嘉靖亲自审阅的,如果抄录时出现讹误,即使不被杀头,也要遭受牢狱之灾,故对碑文的抄录应该不会出现错误。问题是《兴都志》没有正式刊行,是嘉靖皇帝不认可的,其后流传也只能以手抄本形式;然而,在民国二十六年,《兴都志》和《承天大志》都出现了钟祥县志局重刊本,现在一些地方学者所研究和著作中所收录的碑文是依据《兴都志》民国二十六年的重刊本,内容错讹也就在所难免,即使是民国版的《承天大志》[3](后文中加“民国”二字以与嘉靖版区别,若没特别指出即皆据嘉靖刻本)在个别用字上也已与嘉靖版不相同了(具情见后文例)。

其三,从碑文的用词上看。《承天大志》所载碑文的用词富有规律性,符合明代的用词惯例。例如:原文有“於嘉靖三等年,上尊號曰:恭穆獻皇帝,陵曰顯陵”一句,“嘉靖三等年”就是“嘉靖三年”。考之于《明史》,与史书相符。张廷玉等《明史》卷十七《世宗·一》:“(嘉靖)三年春正月丙寅朔,两畿、河南、山东、陕西,同时地震……癸丑,追尊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4]218《明史》卷一百十五《睿宗献皇帝》:“三年,加称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4]3552《明史》卷一百九十一《汪俊传》:“(嘉靖)三年二月,俊集廷臣七十有三人上议曰:祖训‘兄终弟及’,指同产言……至三月朔,乃诏礼官,加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4]5058-5059在明朝的公文中,表示某年常在“年”字前加“等”字,这个“等”无实际意义,是句中助词。这种用法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各工具书亦不记载这种用法。这种用法多见于明代的公文,明末清初的文人也有使用者,其后这种用法就不多见了,例如下面的九则材料,其中八则是明代的用例,另一个是明末清初人的用例:
(1)明王恕《王端毅公奏议》卷十三《议太医院缺官奏状》:“成化八年二月,内蒙掌御药房司设监太监覃文奏取本房,答应成化十三等年用药有效。”[5]
(2)明何孟春《何文简疏议》卷二《马政疏》:“查得成化十三等年,为军务等事节,该兵部议行各边,骑操马匹,遇有倒失,酌量官军朋合出银买补。”[6]
(3)明陆粲《陆子余集》卷五《陈马房事宜疏》:“正德三等年,该尚膳监太监张裕题准,将汤山牧羊草场,开垦一半,征收银两,修理公廨。”[7]
(4)明王樵《方麓集》卷一《审录重囚疏》:“万历十三等年,霜降会审,有词节呈调山东等司,仍拟前罪监候。”[8]
(5)明黄训《名臣经济录》卷三十五储巏《题马政利病》:“自弘治十四等年至今,则一十三万两矣。”[9]
(6)明潘季驯《潘司空奏疏》卷七《报擒屡奉钦依擒拿首贼疏》:“隆庆元等年,不等月内,大鸾又伙同前党打刼。”[10]
(7)明张羽《东田遗稿》卷下《遗楷采桢分单》:“正德九等年,买张家庄后赵政等陆地。”[11]又:“于嘉靖二等年,买三房,东门房地一所,吾赖以栖息。”[11]
(8)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五十二《四译馆》:“查嘉靖元等年,屡经本部题准,各馆官生中,有愚顽不学屡考无成者,若容再试,终于无用。”[12]
对“於嘉靖三等年”一语,《湖广通志》[13]《钟祥金石考》[14]《钟祥县志》[15]《明显陵探微》[16]皆夺“等”字,这说明这些本子的抄录者已经不知道明代在公文中的用词例,妄加改窜。由于不知明代在表示某年时习惯加以“等”字,不仅将“等”字删除,而且还连带删除“錫予良臣,起議大禮,群邪解爭,眾議頓息”等数句,以求意思连贯。
再从介词“于”“於”的使用情况来看,文中用介词“于(於)”的地方一共15处,《兴都志》中均用“於”,而《承天大志》中10处用“於”,5处用“于”,分别摘录如下:
於:(1)錫以恩賚倍於他藩……
(2)誠孝以致於親,迎養之辭,已著於遺治之疏……
(3)士夫百姓毎形於稱頌之詞,至於謹水旱之災……
(4)又至於口授詩書……
(5)於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辰時上賔……
(6)謀於士民……
(7)朕親奉靈輿安厝於此……
(8)於嘉靖三等年……
于:(1)隨遣使聞于皇兄……
(2)朕乃告于國社、國稷等神,請于聖母,謀於士民……
(3)奏于皇兄……
(4)徳配于天……
从上述“于”“於”两组用例可看出,这两个可通用的介词,其用法以及后面所跟对象的不同是很明显的。在碑文中介词“於”的宾语是一般性的普通名词或时间性短语,而介词“于”的宾语则是含有尊崇意味的词语,二者画然分明,绝不混淆。《承天大志》(民国)中也只有“於”,沒有“于”“於”之別,与《兴都志》同。
从词义角度分析,“于”字有“大,广大”等称誉义,如《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况于其身。”王肃注:“于,宽也,大也。”[17]56又如《方言》卷一:“于,大也;于,通语也。”[17]56将具有褒义色彩义项的“于”用于神圣高贵的对象前面应是很恰当的。“於”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的注释是:“象古文乌省。此即今之於字。象古文烏而省之……此字既出,则又于、於为古今字。《释诂》……凡经多用于,凡传多用於,而烏鳥不用此字。”[18]“凡经多用于,凡传多用於”虽然可能是不同时期用字习惯使然,但客观上起到了尊经卑传的作用。用“于”介引高贵者有可能是这种现象的延伸,是符合嘉靖皇帝的心理特点的。
以上三点已充分说明在两个较早的文献中,《承天大志》所载碑文最为权威,当为校勘碑文的依据。
以《承天大志》为依据,笔者再对照《兴都志》《湖广通志》《钟祥县志》《荆门碑刻》[19]《荆门古迹碑文抄注》[20]《显陵探微》《承天大志》(民国)这些古今著作,发现碑文在流传过程中有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名称不一。焦知云著《荆门碑刻》为《御制睿功圣德碑文》,《钟祥县志》为《皇考恭穆献皇帝》,《湖广通志》卷八十二为《世宗显陵碑文》,《明史》卷一百十五为《睿宗献皇帝献皇后》(简称《显陵碑》),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百六为《右元泰定帝》(简称《显陵碑》)[21],李权《钟祥金石考》卷二作《显陵碑文》:碑文名当据《承天大志》卷二十八为《皇考恭穆献皇帝睿功圣德碑》。
其二,随意用字。抄写者未有保持《承天大志》的用字原貌,时有随意使用异体字或将假借字改回本字的情况,这虽对理解文义影响不大,但对恢复原碑或研究明代的用字情况是不允许的。例如,将通假字改回本字,如“蚤膺憲祖之命”中的通假字“蚤”,《钟祥县志》《钟祥金石考》《荆门碑刻》《显陵探微》都改作本字“早”,“錫以恩賚”中的假借用字“锡”,《荆门碑刻》改作本字“赐”;再如随意使用异体字,如“我皇兄龍御上升”中的“升”,《湖广通志》《钟祥金石考》《钟祥县志》作“昇”,“凡天時人事古今事變之迹”中的“迹”,《钟祥金石考》作“蹟”,“復繫之以詩曰”中的“繫”,《钟祥金石考》作“係”,《钟祥县志》作“系”,“辰時上賔”中的“賔”,《金石考》《钟祥县志》《承天大志》(民国)作“賓”,“究其旨趣”中的“趣”,《承天大志》(民国)作“趨”,“及赐命朕暂理府事”中的“”,《兴都志》《金石考》《承天大志》(民国)作“勑”。
其三,脱漏。例如:“又至於口授詩書,手教作字,有非筆墨間所能盡述者矣”,《兴都志》《湖广通志》《钟祥金石考》《钟祥县志》《显陵探微》夺“盡”字,《钟祥金石考》《钟祥县志》又夺“於”字;“又命文臣一人,以掌禮儀”,《湖广通志》夺“文”字;“及賜命暫理府事”,《湖广通志》夺“事”字;“以金册封王”,《兴都志》《显陵探微》脱“封”字;“荷皇天垂鑒,祖宗佑啟,錫予良臣,起議大禮,群邪解爭,眾議頓息。於嘉靖三等年,上尊號曰:恭穆獻皇帝,陵曰顯陵”这样一段文字,《湖广通志》《钟祥金石考》《钟祥县志》并夺“錫予良臣,起議大禮,群邪解爭,眾議頓息”数句。

其五,因避讳而改。例如:“奉安玄室”中的“玄”,《钟祥金石考》《钟祥县志》作“元”,虽不为错,但造成与原貌不符。
其六,用意义相近或互训词代替。例如:“昔承憲祖之嚴訓”中的“憲祖”,《钟祥县志》《钟祥金石考》《明显陵探微》作“憲宗”;“方當日聆嚴訓,膝下承歡”中的“聆”,《兴都志》《湖广通志》《钟祥金石考》《钟祥县志》讹作“聽”;“下命朕入承大统”,《明显陵探微》误作“入继大统”。
除有上述字词问题外,现代版本还存在断句标点方面的问题,如“敬愼而明修國祀,社稷山川罔不鑒歆;忠謹而臣事兩朝,孝廟皇兄屢加褒奬”等,有的编者断句后导致割裂原意,语意不通。
以上所述各种问题,仅仅是举例性质的,并不是详细的校勘记,这些举例说明上述诸书都存在着某些错误,都不足以作为恢复原碑的依据,甚至作为史料也是很不严谨的。如欲恢复原碑,明嘉靖刊本《承天大志》是最正确的,民国时期所翻刻的《承天大志》已经出现了错误,亦不足为据。
原碑文后有落款:“嘉靖六年歲次丁亥孟冬越望日,孝子皇帝臣厚熜。”[19]各本皆无此落款,明嘉靖刊本《承天大志》亦无,盖受文体所限,不需载者。《荆门碑刻》附有原残石拓片,字迹清晰,当据此补。
[1] [明]顾璘.兴都志·典制五·宸翰·卷五[M].钟祥:钟祥方志局,1937(民国二十六年):8-10.
[2] [明]徐阶,李春芳.承天大志·卷二十八·御制纪四[M].北京:[出版者不详],1566(嘉靖四十五年):1-4.
[3] [明]徐阶,李春芳.承天大志·卷二十八·御制纪四[M].钟祥:钟祥方志局,1937(民国二十六年):29-32.
[4] [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5] [明]王恕.王端毅公奏议[M]//四库全书:第42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68.
[6] [明]何孟春.何文简疏议[M]//四库全书:第42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0.
[7] [明]陆粲.陆子余集[M]//四库全书:第127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50.
[8] [明]王樵.方麓集[M]//四库全书:第128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17.
[9] [明]黄训.名臣经济录[M]//四库全书:第4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8.
[10] [明]潘季驯.潘司空奏疏[M]//四库全书:第43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54.
[11] [明]张羽.东田遗稿[M]//四库全书:第126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13-314.
[12]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M]//四库全书:第86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7.
[13] [清]夏力恕,迈柱. 湖广通志[M]//四库全书:第5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68-169.
[14] 李权.钟祥金石考[M]//石刻史料新编:第16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12256.
[15] 赵鹏飞.钟祥县志·卷五·古迹下[M].南京:[出版者不详],1937(民国二十六年):5.
[16] 周红梅.明显陵探微[M].香港:中国素质教育出版社,2011:44-45.
[17] 宗福邦,陈世铙.故训汇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8]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57.
[19] 焦知云.荆门碑刻[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242.
[20] 刘南陔.荆门古迹碑文抄注[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14-215.
[21] [清]秦蕙田.五礼通考[M]//四库全书:第13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48.
[22] [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M]//四库全书:第67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