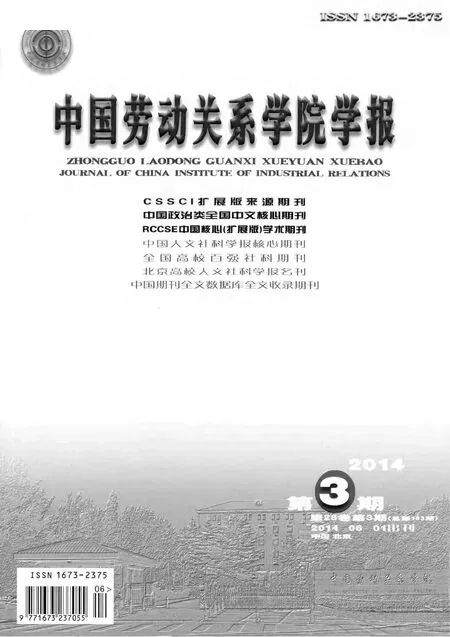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律机制研究*
吴 楠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科研处,安徽 合肥 230053)
生态补偿机制,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础。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真正的生态补偿制度,但是从未停止相关工作,并在森林领域率先开展了生态补偿实践。1998年,《森林法》修订,首次在法律上提出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概念。2004年,中央财政正式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截止2013年,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所覆盖的公益林已达18.7亿亩。
一、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法理基础
(一)权利平等,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法理依据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指的是公民享受平等的权利,也承担平等的义务。唯有这样,才能够做到在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实现制衡,并进而抑制各种专制。[1]“公平负担平等学说”,强调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以平等为基础为公民设定义务。现代法治国家在剥夺或限制了特定人的权益时,应通过社会全体负担的方式,弥补由此产生的损失,以实现相关利益的调整。[2]
森林具有经济、生态、社会多重效益。我国实行林业分类经营,将森林分为生态公益林与商品林。公益林的主体功能是维护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生态产品属于公共物品,其产品功能为公众共同享有,依据权利义务一致性的原则,提供产品的成本也应当由公众共同承担。公益林禁伐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而做出的规定,受益者是社会全体人员,成本应当由社会全体人员公平负担,不应当由林农单独承担。
(二)公民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宪法基础
财产权是一项自然权利,与生命权、自由权密不可分,因为公民财产是公民维系生命、追逐自由的物质保证。承认并保障每个公民的财产权,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责任。各国宪法都将财产权列为了公民基本权利。虽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用公民的私有合法财产,但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件:一是符合法律规定,二是严格依照法律程序,三是给予相关公民一定的补偿。
在我国,林地的权属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林木的权属包括国有、集体所有和个体所有。对于公益林,除“抚育性采伐”、 “更新性采伐”和“低效林改造”,基本上是禁伐。农民的林地一旦被划为公益林,树长得再好,也难以变现。既然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限制了公民的财产权,就应当给予特定的相对人合理而公正的补偿,否则,就会伤害利益主体,阻碍其进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活动。
(三)权利冲突的衡平,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法律需求
权利只有边界和范围,没有等级之分,正如博登海默所言:“人不可能凭据哲学的方法对那些应得到法理承认和保护的利益做出一种普遍有效的权威性的位序排列。”[3]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权利冲突是难以避免的。立法只是个无限接近事实的状态,仅仅通过立法不可能完全解决权利冲突,解决权利冲突最实际的方法就是对冲突关系进行利益衡量,找到平衡点,实现权利配置最大化。
2003年起,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逐步推开,实际操作中,公益林都被纳入了林改的范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关键点是实现林农的承包经营权,而公益林承包户的承包经营权基本处于“无法自主”的状态。在法律无法准确界定公益林承包户经济权利,又需要维护生态利益的时候,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就成为了现实中对受损利益做出的替代,间接维护了权利的平等和正义。
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制建设的缺失
(一)立法的缺失
我国关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立法,主要存在以下缺失:1.基本概念不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内涵只是停留在学术探讨阶段,没有得到统一明确的界定,其目的、价值以及制度顶层设计难以进一步落实。2.权利义务不一致。权利与义务是相辅相成相适应的,权利不应大于义务,义务也不可大于权利。当前,森林生态受益者的收益远远大于支出,甚至没有支出,而森林生态保护者的生态责任却极其严格,管护责任也没有与管护效益相挂钩。3.权利救济乏力。“无救济,无权利”,法律规定了公益林经营者有获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权利,但是如何保障该权利不被侵犯,权利被侵犯了应当依据什么样的程序去救济,没有明确的规定。4.重视程度不足。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践始于本世纪初,2005年,国务院就将生态补偿建设纳入重点工作内容,2010年,又将生态补偿条例列入立法计划,可是一直没有实质进展。这除了现实条件的制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二)公平正义的缺失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4]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生命力不是在于是否对生态保护者的个人利益牺牲进行了补偿,而在于是否给予了合理的补偿。2012年,除了中央财政,已有27个省 (区、市)建立了省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偿一共达到了184亿元。这个数字虽然比最初投入翻了几番,但是平均到18.7亿亩的公益林,每年每亩的补偿金额平均只有7元钱。这个标准不仅远不如外出打工收入,也与林地的经济效益严重脱节。例如补偿标准位于全国中等水平的安徽省,集体所有的公益林,2013年补偿标准提高到了每年每亩15元。而出租林地的年租金是每亩25元左右,商品林种毛竹的年收益约每亩500元,分别是公益林补偿的2.5倍和50倍。按照2012年安徽省的惠农政策,种粮农民每年每亩耕地可获得的直接经济补贴不下于77元。畸低的补偿标准,体现了当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公平正义的缺失。长此以往,公益林管护质量必将下降,这又会产生与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意义南辕北辙的效果。
(三)利益协调机制的缺失
权利在实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不同利益、不同权利的平衡,有时候不得不有所取舍。从目前的情形看,在协调经济与生态利益方面,我们做的远远不够。首先,经营者意志被忽略,无法把握利益平衡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将公益林承包到户,在名份上是优化了产权,激励了公益林管护,可是公益林的经营严格处于政府的掌控之中,对于生态效益的转化,经营户没有任何发言权。其次,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一刀切,违背了利益协调的现实性。利益协调的基本准则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但是在我国,除了简单划分国有、集体、个人所有公益林,不管林种,不论区域,甚至不跟踪生态效益产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都是一样的。再有,维护经济生态平衡没有多样举措,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独臂难撑。森林生态发展并不是一味的“堵”和“禁”,合理的经济利用不仅不会破坏森林生态,还会有利于森林环境保护,激励林农保护森林。《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是承认并允许对公益林进行相适应的经营开发的,然而,政府对公益林的管理政策始终是“管严管死”,公益林经营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
三、对策建议
(一)维护正义,加快相关立法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和最高成就。但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不是如何确证这一点,而是如何达成这一制度美德。[5]实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正义,关键就是要厘清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律关系中各个法律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对生态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给予合理补偿。首先,实现立法的完整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面临的现实经常是“无法可依”、“有法不明”。实现其立法的体系化,就是要深化该制度的顶层设计,明确制度内涵,围绕制度价值,细分权利义务,完善权利救济。其次,增强具体规定的可操作性。及时清理、修改和完善现行的规范,使之更加合理,也是立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森林法》规定违法进行采种、采脂活动的,要依法赔偿或被处以罚款。但是我国《森林法》和相关法律并没有规定如何才是合法采种、采脂,也没有统一的关于采种、采脂的技术指导性文件。再有,落实现有权利。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阻碍权利的实现,就是最大的不公平。保护生态,不代表停止经济发展。公益林是可以适当经营的,相关部门应当依法为经营户创造适当经营的条件,而不是一味“管严管死”。
(二)尊重市场,完善激励举措
我国林权结构比较复杂,林地属性只区分国有和集体所有,但是林木权属包括国有、集体和个人所有。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林地使用权又逐步与所有权分离,个人对公有属性的林地又享有了带有明显私有性质的承包经营权。在产权私有化的情形下,保障足够的公共产品和无价格产品供应,需要的是政府有效的参与和调控,根本方法就是对私人产业提供公共物品的行为通过利益的引导、收益的差异化进行激励。所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应当是根据实际情况,充满差异的。首先,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要尊重市场规律。提供的公共物品,如果能够具有市场价值,个人才会有动力对公共事业进行投资。作为生态产品的提供者,公益林经营户有权参与生态补偿市场,促进生态产品合理价格的形成。其次,补偿主体权利义务相适应。当前,完善补偿责任的重点,就是要使补偿主体权利义务相适应,收益支出相匹配,同时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确定补偿主体,让生态提供者的权利具有明确的请求目标。再有,管护责任要实现软着陆。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区分林种、生态价值、碳汇量的增长情况等,实现补偿差异化,促进管护主动性,更好地实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意义和目的。
(三)加强实践,探索补偿新形式
美国最高法院霍姆斯大法官有句名言:“法律的生命力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法律的经验来自于社会实践。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完善,离不开补偿实践提供的有益经验。当前,国内外都纷纷开展了很多生态补偿创新实践,对于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很有借鉴意义。这些经验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政府购买,比如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34%的德国公益林,完全由政府直接经营管理。我国在贵州省也开展了试点,由政府收购个人投资营造的重点公益林。[6]二是公共事业补贴,如福建省综合参考生态公益林数量及其对流域的贡献大小、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按每年每吨用水量承担生态补偿金。[7]三是生态补偿一体化,根据近期一份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的报告,在全球287个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付费项目中,有61个是与流域生态服务直接相关。[8]国内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践给予我们三点启示:一是落实补偿离不开政府的有效参与,政府有责任积极主动地开展创新实践;二是生态补偿应当逐步实现一体化,让各类生态资源能够共享生态收益;三是补偿实践要因地制宜,尊重市场、尊重规律、尊重各地发展实际水平。
(四)结合国情,协调现实利益
权利是具体的,法律的实践受制于社会的现实条件。在这个资源“适度匮乏”的社会,人的社会性和有限理性,决定了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决定了利益妥协是必须选择的。何为合理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是一个利益衡量问题,各国国情不同,取舍也不同。一方面,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经济水平不高,生产力不够发达,“林业大县”往往是“财政小县”。另一方面,由于前期发展缺少生态规划,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保护环境是一种利益,发展经济也是一种利益。不同群体对生存、发展与环境的需求都有权利得到满足。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他指出,在多种需要未获满足时,首先应当满足迫切需要,这样才能显示出激励作用。所以,生存、发展与环境利益没有位阶,政府应根据现实情况,协调利益,分层次地满足不同需求,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1]黄金兰,周赟.权利冲突中的少数主义原则 [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5).
[2]王太高.行政补偿制度研究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5.
[3]邓正来译,埃德加博登海默[美].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00.
[4]何怀宏,等译.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
[5]万俊人.制度的美德及其局限 [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3).
[6]吴萍.我国集体林权改革背景下的公益林林权制度变革[J].法学评论.2012,(2).
[7]刘克勇.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的思考 [J].中国财政.2009,(9).
[8]梦梦,尹峰,陈文汇.长江上游流域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调查分析 [J].林业资源管理.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