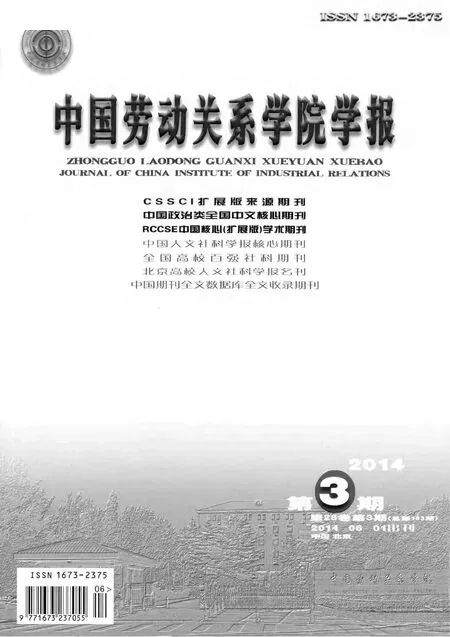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研究*
——兼论我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马 铮
(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被吞噬,进而面临消亡。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挖掘,却在商业开发中与原本的文化渐行渐远。国际社会及各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随之愈发重视。我国也于2011年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虽然该法存在诸多争议,但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明确的宏观保护依据,是我国文化立法领域一个标志性事项。该法内容以行政保护和行政指导为主,着重强调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保存、调查和登记等事项,其实质是一部行政性质的公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私法保护问题并未做出有效规定。在实际的立法起草过程中,也曾试图将民事保护模式作为第二种保护模式在法律中建立起来,但由于对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问题尤其是著作权保护问题存在着不少理论障碍,共识基础依然薄弱,才最终放弃了对私权保护的具体规定。[1]在这些理论障碍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问题是一个无法躲避的难点,对于主体体系划分以及功能界定是法律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试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体系划分为基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体系的法律构建做一些探讨。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内涵界定
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的缩影,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和真实反映。《世界文化多样性公约》第一条:“保持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如同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一样必不可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公共性,也注定了其主体之争带有必然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保护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的民族和传承人是应然保护主体,政府、商界、媒体、学界等则是实然保护主体。实际上,从物的所有权理论角度来划分,这些主体应分为权利主体和保护主体。
所谓的“权利主体”是指参与到法律关系中,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权并承担相应义务的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问题,是理论界讨论最多但也一直存有争议的问题。在此问题上形成的观点有:国家主体说[2]、群体主体说[3]、个人主体说[4]、类型化主体说[5]以及群体与传承人按照建筑物区分所有制度形成的二元权利主体说[6]等观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保护主体是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保有、传承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主体;狭义的保护主体是指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享有所有权,仅对其发展起重要推动作用的群体。广义的保护主体包含权利主体和狭义的保护主体,因为权利主体是产生、保有或传承传统知识并有权采取措施控制、保护、发展自己传统文化的主体,权利主体行使对传统知识的各项权能时,保护传统知识是应有之义。但从所有权归属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所起的作用方面分析,狭义保护主体与权利主体又存在显著的区别:狭义的保护主体并不传承传统知识,而是凭借各自不同的资源优势保护、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静态或动态的发展,其具体包括了国家、学术界、工商界、媒体和中介机构,其职能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政策、资金、智力和舆论支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对保护主体采用狭义概念界定。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保护主体界定的缺失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保护主体界定的正当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更多地被视为是一部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法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上也以行政保护为主,我国从国务院到地方都颁布过一系列关于传统文化保护的行政法规。例如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旨在开发保护传统优秀的手工艺品种和技艺。2000年,云南省率先在全国通过立法程序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出台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随后,贵州、江苏、浙江、宁夏等地也相继出台了民间美术与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各种法规规章。这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国性行政立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而民事性保护模式中由于主体问题的不确定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内容的庞杂,各种利益关系在权利主体问题未确定的情况下更是难以厘清,所以关于民事保护模式应采用何种法律规则并未取得一致结论。加之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性保护的立法研究和经验都比较成熟,为了加快立法的出台,行政法保护模式就成为法律必然选择。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用行政化公权保护是最直接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本身具有行政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均是私权主体之外的主体,本身并不享有私权上的权利和义务,这种主体的非私权性和法律的公权性形成了一种契合。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这些保护主体的地位和功能予以界定就具有了一定的正当性。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保护主体定位的缺失
非物质文化遗产各方保护主体虽在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均有所体现,但规定得过于笼统、抽象。对于保护主体和权利主体的关系应如何定位,在实际开发过程中如何有效保护传承人和传统文化所在地群体的利益,都没有做出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主要规定了政府的职责,在45个条款中以国家或政府做主体的就多达26条之多,涉及非遗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及传承人的认定等方面,虽然非遗保护中强调政府介入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但过度依赖政府的保护而不对其权利加以规范,则会出现政府强势“主导性保护”,致使非遗发展丧失原真性的局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法》37条对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开发行为予以了认定,并在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的基础上给予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的政策,但法律并未建立惠益分享制度,因此,开发后的利益分配问题变得十分模糊,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丧失了积极性,导致了开发中出现的“失真性、破坏性开发”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学界的职责在33条、34条和35条中进行了规定:鼓励学界开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科学技术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整理、出版活动等,在学校层面,应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部署,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教育活动,但应如何开展科学研究以及在何层次教育中开展教育活动法律未予以详细规定。对于新闻媒体的职责仅在34条第2款中做出了倡导性规定。正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未对各保护主体具体职能进行定位,才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了诸多问题:
1.政府的强势主导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失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政府主导力量过于凸显。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追寻当下的经济利益或是为了追求“政绩工程”而有计划地“设计”出一些文化,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从自在的民间习俗发展成为各种展演式的“官俗”。[7]文化保护变成了“官员工程”,政府在轰轰烈烈的保护工作中走过场,使文化保护失去了本来面目。
2.开发商掠夺式产业开发导致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破坏”。在政府文化商业化利用思维的指引下,开发商进行文化产业化运作,随之而来的是文化内容的选择权向“资本”倾斜,影响市场需求的审美感知变化引起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感知率变化。[8]这种变化使非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渐离渐远,文化传承链条被人文割裂。
3.学界被权力和资本“绑架”而丧失自觉自为的保护意识。作为先知先觉的学术群体,却在政府主流话语权高度政治化、资本化运作的指挥下,渐渐迷失在各种项目评审、申报中,其所发掘的许多文化价值成为了资源博弈的工具,权力、资本和文化相互结合以达到其“设计”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而保护的目的。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体系的法律构建
产生上述问题的关键原因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相关的行政法规或规章均未对政府具体职责做出规定,进而导致其他保护主体职能的混乱,致使在实际保护中出现了“不保护不破坏、保护等于破坏”的怪象。除此之外,统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介组织也未在现行各层级法律规范中得以体现,使权利主体与保护主体之间、保护主体与保护主体之间丧失公平有效的沟通平台。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实际保护需要在法律规范层面对非遗保护主体的职能进行明确定位。
(一)重新定位政府角色从“强势主导”转变为“适度引导”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将政府的功能定位在以引导、调解和保护为原则,以法律、经济和宣教为手段,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想得到有效保护,需寻求一条增强其活态性、民间性、生活性、生态性的可持续发展之路。[9]这需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重新定位政府角色,从“主导”逐渐向“引导”过渡,其职责主要是:
1.建立健全完善的文化保护管理体系,采取代表名录设定、传承人认定与资助等行政措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行政制度层面的保护。
2.政府应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
3.建立完善的资金运作体系。一方面,政府应加大专项财政拨款力度;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基金等方式拓宽资金募集渠道,为非遗保护提供资金资助。
4.政府应加强与其他保护主体的合作。政府应出台传统文化商业开发行政审批制度,坚决杜绝以盲目牺牲民族文化而追逐商业利益的行径,商业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相结合,逐步引导消费型旅游向保护型旅游方向发展。
5.从教育抓起,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国家应把非物质文化的宣传融入到从小学到大学的各层级教育中,设置不同形式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使中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精髓能得以撒播和延续。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介组织的构建
在非遗保护中,可以考虑以音乐著作权协会的组织模式为视角,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三方组织。该组织是不隶属于任何行政部门的公益性社团,其主要功能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与保护主体之间、保护主体与保护主体之间搭建对话交流的平台。该组织可以通过某种合理的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做出划分,进而将组织划分成不同的部门。组织成员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志愿者加入,从而确保该组织具有专业化优势。组织的资金来源可以是政府财政拨款,也可以吸纳社会基金以及社会捐助等多种资金进入,还有一部分则来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化获得的部分收益以及在诉讼中得到的赔偿。资金流向主要是资助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推广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度。资金由组织统一管理、运作,政府主管部门、传承人、新闻媒体对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介组织与社区、村委会或居委会相结合,根据不同的文化遗产类型,开展推广与宣传活动。组织与大学或科研机构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进行合作,定期展开学术交流活动。可在大学中设立教学展示基地,通过公益活动、社团组织、科研项目等多种方式在大学生中推广非物资文化遗产相关知识,提高非遗受众群体的层次。由于中介组织具有非官方性、民间性的特点,其所涵盖的范域相当广泛,对民间社会的渗透力极为强大,与民众有着天然的联系优势,[10]因此,它所开展的保护工作能够使国家从行政层面更好地统计、掌握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情况,进而进行有效管理,对于政府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决策咨询机构。
(三)在政府适度引导下,明确商界、学界和媒界的职能
商界应在政府政策指引下,摒弃为追逐经济利益而牺牲传统文化的“短视性”开发思维,在保护基础上进行有序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应建立良好的惠益分享机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在产业开发中能真正、持久获利,从而保持文化传承的积极性,以实现良性开发。学界应与喧嚣热闹的项目评审和申报相剥离,其职能是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在浩瀚如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中,梳理出非遗传承与流变规律,并吸收其他国家在非遗保护中的正反面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构建适合我们文化传统的非遗保护模式,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媒介应积极发挥自身舆论宣传的功能,以纪录片、影视作品、图片、文字等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宣传,扩大非遗受众群体的范围,进而对中华文化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使非遗的保护深入百姓日常生活,成为民众自觉自愿的行为。
非遗保护的关键问题在于使权利主体与保护主体、保护主体与保护主体之间能协调有效发挥各自职能。在这些主体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介组织是在目前制度框架内未明确存在的,但其具有其它主体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地域性、民族性和流变性等特征,因此,如何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介组织,并协调与其他保护主体和权利主体的关系,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1]朱兵.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的民事保护问题 [J].中国版权,2011,(6):14.
[2]王鹤云,高绍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机制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300.
[3]古祖雪.论传统知识的可知识产权性[J].厦门大学学报,2006,(2):14.
[4]崔国斌.否弃集体作者观:民间文艺著作权难题的终结[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5):77.
[5]费安玲.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基本思考 [J].江西社会科学,2006,(5):14.
[6]王吉林,陈晋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研究[J].天津大学学报,2011,(4):325.
[7][9]吕俊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去主体化倾向及原因探析 [J].民族艺术,2009,(2):7,11.
[8]曾芸.文化生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3,(3):93.
[10]刘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非政府组织角色研究—基于治理理论的视角[J].前沿,2009,(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