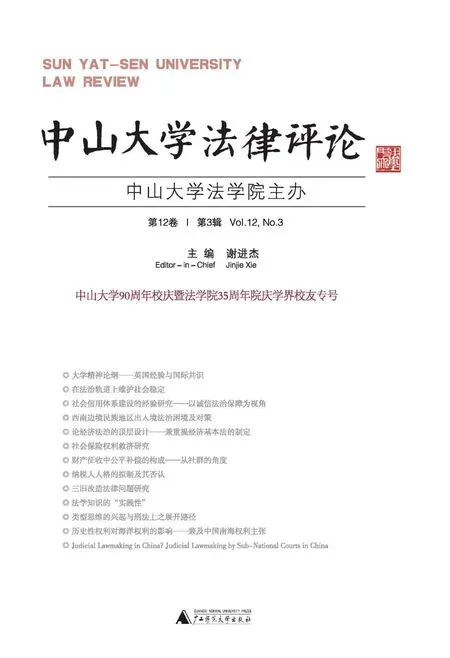大学精神论纲
——英国经验与国际共识
单文华
大学精神论纲
——英国经验与国际共识
单文华[1]
自从17岁考上中山大学以来,我就再没有离开过大学,不是在念书,就是在教书,有时也承担一些管理工作。我在英国的大学里前后待了16年。这期间,我在剑桥大学这所老牌大学做过访问学者,读过博士学位;也在牛津布鲁克斯大学这所新派大学任过教职,从讲师开始,一直做到教授;还在伦敦、利物浦等“红砖大学”兼职从事过教学研究工作。现在虽然已经全职回国,但在剑桥仍然保留着一份资深研究员的兼差,因此对英国的大学可以说有一定的经历和了解。
在我看来,英国的大学精神,就是大学作为一个由学者、学生组成的学术共同体的独立和自由的精神。[2]毫无疑问,这种精神与中大先师陈寅烙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精神,又可分为内外两个层面:对外,是大学治理的独立自主,简称“大学自治”;在内,是学术探索的无界自由,也即 “学术自由”。
大学自治
大学自治是英国大学的历史传统,也是英国大学的基本现实。英国关于大学自治的传奇故事可谓层出不穷。其中,牛津大学拒绝授予撒切尔夫人名誉博士学位一事堪称经典。1985年1月30日,牛津大学的议事厅里人声鼎沸,1000多名教师和学生代表正在激烈地辩论要不要授予他们的校友、当朝首相撒切尔夫人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辩,大学以738票反对、319票赞成的压倒性多数否决了给予撒切尔名誉博士的提案。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自二战以来,授予担任英国首相的校友以荣誉博士学位已经成了牛津的惯例,从无例外。但是,在牛津的绝大多数师生看来,这又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他们认为,“即使是王国最高长官,也不能期待我们授予她荣誉,而忽略她所推行的政策对我们学人所毕生信奉的价值以及所从事的工作的影响”。究其根源,在于“铁娘子”政府对教育经费的大幅缩减,使得英国曾经长期领先世界优势的高等教育陷于严重困难的境地。“如果授予撒切尔名誉学位,那将是对公立教育部门每一个人的沉重打击。”30年过去了,当年决定的对错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牛津顶住了政治和舆论的巨大压力,坚持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展示了数百年名校傲世独立的风范。
所谓大学自治,简单地说就是大学的事务由大学自己做主,不受政治、经济等外在因素的不当干扰。正如欧洲大学协会2011年发布的“大学自治排行榜”所揭示的,大学自治具体来说又可细分为组织自治、财务自治、师资自治和学术自治等方面。在所有这些方面,英国大学均高居欧洲教育大国中的最高位置。英国大学的高度自治,于此可见一斑。
英国的大学始于牛津和剑桥。和欧洲大陆的其他中世纪大学一样,它们一开始就是一个由学者和学生组成的行业性共同体。由于得到教会与王室的庇护,它们不仅拥有高度的自治,而且还享有诸多特权(例如可以免税、可以罢工),有“国中之国”的地位。19世纪以来,牛津剑桥的教育垄断被打破,伦敦大学等大学陆续设立,但大学仍长期游离于英国公共事业体系之外,英国政府并没有对大学进行系统的财政支持。1918年,面对一战过程中大学的财务困境,英国成立了大学拨款委员会,作为政府为大学提供拨款的咨询建议机构。1988年《教育改革法》通过以后,英国成立了大学基金委员会以取代原有的大学拨款委员会,增加了社会产业界人士的比重。随后,英国根据1992年《继续和高等教育法》组建了新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以取代原有的大学基金委员会,但基本延续了大学基金委员会改革的思路,继续扩大委员会中的产业界代表比例,进一步加强大学与社会产业界的联系,同时建立更加严格的质量监督和评价体制,以财政拨款为媒介,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既便如此,英国政府对于大学的调控以及产业对大学的介入依然遵循法治和间接的原则进行,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影响。正因如此,英国才能继续以大学的高度自治岸然立世,英国的高等教育也才能继续保持世界领先的卓越地位。
学术自由
如果说大学自治是大学精神的七级浮屠,那么学术自由就是这座浮屠塔里所供奉的佛骨舍利。大学是学问与知识生产、传承与养护的场所,而学问、知识得以生产与传承、养护的前提,就是有一片能够滋养知识与学问的自由与宽松的土壤。如同在钢筋混凝土里开不出鲜花一样,在没有自由的地方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有生命力的学问。
作为培养了世界上最多诺贝尔奖得主的大学,剑桥无疑是世界科学与学术的重镇。然而,当莱谢克·博里塞维奇校长在谈到剑桥科研环境的优点时,并没有列举有多少先进的实验设备,而是指出其提供了充分的学术自由,让科研人员有根据个人兴趣开展研究的时间和空间。剑桥明文列出的核心价值观第一条就是:“思想与表达的自由。”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曾在剑桥念神学的达尔文,后来却可以冲破神学观念和英国基督教环境的束缚,提出与“上帝造人说”完全对立的进化论。如果他的大学当初不曾给予这种自由思想的空间,就难以想象他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
在英国做研究很少受到干扰,想研究什么领域,召开哪个主题的学术会议,如果不用申请经费,从来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批,也从不会有人以会议议题或所发表言语“离经叛道”而横加干预。刚到剑桥时,我脑子里面更多的是国内几年研究积累的观念、知识和经验,不少带有比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用导师们的话来说,就是有点教条。比方说,谈到外国投资的征收补偿标准,往往就觉得要求充分补偿只是资产阶级贪得无厌的表现,不存在任何法律乃至道义的正当性。我时不时还会引用国内老先生们所确立的论据来和导师们“据理力争”,不惜面红耳赤。导师们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觉得我认真得可爱——只是他们会很温和地指出我需要看到硬币的另外一面。我在剑桥做的博士论文提出欧盟和中国应该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当时不少人都觉得这个主张有点太超前,因为欧盟当时根本就不具备缔结这种条约的法律权能。但是,导师们不但没有反对,反而特别支持甚至鼓励我做这个选题。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10多年以后的今天,欧盟不仅取得了这个法律权能,而且也正在和中国谈判这样一个条约。而这两方面,正是我的论文首次提出的两个核心观点。
事实上,在剑桥,就像在英国其他大学一样,师生平等对话、唯学是问的故事比比皆是。而我的故事要是和维特根斯坦(和罗素一样也是我在剑桥学院圣三一学院的院友)的相比只能算是平淡得不能再平淡的了。故事里说,维特根斯坦的剑桥博士论文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营里写就的,叫《逻辑哲学导论》。当时没有人能够读懂他的这部天书,因此出版商找到他的老师罗素。罗素自告奋勇,为这部书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序言,并为这部书的出版费尽心机。书出版了,但维特根斯坦并不领情,还说罗素根本就没有读懂他的论文!罗素不以为件,反以为豪,因为他知道天才人物往往有个性,而他作为老师,剑桥作为一所大学,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为这样的人才提供一片任其驰骋的广裹天空。
国际共识
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是在英国大学最为彰显的大学精神,但并不是只“属于”英国的大学精神。事实上,英国的大学最初效仿的是欧洲的大学,而英国和欧洲的大学又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大学发展。其结果是,在世界上比较有影响的大学,都遵循大体一致的大学精神。一个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来自世界上80多个国家的700多所知名大学对于1988年《大学大宪章》(Magna Charta Universitatum)的共同拥戴。其中就包括两所中国的大学: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
《大学大宪章》由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所首倡,并于1988年在该大学900周年诞辰之际,由来自世界各国的430所大学的校长们所共同签订。而该大宪章所确立的四个基本原则中,最根本的两个原则,正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其中,“大学自治”是大宪章所确立的首要原则。它开宗明义:“大学是自治的机构……大学的研究和教学必须从道义上和智识上均独立于所有的政治权威或者经济力量。”而关于“学术自由”,大宪章指出:“研究与教学的自由是大学的根本原则;政府与大学必须尽其所能确保对这种自由的尊重。”毫无疑问,这些表述正是大学精神的最好阐释。
千秋基业
大学之所以需要独立于政治与经济之外实行自治并享受学术自由,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在现实的世界里,推动社会的发展演进主要有三种力量:政治、经济和教育。它们各有其主体与载体。其中,政治的主体主要是政客和官僚,其载体主要是各种权力机关及其所掌握的各种权力资源;经济主要以商人与企业为主体,并以金钱以及其所能支配的广泛资源为载体;而教育的主体则主要是受过教育的人群即学者或学生,其主要载体则为以大学为代表的学校以及其所蕴育传承的知识、思想、学识与学问。
这三支力量之间既相互联系、互相支持配合,又相对独立、互相监督制约。其中,一方面,大学与教育亟需政治力量的保护与经济力量的支持,否则其生产与发展均将难以为继。古今中外的经验表明,成功的大学往往得益于政权的呵护和商界的扶持。另一方面,大学与教育又必须保持相对于政治与经济力量的独立性。否则它不可能开展其赖以生存的独立自主的思考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知识创新与文明传承,也就不可能为另外两个部门提供必要的人才供给和智力支持。可以说,对于政治与经济而言,大学与教育的独立自主和自由生发最符合其最大、最长远的利益。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往往是,政治和经济的成就可能倏忽间烟消云散,而大学和教育的成果却可以历久弥新,它们可以更深刻、更久远地定义并滋养着一个民族、一种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维护大学的独立自主与学术自由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和教育部门共同的事业,而且是它们共同的千秋万代的基业。
撒切尔曾经断言:“中国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只能出口电视机,出口不了创新的理念。”话粗理不粗。中国应该如何重拾大学精神,破解“撒切尔魔咒”,值得政治、经济和教育部门的远见卓识和深思慎对。
(初审:谢进杰)
[1]作者单文华,男,1987至1991年间就读于中山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英国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法学博士;曾任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终身教授;现任西安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法学院院长兼丝绸之路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所所长;兼任英国剑桥大学劳特派特国际法中心(LCIL)资深研究员、牛津大学出版社英文期刊《中国比较法学刊》(CJCL)主编、国际比较法科学院(IACL)衔成成员、美国法律科学院(ALI)成员、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长江学者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