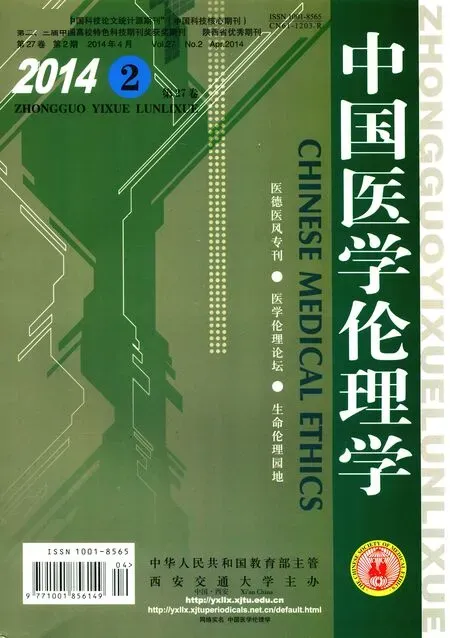从医学人文教学现状谈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路径
王 彧,吴雪松,尹 梅
(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leaf830222@aliyun.com)
1 医学中的人文教育
1.1 医学的二元本质:科学与人文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这段话,表明了医学不仅仅是治病救人的一种手段,同时也体现出一种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的医学人文精神。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说:“行医,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艺术。它是一种专业,而非一种交易;它是一种使命,而非一种行业;从本质上来讲,医学是一种使命、一种社会使命、一种人性和情感的表达。”纵而观之,医学,这个备受瞩目的词汇,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被深深地打上了“人”的烙印。从医学产生发展的目的而言,医学乃是为减缓人类病痛而存在的,因此,可以说它是集目的与手段双重属性于一体的学科。技术性是它的手段,人文性是其最终的目的。在这双重属性当中,医学的人文性是医学技术性中凝结的对人类生命关爱与尊重的精神,是医疗保健服务以行善为目的的宗旨,它涉及医学及保健服务的终极价值目标的定位,因而,医学的人文性可以被认为是医学的灵魂。[1]
1.2 医学人文教育现状:人文性边缘化
我国著名的医著《黄帝内经》中说到合格的从医者应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但长期以来重技术,轻人文的医学发展使得在医学教育过程中过分的强调医学的科学层面,忽视了医学关注人类价值的传统。医学教育中最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失落产生了这样尴尬的局面:疾病被通透彻底的探究,精细的处置,而痛苦却被无情的漠视,甚至被彻底的遗忘,医学的科学性、技术性与人文性、社会性,真理与真谛,正确与正义,痛苦与苦难,生命与死亡,人道与人性,技术与艺术之间的天平严重的失衡。[2]因此,如何借助医学教育这个手段探求医学存在的终极意义,找寻医学人文属性回归的根本路径已成为当代医学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2 医学人文性边缘化的原因
2.1 医学技术化倾向严重
医学的发展与进步要求对技术的追求无可厚非,但长期以来受传统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医学技术出现了激进的势头。尤其是随着一些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医学可以让以往必死无疑的人长期存活,让无法生育的男女获得孩子,让失去功能的废置器官和组织重新获得功能,甚至可以人工培育,克隆自身,组装生命[1]……医学被看成了无所不能甚至可以征服一切的科学。人们在享受着这些高新技术所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忽视了因这些高新技术应用而引发的冲击人类的尊严、医患关系的物化等一系列有着严重后果的问题,忘掉了医学维护人类生命尊严和人的权利这个核心价值。这种丧失了以医学人文精神为依托的对医学技术的狂热追求必然产生严重的后果。
2.2 医学社会化的畸形发展
医学发展的历程表明医学不仅仅关乎医疗这一单纯的领域,时代的进步赋予了医学更多层次的色彩。安乐死、试管婴儿、器官移植、代孕母亲促使医学走出校门,走出书本,成为社会的公众话语;经济利益的追求,商业化的趋势,律法的掺杂,大众媒体的导向、伦理道德的反思、政府的介入等客观因素的存在,也使得医学走下了高高的圣坛而融入到了纷杂的社会洪流当中。在众多利益角色的较量与抗衡中,医学的社会化不仅没有为医学归根结底属于人学的灵魂服务,反而其失人性化的色彩越来越重,并走上了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
2.3 人文学自身的纰漏
“医学本是最人文的科学,最经验的艺术,并且是最科学的人文。”[3]但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早期,人文学与医学日趋疏远。H·T·恩格尔哈特认为,人文学对这种分裂的局面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人文学的目的不再是关注人类的力量和存在的目的反而变得功利化,对狭隘的由少数主流专家确定的学术议题的迷恋成为大多数人文学者的研究方向,人文学者变成了文字与文本的技师,内心少了悲天悯人、关爱苍生的情怀,背离了日益发展的医学、科学与技术力量所带来的挑战。[4]另一层面,国内学者对于医学人文并不是没有关注,只是对于医学人文的内容、医学人文的内涵、医学人文的精神实质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反而是宏观的口号式的呼吁,这样的状况对于人文医学的发展并没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3 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之旅
3.1 原则
3.1.1 注重东西思想融会贯通。
一方面,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吸纳、传承。中华民族有着令世人瞩目的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也随之产生了一大批诸如扁鹊、华佗、孙思邈、张仲景、李时珍等医学大家,他们不仅有精湛的医术,更有着高尚的医德医风,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因此,作为新时代的医学人才,理所应当的要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学习先辈的仁心仁术,并使之发扬光大。另一方面,注重吸取西方的先进理念。医学人文的历史在世界各地都有其辉煌的一页,但真正的端倪却始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自20世纪中叶,他们便开始了艰辛的医学人文的回归之旅,时至今日已取得了丰厚的成绩和经验。因此,在承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接受西方国家的先进理念,去粗取精,为我所用,以便在自己医学的发展中构建与西方文化对话的新文化语境。[5]
3.1.2 注重结合受教育者的兴趣爱好。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医学人文主义教育不能只靠着单纯而呆板的理论讲解,也不能照本宣科的应付了事。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结合受教育者的兴趣爱好,将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相结合,这样既可加深受教育者的感官感受,还可以引导其作深入的思考,培养自觉的学习和接受的态度。同时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的融会贯通——实践永远是检验理论的金标准。
3.1.3 注重人文精神培养的长期性。
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不仅要体现在对医学生的学校教育过程中,更关键的是在走出校门走向工作岗位的过程中培养。毕竟,一个医者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工作岗位当中,学校教育阶段只是整个人文教育的初级阶段。要将医学的人道主义精神贯穿于所有的教育环节,包括工作后的继续教育。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导致人文教育链条的脱节,才能使医学人文精神渗透到每个受教育者的灵魂深处。
3.2 措施
3.2.1 课程整合。
这是最直观有效的方法之一。但课程的设置不是简单的医学人文课程的堆砌。而是按照发挥最佳效益的要求,重新进行组合与协调。哈尔滨医科大学经过积极探索和论证,在医学人文课程上主要采用“一贯制”教学形式。再次,注重隐性课程的设置。哈尔滨医科大学非常注重校园的文化建设,它不仅有着八十多年的历史积淀,而且有着远近闻名的绿化建设,同时它的中轴线式的由梁思成老先生设计的中国古典建筑也被列为了国家保护建筑。同时,哈医大还通过人文讲座、论坛等多种方式,使学生在无意识的心理状态下接受了校园环境由外到内所负载的信息渗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除此,每学期伊始,对于接受医学伦理学课程教育的班级,教研室都要组织学生到侵华日军731遗址、伍联德博士纪念馆、校史展览观、萧红故居等地参观,这不仅增进了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激发了他们的人文主义情怀。
3.2.2 教学方法的改进。
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让受教育者走出课本,走出课堂。在“一贯制”教学形式的要求下,哈尔滨医科大学在教学过程中重点采用情景教学法。此种方法的最大特点在于教师的角色较传统方法相对弱化,由以往的教师为中心转变为学生为中心。具体步骤包括基本理论介绍、场景设计、现场展示及理论总结。下文就哈尔滨医科大学麻醉班级医学伦理学情景教学法做具体介绍:
主讲教师根据所讲授的理论知识,结合临床当中的实践问题,将同学分成不同的小组,每组10~15人,组长一名,每组准备时间一周左右。小组成员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兴趣进行选题。此部分的关键在于主讲教师只交代一些对所有成员共通的要求:任务目标、规则和程序;其他部分诸如情景选择、查阅资料、理论应用、角色安排、组织排练等全部由学生自己完成。这部分是整个教学的重点,不仅检验学生对之前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应用情况,更多的是要考查学生如何在医学伦理学课堂上展现手脑并用的能力,以此更好的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潜能。实践中,各小组选择的主题与形式主要有情景剧与辩论相结合(代孕母亲)、情景剧与课堂ppt讲授相结合(试管婴儿)、分组讨论(医疗红包)、演讲(医患纠纷)、辩论(安乐死)、话剧(器官移植)六种。在此过程中每名学生都有自己特定的职责,能清晰的阐述自己的观点。同时,由于形式灵活,对于很多问题学生间能相互讨论甚至直接与老师对话,这就发散了学生的思维,使得现场气氛热烈,能以点带面的涉及更多重要的问题。每组学生展示结束后,老师会根据他们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此部分不仅包括医学伦理学所讲述的理论知识,还包括学生间的团队合作精神、对问题的应变能力、语言的组织、现场的表现等诸多方面,老师都会给予宏观的指导和建议。对于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老师也会交代学习主流的思想以及处理方式,但不对学生做硬性要求。这样做,既给学生指明了方向,更激发了学生对某一问题深入研究的动力,体现了医学伦理学课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此种方法真正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教师改变了以往填鸭式教学,学生由被动接受转为积极主动的参与。在参与的过程中学生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不仅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拓展知识自身能力,更提高了学生将所学专业知识灵活运用的能力。尤其重要的是教师在此过程中也感受到了学生的热情以及对知识的渴望,这更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无论从单纯的完成教学任务还是培养合格的医学人才都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医学伦理学课程属于对医学生医德教育的重要部分,因此,让学生们选择一些重要的主题进行思考、讨论,将有利于医学生医德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当然,除了为提升医学生的人文素养而积极探索有效的方式外,我们更应放眼世界,因为医学人文主义的回归以及利用医学教育手段对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已成为当代世界范围内的话题。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实际经验,在国际上也有不同的组织专门对此问题进行研究,通过与其他国家和组织的互通有无,才能不断丰富我们的医学人文内涵。
[1]杜治政.当代医学人文理念与实践论纲[J].医学与哲学,2009,30(1):3 -7.
[2]王一方.医学是科学吗[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 -7.
[3]Edmund D Pellegrino.Humanism and the Physician[M].Knoxville:University Tennessee Press,1979.
[4]Tristram H Engelhardt,Jr.The Birth of the Medical Humanities and the Rebirth of the Philosophy lf Medicine:The Vision of Edmund D.Pellegrino[J].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1990,(15):237-241.
[5]杨咏.文化自觉: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发展的价值资源[J].医学与哲学,2009,30(7):65 -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