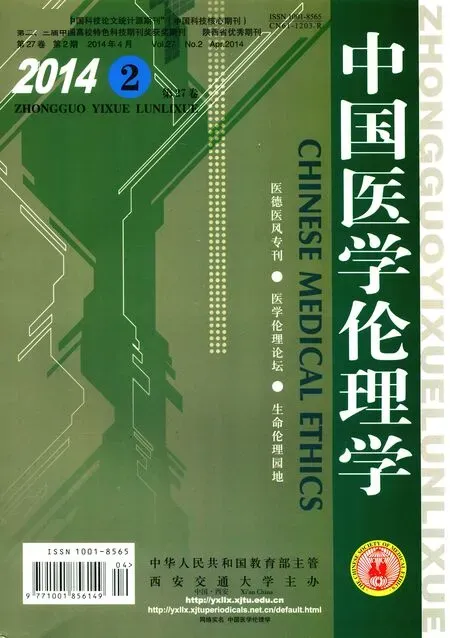Norman Daniels
邱仁宗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05,renzong@gmail.com)
1 学术生涯
Norman Daniels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Mary B.Saltonstall教授及伦理和人口健康教授。前塔夫茨大学Goldthwaite教授,哲学系主任,塔夫茨大学医学院医学伦理学教授,他从1969年至2002年在塔夫茨大学任教。他从卫斯理大学(文学士,最优,1964)、牛津贝列尔学院(文学士,最优,1966)、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普林顿论文奖,1971)获得学位。他在科学哲学(《Thomas Reid的“探究”:可见的几何学和实在论的论据》,1974;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再版,1989)、伦理学、政治和社会哲学(包括《解读罗尔斯》,197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再版,1989)和医学伦理学方面有大量著作。他在文集和学术期刊上已经发表了150余篇文章,这些期刊包括《伊希斯》、《科学哲学》、《哲学杂志》、《哲学评论》、《伦理学》、《哲学与公共事务》、《政治哲学杂志》、《哲学研究》、《哲学和现象学研究》、《国际哲学评论》、《医学与哲学杂志》、《生命伦理学》、《美国生命伦理学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海斯汀中心报告》、《卫生事务》、《自然医学》、《世界卫生组织公报》、《美国公共卫生杂志》、《经济学和哲学》、《戴达罗斯》等。他的著书包括《Thomas Reid非欧几何的发现》(伯特·富兰克林出版社,1974;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9),《公正的医疗卫生》(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我是我父母的看管人吗?论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公正》(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寻求公平待遇:从艾滋病疫情看国家医疗卫生改革》(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公正和辩护: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平衡》(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医疗卫生改革公平性的基准》(与Donald Light和 Ronald Caplan合著,牛津出版社,1996),《从机会到选择:遗传和公正》(与 Allen Buchanan,Dan Brock和 Dan Wikler合著,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不平等对我们的健康有害吗?》(与Bruce Kennedy和河内一郎合著,灯塔出版社,2000),《公平设置限制:我们能学会共享医疗资源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2008年第二版)。他的《公正的卫生:公平满足健康需要》(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8)是《公正的医疗卫生》的续篇,使他的关于健康的全面的公正理论形成一体。他目前的研究集中在“公平基准”,用于发展中国家(WHO 公报,2000,2005),以及为各种条件下设置资源分配优先次序和限制的决定制订公平程序,包括墨西哥新的健康保险计划(《卫生事务》,2003;《柳叶刀》,2005),以及全球公正问题。
作为美国医学研究所(IOM)成员,海斯汀中心研究员,国家社会保险科学院和国际健康公平研究会的创建成员,他向美国的组织、委员会和政府以及国外就公正和健康政策问题提供咨询,包括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总统医学伦理问题研究委员会。他担任美国克林顿白宫卫生保健特别工作组的伦理工作小组成员(1993年春),关于成本效益和临床预防医学的公共卫生服务专家组成员,关于老年人医疗照顾计划社会角色的国家社会保险科学院研究专家组的成员,以及关于老年人医疗照顾计划改革的世纪基金会专门工作组成员。他作为创建成员为由美国医学研究所和生命科学委员会建立的国家癌症政策委员会服务四年,担任美国开放社会基金会医学是专业的研究计划顾问委员会以及泛美卫生组织国际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最近担任美国医学研究所在管制情境下运用成本效益分析委员会委员,以及评价以社区为基础的预防项目委员会委员。他最近还担任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加拿大卫生研究院人群和公共卫生研究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他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医学图书馆、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退休研究基金会、绿色长城基金会等的奖学金和资助。1998~2001年期间,他获得了美国罗伯特·伍德·约翰逊研究者奖,他的基准国际应用研究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2010年,由于他因指导研究生而被哈佛大学研究生协会授予埃弗雷特·门德尔松奖。
(崔庚申,译;邱仁宗,校.)
2 代表作
公平与人群健康 -更为宽广的生命伦理学议题①Norman Daniels挑选这篇论文作为他的代表作,曾发表于Hastings Center Report(2006)。全文2万多字,这里是节译。
在生命伦理学发展的起初几十年中,生命伦理学主要关注两个领域中的问题:医生与病人、研究者与受试者之间非常特殊的二体关系以及普罗米修斯式的挑战,即伴随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中的新知识和新技术而来的权力和责任,包括与延长和终止生命相关的权力和责任问题。这种二体关系带来重要的好处,同时也有值得注意的风险,在权力和权威方面存在不平等,还要受权利和义务的约束。这就给伦理学探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媒体特别喜欢普罗米修斯式的挑战:在人与人、人与动物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我们如何扮演“上帝”的角色,但是又不有损我们的道德立脚点。这些挑战吸引人们对如何为了个体和集体的好处负责任地使用知识和技术,进行严肃的探究。不幸的是,这些挑战也形成了当代文化战争中的前线战壕。
生命伦理学主要关注对这种二体关系和新兴技术进行体制外的考查,这就意味着不去探讨与人群健康及其公平分配相关的重要问题(尽管对这一普遍概括有例外)。由于医学和医学研究对个体和人群的健康有影响,医患关系以及研究者与受试者之间的关系的确影响人群健康。但是如果不考查更为广泛的体制状况和调节人群健康的政策,有时候对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往往是短视的,不能理解和去探讨这些二体关系发生的情境。同理,关注新异技术有可能使生命伦理学忽视更为广泛的影响健康的决定因素,从而忽略影响本国和全球更为广泛的利益的因素。
为了推动更为宽广的生命伦理学议题,我将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公平问题:①不同社会群体健康的不公平以及减少健康不公平所需的政策,②社会迅速老龄化情境下的代际公平,③国际健康不公平以及影响国际健康不公平的体制和政策。上述的每一个方面都具有国内和国际的含义。
为了健康公平,我们必须做什么?
健康均等论者和健康最大化论者。我认为健康意味着正常的功能活动,也就是说没有心理和躯体的病理变化。②这种表征在价值中立的正常功能活动论述(例如Boorse的论述)与规范性的病因学(或进化论)论述(例如Wakefield认为精神障碍是有害的功能障碍的论述)之间取中立地位。这些论述都没有将病理状态简单地看作“不需要的状态”而不提供一种清楚的可归因的观点,这种观点将这种状态视为机体内在某一层次上的功能障碍。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广为援引的定义是:“健康是身体、心理和社会的安康,而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1946年6月19~22日国际卫生会议采纳的WHO章程序言,1948年4月7日生效)生物医学对健康的定义比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显然要窄。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将健康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几乎所有的安康状态,因此健康不再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有些实际测量人群健康的人,例如流行病学家,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偏离正常功能活动的状态。正如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将健康理解为正常功能活动与讨论有关社会决定因素的文献中揭示的健康决定因素的广泛观点是完全相容的。对于健康的这种描述影响到怎样才算是追求健康公平。[1-2]每个社会都会有健康的人和不健康的人。理解健康公平这一目标,即健康均等论者目标的自然方式,就是说我们应该最终使所有人都健康;这就是帮助他们在正常生命期限内功能正常。③Rawls的社会契约境况包括一个简化的假定,即所有人在正常寿命内都是完全有功能的。我们可将它视作一个默认的均等论立场。追求平等意味着“提升”,使所有那些不完全健康的人达到健康状态。④我的健康均等论者其行为类似Parfit的“优先排序论者”:如果对于处于健康糟糕的人没有合理的弥补增益,人们不要将一些健康的人拉下来使他们与处于健康糟糕的那些人平等(将有视力的人弄瞎以与盲人的健康状态均等化)。这样做将破坏使所有人在正常寿命内完全正常这一根本的均等论目标。健康最大化论者的最终目标和健康均等论者的最终目标是一样的:即如果所有人在正常寿命内功能正常,那么我们就是将人群健康最大化了。健康显然与收入(以及安康)不同。收入没有自然的终点,富总是可以更富,但健康是个有限的概念。完全健康就是完全健康(功能活动正常)。
尽管健康均等论者与健康最大化论者的最终目标是趋同的,通常他们主张通过不同的策略或政策,以实现完全健康人群这一共同的终极目标。最大化策略或政策为投入的资源谋求可实现的最高水平的整合措施,而不管健康如何分配。而关心健康公平的人们主张对健康如何分配施加重要的约束。
减少健康不平等和未解决的分配问题:当我们考虑消除健康不公平,甚至健康不公正时,同样产生了分配问题。通过国际协商达成的8个千年发展目标中,有5个是通过减少贫穷或给缺乏教育的人们提供初等教育来减少不平等。然而有3个健康目标是说,减少有关指标的人群总数,例如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David Gwatkin为达到这些总目标提出两种极端进路的模型。[3]最大化的进路是通过将资源给予那些已经比较富裕但更易因这些改进策略而达到预期的人,旨在迅速实现这一目标。均等论的进路旨在首先帮助那些最贫穷的人,然后帮助那些次贫穷的人,如此等等。围绕着千年发展目标的激励方式和地理政治意味着很有可能实施最大化策略,因为即使它实际上增加了人群的健康不公平,但资助者想要快速得到结果。有些人贫穷,他们就是由于某种理由比别人多病,这在道德上不成问题,在这种情境下产生了未解决的分配问题。在千年发展目标问题上,正如普遍担忧群体间的健康不平等一样,由于社会对造成基本健康不平等负有责任,基线分配本身在道德上就成为问题。美国的种族差异、英国的族群差异以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HIV/AIDS现患率的性别差异也许是明显的例子。现存基线的不公正使人们格外关注将不平等最小化,促使人们努力注意美国健康的种族差异,更加努力减少英国、瑞典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阶层差异。
社会决定因素和健康不平等。医疗服务的平等可及本身并不能确保公平,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卫生系统中对公平和总体健康受益最大化之间做出错误的权衡。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公平分配医疗或甚至公共卫生资源来实现健康方面的公平。健康不公平有着更为复杂的根源。影响我们健康的不仅仅是人们能够就医或住院治疗有多容易,不仅仅是减少来自传统公共卫生措施的风险(尽管这些因素确实很重要),也有社会政策更宽广的方面,这种社会政策与我们的社会地位和我们社会的基本不平等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4]如果我们接受我们允许在我们社会存在的不平等在其他方面是公正的,但这些不平等又产生健康不平等,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将这些健康不平等仅仅视为本身是公正的吗?或者群体之间的健康不平等是否始终是改变其他物品分配的根据?我们的答案可能取决我们认为造成健康不平等的其他不平等的种类。
拓展生命伦理学的议题。生命伦理学应当给涉及公平与最大化不同权衡的方法的政策决定提供指南。对于这项工作有两个关键的层面。
首先,有一项纯粹规范性的工作,是对原则达成共识,这些原则会在我们的政策选项形成的种种情况内引导我们,包括那些在发展和传播新技术中所引发的问题。这些生命伦理学议题与这一规范工作有关:
推进在未解决的分配问题上现存的伦理学工作;阐明何时某一健康不平等是不公正;解释不公正如何影响未解决的分配问题;阐明什么算作减少健康不平等的合理进度;在关于减少健康重大差异的实际政策选择情境下,检验他们的含义,包括那些涉及新技术传播的政策。
第二,生命伦理学必须考虑,当我们在对原则(这些原则能够解决这五项议题中我们遇到意见分歧)无法达成共识时,我们要做些什么。所有这些问题必须以被认为是公正和正当的方式实时得到解决。当我们在分配原则上缺乏共识时,我们必须依赖于程序公正来使我们公平和正当地解决道德分歧。实际上,程序公正必须补充解决问题的原则性方法,因为凡是我们能够达成一致的原则总是过于不确定或过于粗糙以至于无法解决争论。我所扩展的议题要求生命伦理学来做如下工作:
研发公平程序的综合论述,以便持不同意见的通情达理的人能够将政策视为公平和正当的;将这种论述应用到必须解决政策问题的种种体制情境中。
在老龄化社会情境下不同年龄组和出生队列之间的公平
社会老龄化,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将会逐渐成为21世纪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社会老龄化与两个缺乏分析的代际公平问题错综复杂地交叉在一起。尽管我早先已经写到过有关年龄组间的公平和出生队列间的公正问题,但我低估了在面临持续社会老龄化时将这些问题整合解决的难度。
在最近许多书籍的标题(通俗用语是“老年地震”,“老人潮”或“世代风暴”)中,社会老龄化被视为一种危机,即使这是一个成功而非失败的结果,即通过广泛追求健康和计划生育的政策来达到减少死亡率和生育率的目的。当某一生育队列远大于其后的队列时社会老龄化就会加重——例如美国战后的婴儿潮或降低死亡率后但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的中国队列。社会老龄化是全球现象,它不仅对健康而且对社会结构都有广泛的影响。
虽然发达国家未来50年后老年人口比例将会翻倍,从15%到27%,但在东亚则是三倍,从6%到20%。到2050年,中国将会有3.32亿年龄在65岁或以上的人,几乎等于1990年全球老年人的人口数量。[5]到2050年,有20亿年龄超出60岁的人将生活在我们这个老龄化的世界上,并且大多数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快速的社会老龄化将会发生在不及发达国家的财富和完善的经济制度的情况下。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中国是未富先老,而且不仅中国一个。在1990年到2025年间例如哥伦比亚、马来西亚、肯尼亚、泰国和加纳等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率预计要高出英国和瑞典8倍。[6]到2050年,东欧的过渡型经济将拥有28%的老年人,拉丁美洲将会有超过17%的老人,远远超过美国现在的比例。⑤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Aging,chapter 3.
社会老龄化的两个效应。社会老龄化显著改变了一个国家内的需求,使得对稀缺资源的需求在不同年龄群体之间产生出新的和强化的竞争。它也降低了社会为满足那些需求而继续采取措施的能力,加强了出生队列之间的竞争。这些效应加在一起引发了代际公正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不同的人口统计学条件下本来可能没有被注意到。
在发展中国家,问题不是像在发达国家那样为老年人提供的公共支持的社会和医疗服务的可持续性问题,而是缺乏正式的社会支持结构问题,例如传统的照护模式的可持续性,这涉及与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老年人,如在中国那样。中国必须面对其非常严格的人口政策所获成功带来的特殊后果。与美国相同,中国将有许多老年人没有子女,并且独生子女赡养的老人甚至比美国更多。中国将此称为“一二四”问题:一个孩子必须照顾两个父母及四个祖父母。1996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一个法律要求:成年子女应赡养他们的父母,显然预见到传统的孝道义务将会由于新的人口现实而被拉紧至崩溃的边缘。但这是法律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在其他快速老龄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尚无有违传统家庭价值的医疗和收入保障系统,这样的法律也不起作用。
随着社会老龄化而增长的医疗需求以及医疗需求状况的转变要比脆弱和老年人群的长期照护问题更为广泛。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心血管疾病、慢性肺病、糖尿病、关节炎和癌症以及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痴呆疾病的患病率增加了。治疗这些疾病的开销不断增长,给发达国家的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并加剧了竞争。这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中将会更严重,这些国家的医疗卫生刚起步难以满足慢性疾病的需要。在极其缺乏资金的医疗系统中,加强对中老年人慢性疾病的医疗服务意味着从所有人群的初级医疗和预防保健中转移走资源。
根据年龄进行配给在一些资源稀缺的条件下是可允许的,因为这样进行分配并不是不审慎的。这种论证并不是基于关于年龄分配公平性的特殊或有争议的直觉(正如Allan Williams所主张的那样,老年人已经拥有过他们美好的时节,[7]或如同Frances Kamm所说,年轻人比老人需要额外的时光)。这仅仅依赖总体上审慎分配的模型。由于通情达理的人们对这种模型的可接受性以及具体问题(例如按年龄配给)尚存争议,我们就需要我之前提到的那种公平程序来解决年龄组间优先顺序设定的争议。
解决年龄组问题的方案必须与解决出生队列问题的方案相容。我曾于二十年前提出,如果这些出生队列通过这种设计拥有可资比拟的“受益比”,那么每一个队列都得到了公平的对待。一些老年人在年轻时不可得的新技术、而现今年轻人在其生命期限内可得,这就提出了队列间公平的特殊问题。
我建议的生命伦理学议题必须解决如下问题:解决由年龄组问题所引起的分配问题,包括新技术对生命期限内资源分配带来的影响;评估按年龄配给的可允许性;考虑卫生体系中年龄的偏见,例如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长期照护的不足,以及我们方法论(例如成本效益分析)中的不足;并考虑在这些问题上通情达理的人有争议时的公平程序;研究持续性的社会老龄化对公平对待各队列同时不损害对不同年龄组问题的解决这一复杂问题如何影响。⑥私有化策略不解决这个问题;它们仅代表这种公平要求的一个结论,而且这样做时没有让我们使用解决年龄组问题的设计。此外,私有化甚至不是像提高收入那样推动生命期限的医疗卫生系统。
国际公平与健康
我之前曾提出,如果健康的不平等是源于影响人群健康的社会可控因素不公正分配(正如被罗尔斯的公正原则规定为公平的那样)的话,那么这种健康不平等就是不公正的。从这种理想的视角来判断,实际上世界范围内存在着许多健康不平等——因种族和族群、阶层和种姓、性别所致。健康不平等遍布全球。
不幸的是,这种说法并未提及国际公正这类重要的问题。在什么时候不同社会间的不平等是不公正的呢?作为一个公正(不是慈善)问题,在改善健康较差社会的人群健康时较为富裕的社会该做些什么?假设A、B两国各尽所能公平地分配了影响健康的社会可控因素,并且在各亚群体间没有明显的不平等。尽管如此A、B两国的健康结局仍不平等,因为相较B国,A国拥有更多的资源投入于人群健康。那么产生的国际间健康不平等是一个不公正问题吗?假设B国通过民主方式选择不尽其所能来维护其人群健康,反之宁愿选择其他社会目标,使得其人群健康比A国较差。因此产生的健康不平等是否是一个国际公正问题呢?
由于下列两个理由,将这个问题重新表述为国际公约及宣言认可的健康及医疗卫生的人权问题,并不能改善实际状况。第一,国际确保人群健康权的法律义务主要将落在对本国人群负责的各个签约国肩上。尽管国际人权协议及宣言也设定协助其他国家确保人权的国际义务,这些国际义务不可能主要集中于健康和医疗卫生的权利上。即便当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援助时,外在力量无法像进行干预防止侵犯其他权利那样跨境确保人群健康。第二,即便在不同国家健康权得以确保,各国间的健康不平等仍可能存在。因为在某国确保某项权利所做的一切不见得总能适用于其他国家,健康和医疗卫生权被视为“逐步地实现的”。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敦促成员国采取步骤,单独地或通过国际援助,尤其是经济和技术的援助,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可得的资源,采取一切合适的手段,尤其是包括立法措施,着眼于逐步地达到完全实现所有人享有最高的、可实现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的标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所有人享有最高的、可实现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的标准的权利”,《人权委员会决议》,2003/28。由于必须权衡制定健康之中的优先次序,通情达理的人对如何最好的满足这项权利或存争议。因此一些不平等或许被归于“逐步实现”的合理努力的范围内。此外,由于各国资源不平等,尽管各国仍努力确保本国民众健康及医疗卫生的权利,但不同国家仍或有不平等的健康结局。诉诸于人权的论证无法告诉我们,这些不平等是否不公正,并且也没有告诉我们较富裕的国家对于解决这些不平等负有怎样的义务。
对健康的伤害:最低限度策略。如果富裕国家采取一种做法或政策,或强加一种制度性秩序,可预见这样会使较贫困国家的健康比不这样做会更糟,具体地说使之比不这样做更难实现健康或医疗卫生的权利,那么,按Pogge的意见,这就是通过造成人权的“赤字”来伤害这一人群。[8]由于这种伤害是相对于国际认可的公正标准(保护人权)而界定的,Pogge论证说,强加这种伤害是不公正的。而且,如果有可预见的其他可供选择的制度性秩序可合理避免人权赤字,就有国际的公正义务来选择促进权利的办法。
医务人员的外流。医务人员从低收入国家人才流失到经合组织国家可例证Pogge的关注。情况是严重的。在20世纪80年代加纳受过训练的医生60%以上移居国外。[9]在2002年加纳47%的医生岗位和57%的注册护士岗位是空缺的。大约有7000名移居国外的南非护士在经合组织国家工作,而在南非公立医院有32000名护士空缺。[10]在美国,每10万人有188位医生,而在非洲的大部分每10万人只有1~2位医生。人才流失大概不是健康工作者分布不平等的唯一原因,但它显著地促进了这一不平等。
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既有低收入国家工作条件和机会的恶劣之“推力”,又有在别的地方更为吸引人的条件之“拉力”。这仅仅是由“移民权利”支持的“市场”在起作用吗?Pogge关于国际制度性秩序的论证对事情把握要比含糊不清地诉诸市场更明确。当20世纪8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条件恶化时,国际借贷人,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坚持这些国家大幅度削减公共资金资助的医疗卫生系统,并采取其他措施减少赤字开支。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喀麦隆。这些措施包括暂停招募医疗卫生工作者,强迫他们在50岁或55岁退休,暂停升迁以及削减福利。卫生部门预算从1993年的4.8%紧缩到1999年的2.4%,而私人卫生部门却在增长。[11]结果,公共部门的医疗卫生工作者转移到私人部门,其他人流失到国外。国际制度性秩序增加了这种“推力”。吸引医务人员到经合组织国家的“拉力”也不仅是经济需求的溢出。发达国家有目标的招募力度如此之大,将整个护士阶层从南半球的大学剥夺走。2000年英国工党政府提出一个目标,到2004年要给国家健康服务系统增加2万护士。这个目标在2002年就达到了。单是2002年英国就吸收了13000名外国护士和4000名医生。从欧盟国家招募不景气(许多欧盟国家在面对人口老化时也面临人才短缺),但从发展中国家引入人才则一直在继续,尽管努力设定了一个符合伦理的招募政策。[12]可以认为,即使有经济溢出的“拉力”,不去积极的招募,其伤害会小得多。救治这种伤害不是禁止移民,移民受人权保护。英国最近宣布了十分严格的限制从150个国家中招募的准则。此外,英国启动了给马拉维医疗卫生系统1亿美元的捐助,旨在为留住医疗卫生人员创造更好的条件。因此,英国采取了两项措施意在减少人才流失的“推力”和“拉力”。其他国家尚未跟进。
国际知识产权和药物的可及。难以将最低限度策略一目了然地应用于其他国际健康问题。国际知识产权以及这些产权形成的激励措施超越了现存药物(例如抗逆转录病毒的鸡尾酒疗法)的可及问题,这是近年来注意的焦点。大制药公司因其对发展中国家市场所需药物的研发存有偏见而遭到批评。实际上,大公司对指责它们目前激励研发富裕市场的“轰动性”药物已有应对办法,包括开发许多类似的药物,只是稍微改善疗效或稍微减少副作用。例如资助研发抗疟疾疫苗所需的研究只好落在私人基金会的肩上。
可以认为,不同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不同的激励设计使那些国家贫穷、市场贫困的人的情况要比目前较好一些。我们应该选择何种设计?Pogge建议,我们在发达国家建立以税收为基础的基金,修改药物研发的激励办法,可按他们的产品对全球疾病负担的影响来奖励药物公司。例如,满足疾病负担非常重的贫穷国家需要的药物将从基金会中获得高额奖励款项,即使药物以接近生产成本的费用分发。这种做法可限于“基本药物”,将目前的激励办法留给其他药物产品。
生命伦理学家必须做以下工作:评估不伤害义务的含义,以减少国际上的健康不平等;为不断演变的国际机构和规则制订团体发展公正论述,这些组织对国际健康不平等有重要影响;从其对国际健康不平等以及有关不平等的公正义务影响的视角来考查普罗米修斯式的挑战。
(刘冉,张迪,王赵琛,邱仁宗,译.邱仁宗,校.)
3 问答
邱仁宗:在你看来,与比如临床伦理学或者研究伦理学相比,公共卫生伦理学的特点是什么?
Norman Daniels:公共卫生伦理学应该被理解为政治哲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它关注国家和社会在保护和促进人群健康中的作用。与之相对照,临床和研究伦理学主要关注个体–医疗卫生人员和他们的病人或研究者和他们的受试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涉及使用分析的工具而不是关于能够弥合这些不同领域的“伦理学”这个术语。临床伦理学和研究伦理学主要引用来自规范伦理学的工具,而适合于分析影响公众健康的国家的活动引发的伦理问题,则来自政治哲学其他领域的类似问题。
对于公共健康伦理学,它关注人群健康,一个社会(主要通过国家采取行动)能够做些什么来改善人群健康,并进行公正的分配。人群健康是一个国家需要采取行动的事情吗?如何把对人群健康及其分配的关注与其他公共安康(wellbeing)——工作、收入和财富、教育和保障加以比较?国家和社会保护健康的义务是什么?以什么样的成本或代价?金钱方面的以及其他方面的(例如自由或个人选择)?这些成本或代价如何承担?在群体层面上什么样的不平等在伦理上是可接受的?我们如何确立优先顺序和限制,以满足健康需要?当在这些问题上有意见分歧时,我们应该如何决策?
与之相对照,临床伦理学和研究伦理学主要关注医务人员对病人提供的医疗或研究者对受试者做的可能产生哪些好处或伤害。谁获得好处?谁为此付出代价(这与社会责任的若干问题相交)?这些关系的哪些特征应该被保留,如何保留——自主性?隐私?诚信?信任?给一些个体提供一些受益是否包括对他人强加伤害,也包括威胁到许多人共享的价值?尽管个体——医务人员或研究者及其病人或受试者——是这些问题的中心,分析的手段则是将此与个体之间其他联系进行类比,这些问题通常包括社会维度,并与公共卫生伦理学其他问题相交叉。例如,对专业规范的一种论述将它们视为来源于与一群医务人员的协商,因此,产生了一个人群层面的维度而不仅是个体的维度的问题。
邱仁宗:为什么在人群健康领域开展伦理学探究是重要的?
Norman Daniels:公共卫生伦理学的重要,至少有两方面的理由:一个人群的健康多数来源于医疗和研究以外的活动,这些活动(就业机会、生活条件、教育、环境保护)都充满伦理问题;在这一人群层次上出现的伦理问题强烈地类似社会(国家)作用于人群的其他问题,因此必须将这些问题放在一起分析。不幸的是,对这些人群健康问题的分析已经远远落后于临床和研究伦理学。
邱仁宗:最近,全球健康越来越成为会议和出版物的话题,你能给我稍微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在全球医学领域,哪些伦理问题比其他伦理问题都重要?
Norman Daniels:在传统上,对全球健康的关注集中于“热带”地区或来自这些地区的对健康的威胁。从“热带医学”到“国际卫生”再到“全球健康”这些术语的过渡,可以说代表了越来越意识到健康全球性整合的性质。全球健康问题被归于若干范畴:①包含传染性疾病的威胁(传统的国际公共卫生的焦点);②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体系;③理解经济更大的全球一体化(如移民对健康的影响)和社会力量(如互联网)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影响人群健康及其分配;④以协调的方式更好地应对本地区或区域性的健康危机(如来自饥荒、冲突或传染病)。所有这些问题在全球层面都存在治理方面的弱点。例如,有效的应对对于本地区或区域性的健康危机,要求相互之间进行协调,但目前缺乏;全球治理必须处理可及性问题,比如研发药物,提供药物的可及,但是这些都是相对新的和落后的。还有一些许多国家共同的问题,其一就是如何确定伦理上敏感的优先次序的问题,这通过全球努力将得到加强。
这应该很清楚,例如这些全球健康问题,都是人群健康问题,处理这些问题的主要行动者是社会,行动要通过国家包括需要处理这些问题的全球性机构进行。公共卫生伦理学既有国内也有全球的维度。
(崔庚申,译.邱仁宗,校.)
[1]E.E.Gakidou,C.J.L.Murray,J.Frenk.Defining and Measuring Health Inequality[J].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0,(78):42-54.
[2]P.Braveman,B.Starfield,H.J.Geiger.World Health Report2000:How It Removes Equity from the Agenda for Public Health Monitoring and Policy[J].British Medical Journal,2002,323(7314):678-681.
[3]D.R.Gwatkin.WhoWould Gainmost from Efforts to Reach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for Health?An Inquiry into the Possibility of Progress that Fails to Reach the Poor,Health,Nutrition and Population Discussion Paper,The World Bank,[EB/OL].http://poverty.worldbank.org/files/13920_gwatkin1202.pdf,2014 -01 -22.
[4]T.Nagel.Justice and Nature[J].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1997 ,17(2):303 -321.
[5]R.Jackson ,N.Howe.Global Aging:The Challenge of the New Millennium(Washington,D.C.: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Watson Wyatt Worldwide,1999)[EB/OL].http://www.csis.org/component/option,com_csis_pubs/task,view/id,892/type,1/,2014 -02 -10.
[6]Aging on the World Stage,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Longevity[EB/OL].http://www.ilcusa.org/_lib/pdf/madrid2002.pdf,2014 -01 -10.
[7]A.Williams.Intergenerational Equity:An Exploration of the Fair Innings Argument[J].Health E-conomics,1997,(6):117 -132.
[8]T.Pogge.Severe Poverty as a Violation of Negative Duties[J].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2005,19(1):55-83.
[9]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 Migration,Health,and Human Rights[R].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3:13.
[10]S.Alkire,L.Chen Alkire,"Medical Exceptionalism"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Should Doctors and Nurses Be Treated Differently?[Z].JLI Working Paper,2004-7-3.
[11]B.Liese,N.Blanchet,G.Dussault.The Human Resource Crisis in Health Services in Sub-Saharan Africa[Z].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2004.
[12]C.Deeming.Policy Targets and Ethical Tensions:UK Nurse Recruitment[J].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2004,38,(7):227 -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