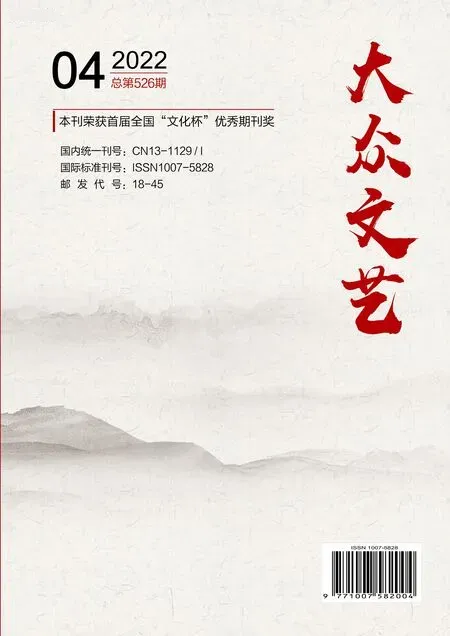论杨慎的历史意识
陈丽娟 (深圳大学 广东深圳 518060)
明朝中叶的大才子杨慎,平生著述一百余种,在哲学、文学、史学等多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得以与解缙、徐渭一起,被后世推崇为明朝三大才子。杨慎“枕籍乎经史,博涉乎百家”,其人集文学家的情愫、思想家的哲思、史学家的理性于一身,其著述,尤其是文学作品,往往有着深厚的历史沧桑感和哲学思辨力,比如他这阙被清人毛宗岗置于《三国演义》开篇的《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短短一阕小词,“痛古今之须臾,悲死生之倏忽”1之外,透漏出作者面对历史、面对人生时的超脱。本文将从杨慎的哲学、历史、文学著作出发,对杨慎的历史意识进行探讨。
一
所谓历史意识,是指一种广义的历史感,是宇宙感、历史感与时代感的融合,这种历史感不只满足于历史的肌肤和一般的历史事件,也不只注重于游离在历史进程之外的孤立的现象,而是要透过历史现象,深入到历史进程的内脏中去把握其中的真正生命力。
英国诗人和批评家艾略特说:“任何一个25岁以上,还想继续做诗的人,历史感对于他,简直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感还牵涉到不仅要意识到过去已成为过去,而且要意识到过去依然存在。”2这里所说的历史感,就是我们所谓的历史意识。与西方“想继续做诗的人”利用历史增强文艺作品的现实感与厚重感不同,对于中国传统文人来说,历史意识不只是体现在文学方面,它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思维方式,他们处世则往往从历史中寻找治安之道与做人准则,内省则也偏向于从历史中搜寻归属感和存在感。中国传统文人这种历史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的形成,大概要归因于孔子。与西方圣贤亚里士多德从逻辑学入手改造人的思维不同,孔子在西周那个战乱频仍、礼崩乐坏的年代,通过笔削《春秋》,生生创造出一个“三代之治”,试图通过这一“礼义之邦”的典型范例,来重构社会秩序。随着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被汉武帝推行,“三代之治”从此成为古人政治追求的最佳模式,崇古、在历史中寻找治国齐家之道,俨然成为传统文人的一种思维习惯,历史意识也就在传统文化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生于弘治元年(1488年),卒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为内阁首辅杨廷和之子,正德六年(1511年)殿试第一,赐进士及第(即状元)。嘉靖三年(1524年),因“议大礼”事件被谪戍云南,后终老戍地。史载杨慎“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3“奋志诵读,不出户外”3,并“勤奋著述,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3
在“议大礼”之前,杨慎可谓一帆风顺,得志青云。父亲杨廷和身为当朝宰相,他本人则科举高中状元,任翰林院编修,充经筳讲官,父子俩名头之响、恩遇之隆,一时无两。学术上,杨慎先后受教、请益于李东阳、杨一清、刘忠等当时国内第一流的政治家、学者,更得以出入皇家密阁,枕籍经史,博涉百家,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为迩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作为中国传统文人中的佼佼者,杨慎无疑是具有深重的历史意识的。人们研究历史,无非两个目的: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以之指导实践,相应的,历史意识可分为认识论和实践论。在历史的认识论方面,杨慎从根本上是属于唯物主义的,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于人类和民族起源的认识上。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类似屈原的这种关于人类和民族起源的天问,人类自有意识开始就在不断地寻求答案。但在进化论和现在物理出现以前,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民智未开的上古时期,类似中国女娲造人以及西方上帝创世纪之类的传说大行其道。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智初开,人们开始对这些有关人类民族起源问题的神话传说生出怀疑,比如司马迁就说:“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4所以司马迁《史记》弃三皇之事,直接以《五帝本纪》开篇,宁肯失之不全,也要求之可信。
作为唯物主义的忠实拥趸,杨慎对民族起源的唯心主义解释一向持批判态度,比如对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他就明确提出质疑,他说:
《诗纬•含神雾》曰:“契母有绒浴于玄邱之水,睇玄鸟啣卵过而堕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蓐,燕不徙巢,何得云啣,即使啣而误堕,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取而吞之哉。此盖因诗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诬……玄鸟者,请子之候鸟也。《月令》“玄鸟至”,是月祀高媒以祈子意,简狄以玄鸟至之月请子有应,诗人因其事颂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贵之神之也。5
杨慎对“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没有任何神秘和迷信色彩。但是对于神话,他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从客观事实与生活实践出发,对其进行批判地继承。
在谪戍云南的三十多年里,杨慎“投荒多暇”3,耳濡目染了云南少数民族古朴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和民族物质文化,与自己所熟知的经史典籍相印证,写下了《滇载记》《山海经补注》《丹铅杂录》等一系列著作,他在这些著作中将中原神话与滇南少数民族神话融合,批判性地吸收,并阐述了自己对神话的见解,产生了在他之前和与他同时代的学者都不可能产生的思想飞跃。
《滇载记》是杨慎谪居云南十九年后撰写的一部云南少数民族史。杨慎将自己翻译的僰语云南古代文献史料《白古通记》“稍为删正”,摘其“九隆神话”作为《滇载记》的开篇:
滇域未通中国之先,有低牟苜者,居永昌哀牢山麓,有妇曰沙壹,浣絮水中,触沉木,若有感,是生九男,曰九隆族。6
这是被杨慎“稍为删正”之后的九隆神话,在《白古通记》中,其原文如下:
天竺阿育王第三子骠苜低,子曰低牟苜,一作蒙迦独,分土于永昌之墟。其妻摩梨,羌名沙壹,世居哀牢山下。蒙迦独尝为渔,死池水中,不获其尸。沙壹往哭之,见一木浮触而来,妇坐其上,觉安。明日视之,触身如故,遂时浣絮其上,感而孕,产十子。他日,浣池边,见浮木化为龙。人语曰:“为我生子安在?”众子惊走,最小者不能走,陪龙坐。龙因其背而沈焉。沙壹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名曰九隆。……九隆长而黠智,尝有天乐随之,又有凤凰来仪、五色花开之样,众遂推为酋长。7
在杨慎所处的明代中叶,九隆族早已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在当时的云南少数民族人民口中,依然相传着“沙壹触木生九隆”的神话,至于这神话究竟是这些少数民族古老相传的,还是中原“感生”神话的舶来品,也不得而知。杨慎通过考察诸葛亮蜀汉时代率军南下时的传说和事实,确认九隆神话是“滇僰于三代为荒服”时期的民族祖先起源神话。
接下来,杨慎通过考证,得出《白古通记》“义兼众教”,于是,在“删正”过程中将《白古通记》版九隆神话中来源于密教的“阿育王”“蒙迦独”,来源于巫教的“沉木化龙”等情节一一删除,仅剩“有妇曰沙壹,浣絮水中,触沉木,若有感,是生九男”等关键情节。
九隆神话经过杨慎的“删正”,宗教色彩尽除,但依然存在着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按理说,杨慎在史家当中最推崇司马迁,他本人又自幼受儒家“子不语怪力乱神”思想的熏陶,应该采取太史公作《史记》之法,对九隆神话这种“怪力乱神”之语弃而不用的,为什么他不但不弃,反而将其置于自己所作的地方性历史著作《滇载记》的开篇呢?窃以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解释:
第一,杨慎不仅是史学家,还是哲学家。人类作为高等生物,自有意识开始,就一直试图在时间的洪流中看透起点与终点,这种求知欲在哲学家的身上表现尤甚。屈原如此,所以他才对天发问,试图察今洞古,杨慎也如此,所以他才力辨神话,试图溯本求源。但是,上古之初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不懂进化论、未窥现代物理门径的屈原和杨慎当然是无法精确回答的。但是,有着哲学追求的杨慎必须在自己的民族史著作中就民族起源问题给出一个解释,以求历史的完整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杨慎所能知道的,就只有九隆神话,虽然有些神秘,姑且带着怀疑接受吧。与司马迁相反,杨慎选择失之迷信,求之完整。
其次,杨慎已然看出,九隆神话与汉族华胥雷泽履雷神的足迹而生伏羲,女节感大星而生少昊等神话传说是颇可相印证的。十五世纪的杨慎,当然不可能知道感生之说是古人类在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漫长过程中产生的,但他敏锐地觉察到,这些惊人相似的神话,肯定不是偶然的雷同,而是因为在中华大地上,各民族都有着相类似的起源。“华风沃泽,同域共贯,昭代恢宇,前是孰并? 《传》称神农地过日月之表,几近是哉!”显然,杨慎辩证地看出了隐藏于荒诞的感生神话背后的各民族在起源上的共同点,他说:“滇僰于三代为荒服。”并据此看出了感生神话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他认为,人类各民族都是由“荒服”演化而来的,所以他才敢于以神话入史,以一个“荒服”时期的神话作为一个民族的起源。对于神话不迷信,但也不放弃,敢于批判地继承,并从中发现历史的本源,这是杨慎在历史研究上的一大创举。
三
民族起源问题解答之后,就产生了新的疑问:人类社会起于洪荒,至明朝已发展成为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封建君主制国家,历史是如何演变到这一步的?是什么东西在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对于事物的发展方式,中国古人早有一种循环的观念,如“物极必反,命曰环流”“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这种循环发展的观念根植于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对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到历史观上,循环发展观直接造就了中国传统的治乱循环观,即认为“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治乱循环观被古人长期接受并反复叙述。
但是,对于治乱循环的原因,却颇有争议,百家之言莫衷一是,孔孟信而好古,言必称尧舜,认为“圣人之道”是社会治乱的根本,“圣人之道”兴则治,“圣人之道”衰则乱,这一典型的唯心史观被鼓吹君权神授的历代帝王所利用并放大,从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被广泛接受的对于治乱循环原因的解释。汉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首先对孔孟的所谓“圣人之道”表示怀疑,王充说:“国当衰乱,圣贤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不能损益。”8认为社会的治乱是由独立于圣人意志之外的“时”与“数”决定的。柳宗元更是明确提出“势非圣意”的命题:“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强调了历史发展自有其客观规律,是不以圣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王廷相继承了柳宗元的“势非圣意”说并有所发展,认为“势中见理”,“民苦则乱,乱久思治,治则思休,乃理势必至之期也。”9在王廷相看来,苦、乱、治、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
王充、柳宗元、王廷相的社会历史学说是一脉相承并不断完善的,作为王廷相的学生,杨慎继承了其老师的唯物史观,他言道:“三代以上,封建时也,封建顺也;秦而下,郡县顺也。总括之曰: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郡县非秦之意也,亦势也。穷而变,变而通也。”10在这一点上,杨慎只是对其唯物主义先辈们的著述换了一个说法,从根本上并无大的突破。
杨慎的真正贡献在于,他在沿袭其先辈们“势非圣意”、“势中见理”学说的同时,看出了人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对于人的价值定位,孟子早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是在君权至上的封建君主制社会,所谓的民贵君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君者政治上的说辞而已。荀子对孟子的话理解透彻,他解释道:“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水不管是“载舟”还是“覆舟”,一滴肯定是不够的,水一定要团结,聚少成多,成为江河湖泊,才能“载舟”“覆舟”。所以,中国传统上对于“民”的重视,是基于“民”这一群体的,对于个体的民,则“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作为一个长期谪居滇南一隅的政坛失意人物,杨慎痛定思痛,开始了自己思想上的再造,由儒家思想的卫道者渐渐转向了道家和佛家,在读遍各家经典,考察完滇南各族风土人情之后,杨慎的思想认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于“民”之一词,也有了不同以往的感受,这一点在其谪居滇南时期的诗文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在杨慎所作《廿一史弹词》中,“三皇五帝宾天去,辛苦阎浮世上人”“千年暗草埋金谷,几辈征夫老玉关”“青春壮士边关老,红粉佳人白了头”等词句随处可见,虽略嫌泛泛,但也可以看出,杨慎在“乌飞兔走、龙争虎斗”的大历史背景下,是把个体的人当做有生命、有思想的存在看待的。不仅如此,他还试图以历史告诫世人弃恶扬善,“按捺奸邪尊有道,赞扬忠孝奖贤能”“指陈是否依前古,剖判贤愚警后人。”
如果说杨慎写出以上这些词句只是出于个人良知,对阎浮世人拥有着一份天生的同情和愿其向善的爱心的话,那么下面这首《击壤图》则真正是对一个普通的个体生命人格上的尊重:
陶唐天子调八风,凤仪兽舞明廷中。谁知鼓腹行歌者,复有山中击壤翁。短袖单衣露两肘,野状村容不自丑。掀髯笑傲肩相随,共道帝力我何有。柳谷饯日晹谷宾,老翁那记昏与晨。一作一息有出入,时耕时凿无冬春。蓂荚开残又朱草,生来未识平阳道。海隅赤日烧九州,寰中息壤汨洪流。已见天戈挥丹浦,更闻风伯殪青丘。老翁其间百不忧,直从红颜到白头。君不见许由逃尧劳步履,巢父洗耳污清泚。华封老人费言辞,康衢小儿强解事。姑射丰姿虽可珍,神仙彷佛信难真。君看击壤千年后,多少行歌带索人。
晋皇甫谧《高士传》卷上:“壤夫者,尧时人也。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夫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夫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与我哉!’”杨慎《击壤图》诗中的壤夫显然取材于此。“天戈挥丹浦,风伯殪青丘”等大事情那是你陶唐天子理应解决的,作为一介壤夫,我只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喝水种田吃饭,没事击个壤玩玩,我快不快活与你天子有德无德可没关系!在这首诗里,杨慎在是平等的看待天子与壤夫这两个个体生命的,诗里的天子不是神,壤夫也不是蝼蚁,都是活生生的个体生命,都有着各自的生存职责与生命诉求。
杨慎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期,他的这一尊重个体生命的思想可以理解为中国的人本主义启蒙。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也是启蒙于一位诗人:但丁。遗憾的是,与但丁的人本主义星星之火最终开启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新时代不同,杨慎的人本主义火花最终也没能在明清这两个中央集权登峰造极的封建政权里形成燎原之势,中华民族这艘航行了几千年的骄傲的巨轮在现代文明的曙光前抛锚了,最后终于被西面而来的后起之秀用坚船利炮炸得处处斑驳。
四
一般来说,人们对事物进行认识和判断可采用两种方法:历史对照的方法和逻辑批判的方法。在中国历史上,逻辑的话语权往往掌握在位高权重者手中,秦相赵高就曾以一个颠倒是非的“指鹿为马”的经典案例将这一话语权用到极致。而历史的批判,由于一些历史事实的确定性,是任何统治者都无法否定的,统治者难以找到压制借口,所以中国传统上更多地采用了历史的批判力量。
关于历史的现实批判意义,唐太宗李世民曾给出过一个著名的论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认识历史,研究过去的人和事,是为了以史为鉴指导现在,可以说,“以史为鉴”是中国古人研究历史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由司马光主编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即被宋神宗定名为《资治通鉴》,由此可见一斑。
“大礼议”之前,出身书香门第,自幼饱读儒家经典的杨慎,自然也是趋向于以历史来评判现实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礼议”事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兴世子(嘉靖)进京继位,杨廷和令礼官按照太子继位的仪式进行。兴世子在路上见了拟定的仪式就表示,“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为皇子也”10,到了北京,拒不进城。杨廷和让步,把仪式改变“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10的规格。兴世子思考了很久,才予同意,过了三天就派遣官员去迎接他的母亲兴献妃,又不久,就命礼部讨论兴献王的主祀称号。杨廷和查了汉定陶王和宋濮王以弟继兄的旧例,嘱礼部尚书毛澄说:“是足为纲,宜尊孝宗曰皇考,称兴献王为皇叔考兴国大王,母妃为皇叔母兴国太妃,自称侄皇帝名。”10嘉靖对此种名分安排很不称意,召群臣议礼,议了几个月,杨廷和等人坚持说:“前代入继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礼”10,“唯宋儒程颐‘濮议’最得议礼之正,可为万世法。”10“三代以前,圣莫如舜,未闻追崇其所生父瞽瞍也。三代以后,贤莫如汉光武,未闻追崇其生父南顿君也”10。此事件中“廷和持礼益不挠”10,事情闹了两三年,最终嘉靖帝得张璁、桂萼等人支持,于嘉靖三年罢杨廷和相位,但“大礼”非但无定论,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吏部尚书何孟春以一句“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10倡议百官聚众请愿,杨慎更是替何尚书添了一把火,只见他慷慨激昂地说道:“国家养士百五十日,仗节死义正在今日。”10会同王元正等二百多人伏于左顺门,撼门大哭。世宗下令将众人下诏狱廷杖,当场杖死者十六人。十日后,杨慎及给事中刘济、安磐等七人聚众当廷痛哭,再次遭到廷杖,杨慎、王元正、刘济都被贬谪。
可以看出,在“议大礼”这件事情上,杨慎完全是秉承着历史经验主义行事的。“议大礼”时,他跟随父亲杨廷和以汉定陶王和宋濮王的旧例,以及虞舜、汉光武等明君的例子,坚决反对嘉靖尊其生父为帝。如果说在杨廷和致仕之前,还令人怀疑杨慎只是追随其父,以“议大礼”之名与嘉靖帝进行权力争斗的话,那么杨廷和致仕之后,杨慎聚众请愿,在当场杖死十六人的情况下竟然二次情愿,直到再遭廷杖并被谪戍,这该是真正宁死不屈的卫道者形象了吧。
杨慎的确是一个卫道者。他的“道”就是儒家经典,是仁义礼智信,这是他的信仰,在他的心中,他的信仰是高于皇帝的权威的。其实儒家的人生哲学是充满着悲剧色彩的。所谓“杀身以成仁”“朝闻道,夕死可矣”都是在劝勉世人不要太拿自己性命当回事,性命跟“道”相比不值一提。很显然,杨慎和那些聚众请愿的官员,尤其是二次请愿那七位,是捍卫儒家思想的死士。为了信仰,他敢于挑战皇帝权威,他强烈地希望用从小自儒家经典中继承的信仰扭转时势、主宰时局,他追求、希望、失败、挣扎,虽死不悔,壮心不已,对他而言,冲突愈烈则体验愈深,生命的价值就愈发丰满充实。这种直致毁灭生命也在所不惜的悲剧的人生态度,很容易形成大规模的现实悲剧,“大礼议”是这样,方孝孺事件也是这样。这种悲剧虽然壮美,但毕竟不是一个身负良知的人所乐于见到的。
还好杨慎没有死,只是被谪戍滇南而已。在谪居的三十多年里,杨慎的思维方式与处世哲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信仰被嘉靖杖死了,那就不要啦,所以谪居期间,曾经的大才子,为了信仰敢于触犯君威的一代儒生,竟然变得衣冠不整、诗酒为伴。历史也不再是摆在案头的“资治通鉴”,不再是自己的行为准则,而成了茶楼酒肆听说弹唱的素材,成了钓叟樵父相逢一笑的谈资。他在滇南写成的长篇弹词《廿一史弹词》,以酣畅淋漓之笔,裁剪中国数千年要事,结合他所擅长的琵琶乐曲轻松又略带悲壮的特质,“普兴亡于弦歌之中,寓褒贬于弹板之内”,自诞生以来广为流传,“贩夫田父,樵童牧叟,皆欣欣而喜听之”。前文所提《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临江仙》即出自《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廿一史弹词》还有一首《西江月》被冯梦龙用在《东周列国志》的开篇,也常被人误以为是冯梦龙所作: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廿一史弹词》中,类似“英雄五伯闹春秋,秦汉兴亡过手”“秦宮汉苑晋家茔”“隋唐相继统中原,世态几回云变”的句子比比皆是。可以看出,虽然政治失意,但谪戍之后,杨慎却也摆脱了权力之于其身和儒家之于其心的束缚。失去了政治权利,他的处世哲学反而变得轻松活跃起来,对于功名、是非、成败有了一种超然的洒脱。这时候的杨慎,真谈得上是“以广博的智慧照属宇宙间的复杂关系,以深挚的同情了解人生内部的矛盾冲突。在伟大处发现它的狭小,在渺小里却也看到它的深厚,在圆满里发现它的缺憾,但在缺憾里也找出它的意义。于是以一种拈花微笑的态度同情一切;以一种超越的笑,了解的笑,含泪的笑,惘然的笑,包容一切以解脱,使灰色暗淡的人生也罩上一层柔和的金光,觉得人生可爱。”
杨慎就是这样从自己或别的普通人的真实体会出发,通过学习、实践、观察、内省,最终在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上摆脱了儒家一味奉行的历史经验主义,继而发挥思维的能动性,形成了自己的逻辑思维标准与是非观念。
综上所述,作为集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于一身的一代大家,杨慎的历史意识无疑是复杂而丰富多彩的。在认识论上,他奉行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人类各民族都是由“荒服”时期演化而来,并发现了隐藏于治乱循环背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变革推动力:“势”。在实践论上,他前期奉行历史经验主义,从政做人一切以圣人经典为纲,后期则随着自我意识的加强,渐渐摆脱历史经验主义的束缚,转而追求自由人格,行事以自我的逻辑是非观念为准绳。 李卓吾在《续焚书》中说:“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人品俊伟,然得弟读之,益光彩焕发,流光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代、宋代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 可见后人对杨慎才学人品的肯定。
注释:
1.王文才.杨慎词曲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2.托•史•艾略特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3.张廷玉.明史•列传第八十.北京.中华书局,1974.
4.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9.
5.杨慎.升庵外集•卷四十二.
6.杨慎.杨升庵杂著•滇载记.明嘉靖本.
7.王叔武.云南古佚书抄•白古通旋风年运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
8.王充.论衡•治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9.冒怀辛.慎言•雅述全译.成都.巴蜀书社,2009.
10.陆复初.被遗忘的一代哲人:论杨升庵及其思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