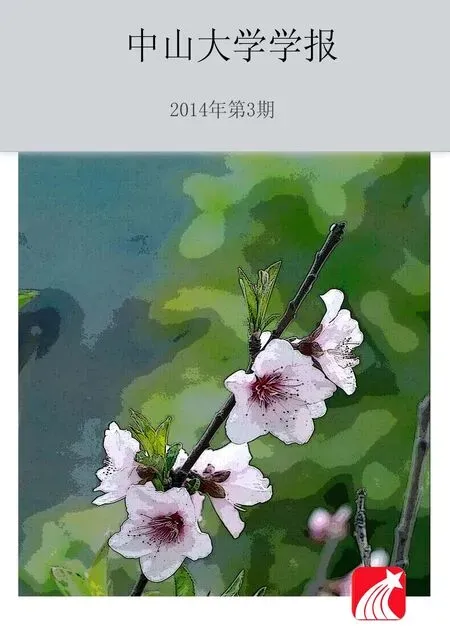对法律规则的规范性评价*
——道义论、后果主义与社会演化
丁 建 峰
一、 导 言
法律可以看做是调整和规约社会运行的一套制度安排,对法律规则的规范性评价是法律哲学中一个难以忽略的问题,即:我们按照何种标准去比较法律规则的优劣?在若干种可选择的法律规则中,究竟选择哪一种?这些都依赖于一个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作为支撑①按照法理学的通行理论,法律哲学可以大致分为“解释性法律理论” 和“规范性法律理论”两类,类似于社会科学中的 “规范理论”与“实证理论”之分。规范理论研究的是“法律应当如何”,而解释性法律理论试图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理解法律现象的本质,关注的是“法律是怎样运行的”和“法律为何如此”。例如,涂尔干、韦伯、马克思、哈贝马斯、福柯的法学著作,其最精彩和富于原创力的部分,基本可以划归解释性法律理论的范畴。再如,批判法学运动之父霍尔姆斯大法官认为:法律就是法律实践中执行的规则,学习法律的人应当关注法律是什么,而不是应当是什么。在此,他仅讨论了实证意义上的法律问题。。大致上,我们可以把法律规则的评价性标准分为两个大类:后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和非后果主义(non-consequentialism)。后果主义认为:评价法律制度是否较优,依赖于它所导致的社会后果,我们可以依照某种社会选择规则确定一套后果评价的标准(例如福利经济学中的“社会选择算子”),然后根据这套后果评价的标准来评定法律规则的优劣高下。而非后果主义则认为:评价法律制度的标准不仅要看后果,而且还要看它的过程自身是否满足某些优良的性质。而道义论(又称义务论,deontology)则是非后果主义(non-consequentialism)的极端,它认为法律制度的正确性是完全由法律程序自身所具有的某些特点决定的,或者是由某些先定的规则决定的,而与由它导致的任何后果都不相关。
在本质上,所有的规范理论回答的都是一个有关“应当”(ought to)的问题,如果不追溯到后果主义和道义论,我们很难对“应当”做出恰当的考虑。事实上,各派法律规范理论对于法律高下取舍的比较和判断,经常可以追溯到某种形式的后果主义或道义论,或者是在两者之间折中。例如,边沁和奥斯丁等法律实证主义者,在规范问题上秉持“最大化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的功利主义目标,是典型的后果主义*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5 ed. London: Murray,2005. Jeremy Bentham.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London: Prometheus Books, 1988.;新分析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哈特,虽然反对边沁和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但仍然坚持功利主义的标准,反对“虚幻的自然权利”*[英]L.A. 哈特著,支振锋译:《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212—222页。。法律实证主义者常常是规范领域内的后果主义者*对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者而言,法律中的“应当”来源于主权者的命令;新分析实证主义则认为,低级的规则受制于更高级的规则。但是,主权者的命令或者高级规则,其“应然”的性质从何而来?边沁主张区分“说明性的”和“审查性的”法学,以前者描述实然世界,以后者论证应然原则。故而,“下位规则服从上位规则”是一个实证判断,而“功利主义”是一个规范判断,二者并无矛盾。从法律的规范评价角度讲,边沁、奥斯丁和哈特等法律实证主义者同时也是后果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高级规则应当符合后果主义。但还有一派“强硬型”的法律实证主义者,在他们的理论中没有规范的部分,如约瑟夫·拉兹认为,“法律”永远只有事实判断而没有道德判断,只能被看做是“社会事实”,即使“权利”和“义务”等源于道德哲学的术语,在法律中也只有事实陈述的含义。。而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思想则保持了极为浓厚的后果主义色彩*[美]理查德·波斯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
而站在道义论立场上的也不乏其人。正如德沃金的名言“权利是王牌”*[美]罗纳德·德沃金著,信春鹰、吴玉章译:《认真对待权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当代的“权利话语”者认为权利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而“程序本位主义者”则认为法律程序至上,并且有不依赖于结果的内在价值*Robert Summers, Evalution and Improving Process-a Plea for Process Values. Cornell Law Review, 1974, Vol.60,No.1, pp. 1—55.。也有一些学派在这两者之间折中。例如菲尼斯的新自然法思想,既追求普遍幸福,又强调自然权利*[英]约翰·菲尼斯著,董娇娇等译:《自然法与自然权利》,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上述的分类,也许会被认为有过度简化的嫌疑,但是,任何一个事态从时间历程上都可以被划分为“过程”和“结果”两个部分,后果主义和道义论分别代表了评价事态的两种典型标准,所以,至少在法律规范性评价这个维度上,“不归于杨,则归于墨”。即使某些学说稍微复杂一些,但揭开它们晦涩的表象,会发现它们无非是主张一种比较特殊的后果评价标准或过程评价标准(或者二者的不同程度的结合)。
本文并不是对后果主义和道义论的正确与否做一个终极性的判定。笔者希望论证的是:相较于道义论和各种非后果主义理论,如果我们考虑对真实世界中的法律制度的评估问题,则后果主义比道义论更适合成为对法律规则的规范性评价的基础。但是,非后果主义理论在现实中有它独特的作用和功能,而用演化理论的框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整合后果主义和非后果主义。因此,笔者希望论证一个规则后果主义的法律规范评价体系。
二、道义论适合作为法律规范评价的基础吗?
作为“伦理学史上的伟大界标”,以康德伦理学为代表的道义论,其在思想上的力量是毋庸置疑的,甚至有人认为,“伦理学成了一门以康德的术语来界定的学科”*[美]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著,龚群译:《伦理学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53页。。从另一方面看,道义论的出现与西方的法律经验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持道义论立场的道德哲学家,实际上是站在“法官”或“立法者”的立场上来评判人的行为的,而其最终目的,是让自然法成为道德法则的一个模型,将法律的根基奠定在道德的基础之上*邓晓芒:《康德论道德与法的关系》,《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尽管道义论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但笔者认为,道义论不适合作为法律规范评价的基础。当然,道义论本身存在伦理学方面的质疑,例如义务本身可能是相互冲突的、绝对义务仍然离不开后果推理、可普遍化检验标准的非充分性与非必要性等等。鉴于伦理学著作已经对这些问题作了许多讨论,本文不拟详加论述*相关的简明介绍可以参考[美]斯图亚特·雷切尔斯著,杨宗元译:《道德的理由》,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2—127页;[美]雅克·蒂洛、基思·克拉斯曼著,程立显、刘建等译:《伦理学与生活》,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56—61页。,仅就道义论为何不适宜用于评判和取舍现实中的法律制度作一论证。
首先,以道义论为基础构建法律体系,会带来对社会福祉的损害。这在法律经济学中被称为“帕累托冲突定理”(Pareto Conflict Theorem),即如果我们赋予某种道德观念以独立于后果评价的特殊权重,那么必然存在若干情形,在这些情形中,每个个体的效用都会降低*Louis Kaplow and Steven Shavell, The Conflict between Notions of Fairness and the Pareto Principle. 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s Review, 1999, Vol.1, pp. 63—77;Louis Kaplow and Steven Shavell. Any Non-Welfarist Method of Policy Assessment Violates the Pareto Principl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1, Vol.109, pp. 281—286.。例如,如果我们像道义论者那样,赋予“信守承诺”以无条件的脱离后果评价的重要性,那么法律就必须要求社会承担远多于必要的承诺数量*康德的伦理学在此方面的表现特别明显,在1797年的一篇著名论文《论出于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法权》中,康德认为,即使撒谎可以挽救一个被杀手追杀的无辜的人的性命,理性的人也不应该撒谎,应当对杀手说实话。康德评断说:“真诚是一种必须被视为一切能够建立在契约之上的义务之基础的义务,哪怕人们只是允许对它有一丁点儿例外,都将使它的法则动摇和失效。因此,这是一个神圣的、无条件地颁布命令的、不能通过任何习俗来限制的理性诫命。”参见[德]康德著,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36页。。又如,合同法中的情势变更原则规定:当合同签订后出现了突发事件,致使合同难以完成,则可以请求法院解除或变更合同(参见《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再如,某省因地震和泥石流致使物流公司无法完成运输合同,此种情况下如果以诚实守信原则为理由强行执行合同,无疑会使承运人以极高成本完成已不具有经济效能的合同,从而造成对社会福祉的巨大损害。如果坚持物流公司无论如何一定要执行合同,实际上是强制物流公司为托运人提供保险;而让托运人分摊承运人的风险,则更为适合现代商业的惯例。从根本上说,是否采纳情势变更原则,其本身只是一个商业风险分担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如果此时过分强调“诚实守信”,很显然是将经济问题道德化了,由此带来社会福祉的损害也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更严重的问题是道义论经常缺乏一个规范性理论应有的决断性(determinancy),在两个法律制度备选项A和B当中,选择者必须有理由确定性地选择A或B,亦即他必须做出决断。对于一个伦理学体系来说,缺乏决断性并不是缺点,因为人的生活并不仅仅是道德生活,需要有大量中立于道德评价的自由选择。但是,对于一个法律规范的评价体系而言,缺乏决断性则是致命的缺陷。这是因为无论是立法、执法还是司法改革,从不同的备选项中所做的选择必须给出理由,如果一个规范性学说在很多情形下对法律制度的选择都缺乏决断,那它显然就不适合作为判断的基础。
道义论之所以缺乏决断性,原因如下。
(1)道义论在理论上来自理性的论证,但在现实中何种具体行为成为绝对义务,高度依赖于判断者的道德直觉。然而,由于受到文化背景、教育和社会经验的影响,不同人的道德直觉在很多时候是具有严重分歧的。但道义论者不会这样认为,他们会通过一套理性的推理论证,给这些原本来自生活经验和自身直觉的结论以事后的证成(justification),形成一个看上去是从实践理性出发、经过严格推理得出的普遍性结论。而实际上,不同的道德直觉时常互相抵牾而难以通约。例如,一个主张生命权至上的现代道义论者必然是坚决的废除死刑主义者*[法]阿尔贝特·施韦泽著,陈泽环译:《敬畏生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而道义论的代表人物康德则认为,基于实践理性所支持的报应正义的逻辑*所谓报应正义,是指“做错事的人应该为这件坏事付出同等的代价,罪犯应该为所犯的罪受到惩罚,相应惩罚的严厉程度取决于行为的危害程度”。Cf.Rawls, J., Two concepts of rules. Philosophical Review, 1955.Vol. 64: pp.4—5.,必须严格执行死刑。正如康德所明确表示的:“即便是公民社会以所有成员的赞同要解体(例如,住在一个岛屿上的人民决定分手并分散到世界各地),也必须先把监狱里的最后一名杀人犯处决掉,以便每个人都亲历他的行为所应得的。”*[德]康德著,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第345页。抛开康德的道德哲学和法哲学的复杂繁密的论证,康德所支持的具体的法律判断,与当时社会发展背景下的一般法律文化高度相关,并不是纯然逻辑推导的结果*例如,康德通过“人是目的”和“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论证了“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负责的方式有多种,到底应当如何负责?康德支持的“报应正义”,并不是一个纯然逻辑的结论,只能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得到解释。在当时的欧洲,“同态复仇”并不认为是残忍而不人道的,康德本人就是同态复仇的支持者。再者,当时欧洲人也不认为死刑是不人道的刑罚,夸美纽斯在教育低幼儿童的画册《世界图谱》中就画了绞架行刑的场景,并说:“(罪行)要通过绞架或车裂的刑车,正当地加以处罚。”参见[捷克]夸美纽斯著,杨晓芬译:《图画中见到的世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35页。可以设想,另一个文化背景下的人,即使同样具有理性并且富于道德义务感,也未必赞同此观点。例如,主张戒杀去嗔、以无量平等慈悲之心看待恶人恶事的佛教徒,就不会支持同态复仇。。
(2)另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是:由于道义论主张评价的基础与后果无关,因此它是一个缺乏对相关后果进行损益权衡(trade-off)的体系。例如,一个社会是否可以牺牲1亿元以挽救1个无辜生命?一个生命至上的道义论者会举双手赞同。但后果论者不会这样考虑问题:1亿元可以营建1家设备齐全的医院,或添置1000辆急救车,所挽救的无辜生命何啻千倍于此。对于道义论者而言,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故而它反对这种“为救1000人而牺牲1人”的数量权衡。但是,如果换一个问题问道义论者:“一个社会可否为了1人而牺牲1000无辜者的生命?”道义论者基于同样的理由也会反对这种提案,这就造成了决断性的缺失。其根本原因在于:道义论的体系中,生命、权利、自由之类的核心价值是绝对不能列入一个损益权衡体系的,尤其不能与经济利益相互换算。这种思想也许在欧陆道德哲学的思想传统中具有充分的理由,也为在日常情况下保护不可侵犯的人权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当我们考虑决断性的时候,缺乏损益权衡将是致命的弱点,因为现实中的不少情境需要进行生死抉择,另有不少情境需要进行不同权利之间的权衡考虑*有些学者反对在生命权与经济利益、生活便利之间做权衡,主张生命权应当处在绝对优先的地位。但这一看法在真实世界中会带来荒谬的立法——如果生命权绝对优先,就应当立法禁止汽车、高铁和飞机等交通工具的使用。一般民众不使用它们只带来了经济损失和生活不便,而使用它们却会带来巨量生命的损失。2011年,中国因交通事故死亡约6.4万人,美国因车祸死亡4.2万人。在当代,车祸的死亡率超过了战争,但任何国家都不会因为保护生命而放弃经济利益。正如卡拉布雷西所说,汽车是一种“恶神的礼物”,而法律只能代表社会接受这一礼物,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量控制其危害而已。参见[美]圭多·卡拉布雷西著,胡小清译:《理想、信念、态度与法律:从私法视角看待一个公法问题》,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
(3)即使退一步,假定社会接受了一个统一的道义论体系作为评价法律规范的基础,另一个问题会接踵而来——道义论在实质上是一个伦理学体系,建立在道义论基础上的法哲学,例如康德的法权哲学,是高度思辨性而不是技术性的。运用到法学领域,它只能评价法律规范中与道德相交叠的部分,然而,大部分法律规范与道德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大部分现代法律规范是高度技术性的,与道德并无直接关系。对于这些技术性的法律规范,道义论无法进行评判。例如,在侵权法领域,究竟由医院还是患者承担举证责任?因果关系是采取近因证明还是采取必要条件证明?在商法当中,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应当如何划分职权?应当采用何种会计方式来盘点库存?证券注册的最低资本要求多少才是较为合适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在道义论框架下不能给予任何明确的答案,而运用后果推理(例如,广义的实效主义原则——成本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则可以清楚地评判不同方案的优劣。这是因为:后果主义虽然经常被狭义地理解为道德理论,但实际上它能够超越道德领域而成为社会政策的一个衡量基础。事实上,边沁创立的最典型的后果主义版本——功利主义,其原初的意图就是为了对法律制度进行规范性评价。可以说,后果主义是为法律的评估和改良“量身定做”的一套理论。
(4)即使采纳了道义论作为规范评价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机制设计。道义论的理论体系固然精美严整,但它无力在细微层面探讨立法的奥妙。因为从古到今,法律实施的基础都是后果评价,道义、责任和义务只能通过后果评价来衡量,没有脱离后果评价的法律责任。例如,意图中的犯罪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过错行为(例如把裸露的电线暴露在闹市区)只要没有引起损害后果,也无须承担侵权法律责任。即使和道德紧密相连的古代法律,其实施的过程也是高度目的化的*例如,中国古代的法律系统与儒家道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它的实施却必须落实到“正名定分”、“禁暴止非”等一系列基于儒家道德而确定的有益后果之上。礼教对于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也要具体化为一个特殊的后果评价体系,例如肉刑不上大夫(《礼记》)、亲亲相隐不为罪(《汉律》)、准五服以治罪(《晋律》),按照亲疏等级确定继承份额等。。法律的实施理论告诉我们,如果立法者意图执行的法律,其结果不构成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那就意味着该法律只是一种“纸面上的法律”,无法实施。这就意味着:即使一个非后果主义者的立法构想,也必须“翻译”成一套后果评估的语言才可能在立法中体现,必须符合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才可能在现实的执法中有效地实施。
那些和道义论紧密结合的法哲学体系,也难以避免以上的困境。例如,流行于中国法学界的口号式的“权利话语”,由于在不同权利发生经验冲突时无法做出抉择,早已受到不少学者的诟病*郭春镇、王云清:《作为法律实用主义的“权利话语”》,《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4期; 桑本谦: 《反思中国法学界的“权利话语”——从邱兴华案切入》,《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再如,传统法学以“矫正正义”作为侵权法的哲学基础,但是,当代学者指出,矫正正义的概念十分模糊,脱离后果评价,难以确定侵权违法性的边界。比如,说谎和在后院烧烤都给他人造成了损害,却不可能通过侵权法来救济*Richard Ponsner, The Concept of Corrective Justice in Recent Theories of Tort Law.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81. Vol.10: pp. 187—206.。矫正正义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采用第三方责任保险机制处理交通事故,比“损害者赔偿”的原则更好*这是因为该方案会提供更及时、充足的赔偿,而且管理成本低廉,如果辅之以交通规则的严格执行,则也不会带来交通事故的上升。但是,矫正正义不会考虑这些后果因素。。西蒙斯认为,如果不诉诸执法成本之类的后果考虑,纯粹的矫正正义将会认为“任何请求都是正当的”,这显然脱离了法律运作的经验常识*Kenneth Simons. Corrective Justice and Liability for Risk-creation. UCLA Law Review, 1990. Vol.38: pp. 113—142.。
正如康德早就认识到的:“法权概念是一个纯粹的,却被建立在实践上的体系……对经验的东西进行完备划分是不可能的。”*[德]康德著,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第213页。这种“纯粹理论”和“现实”之间的断裂与冲突,是道义论的规范体系所难以避免的。当然,本节笔者是从现实应用的角度论证了道义论运用于法学的无力之处,但是,如果不考虑具体的现实应用而仅考虑理论层面的专深思辨,则道义论仍是一个自足的体系,有其独到的不可替代的价值,笔者亦无意于否认此点。
三、后果主义与社会规范的演化
“自然法学派”是法哲学中一个古老的流派,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尽管自然法学派分为许多不同的分支,但所有的自然法学家都相信,现实世界的法律是自然秩序的体现,而自然秩序具有一种内在和谐的倾向。当代的自然法学说分为两大分支:一派是以菲尼斯为代表的采用分析法学方法,重述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式的古典自然法理论;另一派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采用社会演化理论的方法,将自然法纳入社会自发秩序演化框架中的学说。哈耶克式的自然法(natural law),更接近于英文“自然规律”的本意,和社会科学的结合更为紧密*在当代自然法的两个流派中,菲尼斯毫无疑问更接近自然法的理性传统,但笔者个人仍然更为欣赏哈耶克的法律思想。实际上,这种建立在对自然和社会观察基础上的“自然法理学”延续了休谟和斯密的苏格兰启蒙传统,把法律从超验的理念世界拉回到经验的自然世界,因而更为切实可信。参见[英]努德·哈孔森著,赵立岩译:《立法者的科学:大卫·休谟与亚当·斯密的自然法理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沿着哈耶克的思路,笔者试图在本节论证:支配着法律规则演化的基本规律是后果主义,道义论以及与道义论相似的学说,背后也有着后果主义的逻辑。
人类经历了几百万年的演化过程,即使现代智人(Homo sapiens)也经历了十万年左右的演化,作为社会性物种,人类的自然演化和社会—文化演化始终处于并行发展之中,而社会—文化演化的范围之广、速度之快、程度之深,凌驾于自然演化的过程之上。值得强调的是:演化的基本规则始终是后果主义的。自然演化的机制,在于适应性强的有益变异更容易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并将繁衍延续下去。但自然选择的单位是基因型而不是群体,因此“自私的基因”成为演化论的重要结论之一*[英]理查德·道金斯著,卢允中等译:《自私的基因》,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然而,演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也曾猜测,人类的演化可以突破自私的基因的限制,群体在个体的基础之上兴旺发展,人类遵循习俗、纪律和法律的行为,也会带来群体收益的提高*达尔文认为:“当两个居住在同一片地区的原始人的部落开始进行竞争的时候,如果(其他情况与条件相等),其中的一个拥有更多勇敢、富有同情心而忠贞不贰的成员,随时准备着彼此告警,随时守望相助,这一个部落就更趋向于胜利,而征服其他的一个。”显然,此处自然选择的单位是“部落”而非个体。因此,说达尔文是群体选择思想的提出者也并不为过。参见[英]查尔斯·达尔文著,潘光旦、胡寿文译: 《人类的由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1页。。群体选择曾经引起生物学界的极大争论,不少生物学家视之为异端邪说,但现在随着新证据的发现和计算机模拟仿真技术的提高,群体选择已经被主流演化理论家接受,成为解释社会—文化演化的标准理论之一*[美]马丁·诺瓦克、罗杰·海菲尔德著,龙志勇、魏薇译:《超级合作者》,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现代的社会—文化演化理论,已经不是主张“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是以群体选择为基础的一套社会科学理论。它认为那些能够促进群体平均适存度的社会规范,会更容易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取代那些降低平均适存度的规范,而群体的平均适存度是一个后果评价。尽管在孤立、封闭的环境下,某些不利于群体的规范会长期存在,但一旦面临不同群体之间的开放式竞争,这些缺乏竞争力的规范就会败下阵来,让位于自发形成的、不断扩展的较占优势的规范。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同的是,现代社会演化理论认为,缺乏竞争力的群体自身不会灭亡,古老的民族可以通过学习新的规则而重新提高适存度,以达“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效。如哈耶克所说:“演化是新的行为方式利用习惯的传播过程。”在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然法学家看来,法律就是这样一种在人群中不断扩展的社会规范,由此而形成的法律下的自由秩序即称之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法律并不是立法者的“天才设计”,也不是哲学家理性思辨的人工制造品,而是自然演化出的天然秩序(cosmos)*Friedrich Hayek, Law, Legislature and Liberty, Volume 1-Rules and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p.35.。特定的法律规则之所以被采纳,开始时完全是出于偶然,但由于它使群体的适存度得以提高,因此这一规则不断延续,而且被其他的群体所效法,逐渐演化成现在的法律体系。
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如科斯定理,内在地隐含了法律演化的动力机制——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且产权明晰,则人们之间的自主谈判会自动导致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社会福祉。一个更广泛的推论是:即使存在交易成本,自主谈判达到的结果也倾向于最优化总的社会剩余*Ronald 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 Vol.3, No.1, pp. 1—44.。德姆塞茨发现,在一个开放竞争的环境中,由于资源的稀缺性,那些比较明晰的产权制度会逐渐取代原有的模糊产权*Harold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Vol.57, pp. 347—59.。诺斯通过欧洲法律史的考察也发现,倾向于确定产权、减少交易成本的法律会在演化中占据优势*[美]道格拉斯·诺斯著,厉以平、蔡磊译:《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9年。。波斯纳指出,在“法官造法”的英美法系,上诉法院的法官具有改进效率的个人激励*Richard Posner, Judicial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An Economic Approach.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05. Vol.32: pp. 1259—1279.。普利斯特也指出,即使法官本人并不支持效率优先,那些缺乏总体效率的法律也会导致更多的上诉,所以它们被挑战和修改的概率也较大,经过漫长时间的演化,法律体系就会向着促进效率的方向发展*George Priest, The Common Law Process and the Selection of Efficient Rule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77, Vol.6, pp. 65—82.。在大陆法系,学者们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例如,欧洲商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演化过程,经历了上千年的演化。在开放竞争中,欧洲各国的商法经历了从限制自由贸易到保护契约自由、促进商业合作的转变。同时,商人在各国之间的自由流动和跨国贸易的发展,又促进各国的商法走向融合*Leon Trakman, The Law Merchant, the Evolution of Commercial Law. Littleton, Colorado: Fred B. Rothman & Co., 1983.。与社会演化相一致的效率原则也可以解释一些用报应正义难以解释的法律现象,例如,罚款的额度通常比实际造成的损害要大(如巨额的惩罚性赔偿),而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惩罚通常比造成的损害要轻(如故意致人死亡判处无期徒刑)*这两种现象背后的后果主义逻辑是:从增进效率的角度来看,惩罚性赔偿实际上是一种随机性赔偿,如果有大量的侵权者同时侵权,被侵权人可以通过惩罚性赔偿来弥补损失。例如,100万人下载1首价值1美元的流行歌曲,对这100万人各罚款1美元符合报应正义,但却带来了极其高昂的执行成本,而随机挑选其中1人处以100万美元的巨额罚款,可以起到同样的威慑作用,从社会成本耗费的角度看是大大提高了效率。而对于大多数恶性犯罪者,只需执行监禁即可起到隔离犯罪群体于社会之外的作用,其威慑力也已足够,因此没有必要执行死刑。。再如,现代侵权法中无过错责任(严格责任)的兴起,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无论当事人有无过错都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产品责任、高度危险物侵权等)。由于无过错责任通常是受害人无从预防而施害人可以加以预防的,从最优化预防成本的角度很容易解释这一现象,而采用报应正义则难以对此作出解释。
人遵守规则的行为本身,也可以看做是群体选择的结果。为什么我们要遵守一套固定的规则和程序去做某事?大致可以给出如下理由。
第一,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组织而言,程序都是既往经验的总结,具有“操作指南”的性质。遵循程序和规则行事,极大地减少了行动者思考的成本,节省了最宝贵的资源——时间。同时,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生活,都需要建立相当程度的“可预测性”或“确定性”,而依循规则行事可以起到相互协调的作用。从脑科学的角度看,人对那些不遵守社会规范的行为的愤怒感,源于岛叶(Insula)的激活,而岛叶的激活对应着面临不确定性的恐惧*Tania Singer, The Neuronal Basis of Empathy and Fairness, in Empathy and Fairness.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2007,pp. 20—35.。可见,从演化的角度看,人类遵守规则的心理动机实际上是演化过程“内置”于头脑中的情绪反应,它和基于预期收益的后果评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二,在社会过程中,按照固定的规则办事可以约束行动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司法程序中,办案人员和法官都可能受到引诱而犯案,“刑事诉讼程序一般说来不过是法律对于法官弱点和私欲所采取的预防措施而已”*[法]罗伯斯庇尔著,赵涵舆译:《革命法制和审判》,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1页。。而在行政程序中,负责行政执法、行政审批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更为多见。公权力的执行者也是理性经济人,他们具有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原始动机,这当中也包含着滥用权力的动机。为了维护社会的合理运行,需要用程序对这些人的恣意行为进行约束,正如休谟所说:“我们应该设计出一套制度,以便即使在流氓占据政府职位时,也将为我们的利益服务。”*[英]大卫·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集》(原著影印版),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页。
由上可知,那些看上去“不计后果”的遵循规则的行为,实际上恰恰是因为规则产生了有益后果,只不过,这些后果是数学期望意义上的而非个案意义上的。那些在统计意义上产生有害后果、减弱社会福祉的规则,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是难以延续下去的。很多看上去对“过程”的偏好,常常(尽管未必是全部)可以用后果主义来解释*笔者认为,过程偏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建立在有益的后果基础之上的过程偏好,即正文中所举的那些例子;还有一类是建立在“过程带来了纯粹的享受”意义上的过程偏好。例如,一个有偷窃癖的人之所以偷窃只是为了享受偷窃带来的紧张感,而不追求任何对他有益的结果,甚至不追求偷窃成功,但是,这一类型的偏好其实很难与结果偏好区分开,因为在提供效用(满足感)的基础上,二者是等价的。何况,任何满足感的获得都必须通过一个过程实现,吃苹果、看电影、花钱也都是一个过程,如果一切偏好都是过程偏好,那么笔者看不出这种“过程偏好”有什么与传统的偏好效用主义(preference utilitarianism)根本不同的独立价值。。例如,铃村兴太郎教授曾经举过一个著名的“非后果主义”例子说明过程的重要性。父亲为三位女儿购买了一个蛋糕,有两种分蛋糕的方法:第一种是由父亲自己把蛋糕分割为三等份,第二种是由女儿们经过商谈之后进行分割。铃村认为,从后果主义的视角来看,这两种分蛋糕的方法没有任何差异,但女儿们通常会偏好第二种方案而不喜欢第一种方案。“如果经济分析仅仅关注后果,那么它显然没有把握住最关键的方面”*Kotaro Suzumura, Consequences, Opportunities and Procedures.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1999, Vol.16, pp. 17—40.。然而,从规则后果主义的角度看,这两种分法所代表的规则,其后果并不是没有差异的——绕开利益相关方,把切分蛋糕的权利赋予相关群体之外的另一个人,虽然在个案上可能会分得很公平,但完全不能保证每次父亲都不会偏心,这与人们认为民主制度优于“圣君明主”的逻辑十分相似。正是由于对结果公平的疑虑,才会有对程序公平的诉求。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后果主义的相对复杂性,给机会主义者留下的操纵机会也会较多,所以,规则后果主义要优于行为后果主义。在法律实践中,往往会采用“规则至上”,而不是赤裸裸地采用后果主义的逻辑。但是,规则的确立本身,却遵循着后果主义的判断,甚至道义论者所捍卫的“道义”,在其具体目标上,与后果主义也是大致重合的。正如西季维克所说:“我们发现,当康德转而考察德性行为追求的目的时,他阐明的唯一真正的终极目的就是通常所理解的合理仁爱的目标——人的幸福。”*[英]亨利·西季威克著,廖申白译:《伦理学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80页。R.M.黑尔也认为,康德的具体目标与功利主义并没有重大的分歧*[英]布莱恩·麦基著,周穗明等译:《思想家》,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232页。。当然,如我们已经论述过的,由于道义论缺乏具体性和灵活性,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法律上的偏差,因此,决定法律规则评判的仍是后果主义。
以上,我们循着演化理论的思路,论述了后果主义作为法律判断标准的相对合理性。但是,这种演化论证是否突破了休谟所说的“是”与“应当”的界限,“从描述性命题推出评价性命题”*[英]大卫·休谟著,关文运译:《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97—498页。?或者犯了如G.E.摩尔定义的“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英]G.E.摩尔著,长河译:《伦理学原理》,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57页。?尽管对于“是”与“应当”绝对分离的命题已经有了若干怀疑意见,当代自然法学家也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但笔者不愿卷入这一浩如烟海的文献漩涡,而毋宁用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来对演化稳定和后果主义的法律评判标准做一支持性论证。即使我们承认休谟和摩尔的看法正确,认为“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一方面,以上论证的前提之一是:法律制度应当使它所在的社会群体不断延续下去且能促进其繁荣发展,这应当是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评价性命题”,因此并不存在逻辑前项中完全是“描述性命题”的情形。另一方面,既然社会制度的演化遵循后果主义的原则,而法律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那么法律的演化也就遵循着后果主义的规律。虽然此判断是个实然判断,但“实然”对“应然”已经构成了一个强约束,即使“是”推导不出“应当”,“应当”也意味着“能够”,亦即凡是应然命题必须有一种现实上的可能性。同样,既然法律在演化中遵循后果评价的规律,那么抗拒这个规律就是不明智的。一个在演化中使种群趋于灭亡的评判标准,在社会选择的过程中也不会被通过——从这个角度看,后果主义的法律评判标准显然也更具可行性。
笔者是否持一种庸俗进化论的观点,认为“凡是具有适应性的都是好的”?或者认为“(演化意义上的)善优先于正当”呢?毋庸置疑,那些好的或善良的个体,经常不具有很强的演化适应性,从个体修身养性、出处抉择的标准来看,适应性与个体的善良的确不相关。善良的个人,也许会拥有一种不计报酬只求奉献的人生观,但是,生存竞争的规律趋向于让降低了适存度的个体从社会上消失。然而,道德楷模和耿介拔俗之士毕竟只是社会中的少数,绝大多数人都是有着七情六欲的人。立法的基础是“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可以做到”,而不是要求每个人都成为恪守道义的贤人君子,故而法律对人的道德要求决不宜过高。进一步说,从社会演化的角度来看,“丛林规则”和“庸众统治”也不是故事的全部,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必须用各种方式“补贴”那些因为善良而降低了适存度的个体——例如见义勇为者、助人为乐者、遵守社会规范者。这种补贴未必是纯粹金钱或货币上的,但一定会有益于善良与公正的行为在这个社会中不断繁衍复制,至少不至断绝,这是因为行善者的行为,对提高整个种群的适存度大有好处。故而,一个依照后果主义的互惠互利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反倒有益于道义论者的生存。这被现代演化理论家金迪思称为“社会学基本定理”*Herbert Gintis, Solving the Puzzle of Prosociality.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2003. Vol.15: pp. 155—187.。相反,“原汁原味”的道义论则未必支持对善行的物质奖励,行善者的付出不应得到补偿。故而,一个按照道义论原则组织起来、完全放弃后果计算的社会,甚至有可能不利于道义论者的生存。
还有一点需要申明,后果主义并不等同于功利主义,不一定意味着个体效用的简单加总,尤其不意味着个体货币收益的简单加总。符合实践理性原则的后果评判可以有多种形式。实际上,社会对于后果评估标准的变化以及引致特定后果的技术变迁,都会引起法律形式的变化。例如,古人对生命价值的评价,相对地低于现代社会(很可能是由于古代社会的物质资源极为匮乏,古人生育率高、人均寿命低而意外死率高,因此生命价值相对偏低),这导致古代社会相对不重视刑案中人权的保护;而现代社会发展出严格的刑事诉讼程序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并极为谨慎地适用死刑。然而,如何选择合适的后果评价标准,是一个重大而又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迄今为止的后果评价体系中,阿马蒂亚·森等人发展出的一套比较复杂精致的后果主义原则,可能是最适合现代社会的框架*[印度]阿马蒂亚·森著,葛四友等译:《后果评价与实践理性》,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森认为,评价优良后果的最重要标准是人的自由发展,而人的自由发展所依靠的不是哲学思辨意义上的“自由”,而是“实质自由”(substansive freedom),亦即尽可能地增加人们在各个维度上的可行能力,使人们发挥自己的潜力,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印度]阿马蒂亚·森、[美]玛莎·努斯鲍姆著,龚群译:《生活质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面对以创新为主导的社会,承认人的多样性和自由发展,无疑是人类社会走向“有意识演化”的最充分保障*[印度]阿马蒂亚·森著,任赜、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四、结语:走向规则后果主义
后果评价理论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后果评估的标准如何设定?如何计算一个制度所带来的所有后果?不同后果之间的权重如何确定?),但这些问题都应当在后果主义的内部解决,不能因为这些问题而放弃对法律制度的后果评价,就如同我们不能因为做不到在绝对无菌的状态下手术,就认为杀菌消毒可以取消一样。非后果主义的学说——只要不是极端的道义论——最终也必须把立法者的道德理想化约成某种后果评价体系,才有变为法律方案、在真实世界加以实施的可能;而极端的道义论是无法被实施的(极端的道义论必须考察每个人的行为动机,其信息成本过高)。
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法律制度设计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而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经济学,背后都有后果主义的逻辑。当代的行为心理学通过研究实际可测量的后果而探索主观经验,现代的脑科学则探索特定的事件与行为在脑区中的激活反应。它与法学理论的结合,形成了一门新兴前沿学科——神经元法学(neurolaw)。而法律经济学的兴起则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法学进展之一。作为法律经济学规范基础之一的福利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后果主义的。因此,后果主义可以构成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法学共同交流的“平台”和“桥梁”。
在立法和法律实践过程中,规则后果主义是最具有演化稳定性、最为可行的规范评价体系。所谓规则后果主义,亦即在执法层面上实行“规则优先于后果”,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比较严格地执行既有的规则,不斤斤计较是否达到了个案的正义,而在立法层面上则优先考虑规则的整体社会后果*这里所指的“立法”是广义的概念,既包括立法机关的立法,也包括行政机关设定规章制度,司法机关进行司法解释。。规则后果主义融摄了道义论的优长,又避免了道义论缺乏决断性、在某些情形下过于僵化的弊端。同时,道德哲学中的规则后果主义遇到的困难,在法律领域并不构成严重的问题*道德哲学中的规则功利主义遇到的问题是“规则的边界不确定”。例如,利用规则功利主义,我们无法判断“赤贫的穷人偷面包店里的面包给自己的弟弟妹妹吃”是否道德,因为“不许偷窃”的规则是否允许例外,而容纳这种例外是否又构成一个独立的规则,规则功利主义无法给出明确答案。但是,在法律层面上,这种问题至少可以得到缓解——因为法律本身的界限是明确的。如果现行法律惩罚一切偷窃,那么此穷人就应被判有罪,但在立法层面上,根据规则后果主义,我们可以认为这条规则是不正确的,应当补充修订。事实上,在现代刑法学当中,根据“期待可能性理论”,这类行为确实也可以被认为无罪(参见童德华:《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论》,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我国《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2008年试行)第三条已经规定:“因生活无着偶然实施盗窃等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不大的,可以依法决定不起诉。”。同时需要注意:坚持社会演化协调一致的规则后果主义,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评判所有法律规则时都必须处处考虑它们的后果,恰恰相反,当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许多重大信息缺失,以致我们无法完整评估某一规则的后果时,遵循既有的法律原则(例如富勒提出的法治的八个基本原则)或既有的立法例,反而是比较好的演化策略,因为这些原则和先例是引致有益后果的海量经验的浓缩,可以避免在演化中盲目试错的成本。但是,如果立法者能够确当地评估既有法律规则的后果,则可以不必拘泥于原则和既有的立法例,直接运用后果主义即可做出判断。由于法律系统经过了几千年的演化,已经形成了一套足以较好地促进社会福利的规则体系,因此做出这类改革的机会并不多;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机会,规则后果主义者就应当不失时机地对法律制度进行合宜的调整,以促进法律系统乃至社会群体的有意识演化。
限于篇幅,笔者并没有评述当代的美德伦理学和社会规范评价之间的关系。但笔者对美德伦理学的看法,与对道义论的看法是相似的。道义论在道德哲学上是伟大的,对个人培养坚卓弘毅的善良意志、养性成德大有益处,也可以对法律起到一些原则上的启发作用,但归根结底,法律是一套激励机制,具有明确的社会功能,把它建立在道义论的基础上是不甚合适的。对于美德伦理学,笔者同样充满尊敬——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心心相通的同情共感之仁和社群中的友爱互助之德,构成了我们生命幸福的最主要源泉,而且在社会演化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些德性并不适合作为一个大规模的、以陌生人交往为主的市场社会的规范基础。只有以规则后果主义为根本,融摄和消纳道义论、美德伦理学的优长之处,以此指导立法和法律实践,才是一条现实中可行的中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