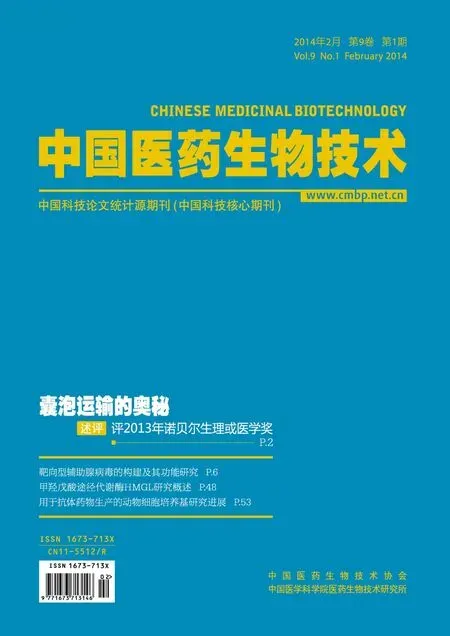第二制药用途类专利申请中新颖性、创造性的问题分析和申请策略
曲凯,武雪梅
第二制药用途发明专利是指,将某种现有技术中已知的且已经用于治疗某种疾病的药物用于治疗其他不同的疾病,从而针对该用途获得的相应专利。由于新药的筛选和设计具有可预测性低、成本高的特点,且临床安全性检测期十分漫长,而进一步开发已知药物的新用途可有效降低高研发成本,通过临床实验检测的成功率也相对较高,因此对已知化合物的第二制药用途研究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新颖性和创造性问题是第二制药用途专利申请中最常见的问题,对于专利能否获得授权具有决定性意义。
目前来看,第二制药用途类专利的保护方式和专利权界限在各国都有所不同。欧洲专利局(EPO)扩大申诉委员会的第 G02/08 号决定裁定:新的欧洲专利公约 Art.54(5)不仅将承认“用于新的疾病适应证用途”的已知药用化合物和组合物的新颖性,还将承认“用于已知疾病适应证的新的治疗方法”的已知药用化合物和组合物的新颖性,且其中的“新的治疗方法”包括“新的给药方案”[1]。这意味着该决定生效后,制药用途类权利要求(瑞士型权利要求)在 EPO各成员国的申请将不再有必要了。而我国的审查标准尚与之不同,《专利审查指南 2010》在第二部分第十章中明确规定,对于涉及化学产品的医药用途发明,其新颖性审查应当考虑新用途是否被原已知用途的作用机制、药理作用所直接揭示,与原作用机制或药理作用直接等同的用途不具有新颖性;给药对象、给药方式、途径、用量及时间间隔等与使用有关的特征是否对制药过程具有限定作用,仅仅体现在用药过程中的区别特征不能使该用途具有新颖性[2]。
笔者谨希望通过分析第二制药用途权利要求在新颖性和创造性审查中常见的几种情形,对申请人如何在目前审查标准下,提高专利申请的质量、争取有效的保护给出建议。
1 案例介绍和分析
在制药用途权利要求的审查过程中,常见多种撰写方式,根据目前的规定,物质的医药用途发明通常的撰写方式应为“物质 X 在制备治疗 Y 病的药物中的应用”,对于“物质 X 作为药物在治疗 Y 病中的应用”则属于治疗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对于第二制药用途的新颖性和创造性审查,争议较多的情况有:对比文件泛泛提及的“公开不充分”的技术方案能否作为证据使用;取得了预料不到技术效果的给药方案和给药方式是否能够获得保护;针对第二制药用途的非显而易见性该如何划界;联合用药的创造性评判标准等。以下将结合案例对这四种常见情形加以分析。
1.1 第二制药用途被对比文件“泛泛”公开
第二制药用途是基于已知化合物或药物的新用途进行保护。在该药物最初被筛选到并申请第一制药用途时,往往在该申请文件中泛泛提及多种适用证,又或者在其他治疗某种疾病的申请中提及了该药物的使用。此类申请的共同特点是,对比文件中通常没有记载该种药物治疗该种疾病的具体实验或临床实验数据。
【案例 1】 “权利要求 1:促红细胞生成素在制备治疗和(或)预防糖尿病性视网膜病的药物中的用途。”
驳回决定中认为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已被对比文件1 公开,不具备新颖性。对比文件 1 未公开促红细胞生成素治疗糖尿病性视网膜病的任意实验数据。本申请通过实验结果论证了促红细胞生成素能够防止糖尿病视网膜厚度降低和降低神经元细胞损伤、死亡,从而具有治疗用途。
本案的争议点在于:申请人认为对比文件 1 中的证据为公开不充分的技术方案,其罗列了数百种促红细胞生成素能够治疗的疾病(包括糖尿病性视网膜病),但未披露使用方法和效果,且由于没有记载具体的治疗效果试验,公众需要无限次的试验(undue experimentation)才能从数百种疾病中鉴定出促红细胞生成素是否可以治疗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及其使用方法,这需要付出大量创造性的劳动。
分析:对于此类泛泛提及技术方案但无验证结果的对比文件,其能否作为证据使用,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生物制药属于技术效果可预见水平相对较低的领域,在对比文件未记载实验数据的情况下,泛泛提及的制药用途技术方案不能确定是有效的,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现有技术中明确或隐含公开了药品 A 具有特定药理活性或治疗用途,则无论其是否公开了效果实验,通常都破坏药品 A 的相同治疗用途发明的新颖性,因此可作为证据使用。
对于上述情形,申请人是否能够提交证据表明该现有技术的描述不正确是关键。何为“表明该现有技术的描述不正确”的证据?审查指南和操作规程中都没有明确定义。对于本案来说,申请人提供证据证明在对比文件 1 公开的阶段,本领域对促红细胞生成素的作用存在不同观点,部分观点认为促红细胞生成素会导致增生性糖尿病视网膜病,这与对比文件 1 的观点相反。因此,在对比文件 1 未公开实验结果的情况下,本领域人员会因现有技术中存在不同教导而混淆,得不到确切答案。
然而,反观对比文件 1 会发现,对比文件 1 公开了促红细胞生成素可用于治疗和预防由低氧状况引起的疾病,包括视网膜相关疾病(如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并公开了促红细胞生成素治疗缺血、缺氧动物模型的实验结果。而在对比文件 1 公开的现有技术阶段,也有证据显示低氧确实与糖尿病性视网膜病之间存在关联,该文献同时公开了具体的机制和实验结果。也即,对比文件 1 和现有技术都给出了这样的教导:促红细胞生成素可治疗缺氧相关疾病,而糖尿病即导致视网膜缺氧。因此,即便对比文件 1 中没有记载明确的实验结果,本领域技术人员也可以通过有限的试验进行验证,对比文件 1 的描述仍然是“正确”的。
综上,基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角度,如果现有技术公开了某种化合物通过某种机制或药理治疗疾病,对于该机制或药理致病的适应证,即便该现有技术未公开具体的实验结果,但本领域技术人员仍可推知其是有效的;反之,如果现有技术中无其他证据支持对比文件甚至存在相反证据,且对比文件中该技术方案无法根据其记载的其他内容或实验数据推断有效,则需另加考虑。从行业角度来说,判定在后申请的作用机制或药理直接等同的制药用途不具备新颖性,也有利于维护创新药物企业的利益、激励新药的研发创新。
1.2 给药方式、途径、方案等特征限定的第二制药用途的可专利性
除美国外的各国都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排除在可授予专利权的主题之外。因此,涉及给药方案、方式的改进能否获得专利权以及保护范围和效力如何均备受关注。
【案例 2】 “权利要求 1:促红细胞生成素在制备治疗和(或)预防糖尿病性视网膜病的药物中的用途。
权利要求 4:如权利要求 1 的用途,所述哺乳动物为人且所述促红细胞生成素玻璃体内给药至人眼的量为1.33~60 μg/眼。
权利要求 5:如权利要求 1 的用途,所述促红细胞生成素在 3 周~3个月时间增量内间歇性地给药至眼睛。”
驳回决定中认为,权利要求 4、5 进一步限定的是给药剂量、给药方案,其对化合物的制药用途不具限定作用,因此在权利要求 1 不具备新颖性的基础上,权利要求 4、5 也不具备新颖性。
本案的争议点在于:给药方式或用量对制药用途权利要求是否产生限定作用?有观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十章附则第一百零二条给出的药品定义中,明确认定用法和用量是药品的必要特征,同时,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曾认为给药/用药特征可以使此类权利要求具备新颖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8]高行终字第378 行政判决书中,针对以医药用途权利要求方式撰写的医药用途发明提出:“医药用途发明本质上是药物的使用方法发明,如何使用药物的技术特征……应当属于化合物的使用方法的技术特征而纳入其权利要求中。实践中还存在使用剂型和剂量等所谓‘给药特征’方面进行改进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技术效果的需要。此外,药品的制备并非活性成分或原料药的制备,……当然也包括所谓使用剂型和剂量等‘给药特征’,……不考虑这些所谓的‘给药特征’是不利于医药工业的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健康需要的,也不符合专利法的宗旨”。
分析:对药物的进一步研究中,除了新的治疗用途外,某些剂型、剂量等药物特征的改变或治疗方案的改进也往往产生预料不到的效果。我国目前的审查标准是允许以适应证、给药途径、给药部位等限定制药用途类权利要求。可以发现,上述特征的共同点都是对制药过程产生了限定作用,这是判断制药用途类权利要求的重要标准,仅仅体现在用药过程中的区别特征不能使制药用途具有新颖性。对于本案来说,即便“1.33~60 μg/眼”的给药剂量或“3 周~3 个月时间增量内间歇性地给药”的给药方案取得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其更多的属于医生在治疗过程中的职业行为,不能够带来对工业界的推动和革新,因此不能构成具有新颖性的制药用途,这也与我国目前专利法的立法本意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权利要求 1、4、5 实质上限定了促红细胞生成素的剂型是眼部外用,该技术特征是对制药过程产生了限定的。如果在本申请之前,该药物的该种给药方式没有先例或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如需要施用难以实现的剂量或存在较大副作用),而本申请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那么,眼部外用给药这一给药方式隐含的剂型特征的改变构成了权利要求与现有技术的区别。在权利要求具备新颖性的基础上,结合剂型改变带来的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能够判断权利要求进一步具备了创造性,本申请可能藉此获得专利。
1.3 第二制药用途的“非显而易见性”判定
阿司匹林之前一直作为解热镇痛药物使用,之后被发现可用于预防心脏病和高血压,该第二制药用途被授予专利主要是因为取得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这应当属于医药用途类的“开拓式”发明。然而,在现实申请中,“开拓式”发明并不常见,基于已有发明的改进则占了绝大多数。对于此类申请,其在现有技术中往往存在或多或少的“技术启示”,因此,创造性判定在审查和意见答复中也争议较多。
【案例 3】 “权利要求 1:干扰素 λ 在制备用于施用以治疗病毒诱导的呼吸道疾病的恶化的药物中的应用,所述病毒诱导的呼吸道疾病为哮喘。”
对比文件 1 公开了表达干扰素 λ 的病毒在鼻内感染模型中感染能力显著下降,干扰素 λ 在不同细胞中的表达,可能对于呼吸道感染后的影响较大,具有潜在治疗用途。第一次审查意见中认为,基于对比文件 1 公开的内容,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推知干扰素 λ 可能用于治疗呼吸道病毒感染,并通过有限的实验验证,因此发明不具备创造性。申请人认为,对比文件 1 仅仅涉及表达干扰素 λ 的重组病毒的鼻内输送,且现有技术中存在以下教导,“尽管先前报道IFN-β-ser 具有抗病毒活性,但已经证明它在预防自然感冒的试验中无效”。也即,申请人提供证据证明了现有技术中教导不能根据干扰素表现出抗病毒活性,就认为其将具有抗体内天然呼吸道病毒感染的治疗价值。根据现有技术的教导,不能预期基于对比文件 1 能够获得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本案最终获得授权。分析:创造性判断的主要标准在于是否取得了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辅助标准为是否取得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纠正了普遍的观念或获得了商业的成功。对于第二制药用途发明,除了遵循普遍的创造性判断标准外,尚有其特殊性。具体来说,对于医药用途的有效性判定,说明书公开充分的基本条件为:确定的实验对象、可实施的实验方法、足以判断结果的定性或定量实验数据、明确的实验结果与用途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判断一个(一类)化合物是否能够用于制药的标准是相对较高的,其所需要的实验体系或实验方法是相对复杂的。因此,基于现有技术中相对简单或基础的实验数据(如细胞学实验)或断言性定论,是否就足以“容易地”推断出其制药用途,这种结果是否为难以预料的,这是判断发明是否具有创造性的关键所在。
具体到本案,对比文件 1 给出了表达干扰素 λ 能够抑制病毒鼻内感染的实验结果,但现有技术中同时存在干扰素的抗病毒活性与其预防/治疗呼吸道病毒感染的能力无关的证据,因此,基于上述两方面内容,本领域技术人员就不能“容易地”推断出干扰素 λ 一定能够治疗呼吸道病毒感染,这需要实验结果加以证实,也是申请能够获权的发明点所在。相反的,如果现有技术中存在干扰素的抗病毒活性与其预防/治疗呼吸道病毒感染的能力直接相关的证据,基于对比文件 1,本领域技术人员就能够“容易地”推断出干扰素λ 能够治疗呼吸道病毒感染,并通过有限的实验验证,也即,如果发明点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通过合乎逻辑的推理、分析获得的,那么发明就不具备创造性。
对于此类发明,EPO 也有相似的观点,EPO 第T241/95 号裁决中认为:简单的药理活性并不必然得到医药应用,例如发现给定化合物与特定受体的结合不能认为是一种医药应用,即便这种发现代表了重要的科学知识,也需要进一步发现对于病理状况确切、真实的治疗形式的应用。
1.4 联合用药的创造性判定
联合用药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化合物共同作为有效成分治疗疾病,由于有效成分的改变通常涉及药物在治疗过程中作用机制的改变,因此,联合用药也可以作为一类特殊的第二制药用途发明。
【案例 4】 “权利要求 6:奥曲肽和帕瑞肽在制备用于治疗肢端肥大症的药物中的用途。”
现有技术中,奥曲肽和帕瑞肽都可以单独用于治疗肢端肥大症,其作用的机制相似,都是靶向 SSTR 的 SRIF-类似物。第一次审查意见中认为,选择两种作用机制相似的同类药物共同治疗某种疾病是常规选择,因此发明不具备创造性。申请人在意见陈述中认为,本申请的发明点在于奥曲肽和帕瑞肽联合使用,不仅协同增效,且奥曲肽的存在有效降低了帕瑞肽促血糖升高的副作用,这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不能预期的,因此也就没有技术启示从众多同类药物中选择奥曲肽和帕瑞肽联合用药,因而发明具有创造性。本案最终获得授权。
【案例 5】 “权利要求 8:干扰素 α 与氨溴索的雾化吸入剂在制备治疗病毒性肺炎药物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单次给药剂量 1 ml 中含有 10~20 μg 的干扰素 α,3 ~4.5 mg 的氨溴索。”
现有技术中公开了干扰素 α 与氨溴索的联合用药,其用途与本发明相同,都是用于治疗病毒性肺炎。第一次审查意见中认为,所述单次给药剂量中干扰素 α 与氨溴索的比例可以通过有限的常规实验筛选获得。申请人在意见陈述中给出了药效对比实验数据,认为仅该数值范围内两种药物的配比才具有协同增强作用,因此属于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本案最终获得授权。
分析:案例 4 和案例 5 是联合用药中常见的申请类型,其分别是针对联合用药的活性药物组分和组分的含量进行了选择。如果联合用药的药效仅是单个组分的简单加和,且可以通过有限次的实验确定合适的比例或用量,则不具备创造性。如果组合发生了显著的协同或增强作用,例如案例4 中奥曲肽有效降低了帕瑞肽促血糖升高的副作用、案例 5中的干扰素 α 与氨溴索按一定比例使用才能有效降低总体用药量并协同增效,这都属于本领域技术人员难以预料的技术效果,则发明具备创造性。
2 对相关专利申请的建议
我国目前生物医药领域总体技术水平较低、国际竞争力较弱。出于激励企业自主创新、促进行业发展的考虑,我国对于生物医药领域专利的审查标准也在不断调整,其总体趋势为加强对药品专利保护力度的同时,提高对制药用途的审查标准。基于此,综合前述案例对医药行业相关专利的申请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对于制药企业来说,专利申请前就需要考虑到对核心技术进行专利布局,也即,以核心专利为基础申请一定数量的外围专利,形成必要的组合专利。药物组合专利的申请除生产工艺、用途、使用方法外,还可以具体到产品的颜色、大小和形状等,其目的是编制密集的专利网,扩大权利保护范围的外延,尽可能地抵制后继仿制药侵权。这既有利于形成稳定的专利权范围,也有利于必要时专利攻击策略的使用。
第二,专利撰写前应当进行系统的专利检索和分析规划。由于制药用途容易被现有技术中“泛泛”提及的技术方案破坏新颖性,申请前的检索就显得尤为重要。此外,通过检索可以分析、了解竞争对手和整个行业的前沿趋势,利于调整自己的技术发展方向,进行有效的专利储备。
第三,即便通过检索发现核心技术已被申请专利,仍可考虑申请周边专利。如药物仿制、衍生物或新剂型开发可能获得新的产品及用途专利权。其优势在于当遭遇侵权诉讼或纠纷时,既使不能绕过对方的专利,也可以以守为攻,通过申请周边专利增加谈判的筹码,在司法实务操作中,专利越多越密集的企业在专利战中一般越能占据有利地位。
第四,合理利用国内外专利制度的差异,我国目前对于给药方式、方案等特征限定的制药用途的标准仍然是判断其是否对制药过程产生了影响,而不同国家对于制药用途类申请的规定并不相同,应当及时关注。例如,前述 EPO 各成员国对第二制药用途的审查策略就发生了改变,针对同样的发明应当依据各指定国的法规政策进行撰写,仅仅通过国内PCT 途径进行申请,不利于在国外的专利权保护。
第五,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也是一项“创造性”劳动,是对发明的进一步完善和升华。如何在保证说明书公开充分的基础上合理隐藏技术秘密,如何通过层层递进的方式撰写权利要求书,如何使权利要求保持合理稳定的范围,如何通过对基本概念和技术参数的定义在后继侵权诉讼中争取有利地位,都需要专业技巧。对于第二制药用途权利要求,如果发明点在于发现了药物的新的作用机制,完全可以使用机制限定的方式撰写权利要求,其涵盖了与该机制有明确对应关系的各种病症,能够获得较宽的保护范围;如果发明点仅在于发现了药物作用于某一特定病症,在机制不甚明了的时候,可以在说明书中不涉及机制的证明,仅通过药效学实验也能满足说明书公开充分的目的,这样能够合理保护技术秘密。此外,也可以将药物与领域中各种常规技术手段(比如佐剂、辅料)结合来保护制药用途,能够在后续发生侵权的时候占据有利地位。
第六,在专利审查过程中,面对创造性质疑时,合理、有效的答辩理由也很重要。可以使用的策略包括:将发明的区别技术特征与现有技术明确划界、从现有技术中寻找第三方证据支持发明点的“非显而易见性”、必要时提供与对比文件的对比实验结果等。
[1] Xiao P, Feng YZ.The end of pharmaceutical use patents in Europe and the influence and inspiration on China.Intellect Property, 010,20(117):38-45.(in Chinese)肖鹏, 冯铻战.制药用途专利在欧洲的终结及对我国的影响和启示.知识产权, 2010, 20(117):38-45.
[2] State Intellectural Property Offi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atent examination guidelines 2010.Beijing: Intellectural Property Publishing House, 2010.(in Chinese)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指南 2010.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