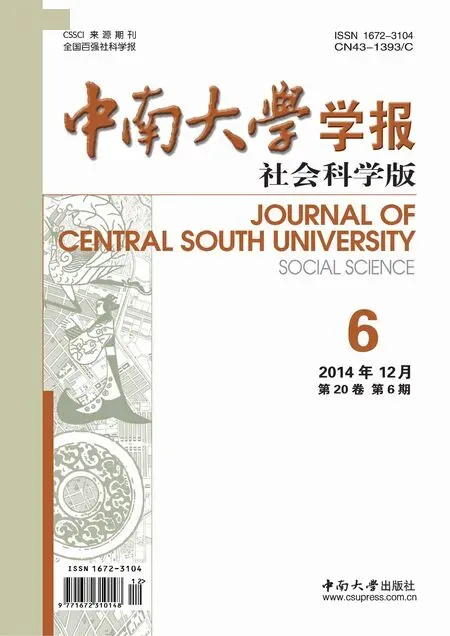后经典叙事学与文学研究的“话语转向”
李林俐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江苏南京,211189)
后经典叙事学与文学研究的“话语转向”
李林俐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江苏南京,211189)
“话语转向”作为文学理论从“现代”向“后现代”过渡中最重要的范式转换之一,在将文学置于开放性的外在向度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失落了对于文本结构本身的关注。作为伴随“话语转向”而兴起的一种新的学科架构与知识体系,后经典叙事学一方面将人们的视域延伸至更宽广的社会文化语境,一方面也不忘立足文本,对文本自身各要素的复杂关系加以审慎的梳理与细致的辨析,并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系列切实而具体的文本解读方式。后经典叙事理论不仅矫正了当前文学研究对于文本本身的相对忽视,同时也缓和了文论转型中“语言”和“话语”两阶段之间的张力,从而在“话语转向”的总体背景下展现出了充分的生长可能。
后经典叙事学;语言;话语;话语转向;文本结构;社会文化语境;文论转型
一
在文学理论从“现代”向“后现代”的历史性位移中,由“语言”(language)向“话语”(discourse)的过渡无疑是最具特色的范式转换之一①。“从文学理论在20世纪的范式建构来看,我们可以概括出语言学转向出现了两次:第一次转向从世纪初到60年代,呈现在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捷克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的理论探索中;第二次转向则出现在后结构主义之中。前一次转向建构了分析抽象语言系统和规律的理论范式,后一次转向则反其道而行之,将抽象的语言转换为实践性的话语,完成了以话语为范式的理论建构。”[1]如果说,对语言的强调主要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说为理论支撑,侧重于一种与外界社会文化隔离的封闭、微观的研究方式,这种研究取向在科学主义思潮兴盛的背景下发展壮大,并实现了对西方文化自古希腊开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或“语音中心主义”传统的遥相呼应——无论是形式主义者对导源于语言的“文学性”的强调,还是新批评理论家对“张力”“反讽”“谬见”诸说的推崇,抑或结构主义者对作品内部抽象结构单元的细致划分,都是这一理论取向的突出例证。那么,对话语的关注则在相当程度上作为对语言的逆反而凸显出来,它改变了传统文学研究局限于闭锁的、孤立的语言体系的理论取向,为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种别样的思维路径。
所谓“话语”,来源于拉丁文“discursus”,而“discursus”又由动词“discurrere”转换而来,意为“到处奔跑”“四处游走”[2](647)。不难发现,在话语一词的语源学意义上,其实已经包含了一种打破封闭状态,将视野拓展至更广泛领域的初始动因。早在结构主义代表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的论述中,话语的这种开放性特征便已经有所表现:“话语概念是语言应用之功能的对应物……语言根据词汇和语法规则产生句子,但句子只是话语活动的起点,这些句子彼此配合,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里被陈述,它们彼此变成言语事实,而言语变成话语。”[3](17)毋庸置疑,他的表述强调了话语作为一种表达行为的实践性,以及对于交往情境的依赖。伴随文学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被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戏称为“没有主体的符号链”的语言已经无法穷尽文学本身的无限丰富性[4](100)。于是,在倡导多元化、反对本质主义的后现代思潮的推进下,人们不再将文学贬低为一只封闭而脆弱的“精致的瓮”,不再将文学研究贬低为一种局限于真空之中的纯语言学意义上的操演,相反,将文学理解为一种“话语”,将文学研究理解为一种“话语批判”的趋向已经愈发显著。作为“话语批判”的文学研究,将过去常常为语言中心主义者所忽略的社会文化维度引入了研究框架,注重“言说者”-“言说过程”-“言说对象”三者在具体文化情境中的相互关联,“话语必须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任何一种表述,只要它假定了一个说话人和一个听话人,在说话人身上便存在着一种以某种方式来影响他人的动机”[5](208-209)。于是,一方面,文学研究不再局限于狭隘孤立的“语言”领域,而是成为了一种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话语”层面的考量,从而扩展到更加广泛的文化价值领域;另一方面,研究视野的开放、扩充又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文化向度上的意义附载于作为话语的文学范畴本身。例如,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反对文学写作中那种中心化、强制性的“权威话语”,转而推崇一种民主化、多元化的“对话”格局;阿尔都塞(Louis Ahhusser)将文学视作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操控的制造幻觉的话语工具;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将文学话语看作承载象征资本威权的符号,注重挖掘其中隐含的政治经济学内涵……无不是鲜明的例证。当然,话语理论的最显著代表莫过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权力与话语”的阐述。福柯不主张将话语简化为纯粹的语言符号,而是更多聚焦于“系统地形成话语的谈论对象的多种实践”[6](54)。在他看来,权力作为一种微观、多元、流动的关系性存在,与话语彼此依存,难以分离。话语的广泛传播带来了权力的加固与不断增殖;与此同时,权力又为话语提供了维系其存在所不可缺失的绝对的依凭。福柯相信,文学实际上便是一种话语,它由作为权威的大学机构赋予了特权,而文学的不断传播、流行又逐渐强化了大学的影响力与神圣地位。“从来没有人分析过,在大量的言谈中,在所有实际的话语中,一些这种类型的话语(文学话语、哲学话语)被赋予了特别的神圣性和功能。……文学是通过选择、神圣化和制度的合法化的交互作用来发挥功能的,大学在此过程中既是操作者,又是接受者。”[7](87-89)
无需赘言,在层出不穷的“话语理论”的带动下,在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直至新近发生的赛博批评、空间理论、生态主义、鬼怪批评中,文学作品已经越来越被看做是一处充溢着权力、意识形态、性别∕种族歧视、象征资本等因素的,不断发生着抑制、抗拒、冲突、流变的充满张力的地方,成为了一片各种力量彼此角逐、互不相让的“战场”。这种由“语言”向“话语”的转向无疑能极大地拓宽研究者的理论视野,将作者、读者、批评家乃至更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纳入其探讨的范围之内,从而使文学告别“语言中心”阶段封闭、抽象的意义指涉,获取更加多元化的理论内涵与价值取向。进而言之,话语转向也意味着对于启蒙时代“理性万能”的宏大叙事的强烈反拨:既然局限于语言之内的精确解剖无法穷尽文学的本真存在,那么推而广之,局限于理性(它是语言背后的最强有力支撑)之内的谋划与操作也绝不可能穷尽客观世界的无限可能性。自然,文学研究由“现代”向“后现代”的推进也将伴随这种认识的转变而循序渐进地发生。
然而,作为“话语分析”的文学研究同样潜藏着严重的隐患。首当其冲的,是文学研究中的“过度语境化”趋向。在话语观念支配下的文学研究中,人们总是先入为主地将权力、压迫、意识形态等因素作为最核心的考察对象,总是习惯于借助一种外在的框架对文学话语加以梳理与规范,这种对语境的过分强调可能导致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化”,甚至是“庸俗社会学化”。其次,正如福柯所言:“为了弄清楚什么是文学,我不会去研究它的内在结构。我更愿去了解某种被遗忘、被忽视的非文学的话语是怎样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和过程进入到文学领域中去的。”[7](90)在研究者对于外部语境的日复一日的强调中,文学自身的内在组织构造遭受了可想而知的遗忘。如此一来,文学研究也便极有可能失去其安身立命的最重要出发点,并逐渐沦落为一座失去立足根基的虚妄的“空中楼阁”。
二
从“语言”转向“话语”,从精密、封闭的真空式研究转向游牧般四处弥散的开放性思维,这样的差异不仅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价值取向,同时也印证了“现代”与“后现代”理论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张力。“如何超越两极对立而建构‘第三条道路’,是黑格尔式的“正、反、合”螺旋上升辩证过程?还是两极对立依旧但却衍生出其他另类路径?”[1]这是每一个文学研究者必须思考的问题。不过,需要注意,语言和话语之间的界限或许并不像表面上那般泾渭分明,或许,在这两种研究取向之间还潜伏着千丝万缕的隐秘关联。诚然,一种总体化、宏观性的描述式考量并不能彻底缓解乃至消弭这两种理论趋向目前的紧张关系,但是,倘若采取一种更加具体、细致,更富实践性与操作性的研究方式,以之切入话语转向背景下的文学研究中,人们也许可能发现语言同话语之间更加微妙而深刻的“同构性”,进而使沟通这两种研究状态的理论方式在更具可感性的实践层面上得以彰显。于是,当前蓬勃兴起的“后经典叙事学”(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便成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考察路径。
所谓后经典叙事学(亦称“新叙事学”或“后现代叙事学”),与兴盛于20世纪50~60年代以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为根基的“经典叙事学”(classical narratology)不同,是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兴起,以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修辞学、文化研究等理论思潮为支撑,以开放、多样、“消解距离”为宗旨的叙事学的理论态度与研究立场。美国学者戴卫·赫尔曼(David Herman)曾谈到,后经典叙事学注重“揭示结构主义旧模式的局限性”,同时,又主动“吸纳了大量新的方法论和研究假设,打开了审视叙事形式和功能的诸多新视角”[8](3)。有国内学者则指出,后经典叙事学的最鲜明特色在于克服经典叙事理论固守于文本自身的缺陷,进而“将叙事作品视为文化语境中的产物,关注作品与其创作语境和接受语境的关联”[9](6)。诚如此言,后经典叙事学将新的学科范式作为其终极归宿,表现出了多元化、跨学科、跨文类、跨媒介等一系列全新的特征,从而由多个层面完成了对经典叙事观念的“反叛”与“超越”。当然,后经典叙事学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脱胎于经典叙事学的“母体”,并倾向于“把经典叙事学视为自身的‘重要时刻’之一”[8](3)。但必须承认,在后经典语境下,任何传统的理论术语和概念范畴往往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炼、拓展与升华,从而也呈现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精神取向与方法论立场。可以说,正是这种新旧交接点上的超越与提升,使后经典叙事学能够同“话语转向”中的文学研究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契合,从而为二者之间更深层次的对话、沟通与交融奠定了学理上的坚实基础。
首先,是“叙事”(narrative)与“话语”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联。如前所述,“话语转向”的出现意味着较之从前更加明确、集中地将各种社会文化成分引入文学研究之中,进而将包括作家、读者、文本等等在内的整个文学体系视作任由种族、性别、阶级、伦理等因素激烈争斗、无限蔓生的动态场域。这一理论操作本身便隐含着这样的思路:作为话语形态的文学表达绝不能完全等同于(哪怕只是相对接近)言说或表述的对象本身,相反,多种力量的彼此抗衡、商谈、妥协使文学表达总是或多或少地成为了被这些力量所重塑、改造的“客体”或“对象”。例如,后殖民主义者总试图通过文学研究揭穿“西方中心主义”的阴谋,女性主义者往往把文学视作她们深恶痛绝的白人中产阶级男性实施其威权的手段,而文化民粹主义者则倾向于将主流文学当成是可以不断拼接、改造,从而制造逃逸的“快感”的契机……在一次又一次的阐释乃至“过度阐释”中,文学的“能指”外壳越来越脱离其“所指”而肆意飘荡,文学作品的本真存在也变得比任何时刻都难以轻易触及。
在“经典”到“后经典”的演进历程中,类似的层次划分得到了愈发清晰、集中的贯彻与体现。美国叙事学家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曾就“叙事”一词作出过这样的界定:“由一个、两个或数个(或多或少显性的)叙述者向一个、两个或数个(或多或少显性的)受叙者传达一个或更多真实或虚构事件(作为产品和过程、对象和行为、结构和结构化)的表述。”[10](136)不难发现,在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叙事行为中,实际上包含着如下两个环节:① 作为叙述对象的特定事件;② 实际的叙述行为以及对这种叙述的效果预期。二者分别表征着不同的组织构造、逻辑思维乃至文化价值关怀。这种层次划分的明确意识清晰地贯穿于叙事学从“经典”向“后经典”演进的整个过程中:俄国形式主义者的“素材”与“情节”,热奈特(Gerard Genette)的“故事”(histoire)和“叙事”(discours)以及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的“故事”(story)和“话语”(discourse),无不是上述区隔意识的明确体现②。如果将叙事学中的层次划分同作为“话语解读”的文学研究相互参照的话,那么不难发现:正如在作为“话语”的文学表述与被表述的特定事件之间横亘着难以弥合的鸿沟,在被叙述的具体事件与叙述过程及其结果之间,同样存在着巨大而耐人寻味的张力——客观而本真的事件是异常复杂、生动、难以捉摸的,它不可能被作为符号序列的叙述话语所完整把握并精确还原。更进一步,在叙述的实际行为中,每一段语词序列都并非单纯、透明的“容器”,它们都无法摆脱叙述者主观意念乃至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与渗透,自然也不可能与“原初事件”产生真正的呼应与契合。当然,在作为微观操作技法的“叙事”同作为宏观研究范式的“话语”之间进行这样的类比也许略显牵强,但无可否认,二者在理论姿态上的暗合之处恰恰成为了后经典叙事学与“话语研究”产生交集的最重要前提。
其次,从研究方式上看,在后经典叙事学同“话语转向”中的文学研究之间也存在着类比的空间。毋庸置疑,作为一种“话语批判”的文学研究,强调的是一种“跨学科”乃至“超学科”的研究方法。如果对“话语转向”背景下的文学研究稍加梳理的话,不难见出,不同理论家对于特定文学作品所采取的学科态度、所征引的理论资源显得格外错综复杂。如巴赫金对文学中“权威话语”与“对话”状态之间两极对立的研究,便主要来源于对中世纪官方文化与民间“狂欢节”文化之间张力的历时性考察;布尔迪厄将文学话语视作权力的符号化形式的思路,主要来源于他的社会经济学素养与语言学积淀;阿尔都塞对文学作为被“多元决定”的权力话语的相关思考,则可以追溯到他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以及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采纳……在福柯的理论视域内,对于包括文学话语在内的各类话语体系的研究则呈现出了更加驳杂多元的知识谱系:在他的早期研究中,主要体现出一种哲学与考古学融会贯通的知识状况,以此为基点,他不仅概括出了古典、现代、当代各种“知识型”(episteme)的独特品质,更注重考察知识型的变迁所造成的话语方式的改变;而他的后期研究更是展现出了伦理学、法学、临床医学、精神病学等诸多知识成分相互交织、彼此勾连的驳杂面貌,他的目标在于从尽可能多的向度出发,对权力话语的组织、构造、内在规范以及压抑机制等等作出更为全面、清晰的体认。
而后经典叙事学同样体现出了对这种“跨界整合”趋向的天生的狂热。英国理论家马克·柯里(Mark Currie)曾将“多极化”设定为当代叙事理论的最突出特征之一,他所说的多极化主要指“叙事学研究范围的大规模拓展和研究对象的日益包罗万象”[11](3),其中,自然也隐含着打破固有学科边界的冲动以及通过多个角度并采取多种策略对特定对象加以探究的热切渴望。由此看来,后经典叙事学始终不忘将“马克思主义、接受理论、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融为一炉[11](16),进而全方位、多层面地作用于既定叙事文本的研究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这种多样化的姿态与包容性的视野无疑与“话语转向”背景下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呼应。
再次,在理论诉求上,“话语转向”推动下的文学研究背弃了“语言中心”阶段对于启蒙理性的绝对信仰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深层次结构与绝对意义的执著追寻,它往往青睐于描绘文本疆域内各种因素彼此争斗、相互抗衡,不断迁移、流动、转变的生动图景。如霍尔(Stuart Hall)便明确意识到,依照话语研究的运行逻辑,意义并非俯拾即是、触手可及,并非驯顺地寓居于文本内部,相反,意义总是被种种外在力量所规训、所塑造,总是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并“一直在推迟和延缓与绝对真理会面”[12](9)。福柯更是很大程度上流露出了后结构主义的鲜明气质(尽管他自己对此矢口否认),在他看来,对于整个话语体系的考察不仅应当涉及具有绝对统摄性的所谓“宏大权力”,更应当着力关注以多种形态渗透于话语之中的“微观权力”的生动、灵活的游移与流变。于是,权力也便结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性网络,“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的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权力运转着……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13](27-28)。
同样,这样的理论姿态也存在于后经典叙事学对传统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二项对立”(binary opposition)模式的瓦解过程中。可以说,经典叙事学通常热衷于将叙事理解为“一种基本解释模式、一种不可化简为普遍涵盖律模式的模式”[14](194),并力图对蕴藏于文本深处的,包括“中心—边缘”“男性—女性”“白人—黑人”“光明—黑暗”等等在内的二元模式加以开掘。这样的状况注定了叙事学自其诞生伊始便面临着被“架空”的困境,面临着被贬抑为流水线式的,机械、僵化的“操作技法”的危险。而后经典叙事学则试图扭转上述局面。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倡导者强调,“任何故事都具有永无止境向前发展的潜能”[15](225)。在他们的眼中,叙事的目标不是要找到一个本质主义式的意义的“终极”,相反,意义就如同古希腊神话中佩涅洛佩的织物一般难以穷尽,并始终将伴随叙事的展开而处于不断叠加、蔓延、重构的动态进程之中。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推动下,后经典叙事学家才会义无反顾地相信,任何深度模式的确定、任何“惟一典范”的树立都将阻断文本各细微部分微妙交织所产生的意义的无限可能,而只有当刻板、凝滞的“大叙事”被拆解为复数的,更加开放、灵活、更具活力的“小叙事”时,过去被“悬置”的意义的无穷魅力才能够在文本的缝隙间敞亮,裹挟在叙事话语之中的无限丰富的内涵也才可能得到源源不断的开掘与提炼。也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后经典叙事学才得以在精神向度上与“话语转向”中的文学研究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由此可见,无论就研究取向、视域还是就理论态度、方法而言,在后经典叙事学与文学的“话语研究”之间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契合之处,这样的契合也为后经典叙事学对“话语转向”背景下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推进与提升带来了充分的可能。
三
前文已经谈到,在“话语转向”背景下的文学研究中,语言性文本成为了承载各种权力、意识形态、利益关系等等的最基本的“载体”,它的意义和价值是任何人都无法轻易抹杀的。然而,必须承认,在越来越多的当代研究者眼中,“载体”的重要性却往往为更加显在而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所取代。如法国学者伊里加雷(Luce Irigaray)便针对当前文学研究中“文本”地位的相对失落而发出过这样的感慨:“我们发现,关于内容的争论几乎没有考虑到内容信息的‘载体’……科学持续不断地改进新的工具、新的机器(并且是以极其昂贵的代价),但在一切研究中,语言技巧、语言工具仍然很少得到研究。”[16](41)有学者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现今中国学术界总是沉迷于“意识形态”或“审美文化”之类的“理论热点”,而远未能将文本形式建构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最终也连带引发了所谓“超越形式直奔主题”的病态景观[17]。
同样,后经典叙事学的种种固有特质决定了其对于“外在背景”的热切关注。这种关注首先表现为它不再将作品视为相对封闭的自足有机体,而是将其进一步投入了作者-文本-读者的互动循环之中。早在经典叙事学阶段,理论家对“隐含作者”“理想读者”等概念的阐述其实已经隐隐体现出了一种突破封闭文本层面、将叙事置于动态过程之中的内在诉求③。在后经典叙事阶段,这种打破封闭状态的潜在诉求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人们更多聚焦于文学活动中作家与读者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协商”所带给叙事的深刻影响,而过去常常遭受无视的“读者”更是得到了尤为突出的强调。后经典叙事学积极介入对读者的研究,通过划分读者类型、归纳读者功能等方式,重新建构起叙事同读者之间曾经缺失的纽带。更进一步,后经典叙事学还将关注的重心延伸至整个历史、文化、精神层面。在马克·柯里眼中,“政治化”可被视作后现代状况下叙事学的一个主要标签:“从诗学到政治学的过渡亦可看成是解构主义的一大遗产。因为解构主义引进了揭示意识形态面目的新方法。”[11](6)虽然叙事的动因并不能一味归结为政治意识形态,但这样的表述的确也充分道出了后经典叙事学对于精神性向度的高度重视。也就是说,叙事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法问题,它由更加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所生成、所塑造、所牵制,而对于这种情境的不懈探寻也成为了后经典叙事学拓展其理论视域的关键所在。正因为如此,后经典叙事学才体现出了与“话语转向”异曲同工的理论旨归。
不过,在高度重视外部因素的同时,文本自身的组织构造却并未在文学研究中全然失落。“叙述可以采用几乎任何可以表意的工具。实际上凡是用一种符号手段再现一系列的事件,而这些事件的排列又是具有一定的‘可跟踪性’,这个符号意指过程就称为叙述。”[18](1)由此可见,叙事学就其原初状态而言就已经蕴含着超越语言文字的疆域而走向更具开放性的“后经典”状态的巨大潜能。然而,对于后经典叙事学而言,根植于语言文字的叙述性文本才是其最不可或缺的立足根基。原因很简单,首先,语言性文本是叙事学作为学科得以成立的最基本前提,也是其理论操演的最重要平台,因此,无论在“经典”还是“后经典”阶段,叙事学都不可能放弃对于文本的强调而一味地迎合与“叙事”不存在明确“同构性”的外在文化现象。第二,语言所具有的概括性、形象化以及强大表现力等特质决定了它始终在人类的思维与认识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因而,即使是后经典叙事学也不太可能脱离语言文字这一“基石”而进入漫无边际的领域。第三,最为关键的是,在后经典叙事学的理论框架内,文本各组成部分的微妙关联,如文本中层次、母题、情节、时空等等的巧妙安排,叙述者、视点、引语、人称等环节的复杂交织,以及诸形式因素之间的矛盾与张力等等,才是真正通往外在社会文化语境的值得信赖的渠道。后经典叙事学不再像传统叙事学一般拘泥于对文本内在结构的发掘或是对叙事话语的修辞性考量,而是将文本视为被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种种外界因素所浸染、所决定的对象,认为只有从语言文字本身出发,从文本自身所包含的含混、悖谬、乃至“空白”“失语”之处入手,才可能真正把握叙事性文本同外在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互动,才可能真正达成对叙事研究的延伸、演绎与开拓。如女性主义叙事学家苏珊·兰瑟(Susan S. Lanser)便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在她看来,“叙事负载着社会关系,因此它的含义远远不止那些讲故事应遵守的条条框框”[19](3)。由此出发,兰瑟主要对简·奥斯丁(Jane Austen)、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等若干女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加以解读,探究这些作品是怎样借助含蓄、迂回、曲折的叙事方式与修辞策略来建构女性的立场并发出女性的声音,从而真正将抽象的叙述形式与社会化的性别认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中国学者谭君强同样也作出过颇为有益的尝试。他强调指出,研究者绝不能把叙事局限于语言结构的狭隘领域,而应当主动将叙事理解为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动态的“编织”过程,并尽可能从一个更宏阔的社会、文化视域出发而对其加以观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创建“审美文化叙事学”(cultureaesthetical narratology)的理论构想,主张“将形式与语境,与历史、文化,与审美判断和审美价值意义等多方面要素连接起来”[20],从而为叙事研究的既有格局注入了新的活力。
注释:
① “范式”(paradigm)一词来源于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Samuel Kuhn)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相关论说,用以指涉科学共同体得以运作所必需遵守的最基本的学科规范。库恩认为,范式凝聚着某一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范例、符号、价值观以及形而上体系,从而对该共同体成员的思维与行动产生了强有力的凝聚作用。同时,范式也并非始终处于稳定不变的状态,它始终都可能伴随社会、文化情境的改变而发生大幅度的调整与变迁。范式概念在当前已经被人文研究者主动吸纳并普遍应用于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各学科领域中。参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② 稍加留心,便可观察到包含于上述几组对立项当中的“家族类似”式的同构之处,要言之,前者多半涉及未经修饰与渲染的叙事的“原始材料”,后者则大多意指叙事者在特定思想与价值观念的引导下,针对“原始材料”所作出的再度加工、整合与规划。
③ 当然,必须认识到,这些叙事范畴就根本而言都是理论家为了使叙事结构更加严整、充实、完满而概括出来的抽象类型,它们仍然未能真正跳脱语言性文本的层面而产生现实的指涉性。
[1] 周宪. 文学理论: 从语言到话语[J]. 文艺研究, 2008(11): 5-15.
[2] Philip Babcock Gove and the Merriam-Webster Editorial Staff.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Unabridged[M]. Springfield: G & Merriam Company, 1961.
[3] 托多罗夫. 巴赫金, 对话理论及其他[M]. 蒋子华, 张萍译,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4]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5] Emile Benveniste.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Coral Gables FL: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6]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M]. London: Routledge, 1989.
[7] 福柯. 文化的斜坡[C].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 严锋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8] 戴卫·赫尔曼. 新叙事学[M]. 马海良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9] 申丹, 王丽亚. 西方叙事学: 经典与后经典[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0] 杰拉德·普林斯. 叙述学词典[M]. 乔国强, 李孝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11] 马克·柯里. 后现代叙事理论[M]. 宁一中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2] 斯图尔特·霍尔. 导言[C]. 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 陆兴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3] 米歇尔·福柯. 必须保卫社会[M]. 钱瀚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14] 华莱士·马丁. 当代叙事学[M]. 伍晓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5] J. 希利斯·米勒. 解读叙事[M]. 申丹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16] 吕斯·伊里加雷. 三种风格[C]. 文学理论精粹读本. 傅其林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7] 赵宪章. 形式美学与文学形式研究[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2): 162-168.
[18] 赵毅衡.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19] 苏珊. S. 兰瑟, 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 黄必康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0] 谭君强, 陈芳. 叙事学的文化研究与审美文化研究[J]. 江西社会科学, 2009(4): 29-38.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and “discursive turn” in literary studies
LI Linli
(Art College, Southeast China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Discursive tur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formations in the movement from “modern” to“postmodern” in literary theory. Placing literature into the open and external dimension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to a certain extent, discursive turn overlooks the texture and structure of the text.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is a new disciplinary structure and knowledge system which emerged with the tendency of “discursive turn”. On the one hand,“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extends people’ horizons to the broader dimension of society and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it mostly focuses on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among elements of literary work, and provides a series of practical critical mode to researchers.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not only corrects the contemporary prejudice of neglecting the text itself, but also eases the tens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discours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theory. In conclusion,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unfolds sufficient space of development under the general background of“discursive turn”.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language; discourse;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 text structur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trans formation of culture
I02
A
1672-3104(2014)06-0260-06
[编辑: 胡兴华]
2014-04-25回日期:2014-10-1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视觉文化视域中的艺术生产理论”(13YJA760025)
李林俐(1988-),女,四川自贡人,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西方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