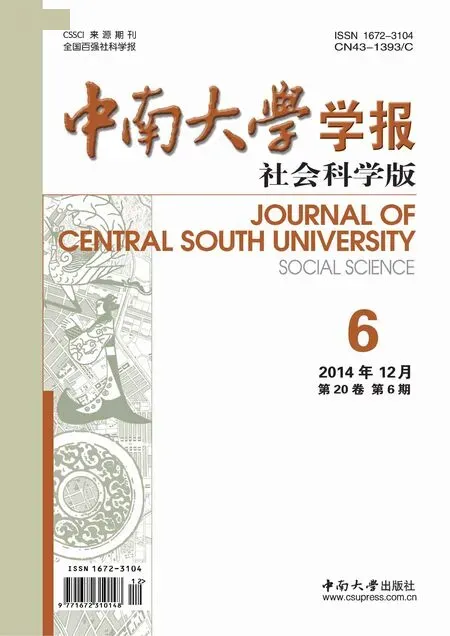鲁迅眼中的俄国诗人:形象学视野下的《摩罗诗力说》
俞航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鲁迅眼中的俄国诗人:形象学视野下的《摩罗诗力说》
俞航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描绘了一个以拜伦为宗的摩罗诗人谱系,提出了诗人的任务是“撄人心”的观点。俄国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是鲁迅刻画的两位作为“精神界战士”的摩罗诗人。作为注视者,鲁迅在建构诗人形象时根据自身的期待视野使用了新的参考系,以这一参考系评价了俄国诗人。同时,形象建构过程不仅是主体与客体的对话,也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产物。中国的特殊境遇使鲁迅在建构俄国诗人形象的过程中以中国的文化模式意识形态化了他者形象,其目的是通过宣扬摩罗诗歌的精神,改造国民性,改变弱国弱民的状况。
鲁迅;《摩罗诗力说》;俄国诗人形象;他者;社会集体想象物;国民性改造
《摩罗诗力说》写于1907年鲁迅留日期间。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谈到,当时他欲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筹办一个名为《新生》的杂志,来倡导文艺运动,目的是文学救国,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状态,唤起国人的精神觉悟。但后来因为人力物力的缺乏,杂志没办起来,鲁迅便把为杂志写的五篇论文投寄《河南》月刊,其中就有这篇《摩罗诗力说》。《摩罗诗力说》集中表现了鲁迅早年的文艺思想与美学观点。在该文中,鲁迅描绘了一个以拜伦为宗的摩罗诗人谱系,提出了诗人的任务是 “撄人心”的观点。在弃医从文,立志文学救国之后,鲁迅广泛涉猎了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同时十分关注日本以及西方文艺批评界的动向。通过阅读丹麦文艺批评家勃兰兑斯的著作,鲁迅接触到了研究各国的文学的新方法,即比较的方法①。在此基础上,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成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
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中,俄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虽然数量并不多,但是多为经典作品。鲁迅在这个时期的中俄文化交往活动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鲁迅对俄国文学的了解和把握都远远高出于同时代人之上。他不仅在‘中俄文字之交’的发端期就和周作人一起对俄国文学作了极为珍贵的译介,而且如他后来所说那样俄国文学成了他走上文学道路的重要外因。”[1](70)鲁迅在试图唤醒沉睡的中华民族的过程中开始文学创作,他的视野越出中华,“别求新声于异邦”。当他的目光触及俄国,他感到革命活动蓬勃兴起,思潮纷繁涌动的俄国如同年轻人,而其故土却如垂垂老者般静滞腐朽,缺乏新声,“惟文化已止之古民不然:发展既央,隳败随起,况久席古宗祖之光荣,尝首出周围之下国,暮气之作,每不自知,自用而愚,污如死海。其煌煌居历史之首,而终匿形于卷末者,殆以此欤?俄之无声,激响在焉。俄如孺子,而非喑人;俄如伏流,而非古井。”[2](13)《摩罗诗力说》开篇鲁迅就点明中华民族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但其发展却停顿了,需要由具有强大力量的摩罗诗人来唤醒。鲁迅将俄国诗人普希金与莱蒙托夫归于摩罗诗派。他们与拜伦一样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众,与拜伦一样是异邦的“新声”,是鲁迅热切期待的精神界战士。但是,根据两位诗人所处的特定社会和历史条件、独特民族性以及独特的内在秉性,鲁迅意识到他们与拜伦是不同的。他对两位俄国诗人与拜伦的不同给予了重视,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和评价。当鲁迅注视着这两位异邦诗人,并试图描绘这两位诗人时,他眼中的两位诗人形象实际上传递了鲁迅本人的意识,反映了鲁迅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北冈正子在《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中指出鲁迅的这篇文章是超出文学介绍与批评的,他的出发点是在人类精神的发展中求得救国救民的策略。
一、注视者的参考系:俄国诗人与拜伦
鲁迅对俄国诗人的想象是注视者的一种表意实践,想象和实践的主体是鲁迅。他者形象作为注视者欲望的投射对象,不可避免包含着注视者丰富的感情能量。俄国诗人形象所传递出的是鲁迅的意愿、观念和无意识,也反映了他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以及解决之道。正如巴柔指出的,“我想言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时,我却否认了他,而言说了自我。我也以某种方式同时说出了围绕着我的世界,我说出了‘目光’来自何处及对他者的判断:他者形象揭示出我的世界。”[3](124)因而,在讨论《摩罗诗力说》中的俄国诗人形象时,我们的关注点不应仅仅放在文本中的普希金、莱蒙托夫的形象是否忠实于历史上真实的二位俄国诗人,而应更多探寻构造俄国诗人形象的主体想象轴因素以及形象再造过程中差异所形成的原因。通过鲁迅对材料的取舍以及对俄国诗人的评判,我们可以看到注视者本人的期待视野、价值取向和情感判断。
形象建构过程中存在着主体与客体两条轴。在客体方面,是在场和缺席轴;在主体方面,则是迷恋和批判轴。在客体上,形象学研究摒弃了休谟所持的形象归诸于感知的观点,而是采纳了萨特的理论,即认为形象基本上是根据缺席的他者来构思的,是依据一定参考系的创造性想象。《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在建构俄国诗人形象的时候创建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参考系,这一参考系不是建立在真实的俄国诗人形象上,而是建立在注视者鲁迅的期待视野(the horizon of expectation)上②。鲁迅在阅读与俄国诗人相关的材料以及写作《摩罗诗力说》过程中,他的“期待视野”是寻找异邦摩罗般的诗人:他们充满激情,以诗歌向不合理的社会宣战。因而他在建构和评价俄国诗人时的参考系主要内容就是俄国诗人与摩罗诗派的关系。而当涉及到形象建构中的主体轴时,主体对客体的态度是迷恋还是批判将根据主体所创建的参考系。因此,当俄国诗人形象符合参考系时,鲁迅的态度是赞扬,当其偏离了参考系,鲁迅则持批判的态度。
根据鲁迅建构的参考系,即普希金与摩罗诗派的代表人物拜伦的关系,他着重指明普希金与其所处的沙皇俄国这一环境的不容,因此被贬黜南方(拜伦同样与环境不容,离开故土)。在贬黜期间普希金接触到拜伦的作品,相似的遭遇相似的观点使普希金创作了与拜伦诗歌风格相似的诗篇:
普式庚(A.Pushkin)以千七百九十九年生于墨斯科,幼即为诗,初建罗曼宗于其文界,名以大扬。顾其时俄多内讧,时势方亟,而普式庚多讽喻,人即借而挤之,将流鲜卑,有数耆宿力为之辩,始获免,谪居南方。其时始读裴伦;尤著者有《高加索累囚行》,至与《哈洛尔特游草》相类[2](118)。
鲁迅十分赞赏普希金对当时沙皇统治的讽刺,因为这一点与拜伦反抗英国上层社会的腐朽是类似的。例如在分析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时,鲁迅说主人公“力抗社会”。事实上,在这节选文的原作中只是说主人公叶甫盖尼·奥涅金对社会厌恶,对人生失望,而“力抗社会”是鲁迅自己的理解。在这里,鲁迅显然是通过加强力度来点明普希金与拜伦之间的继承关系,以使普希金的形象更符合鲁迅的参考系。
从这一改造我们可以看到,在建构俄国诗人形象时,客体轴并不是复制鲁迅对真实俄国诗人的感知,而是创造性地使用了新的参考系,以在场的成分置换了缺席的原型。普希金所处的时代正是俄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大范围接触对话的时期,诗人本人确实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包括莎士比亚、卢梭、拜伦等。因而,普希金的诗作有一部分深受西方思想以及拜伦的影响。然而,正如八衫贞利所认识到的,“普希金接近拜伦不过是因为拜伦投合普希金为暂时出现的外界事物的乌云所蒙蔽的意向,拜伦主义毕竟是西欧的东西,与普希金的民族天性不相容。”[4](84)因此,普希金是不可能成为拜伦的翻版的,很快他就显示出了自己的独特性。鲁迅同样认识到普希金后来渐离拜伦,并分析了原因:一方面是普希金个人与拜伦性格不同,另一方面则是西欧思想与俄国思想的不同,更进一步说,是俄罗斯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性。如鲁迅在介绍《高加索囚徒》等模仿拜伦的作品时指出:“二者为诗,虽有裴伦之色,然又至殊,凡厥中勇士,等是见放于人群,顾复不离亚历山大时俄国社会之一质分,易于失望,速于兴奋,有厌世之风,而其志不固。”[2](119)同样的,鲁迅在介绍普希金最出色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主人公与拜伦诗歌中主人公的不同:“厥后外缘转变,诗人之性格亦移,于是渐离裴伦,所作日趣于独立。”[2](119)从这些例子可见鲁迅十分清楚普希金脱离拜伦的内外原因。
分析了原因后,鲁迅根据自己的参考系给出了评价。这里涉及到形象学的第二条轴——主体迷恋与批判轴。当俄国诗人形象符合参考系时,鲁迅的态度是赞扬,而当其偏离了参考系,鲁迅则持批判的态度。从鲁迅偏否定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否符合拜伦为鼻祖的摩罗诗派是评价俄国诗人的标准:“特就普希庚个人论之,则其对于裴伦,仅摹外状,迨放浪之生涯毕,乃骤返其本然……故旋墨斯科后,立言益务和平,凡是与社会发生冲突者,咸力避而不答道,且多赞颂,美其国武功。”[2](120)鲁迅指责普希金仅仅是描摹拜伦的外在,当诗人回到莫斯科沙皇的管辖范围时,便脱离拜伦返回到自己的本性状态了。这里的“本然”即意指俄国诗人形象的原型。因为普希金的“本然”状态不符合摩罗诗人,因此在主体轴上,鲁迅对普希金的评价是偏否定的。
鲁迅对另一位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评价比对普希金的高③,而原因正是莱蒙托夫更符合鲁迅的参考系,即更接近拜伦。从对莱蒙托夫的介绍开始,鲁迅就点出莱蒙托夫有英格兰血统,“其先来尔孟斯(T.Learmont)氏,英之苏格兰人;故每有不平,辄云将去此冰雪警吏之地,归其故乡。”[2](120)也就是说莱蒙托夫每当在俄国遇到不平事,常常说要离开俄罗斯这片冰天雪地和警察统治的国土,回到他的精神故乡苏格兰去。他的目光常常远眺异邦,他祖先生息的西方是他想象中的自由之邦。1830年,年仅16岁的莱蒙托夫写了题为《奥西昂的坟墓》的诗歌,在诗中,他凭吊了传说中的苏格兰诗人奥西昂,并表示想在苏格兰重新开始自己的一生。
对莱蒙托夫形象的建构同样在鲁迅的参考系内进行,不同于描绘普希金时着重点在普希金如何脱离拜伦的影响,在描绘莱蒙托夫时,鲁迅的重点则放在莱蒙托夫如何在拜伦、雪莱的影响下开始自己的创作旅途。
及为禁军骑兵小校,始仿裴伦诗纪东方事,且至慕裴伦为人。其自记有曰,今吾读《世胄裴伦传》,知其生涯有同我者;而此偶然之同,乃大惊我。又曰,裴伦更有同我者一事,即尝在苏格兰,有媪谓裴伦母,此儿必成伟人,且当再娶。而在高加索,亦有媪告吾大母,言与此同,纵不幸如裴伦,吾亦愿如其说。顾来孟多夫为人,又近修黎。修黎所作《解放之普洛美迢》,感之甚力,于人生善恶竞争诸问,至为不宁,而诗则不仿[2](121)。
鲁迅指出莱蒙托夫在许多方面都与拜伦十分相似,例如自信方面,他像拜伦一样,认为“吾之良友,仅有一人,即是自己”。莱蒙托夫以自己的人生展现了拜伦笔下那些孤高决绝的拜伦式英雄,傲然独立于浑浊的世界。鲁迅认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虽然同样受了拜伦的影响,属于拜伦诗派的摩罗诗人,但是又各有区别。在这点上他同意勃兰兑斯的观点:“前此二人之于裴伦,同汲其流,而复殊别。普式庚在厌世主义之外形,来尔孟多夫则直在消极之观念。故普式庚终服帝力,入于平和,而来尔孟多夫则奋战力拒,不稍退转。”[2](120)普希金与拜伦相似处在厌世的外在,而莱蒙托夫则在纯然的消极的观念,因此最终普希金回归对帝王的驯顺,而莱蒙托夫则从未屈服。莱蒙托夫与普希金在接受拜伦主义的情况上是不同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接受主体的差异。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两者相较,莱蒙托夫诗中对生活不合理面的挑战,对时事的不屑以及弥漫在诗歌中的孤独、绝望、坚毅都较普希金深重,这些部分来源于被普希金忽略的拜伦的一些特征。对普希金而言,拜伦是他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一个源头,拜伦的影响主要在诗人蛰居南方时发挥作用,而莱蒙托夫短暂的一生所写的桀骜孤独的诗篇都有拜伦创作的影子。拜伦的理想给他激励,在他短暂而波澜壮阔的一生中,为了这种理想,他写下了无数动人的诗篇,他斗争、受挫折,入囹圄,甚至献出了生命。
作为鲁迅自我意识的他者形象,普希金与莱蒙托夫所起的作用就是与鲁迅期待视野中的新人对照与对比,从而为确立“精神界战士”发挥作用。根据这一期待视野,鲁迅在创建俄国诗人形象时在客体轴上使用了自己的参考系,而主体轴上的评价也是依据是否符合这一参考系来进行的。
二、意识形态整合功能:“兽爱”或真正的爱国
形象学研究是一种总体研究,即将文学文本放入文化大背景中,分析文本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语境。一个作家对异国现实的感知是以其所隶属的群体或社会的观念即社会集体想象物为媒介的。写作《摩罗诗力说》的前后,鲁迅看到了祖国正在经历的一切。对故土命运的担忧使鲁迅在描述俄国诗人形象时将俄国与中国进行比较,他感到中国的状况与曾经的沙皇俄国是相似的,同样处在黑暗之中。以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里为代表的俄国文学有着与鲁迅的创作相似的宗旨,即批判现存社会的不合理,思考应该建立怎样的社会。鲁迅建构的俄国诗人形象所发挥的符号功能,不仅表现了文本内部的关系序列,而且是文学形象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互动的结果。鲁迅对俄国诗人形象的建构是一个处在华夏文化中的注视者对他者文化的想象,这一过程贯穿着两种文化的对话。我们可以在《摩罗诗力说》这一文本中进一步看到中俄两国文化之间的对话。在这一过程中,对话精神是两种文化在注视者视野中融合的基本原则,引导并规范着以想象方式建构形象。俄罗斯诗人形象是一种他者镜像,想象俄罗斯诗人就是在观念领域与俄罗斯相遇,俄罗斯诗人形象作为一个对话者与华夏文化互动。
《摩罗诗力说》中中俄文化对话可以从鲁迅对俄国诗人的“爱国”情怀的评价中显示出来。在俄国历史上,普希金与沙皇的关系是异常复杂的,诗人曾写过许多与沙皇相关的作品。尤其是《青铜骑士》中对彼得大帝的分析,很能体现诗人对沙皇的态度。别林斯基认为,《青铜骑士》表达了普希金对作为历史理性象征的彼得大帝的赞颂。早年的普希金受西欧文化的影响,崇拜单枪匹马与整个社会做斗争的拜伦式英雄,但在写作《青铜骑士》时,诗人已经认为未来的真正创造者应该是代表“历史的创造精神”的英雄,而彼得大帝正是这样的英雄。彼得大帝的形象寄予了普希金对当时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一种期望。在长诗里,普希金表现了某种群体主义意识,即认为个人因素如果阻碍社会因素,应该被后者从道路上清除掉。卢那察尔斯基说普希金“完全确定专制政权是一个现实。同时,由最积极的君权代表彼得的形象体现出来的专制政权,又被描写成一项有组织能力的因素,根据远大的计划行动的因素——从这个观点看,即是一项对社会很有利的因素”[5](75)。《青铜骑士》的作者普希金已经离拜伦式的个人主义英雄很远了。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民族性的两面:“俄罗斯人是无限自由的、精神幽远的国家,是漫游者、流浪汉和探索者的国家,是自发的狂乱和恐怖的国家,是不需要形式的狄俄尼索斯名族精神的国家。接下来就是那个反命题,俄罗斯是一个骇人听闻的甘受奴役、驯顺服从的国家,是失去了对个体权利的知觉和不会维护个人尊严的国家,是怠惰的保守主义的、宗教生活为政府奴役的国家,是古板的生活和沉重的肉体的国家。”[6](14)普希金是伟大的诗人但同时也是个俄国人,他身上自然也具有这种俄罗斯民族的双重性。
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源自于一个宽泛且复杂的总体,即社会整体想象物,并在文学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社会整体想象物是“全社会对一个集体、一个社会文化整体所做的阐释,是双级性(同一性/相异性)的阐释。它显然部分地与事件、政治、社会意义上的历史相联”[7](24)。鲁迅笔下的普希金虽然处于俄国文化和俄国19世纪初期的历史背景中,但普希金与沙皇的复杂关系体现出的俄国文化的复杂性被鲁迅对本国的国民性的探讨所取代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集体想象物是如何影响到鲁迅对俄国诗人形象的塑造与评价的。针对普希金在俄国入侵波兰之后所写的维护沙皇的诗歌,鲁迅转引了勃兰兑斯的批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连类比照。俄国入侵波兰后,普希金为应对西方的“诘难”写下了《给俄国谗谤者》和《波罗及诺纪念日》这两首诗支持沙皇,对此鲁迅持批判态度。在鲁迅看来,借用勃兰兑斯的观点即是:“虽云爱国,顾为兽爱。”[2](120)也就是说普希金的爱国并不是真正的爱国,而是“兽爱”。随后鲁迅将注意力转向本国:“特此亦不仅普式庚为然,即今之君子,日日言爱国者,于国有诚为人爱而不坠于兽爱者,亦仅见也。”[2](120)这里的“今之君子”指鲁迅本国的一些人。鲁迅认为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每天喊着爱国,但这种爱国不坠入兽爱的十分稀少,而兽爱并不是真正的爱国。在这里鲁迅有感于本国国民性中的“奴性”,使用勃兰兑斯的“兽爱”一词揭露这种“奴性”。鲁迅对祖国衰弱的现状,国人麻木的精神状态深感沉痛,在塑造普希金形象时,他笔下的诗人形象已经走出“小”文本,进入包含历史、文化以及社会语境的集体想象物这一“大”文本。
分析鲁迅眼中的俄国诗人形象不应仅局限于文本内部,而应该“将文学形象主要视为一个幻影,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乌托邦迹象,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象的再现,通过这种再现,创作了它(或赞同、宣传它)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说明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意识形态和文化空间”[7](24)。这里的意识形态指一种整合功能,即注视者按照本社会的模式,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建的他者形象,宗旨在通过改造他者,强化自我。鲁迅关注俄国社会与俄国文学是出于他对自己祖国现状的担忧,因此他更多地以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意识形态重构了俄国诗人形象的社会历史背景,通过这种改造,强化了他改变祖国弱国弱民现状的呼吁。“当时中俄双方的往来是如此之少,中国知识界精英对俄国也是知之甚微,几乎很少有几个中国人去过苏联, 那么他们就会对中国知识分子会如此迅速地对俄苏文学产生兴趣而感到惊讶。产生这种兴趣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同情, 随后是共产主义思想对中国文化界的强大影响。然而更重要的理由是那些正在寻找中国新出路的知识分子认为, 沙皇俄国的状况与中国当时的状况相似,于是他们就把俄国古典文学的民主和人道精神当作学习的楷模。”[8]这种认同感使鲁迅用本国文化的视域和本国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了普希金的形象,同时通过批判普希金自身的矛盾性表达了对本国国民性中奴性以及保守、停滞、愚昧等劣根性的批判。“在这时鲁迅的思想中,具有‘心声’的人——《摩罗诗力说》所追求的就是这个——是同‘奴子性’‘奴隶’‘兽性爱国者’对称的。”[4](85)
鲁迅建构普希金形象时受到社会集体想象物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的影响,还体现在他对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与普希金的比较中。普希金与密茨凯维支曾有过文学交游活动,二人均根据圣彼得堡的青铜骑士作了诗歌。鲁迅更倾向密茨凯维支,认为他一直保持对黑暗现实的反抗。鲁迅引用的材料来自勃兰兑斯,但却与之分析的角度不同。勃兰兑斯把两位诗人作为虽然有共同之处但仍然走不同道路的同一时代两种精神的对比来描述的,即被异民族统治的人的直接抵抗和被本民族强权压迫的人的曲折抵抗对比。而在《摩罗诗力说》中却看不到勃兰兑斯这方面的对比⑤,鲁迅的评判标准主要是是否遵循拜伦诗派,价值判断是很明显的。“这种偏向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岂不都是从鲁迅作为清朝统治下异民族一员的自觉产生的结果吗?”[4](150)
鲁迅对普希金赞同沙皇对外战争颇多批评,因为在鲁迅看来普希金这是在宣扬强权的压迫,即帝国意识。埃娃·汤普逊在《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中对这种帝国意识进行了分析⑥。她指出,普希金的高加索叙事为俄罗斯帝国意识的建构提供了充分的话语资源,促成俄罗斯帝国神话的形成。“从早期诗歌《高加索俘虏》到成熟的《1829年远征前往阿尔兹卢姆旅行记》,普希金动手创造了一个无声的、智力不足的高加索,在毫无疑义的战争中有勇无谋,正好该受俄国治理。”[9](71)她的分析与鲁迅对普希金的批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虽然鲁迅不可能用后殖民的眼光去审视普希金作品中的帝国意识,但是中国半殖民的现实情况使鲁迅在普希金与莱蒙托夫之间更倾向于莱蒙托夫⑦。莱蒙托夫比普希金更孤傲,而且他离沙皇的距离比普希金远。鲁迅指出莱蒙托夫与普希金的爱国情怀的不同处:“来尔孟多夫亦甚爱国,顾绝异普式庚,不以武力若何,形其伟大。凡所眷爱,乃在乡村大野,及村人之生活;且推其爱而及高加索土人。此土人者,以自由故,力敌俄国者也;来尔孟多夫虽自从军,两与其役,然终爱之,所作《伊思迈尔培》一篇,即纪其事。”[2](189)鲁迅在这里赞扬莱蒙托夫的爱国是真正的爱国,即爱平民而非沙皇统治的官僚体制。同时,莱蒙托夫对为自由而与俄国作战的高加索土著民族也怀着深深的敬意。莱蒙托夫对高加索人的敬爱以及对他们的帮助,非常贴近于拜伦对受奴役的希腊民族的感情。
社会集体想象物代表了异国形象的历史层面,是整个形象在社会、历史、心理层面的深化。形象建构过程不仅仅是建构主体/注视者与客体的对话,同时也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鲁迅所处年代中国的特殊境遇使他在建构俄国诗人形象时,以属于自己文化的模式意识形态化了他者形象,其目的依然是通过宣扬摩罗诗的精神,改造国民性,改变弱国弱民的状况。
三、结语
鲁迅写《摩罗诗力说》的目的性很明确,即通过介绍摩罗诗派来唤起本民族的国民精神。他看到了祖国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当时却趋于颓败,感慨道:“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沉思而已夫!”[2](189)因而他对两位俄国诗人普希金与莱蒙托夫形象的接受与塑造一定受制于他写作此文的目的。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接受程序重组的。注视者的想象使他者的形象产生一定的偏离,因为在场成分在形象塑造过程中置换了一个缺席的原型,注视者一方以自我的文化观念模式对他者的历史文化现实进行变异。注视者显然会更关注他者身上具备某些因素,而忽略了另一些。因此,我们在考察文本中的异国形象时,不应该仅仅关注一个形象与“被注视者”相比的忠实程度问题。形象学研究的重心应该在形象制作主体即注视者一方,重视制作主体对他者的创造性阅读和接受,并探讨这其中的原因。在开眼望世界的过程中,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是一篇颇具典型意义的比较文学文本。我们考察文本中的普希金与莱蒙托夫的形象,从鲁迅对材料的取舍与创造性“误读”中,我们看到急切寻找精神界战士的鲁迅在摩罗诗人身上的关注点:反叛的普罗米修斯般的热情,对社会的辛辣讽刺,对自由的热爱,对奴役的仇恨等。因而,普希金与莱蒙托夫这两位俄国诗人的形象揭示出鲁迅的视域以及他对国人的期待。
注释:
① 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孤独的丹麦人:格奥尔格·布兰代斯”中指出,布兰代斯的六卷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是一部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德英三国文学的比较史著。参见杨自伍译《近代文学批评史》第4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415页。
② “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的重要概念。在海德格尔的 “先在结构”与伽达默尔的“成见”理论的基础上,接受美学理论家姚斯提出了“期待视野”的概念。姚斯认为读者的想象和体验是作品意义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读者使作品产生构造性意义(configurative meaning)的来源就是读者的期待视野。期待视野存在于阅读之前,是接受者头脑中已经存在的审美标准与取舍标准。一旦进入阅读,接受者的期待视野就与作者在作品中提供的未定点发生相互作用。而在形象创造的过程中,注视者由人生经验和审美经验形成的期待视野构成了一种特定的心理结构图式,对构建形象的种种材料进行取舍、改造和创造。
③ 鲁迅描绘莱蒙托夫所引用的材料来源主要是克鲁泡特金的《俄国文学理想与现实》,辅之以日本学者升曙梦的《莱蒙托夫之遗墨》和《莱蒙托夫》。
④ 与鲁迅相比,材料来源《师宗普希金》的作者八衫贞利则是在政治力量消长的过程中理解普希金与沙皇的关系。
⑤ 试比较勃兰兑斯中对普希金与密茨凯维支二者的叙述:“对普希金来说,做一个民族的诗人意味着和统治当局和解,同时和对自由以及对欧洲未来的信念决裂;而密茨凯维支只是在割断同俄国当局的一切瓜葛,表现出一种同普希金的日甚一日的志得意满形成鲜明对照的的乐观的热忱,才成为民族诗人。……普希金是俄国的,恰如密茨凯维支是波兰的。但是正如米西勒在一个地方说过,当时俄国还不成其为一个国家,只是一个行政当局加上一根皮鞭。……然而就在俄国是一个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时候,波兰的命运倒比较好一些,它是一个国家,只是没有政府。”参见《十九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第60页。北冈正子评论到:“在这里,勃兰兑斯未必不理解普希金的苦衷,片面地肯定密茨凯维支的明快。”第150页。
⑥ 这本专著从后殖民的角度对俄国文学所制造的文化霸权对俄国的非俄罗斯族的涂抹与勾销进行了分析和揭露。
⑦ 鲁迅在日本期间,原来准备翻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后来他建议冯至翻译这部作品。他对莱蒙托夫的特殊感情由此可见。鲁迅小说中的愤世者形象,来自尼采,来自拜伦,与莱蒙托夫也有关系。参见陈元垲《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解读〈摩罗诗力说〉》,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6月,第22页。
[1] 陈建华. 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2] 赵瑞蕻. 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M].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3]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 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M].孟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4] [日]北冈正子. 摩罗诗力说材源考[M]. 何乃英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
[5] 自刘亚丁.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9.
[6] [俄]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的命运[M]. 汪剑钊译, 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7] [法]让-马克·莫哈. 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M].孟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8] 雷纳特·兰德伯格. 鲁迅与俄国文学[J]. 王家平, 穆小琳译,《鲁迅研究月刊》, 1993(9): 33-43.
[9] 埃娃·汤普逊. 帝国意识: 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M]. 杨德友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Russian poets in Lu Xun’s eyes: “on the power of satanical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ology
YU Hang
(Department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In “On the Power of Satanical poetry”, Lu Xun described a system of satanical poets which treats Byron as the ancestor, and insisted the point that the mission of a poet is to inspire people’s heart. Russian poets Pushkin and Lermontov are satanical poets whom he described as the “spiritual warrior”. As a watcher, Lu Xun used a new reference system based on his horizon of expectation when he constructed the image of Russian poets, and evaluated them based on this new reference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the image construction process is not only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but also the dialogue between two cultures, which is the production of the social collective imagination.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of China made Lu Xun employ ideology of Chinese mode to reconstruct the Russian poet images, of which the purpose is to spread the Satan spirit of poetry to reform the weak national characters and change the weak situation.
Lu Xun; “On the Power of Satanical poetry”; the image of Russian poets; other people; the social collective imagination; reform national characters
I106.6
A
1672-3104(2014)06-0242-06
[编辑: 胡兴华]
2014-08-20;
2014-10-23
俞航(1987-),女,浙江绍兴人,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