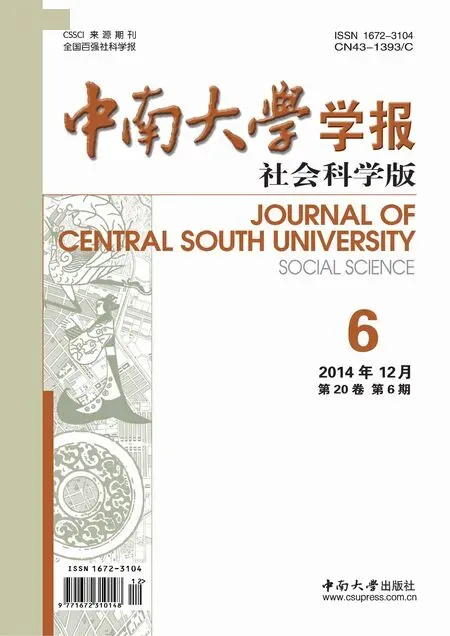拟话本小说冥游故事的仪式解读
杨宗红,曾秀芳
(贺州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广西贺州,542899;贵州财经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贵州贵阳,550004)
拟话本小说冥游故事的仪式解读
杨宗红,曾秀芳
(贺州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广西贺州,542899;贵州财经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贵州贵阳,550004)
话本小说的形式结构类似于僧讲、俗讲仪式。小说中众多冥游故事,显示了冥游者从一种境况到另一种境况的转变,冥游成为冥游者成长过程的通过仪式。对冥游者的经历及冥游场景的描写,揭示了边缘人物作为“替罪羊”的必然性以及考验仪式对部分冥游者的必要性,冥府的恐怖也成为伸张正义的仪式象征。冥游不仅具有仪式功能,也具有文学功能,它实现了虚与实的交融,叙事时空的转换,巧合与必然的联系,实现了娱乐与恐惧情感的无缝结合,将庄严与狂欢融为一体。
拟话本;冥游;仪式;文学性;虚实交融;时空转换
白话小说的产生与佛教的僧讲与俗讲相关。无论僧讲还是俗讲仪式,先来一个押座文以导引正题、收摄心神,再说主要故事,最后收场。佛教的传道仪式直接影响了说话技艺。说书场的说书过程,近似于仪式过程:开场白——说话——收场。演变到拟话本小说,则有入场诗——头回——正话——结尾,这种结构正是书场说话仪式的复现。拟话本小说仪式化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空间场景的仪式化,说书过程与内容构成的仪式化,部分情节的仪式化(如冥游、审判等)。杨义先生论及话本小说的仪式性时指出,话本小说的葫芦格体制,是“把说书场上的程式转化和提升为文学祭坛上的特种仪式”[1](228)。
《说文》曰:“冥,幽也。”《太玄·玄文》云:“冥者,明之藏也。”广义的冥游故事,是指人的魂魄进入幽暗晦明之地,如地府、地下仙境或各种洞窟。冥游故事,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常见的叙事母题,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类是假死,灵魂暂时脱离肉体,到冥界游历;二是睡梦中因为某种原因,灵魂暂时到冥界游历。二者在本质上无差别,只不过前者在他人眼中是暂时性死亡而已。弗莱指出,“从原型方面而言,仪式和梦幻分别成了文学的叙事内容和意义内容。对一部小说或一出戏剧的情节进行原型分析时,都要按照与仪式相似的归类、复现或定型程式的活动。”[2](150)拟话本小说中,存在诸多冥游叙事。这些冥游对作者、作品的主人公或其它而言,仍具有仪式意义。
虽然拟话本小说冥游叙事的“仪式性”特征尤为明显,但学界研究的重点却在文言小说,焦点是冥界观念的演变、冥游故事的类型及特征、与佛道二教的关联等①。有鉴于此,笔者拟从仪式角度出发探究明清之际的拟话本小说的游冥故事,窥见它所蕴含的民族心理与时代内涵。
一、冥游与人生通过仪式
德国民俗学家范·根纳普在《通过仪式》中将从一种境地到另一种境地或者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换的仪式统称为通过仪式。仪式的通过者,往往是边缘化人物。所谓边缘化,是指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生存状态等在社会上处于非主流的、非核心的地位。未经“通过仪式”前,主人公是边缘化的人物,处于一种特殊的阶段,既不属于原有的群体,也不属于新的群体。拟话本小说中冥游的人物,有贫寒的儒家知识分子,也有富庶的市井民众;有后来仕途得意者,也有终身贫贱者;有道德楷模,也有奸诈令人厌恶者。以周必大、罗隐为代表(《西湖二集》第二十四、十五卷)的久经儒学浸染的读书人,他们笃信儒家之道,怀抱救世之志,力求通过修齐治平实现个体价值。然而,社会的腐败、科举的黑暗,他们被一再排除在社会政治中心之外,由此带来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加重了他们的边缘身份。周必大五十岁才中进士,所授官职也不过是“临安府和剂局门官”,未到一年即被削职,只好投奔岳父;罗隐才高八斗却贫困潦倒,甚至借贷无门;司马貌八岁纵笔成文,到五十岁还空负一腔才学不得出身;胡母迪“一气走了十科都不中”,只好隐居读书治圃(《喻世明言》第三十一、三十二卷);薛伟虽然中第授官,看似可以在儒道中立命安身,但“谪仙”的根基使其不仙不凡、亦仙亦凡(《醒世恒言》第二十六卷)。陈祈与屈突仲任二人,一人嗜财一人嗜杀,都非主流道德世界所能接受的人物(《二刻拍案惊奇》第十六卷、《初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七卷);杜子春在道德上无多大缺陷,但“万万贯家资,千千顷田地”使其异于平常世界,挥金如土、肆意散漫的性格也使其别于主流世界的勤俭持家的要求(《醒世恒言》第三十七卷)。
从群体边缘进入群体内部,必须经历相应的通过仪式。通过仪式分为分离、阈限(边缘)和聚合三个阶段。分离阶段是与原阶段相脱离,阈限阶段是边缘阶段,聚合阶段是新身份的获得[3](95)。经历通过仪式,个体生命状态或身份发生改变。上述冥游者在冥游之后,转变极大:周必大原本的穷酸相上多了一部帝王须,原本坎坷的仕途也一下子顺到起来;罗隐却由帝王之相转为小鬼之相,失却帝王之命;司马貌、胡母迪由原来的怀疑天道、怨天尤人转变为相信天道,司马貌投胎转世为后来的宣皇帝司马懿,胡母迪则由此绝意仕进,安贫乐道,后成冥王;薛伟作为谪仙,却做起儒家事业,一番游历,重修仙道(他化鱼游历,除了不是冥府之外,整个过程与冥游类似,故仍以冥游视之);陈祈自冥游之后,害起严重的心痛病,又将平日欺心所占兄弟的田产平分给他们,还做起了法事,家计一日不如一日;屈突仲任冥游后,面色变得腊黄,不再吃牛肉,刺血写经劝人放生戒杀;杜子春作为扬州大户,散漫的都头,冥游之后,诚心向道,一意在神仙路上。
这些人冥游原因虽然各有不同,冥游的过程则有很多相似之处:经过冥游,与以前脱离,以新的姿态出现。对他们而言,冥游就是一种仪式,一种生命过程的通过仪式。冥游阶段,是冥游者通过仪式的阈限阶段。特纳认为,阈限是二元对立的。在阈限中,主体从原有的状态(正常的状态)中脱离,既是A,又是B,既不是A,也不是B,具有正反同体性[3](106)。以此考察冥游者的冥游,也是如此。如罗隐的冥游过程,是健康/疾病,英俊/丑陋交替。周必大冥游,兼具穷
/贵,无胡须/有胡须状态,胡母迪冥游是处于人/鬼、人/判官之间。倘是假死多日,则展现为生/死、人/鬼的二元性,陈祈、屈突仲任属于此类。入冥者入冥的几种情况说明,入冥本身对入冥者意义重大。通过入冥,入冥者呈现前后不同的情况:或由坏而好,或由好而坏(身体的、家境的)。当冥游完成,小说人物的身份或境况发生相应变化。
二、冥府赏罚:替罪羊、考验仪式与仪式展演
按照冥游者在冥游过程中的待遇不同,冥游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受赏罚型,二是见证地狱刑罚型,三是考验型。前两种包含着审判程序,断案场景及各种刑罚是重点,冥游场景中的断案过程及刑罚是人间断案或刑罚的模拟,是现实司法仪式的文学性再现。
仔细审视冥府中的受罚者,他们所犯之罪与其所受惩罚并不相应。受刑罚处罚者,只不过是社会危机时刻的替罪羊。
“危机”是替罪羊机制发生的背景条件。拟话本小说的冥游叙事,往往是社会危机聚集之时。灵帝卖官鬻爵非常严重,致使众多人空负一腔才学,不得出身,屈埋于众人之中,于是有了司马貌的冥游;《游酆都胡母迪吟诗》中所交代的奸臣专权,忠义之士不得善终,正是元顺帝时的写照;屈突仲任纵情好色,荒饮博戏,亦不过是晚明社会纵情声色的形象再现;罗隐生于唐朝末年,正是社会混乱不堪之时;富民贪奸不义,“阳世全凭一张纸,是非颠倒多因此”,“富家容易受天恩”,诚信友爱等伦理道德皆被金钱践踏,陈祈诅咒、冥游才会实现。法国人类学家勒内·吉拉尔指出,人们在选择替罪羊时,通常选择那些极端者:极端富裕和极端贫穷,极端成功和极端失败,极端漂亮和极端丑陋,极端恶习和极端德行,极能诱惑人或极令人讨厌,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者的弱小和强者的极端强大都是众矢之的[4](23)。冥游者多为边缘人物,他们或极富有,或极为贫困,或极有道德,或极为贪酷,这些都成为选取“替罪羊”的条件。替罪羊既是无辜的,又是有罪的。“当说他无辜时,是指他所遭受的不幸大大超过他的所作所为应得的报应,就像登山运动员一声喊叫竟引起一场雪崩一样。说他有罪,是指他是一个罪恶社会的成员;或者说,在他所生活的世界中,类似的不公正构成了生存的无法回避的一部分。”[2](60-61)罗隐早年丧父,守着母亲过活。“生性轻薄,看人不在眼里。一味好嘲笑人,或是俚语,或是歌谣,高声朗诵,再也不怕人嗔怪。”借贷连吃闭门羹,冥游地狱,受剔骨之痛,堂堂相貌变为小鬼一般,其理由是吃闭门羹时不该有不良之念。冥王说道:“汝怎生便生好杀之心,辄起不良之念,……上帝好生,汝性好杀。明日做了帝王,残虐刻剥,伤天地之和气,损下界之生灵,为害不浅。”罗隐地狱遭受的刑罚,是替历代贪杀帝王将相受罪。小说家以罗隐作为替罪羊,力图净化统治者,重建社会秩序。陈祈狠心不守分,设计侵占三个兄弟财产,冥游后却得了心疾,“一痛发便待死去”,终身不愈。承受社会之罪,他人之罪最为严重者,是与陈祈有过节的毛烈和屈突仲任的仆人莫贺咄。此二人并非是小说的主要人物,却是冥游过程所见的受罪者。毛烈“平日贪奸不义,一味欺心,设谋诈害。凡是人家有良田美宅,百计设法,直到得上手才住。挣得泊天也似人家,心里不曾有一毫止足。看见人家略有些小衅隙,便在里头挑唆,于中取利,没便宜不做事。”被陈祈告阴状后,毛烈立丧性命,还在地狱受苦。莫贺咄只是一个听命于主人的仆人,但因协助主人杀害生灵,在冥府受尽诸苦,一一偿命。当现有各种社会秩序遭受破坏,必须寻找一个替罪羊代替群体受罚,洗除群体罪孽。选择替罪羊时“不是罪状起首要作用,而是受害者属于特别易受迫害的种族”[4](21)。无论冥府的受罪者是否是冥游者本人(或者小说的主人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替罪羊”转移了民众的注意,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民众潜藏在心底的对该群体的仇视,恢复了他们对该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希望。
在个体成长或群体成长过程中,从世俗世界进入神圣世界,考验必不可少。考验的内容,因目的与个体情况而异。拟话本小说中的冥游故事体现的考验仪式有两种:一是受难考验,通过设置磨难,考察冥游者的道心,或使之悟道,道教色彩较浓;二是解难考验,以种种难题考察冥游者解决问题的能力。杜子春与薛伟都与道教关系密切,而又与尘世纠葛不清。经过冥游,杜子春经历了自己、妻子、儿子生命的威胁时经受的肉体之痛及灵魂折磨,经历了个体生命、爱情、亲情的考验。冥游的种种幻象象征着喜怒哀憎恶欲,其间的成功与失败也就暗示对它们的征服与妥协。杜子春在考验仪式最后关头失败了,但这种冥游的经历促使他日后进一步修行。薛伟本是谪仙下凡,但仕途得意让他迷失自己。在冥游中,见识人情冷暖,几经生命的不自由,尤其是生死由他人掌控的事实,促使他重新体认道教成仙信仰。由儒而道,冥游游历是重要转折点。司马貌的冥游属于第二类考验型。司马貌乃后世的司马懿,由一读书人而为一代开国之帝,与原始民族甄选部落首领类似,他必须经受某些考验。司马貌冥游,六个时辰断三百五十余年未曾断结的案,窥见他经天纬地的政治才干。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罗隐、周必大、胡母迪、陈祈、屈突仲任等冥游过程中经历或见证的种类繁多而且极为残酷的刑罚;罗隐进入冥府后,作者以赋的手法写其所见场景,既有对冥府各级官员及其职能的介绍,也有犯法者在地狱所受的各种刑罚,“当殿中坐着一尊活神道,事事无差;丹墀下伏着许多横死鬼,缘缘有错。日游神,夜游神,时时刻刻来报正心邪心、善心恶心;速报司,转轮司,慌慌忙忙去推天道地道、人道鬼道。有记性的功曹、令史,一枝笔,一本簿,明明白白,注定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尽是孽来报往、报重孽深;没慈心的马面、牛头,两股叉,两条鞭,恶恶狠狠,照例或杀或剉或舂或磨,总之阳作阴受、阴施阳转。”周必大入冥,见到东岳帝君对他同榜进士赵正卿罪名的控诉,指责他妄尊自大、刻剥奸险、盗取朝廷名器、奸淫室女、破败寡妇等罪名,见其被抠双眼,劈破其腹,滚汤洗涤其肠,并被押入“无间地狱”受罪,兼追其三子,斩绝后嗣。胡母迪冥游地狱,见到“风雷之狱”“火车之狱”“金刚之狱”“溟冷之狱”“奸回之狱”“不忠内臣之狱”等各种酷刑。屈突仲任到冥府后,物类皆咆哮大怒,腾振蹴踏,欲吞噬他,最后食其生血深达三尺。陈祈亲眼见到冥府如何取证,如何断狱。从控诉到审判,再到受刑,从场景到举证到结案,整个过程几乎是人间司法程序的复制。
三、冥游:仪式的社会整合功能
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仪式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尤其是宗教仪式,“是纪律的基本形式”,“它有助于团体的整合”[5](257)。冥游过程是主人公主体的意识活动,表面上不具备仪式的互动功能与整合功能。但是,当冥游成为一种文学活动,主人公的冥游便成为一种公众活动,除了冥府中的各司其职的官员,现实中的人物也参与其中,如陈祈冥游,与之相关的毛烈与邱大、高公也进入到冥府中。至于读者,在冥府审判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是“旁听者”与“旁观者”,监督着冥府司法的公正性。
冥府刑罚中,“恐怖”是最基本的要素。在此,各种针对肉体的刑罚以及肉体遭受这些刑罚后的惨状,将犯罪观念与惩罚观念联系在一起,不仅对当事人,也对读者产生了有形的恐惧与无形的恐惧。按照福柯的观点,极端残暴的酷刑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它是一种仪式,也是一种经过精确计算的技术,通过为受刑者打上耻辱的标记或通过酷刑的场面,制造一种威慑力。酷刑是伸张正义的仪式,是一种正义的凯旋形式[6](35-38)。“在‘过分’的酷刑中,包含着一整套的权力经济学。”[6](38)在冥府的惩罚仪式中,冥游者的作用不可忽视。“在文学作品中,意识形态往往也是通过仪式或者仪式化的描写进行再生产的。”[7](66)冥法的公正无私及恐怖通过冥游者的经历或见证,变得“真实可信”。
更重要的是,仪式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在创造一种情感。仪式与艺术一样,“是想通过再现,通过创造或丰富所希望的实物或行动来说出、表现出强烈的内心感情或愿望”[8](79)。“仪式的意义在于通过隐喻或转喻来陈述心灵体验。”[9](135)冥府奖惩仪式作为现实司法的仪式模拟,不仅可以补充尘世司法的不足,也可借机抒发作者、读者、小说主人公心中的不平,在恐惧感中获得愉悦,在狂欢中重构庄严。话本小说的僧讲、俗讲的源头及作为书场仪式的文本,使其在表达仪式场景中主体的宗教或现实情感时尤为灵活。创作主体的情感或附在说话人身上,或附在主人公身上,或独立于二者之外,因时、事、人、景的不同而随时变化,而其教化人生、社会的旨趣未尝改变。
可以说,冥府刑罚是尘世刑罚仪式的真实展演,作者、冥游者与统治者一道,共同参与了社会秩序的重振。杨义阐释话本小说的仪式性时曾说道:“把入话故事作为说书场上等候听众的热场手段,对于书面文学已属多余,但参与话本的文人不是删节它,反而强化它、增补它,这就不能不令人设想,他们是想利用这种仪式激发“看官”的哲理思维。他们借助入话故事及其前置诗、后置诗证,引导读者建立某种心理定势,并通过与读者的议论对话,在把入话故事和正话故事进行正反顺逆多种方式的牵合中,引发人们对人间生存形态的联想和哲理反省。”[1](228)小说家要喻世、明世、醒世、型世,要借“奇”使人明、使人醒、使人悟,令顽石点头,使人拍案惊奇,便不自觉地借助话本小说本身所具有的仪式功能与冥府的场景、审判仪式、考验过程等所具有的仪式功能一起,通过模拟、隐喻与象征,重构社会秩序。
四、冥游:从仪式功能到文学功能
在小说中,冥游的功能不仅在于作为个体生命的通过仪式或群体的通过仪式确认社会秩序的意义,也在于冥游这一母题带来的文学审美。冥游实现了虚与实的交融,叙事时空的转换,巧合与必然的联系,实现了娱乐与恐惧情感的无缝结合,将庄严与狂欢融为一体。
尘世与冥府,一实一虚,一阳一阴,一明一暗,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前者属于此岸世界,后者属于彼岸世界。两个世界各有其道。冥府之有无,无人可见;冥府诸神及冥府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无人能证。作者先用大量笔墨写现实生活,交代故事的起因,也用部分笔墨,写冥游后的生活,交代故事的结局。冥游过程连接起因与结果,使前因后果之间承接自然。前有起因,虚的冥游就有了深切的现实基础;后有结果,冥游之虚有了现实之实。而且,冥游的场景是建构在冥游者的梦幻或昏迷情况下,在他者眼中是冥游者的梦幻与昏迷,而在冥游者却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的旅行。现实的睡眠和昏迷与意识领域中的虚与实,主人公的阳世存在与阴世旅游借助冥游融汇在一起。
虽然,冥游情节只是插入叙事,没有冥游描写,整篇小说依然完整。但是,没有冥游,小说人物前后的转换缺乏合理的解释。原本帝王之命的罗隐何以改貌又改命?周必大如何一夜之间就有了帝王须?愤懑不平的胡母迪为何平心下来,绝意仕进?仕途风顺的薛伟为何病后就朝向成仙之路前行?贪杀嗜肉的屈突仲任为何不再吃牛肉,不再杀生?陈祈如何突得心痛病?冥游拓展了叙事视野,将某些巧合变成必然,给情节发展以合理的解释。
冥府与尘世是两个不同的空间。冥游,将视野引入另类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有诸多异于此岸世界的人、事、景。冥府里,有冥王、东岳大帝、判官、牛头马面,日游神夜游神、增福神等,他们不是尘世中的泥偶或木偶,而是活生生的惩恶扬善、各司其职的神祇;有独特的查案方法,如罗隐就是被日游神听见抱怨语而记录在案,上报冥府;有办案工具业镜,通过业镜,人在凡世所作所为都可以重放,不可以丝毫隐瞒;还有名目繁多且残酷的刑罚所构筑的血腥受刑场景等。凡世是“常”,冥府是“非常”。此岸世界里的诸多不平、没有办法用法律去解决的事,在冥府都有相应的惩处。冥府甚至可以将几百年时间与空间的人物连接在一起,实现跨时空交流,使梁冀、董卓、卢杞、李林甫与秦桧之流同处一处,也可令人畜对话。倘若没有彼岸世界的描写,不仅缩短了叙事时间,也压缩了叙事空间。单一的现实空间与能力有限的尘世生活的描写,带来的艺术审美是刻板的。尤其是因冥游而拉长了叙事长度的小说,或冥游长度占主要地位的小说,没有了冥游,小说的小说味也将大减。
注释:
① 如韦凤娟的《从“地府”到“地狱”---论魏晋南北朝鬼话中冥界观念的演变》(《文学遗产》2007年第1期),郑红翠的《中国古代游冥故事的分布及类型特征探析》(《学术交流》2009年第3期);栾保群的《“泰山治鬼”说的起源与中国冥府的形成》(《河北学刊》2005年第3期);夏广兴、王伶的《汉译佛典与唐代入冥故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等。
[1] 杨义.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2] 诺思罗普·弗莱. 批评的剖析[M]. 陈慧等,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3] 维克多·特纳. 仪式过程: 结构与反结构[M]. 黄剑波,柳博赟,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4] 勒内·吉拉尔. 替罪羊[M]. 冯寿农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2.
[5] 于海. 西方社会思想史[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6]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M]. 刘北成, 杨远婴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7] 余晓明. 土改小说: 意识形态与仪式[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2): 66.
[8] 赫丽生. 艺术与仪式[C]// 叶舒宪选编. 神话原型批评.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9] 陈国强. 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Z].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Ceremony interpretation of travel in the hell of nihuaben novels
YANG Zonghong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Hezhou University, Hezhou 542899, China;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The structure of Nihuaben novels is quite similar to ceremony forms of the monks’ narration and Su-jiang (俗讲)narration in temples. Many protagonists in the novels change from one situation to another through their tour in hell, and the peregrination becomes their rites of passage in the life. The protagonists’ experience and travel scene description reveal the edge characters as “scapegoat” and the test ceremony is a necessity for some tours, and the horrible views in the hell have also become the justice ritual symbols. All in all, hell visit has not only ceremonial functions, but also 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such as fictitious and real integration, conversion of narrative time and space, the coincidence relation and inevitable, seamless combination of entertainment and the sense of fear, the solemn and carnival atmosphere.
Nihuaben novels; hell visit; rites; literariness; fictitious and real integration; conversion of time and space
I207.41
A
1672-3104(2014)06-0231-05
[编辑: 胡兴华]
2014-01-23;
2014-10-25
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研究”(13XZW008);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一般项目“民间信仰与明清话本小说神异叙事研究”( 11YJAZH112)
杨宗红(1969-),女,湖北恩施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贺州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曾秀芳(1968-),女,湖北鹤峰人,文学博士,贵州财经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