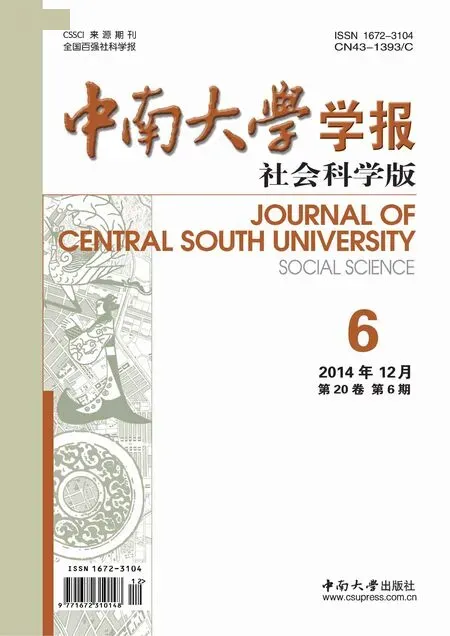从文本到实践:论教育平等权的宪法保障及其路径选择
王瑜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重庆,401120)
从文本到实践:论教育平等权的宪法保障及其路径选择
王瑜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重庆,401120)
我国“八二”宪法虽然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利,但是教育平等权却是间接得来的。教育平等权的内涵虽在学界未达成共识,但应蕴含两类平等性原则:形式及实质之平等原则。我国宪法文本对教育平等之规定经历了从“入宪”到“删除”,随后从“再次入宪”到“强调权利属性的教育平等”之发展历程。实践中,更是因为教育平等权之法律文本缺位,使得公民应当平等享有的宪法基本权利受到本质的侵害。在思考教育资源公平配置且效益最大化的同时,提出教育平等权之宪法确认、教育平等权之宪法救济及其技术路径。
受教育权;平等权;教育平等权;宪法诉讼;教育资源
公平是民主社会中所有公民对一切社会资源分配的价值诉求。绝对的不平等是存在于资本主义之前的封建等级社会,但随着商品经济之内在逻辑即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在政治以及法律上,必然会要求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平等和自由”。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折射于政治、社会及法律之上的平等夙愿当然要求人人在各分配领域理应享有平等性[1]。综观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可知:我国社会结构中“城乡差别”之禁锢在改革开放之前早已存在,并在其各自的体系之下,出现过绝对平均主义的“平等状态”。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财富不断积累,个体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各阶层及其群体间的社会心理随着经济、社会政治地位的变化更加渴望“公平”这一价值诉求。在教育领域,虽然公众接受义务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机会比率在提升,但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及资源分配不公已成为社会不稳定之诱因。2013年两会期间,教育公平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特别是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重点。我国“八二”宪法虽然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利,但是教育平等权却是间接得来的。如何重新理解教育平等权的内涵,在分析我国教育平等权自“八二”宪法颁布近三十年来的文本变迁及其实践发展历程并与横向域外对比来看,在宪法文本中纳入教育平等权是具有必要性的。
一、平等与公平:教育平等权之文本析要
(一)教育平等权之内涵
作为国家兴旺的百年大计,教育入宪早已成为各国宪法的重要内容。我国“八二”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①。早在两千年前,柏拉图就曾有教育平等的主张,即不论性别的男女应平等享有受教育权之机会[2]。但究竟何为教育平等权,“平等”与“公平”的异同之处、教育平等之内涵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教育平等权,从而更好地推进教育公平。
1. 平等与公平之内涵
文中所涉及的“平等”(fairness)一词,首先,是兼具社会资源分配之“平等享有”以及社会普世道德标准之“正义”价值的概念。其次,“平等”是具有一定实证意义的,即在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不论种族、性别、阶层,共同地平等享有。与“公平”倾向于定性的价值判断相比,这里所讲的平等是不同于“均等”的,它不仅具有定性的价值判断,更具有定量、特别情况下允许合理差异的资源分配价值标准。因此,“平等”的价值意义可以说是“公平”一词的实践注释。
而“公平”(fair或equitable)一词,总体上更倾向于关注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结果之价值判断,体现的是一种各阶层及群体间利益分配关系。正如罗尔斯所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3]因其具有社会资源分配结果的量化判断,这种公平也是可以实证衡量的。因此,笔者文中“平等”一词,是蕴含了社会资源分配之“平等”“公平”价值的综合。可见,教育平等不仅蕴含利益分配之平等、公平,也具有“公平”的主观评价意义。
2. 教育平等权之内涵
从理论法学的视角看,教育平等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具有公民权和人权的属性。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价值依据,是个人的尊严以及作为人的价值;文本依据是国际人权法文件②。作为公民权,其权利主体是公民,义务主体是国家以及经授权的教育主体,即作为权利主体的国家或授权主体不仅不得制定任何可能导致教育歧视的决定或法律规范,也要承担不作为之义务;其文本依据则是各国宪法文本及其他法律文件。
从政治学之视角看,教育平等权则应强调其权利属性。有学者就教育平等权的基本属性定义:“对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该分配方式要符合教育平等性之原则。”[4]在该视角之下,受教育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教育公平是受教育权的首要特征。英国法哲学家约翰·奥斯丁认为,“权利的本质特征在于给予所有者利益”[5],教育平等权作为一项法律权利,当然与一定的利益相关,这种利益即教育资源。因此,教育平等权的首要要素是公平正义原则。其次,政治领域的教育平等问题之核心即教育资源的分配。教育权利主体的受教育权利需要教育权力的保障方能实现。因此,从政治学角度,更强调教育权力主体的公正性,在其分配教育资源的同时要充分考虑教育平等权所指向的公正原则。
何谓“教育平等权”,学界迄今还未达成共识。学者可以从不同学科或视角得出不同的关于其内涵的界定,还有学者从范畴论、本体论等角度解析其内涵③。笔者认为其内涵应蕴含两类平等性原则:形式上及实质上之平等原则。前者要遵循相同情况平等对待以及允许合理性差别对待,后者的实质平等即要使受教育权利主体得到事前机会平等、程序平等以及事后之弱势补偿保障。
(二)教育平等条款之文本释义
著名美国教育学家贺拉斯·曼曾说过:“实现人类平等,最伟大的工具是教育,教育的作用之大是任何其他人类发明都难以比拟的。”[6]也正因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7]。因此,“教育平等权”作为公民的原始权利,这一概念的广泛传播是在二战之后,1945年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中正式重申“不论男女的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平等权利之信念。”次年3月国际教育局第九届大会首次明确将“教育机会均等”列入议程之中,这也是教育平等权的最早文本记录。
1948年旨在维护世界人类基本权利的《世界人权宣言》正式明确了平等原则,并将教育权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④。因此源于国际法的教育平等权正式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同。1960年,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第十一届大会通过了两个有关“教育平等权”的国际性文件,即《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和《反对教育歧视建议》[8]。此后,联合国又接连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世界全民教育宣言之满足基本学习需要》(1990年)等,这些国际文件之共同点就是反复强调“人人都应当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以及受教育之机会平等”,使得“教育平等权”更加明确地成为被国际法所保障的一项重要人权。
我国国内立法关于教育平等的规定与上述国际法的主要精神是相同的。我国1954年宪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随后的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都删除了“平等”之规定,教育平等更是无从谈起。1978年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现行1982年宪法之第三十三条,“平等权”再次入宪,结合第四十六条受教育权之规定以及受西方国际人权法影响,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之教育平等权应运而生。
二、理想与现实:教育平等权之宪政实践
实践中,教育平等权如何落实,其核心当然还是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教育资源的竞争,这是难以避免的,更何况教育平等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必然与一定的利益密切相关,这种利益即教育资源。而教育资源配置问题的核心目标即教育资源公平配置且效益最大化。也就是其理想目标是追求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学历教育等各级教育之间以及各区域间的教育资源的国家供给总量在满足各教育需求的同时,是本着公平正义之原则进行分配的[9]。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权利义务明确的教育公共资源配置体系,导致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资源的各自分配不均,以及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资源分配不均。“齐玉苓”案、2001年的“青岛考生状告教育部”案等典型案件的发生,预示着如何均衡地配置教育资源是我国实践中实现教育平等权的应然要求。
(一)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
我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最为突出的表现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国家投入高等教育领域的教育经费比例偏高,而基础教育经费短缺已成为现实。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于2001年的基础教育经费与人均GDP比值为6.2,初高中教育与人均GDP比值为13.2,而高等教育与人均GDP比值高达86,同比世界水平,而我国的基础教育及职业教育投入与世界人均水平相差悬殊。这种公共性教育资源分配之份额,高等教育所占比例偏高之趋势延续至今。高等教育所占比例在我国整体财政预算中的教育和基建支出中,1996~2002年间从21.8%到23.6%,提高了近两个百分点。而与之相对应的基础教育所占比例从20.5%降低到18.5%[10]。然而,随着2000年之后的高校不断扩招,高校人数急速增长以及在国家倡导的大力发展大学教育的政策不断推进的背景之下,各大高校争相买地、盖楼,总体上我国高校在近10年内都是沿着相同的趋势发展,即入学人数的增长伴随支出的同步增长。但在此趋势的发展过程中,不论是高校自身状况或社会效应是否趋向良性发展还有待讨论。
因此,鉴于我国尚处于教育水平整体较低的初级阶段, 我国当前这种对高等教育阶段资源投入与西方国家接近,而与基础教育阶段的资源投入相比差距巨大的资源分配方式不仅不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更不利于公民的教育平等权的实现。我国是尚处于整体教育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高等教育投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近,而基础教育相差甚远,这种教育资源的分配不仅违背了公平原则,违背了宪法中的教育平等原则,更不符合教育可持续性长远发展的目标。因此,现阶段我们最迫切的是需要加大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等基础教育阶段的资源投入,其产生的社会效益会远大于如今高等教育过高比例的资源投入。
(二)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
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实质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平等。在以各省为单位的高校录取名额所占比例的配置上一直向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倾斜,而在各省内部高校录取名额比例则向省会城市倾斜的情况严重。以北京的清华大学为例,其近十年的录取名额在京比例一直超过了录取其他几省名额的总和。清华大学2001年录取北京本地考生的人数高达近两成,而北京当年的高中毕业生只占了全国总量的不足1%。也就是说,同样的试题,河南某考生与北京某考生都考了500分,北京考生可以上清华,但是河南考生二本都上不了,这种分数在其他省份则可能无学可上。
因此,即使是城市人口,升入高校也并非是考分相同基础上的人人平等,考分高于很多城市的考生也可能落榜。 以北大、清华两重点高校的招生为例,在1999年,两校共招本科生5080名,农村学生只有902人,不足20%。而1999年北京市考生的大学录取率高达73%,这与有的省还达不到三成录取率形成鲜明对比[11]。
这种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平等的原因首先在于,考生在基础教育阶段享有公共教育资源之机会不平等,再加上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财富的倒三角趋势,使得平等享有高等教育资源之机会更加难以获得。
高等教育资源的享有,已处在公民受教育阶段的最高位阶。正是由于基础教育阶段对教育资源享有的不断分化,外加国家政策的城市化倾斜等因素的不断积累,导致了最终的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因此,为了防止教育分化的不断扩大,政府机关作为公共资源的调配者,必须介入并合理地对公共教育资源进行配置,特别是针对基础教育阶段。
三、确权与维权:教育平等之宪法保障
(一)教育平等权之宪法确认
当前我国宪法中是没有直接规定教育平等权的。对于如此重要的公民基本权利,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就已经明确了平等原则并将教育权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1960年又通过了两个肯定“教育平等权”的国际性文件,而我国宪法针对教育平等权的规定还需要通过间接方式予以推定。
首先,从个人生存发展的角度讲,“教育平等权”已是世界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教育通过向个人传授基本的文化信息、生产技术、价值观念等来实现并促进人的独立生存或自身社会化的过程。教育对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使人离不开教育。正是由于这种需求,使得公民是否享有公共教育资源的平等性越来越受到关注。而宪法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大法,所有法律都不能与宪法相抵触,教育平等权入宪无疑会大力推进公民享有教育资源的实质平等,这也是教育平等权的内涵。当然,这里的平等享有并不是指每个人都享有相同的教育资源,而是确保每个公民都可以享有其应得的公共教育资源,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实质公平。
其次,宪法中关于受教育权的具体规定过少。一切国家机关在行使宪法赋予的立法权时都声称“依据宪法制定本法”,因此,从立法机关的角度讲,宪法若关于公民基本受教育权之内容规定得过于模糊或篇幅过少,立法机关就难以“凭空”制定出满足实践需求的教育法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教育平等权入宪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教育平等权之宪法救济
教育平等权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内的保护是不完善的,以公民理应平等享有基础教育资源的权利为角度,教育平等权所针对的对象是国家。公民个人与享有分配公共教育资源的权力主体之间的身份地位差距悬殊,若公民应享有的平等受教育权受到侵害,而囿于我国行政诉讼主体标准、受案范围之阻却,那么,此时无论行政诉讼亦或民事诉讼都爱莫能助,公民的教育平等权受保护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就必须发挥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效力。以宪法保护之技术路径进行探讨,可以有两种选择。
1. 人大审查之技术路径
针对公民平等享有的教育平等权的保护,应包括“提请人大审查之路径”。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体系之中,由于法院并未有违宪审查权,当审判机关要选用的法律存在违反宪法的情况下,必须停止该项诉讼,将可能违宪的法律交由有违宪审查权的机关审查,待其作出最终裁决之后,再继续启动诉讼程序。《德国基本法》以及《奥地利宪法》都有相关规定⑤。学界将此项由法院主动提起违宪审查之程序,定义为“法规的具体审查程序”。在法院提起该程序之前,其个案法官必须对引起争议之法律进行审查并确信该法律确实违反宪法。因为有权进行违宪审查的机关必须是宪法的最高维护者但并非唯一,而普通法院作为案件的一般审判机关也应具有维护宪法的基本义务[12]。
我国亦是如此。《立法法》第九十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至此,我国法院若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确定将其选作定案之法律依据,可能存在违反宪法之情形的,理应先裁定中止诉讼,并可以就该问题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申请。但不足之处在于,我国《立法法》第九十一条未对普通法院之申请违宪审查程序作出法律规定。
注意,提出违宪审查之申请时,必须遵循一定原则:首先,要穷尽其他救济途径。其次,只能针对案件争议必须适用的法律提出违宪审查申请。
2. 宪法诉讼之技术路径
首先,作为静态之宪法要运作起来才能发挥其保护公民权利之作用,这与司宪机关在个案之中对宪法的适用相关,否则宪法永远被束之高阁而难以实现它的权威性。其次,教育平等权作为一项积极的公民基本权利,需要有效的途径对其进行救济,而宪法诉讼作为一项向公民个人开放的宪法救济途径是保障公民教育平等权的最佳路径。宪法诉讼是指,在穷尽其他救济途径,或其他途径之救济方式不济时,作为公民之基本权利受到公权力侵害,可以向宪法审判机关提出诉求,请求给与救济的制度[13](235)。宪法诉讼案件类型可以分为:基本法律违宪案件,法律法规违宪案件,机关之间权限之争议案件,宪法诉讼案件,弹劾案件,社团违宪案件及选举案件等[13](235)。
之所以认为宪法诉讼是保护公民基本教育平等权的可能路径,是基于以下考量:一是宪法诉讼能够满足公民之宪法权利享有救济途径之要求。有权利必有救济,这句谚语告诉我们,权利与救济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1949年的《德国基本法》、1974年《瑞士宪法》以及1978年的《西班牙宪法》都规定了宪法诉讼制度。宪法权利的可诉性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得以真正实现的最后程序化保障机制。二是宪法诉讼向个人开放之特点可以有效调节公民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其他诉讼案件之类型相比,只有宪法诉讼是直接向公民个人开放的。宪法诉讼制度也是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最直接宪法救济路径,这在客观上会提升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力度。因为,只要公民个人认为其平等享有受教育资源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且在其他救济方式用尽或不济时,就可以选择提起宪法诉讼之路径[14]。并且,宪法诉讼类型在具有对公民基本权利救济的主观功能的同时,也同样履行着排除公权力违宪行使的可能性以及公权力之消极履行,保障及维护宪法秩序之功能[15]。简而言之,宪法诉讼制度不仅可以救济受到侵害公民之基本权利,其在客观上也会起到保护和维持宪法秩序的功能。
注释:
① 《宪法》第4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第33条:“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由此能够间接推出公民的受教育权是平等的。
② 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26 条第1 款规定:“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在序言中回顾了《世界人权宣言》确认不歧视原则并宣告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 条第1 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儿童权利公约》第28 条第1 款规定:“缔约国确认儿童有受教育的权利”;《关于特殊需要教育的原则、方针和实践的萨拉曼卡宣言》第2 条宣布:“每个儿童都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必须获得可达到的并保持可接受的学习水平的机会,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必须有机会进入普通学校,而这些学校应以一种能满足其特殊需要的儿童中心教育思想接纳他们。”
③ 有学者认为“从范畴意义讲,教育平等是反映相对性的范畴而非确定性或绝对性范畴,是反应质的范畴而非量的范畴”;“教育平等的主观标准应以个人公平感的评测来实现,客观标准应为起点之平等以及竞争规则的合理性。”
④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23条:“(一)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质。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二)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并应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
⑤ 《德国基本法》第100条第1项规定:“法院认为某一法律违宪,而该法律之效力与其审判有关者,应停止审判程序。如系违反邦宪法,应请有权受理宪法争议之邦法院审判之;如系违反基本法,应请联邦宪法法院审判之。”《奥地利宪法》第89条第2款规定:“任何法院如果对某项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的适用发生疑问,应即中断诉讼,向宪法法院提出要求取消该法律的申请。”
[1] 王惠岩. 政治学原理[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313.
[2] 柏拉图. 理想国[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103.
[3]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83.
[4] 师东海. 教育公平的政治学思考[M]. 吉林: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1: 78.
[5] [英]约翰·奥斯丁. 法理学的范围[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3: 230.
[6] John Seiler Brubacher. Modern philosophies of education: Studies in Philosophies, Schooling, and Educational Policies [M]. London: Waveland Press, 1990.
[7] [法]卢俊. 社会约论(第一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99
[8] 周永坤. 教育平等权的宪法学思考[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06(4): 34.
[9] 史中良, 肖四. 中国经济资源配置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8: 77.
[10] 王蓉. 教育水平的差异与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J].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 2004(3): 126.
[11] 张玉林. 2004中国教育不平等状况蓝皮书[J]. 校长阅刊, 2005(5): 35.
[12] Raphael D D. Problem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M]. London: Macmillan, 1970: 68-70
[13] 胡肖华. 宪法诉讼原论[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2.
[14] 韩大元. 论宪法诉愿程序的价值[J]. 学习与探索, 2007(1): 67.
[15] 李熙勲. 关于韩国禁止裁判诉愿的宪法评价[J]. 浙江社会科学, 2010(5): 56-67.
From text to practice: the protection of equal rights of education constitution and its path choice
WANG Yu
(Administrative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In 1982, the Constitutional text defined the citizen education rights clearly, but education equality was indirect. The connotation of education equality should contain two principles though there is no agreement: form and virtual principle of equality. Education equality in constitutional text changed from “writing into the constitution” to“deleting”, and from “again writing into the constitution” to “emphasizing education equality”. In practice, the absence of the legal text makes the equal right of the citizens violated. We should think about the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fair allocation of the maximum profits.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put forward constitutional confirmation, constitutional relief, and take technological path of the education equality.
right to educated; the right of equality; education equality; constitution appeals; education resources
D911
A
1672-3104(2014)06-0121-05
[编辑: 苏慧]
2013-10-19;
2014-10-05
王瑜(1984-),女,陕西西安人,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宪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