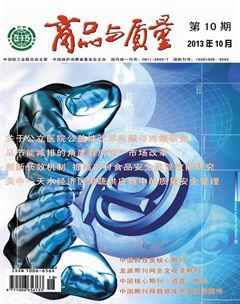戏梦人生潜流下的悲凉
杨蕾
【摘 要】《霸王别姬》是陈凯歌他创作的一个高峰,在跌宕起伏的叙事背后,导演并没有仅仅流于坎坷命运的叙事表面,在繁复的讲述背后是对人类生存态势的全部表现以及在历史下突变的深沉思索。
【关键词】霸王别姬;叙事结构;人性表现
作为第五代导演无可厚非的精神领袖,陈凯歌一直以浓重的哲学底蕴和宏大的人文思考而著称。在他的作品序列中,毋庸置疑的,《霸王别姬》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它不仅为陈凯歌赢得了金棕榈的桂冠同时也在中国电影长廊里留下了程蝶衣、段小楼、菊仙这一系列深入人心的形象。相对于前四部作品的晦涩难懂和叙事隐退,《霸王别姬》终于回归到了叙事本体,将主观思考隐藏于生动的文本叙述与复杂的人物性格塑造之下。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变迁中,以感情纠葛的三人命运为线索并将精美绝伦商业卖点十足的京剧点缀其中。而最重要的是在跌宕起伏的叙事背后,导演并没有仅仅流于坎坷命运的叙事表面,在繁复的讲述背后是对人类生存态势的全部表现以及在历史下突变的深沉思索。
影片整体上运用的是环形叙事结构,首尾呼应时间都是1977年,中间用插叙的方法,结合中国社会的几次时代变迁,交待了三人五十多年间的恩怨情仇。一曲《霸王别姬》的选段将观众带到程蝶衣与段小楼的命运世界。世事苍茫后再聚首,戏台上的霸王早已失去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力,然而虞姬却依旧是风华绝代,词言清亮,拖着长长的余音,好像千年的哀怨依旧不绝。那些惨烈与美丽并存的岁月早已如烟尘一样消失在历史车轮之后,当一切都成为过去,当生命已经四面楚歌,蝶衣所能做的也正是虞姬所能做的,拔出霸王的剑自刎而亡,他和虞姬终于化为了一个人,完成了师傅的教诲:从一而终。
影片从一个长达两分半钟的长镜头开始追溯故事的渊源。通过小豆子和母亲去戏班的一路行程电影像我们展现了1924年北平北洋政府时期的芸芸众生与世俗民情。长镜头在影片中被多次用到,这些长镜头不仅客观的展现了各个历史变更时期的社会状况,更是将宏大的历史叙事和人物的细微心理相结合,有一种磅礴与细致并存的气质。随着小豆子的母亲走进戏班大院,京剧这一中国传统精萃艺术的幕后景象逐一揭开面纱。就在这些板子声、训斥声、吊嗓子声里,在严厉的师傅、精美的唱词里隐藏着多少才子佳人、盖世英雄的古老故事。也同样是在这个环境中,小豆子与小石头两个人在演绎江山美人的历史中成了现行历史的牺牲品。戏班这一特殊的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的艺术背景,在满足外国观众的猎奇心理的同时也成为导演重要的叙事工具。他不仅通过“霸王别姬”戏文与现实中程、段悲剧的契合来展现人生如戏的命运,而且通过艺术与现实的双重交叉来探讨隐藏在其中的人性悲剧。
在影片中,程蝶衣、段小楼、菊仙三人都是孤独的个体,却又各自代表了三种基本的生存态势,程蝶衣是纯精神的人性表现,段小楼是纯物质的人性表现,而菊仙则是处在二者之间的游弋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人性表现。当这三个原本平行发展的生存境遇处在同一个感情纠葛里,并与强大的历史作用纠缠在一起时,悲剧自然也就产生了。而在三位主人公中,程蝶衣显然是中心,导演不仅围绕他的人生轨迹来塑造段小楼、菊仙和其他人物在时代中的众生相,同时也集中体现作者关于人性的反思。而对于京戏的态度其实也正是他做人原则的一个缩影,就像他对蝶衣的保护出于一种男性气概和兄弟情谊一样,京戏对于他只是一个生存的方式而不是生命的全部。所以,他可以几度转行,可以在台上演着楚霸王台下却救了潘金莲,甚至连霸王出场究竟走几步都不在意。随时势而变是小楼的做人原则,于是在没有利益冲突时,他是情义无边的楚霸王,但是一旦世事压倒自己的头上,爱人可以抛弃,朋友可以背叛甚至艺术也可以侮辱。也正是他的背叛完成了蝶衣与菊仙两个人生的破灭。
“背叛”是电影的另一个主题,是对戏文《霸王别姬》里忠贞的一种嘲讽。蝶衣的一生是遭遇背叛的一生,这种背叛既包括女性的缺失也包括男性的离开。第五代电影中经常运用的失父元素在影片开头以小豆子母亲妓女身份的交待的出现,就注定了蝶衣悲怆的命运将与寻找和叩问紧紧相连。当母亲在斩断他多余的手指然后消失在门外的风雪中时,以母亲为代表的女性身份也告别了他的生活。所以他开始在生命中寻找母爱与父爱的替代品。首先是他在从张公公的府里出来时拾到小四自己充当了母亲的角色,但最后小四替代他出演了虞姬,再后来是在戒毒时菊仙给予的母性的爱,可是菊仙的身份也是妓女,这种身份的再次回归又证明了这种爱是短暂的停留、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在父爱的寻找中,因为女性身份的转换和舞台上霸王虞姬的表演使得他把霸王当成唯一的男性依附,唯一屈服于袁四爷的那一次也只是因为袁四爷画上了霸王的脸。可是他的背叛却是致命的。从小楼一次次把他单独留在舞台上再到用别人替换出演了虞姬,直至在红卫兵的强压下与他划清界线,一切虚景良辰变成了废墟,才子佳人成了牛鬼蛇神,人性中赤裸裸的恶毒才真正如一瓢冷水把蝶衣做了几十年的霸王别姬的梦浇醒。
在影片我们还可以看到陈凯歌一贯的象征性手法的运用。在他的所有影片中自始至终都有一个经典的性格发展模式,即主要人物往往被无端的放置于一个极度拂逆的生存境遇,身世跌宕无常,性格也由最初张惶失措的软弱而逐渐变得强势最终成就性格上的偏执,这一变化又往往是在历史环境的强压下被迫改变。在《霸王别姬》中,这一模式集中表现在程蝶衣的身上,他从出生时就带有孤独感在戏班的生存原则(要么成角儿要么像小癞子一样死去)和历史变迁的双重强烈扭曲下而变成了一种对理想主义的狂热迷恋,像一个宗教信徒一样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京剧,以致人戏不分雌雄同在,最终像虞姬一样“无论怎么演都逃不了一死”。影片贯穿始终的对从一而终的强调也正是一种集体意识对个体意识的强暴和吞噬。其实这恰恰是陈凯歌自己的一种隐喻,他表面上把蝶衣置于舞台中间,京剧的舞台人生的舞台,让他成为唯一的表演者我们是台下的看客,实际上他却是把历史当作了一方舞台,只是表演者变成了我们,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蝶衣却是那微笑的沉默不语的旁观者。正是通过这一理性化的象征,陈凯歌完成了欣赏者与被欣赏者的成功置换和反观。
参考文献:
[1]戴锦华.电影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彭晓红 . 《霸王别姬》:戏如人生—从程蝶衣看人性迷失 [J].
贵州工业大学出版社 ( 社会科学版 ),2008 年 5 月
[3]黄鹂.隐喻人生的戏———论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内涵[J].河南教育学院院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2): 46-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