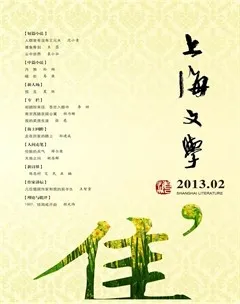天地之问
几年前,我和我哥在上海为翻译家草婴先生拍照时,他问了我们一些问题,我们都一一作答。他对我们自费为名人拍照非常理解,我就趁机向他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介绍我们拍摄高莽先生呢?”
“好啊!”但老先生眉宇间掠过一丝无奈,“你们得要去北京啊!”
2006年冬天,我们来到了北京。我给草婴先生打了电话,老先生告知了高莽先生的联系方式,同时叮嘱我们兄弟注意身体。
终于与高莽先生联系上了。他希望我们第二天下午三点之后过去,并叫他的女儿晓岚详详细细地告诉我们去他家的线路,这使我们倍感温暖。
高莽先生不仅被俄罗斯多个机构授予“名誉博士”、“荣誉院士”等称号,而且还获得过“友谊勋章”、“俄中友谊纪念章”、“友谊贡献荣誉奖”、“普希金纪念章”、“高尔基奖”、“奥斯特洛夫斯基奖章与奖状”等,其在翻译﹑写作﹑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国内外人士为之折服。
见到高莽先生我就说:“您老还有个名字叫……”
“乌兰汗。”我话音未落,他说道,“乌兰汗这个笔名只在翻译文学作品时使用……”
我说,我是在一篇文章中知道大名鼎鼎的高莽和乌兰汗是同一人。他笑道:“我的笔名太多了,好多我自己都不记得了。现在收录在翻译家词典里用的是‘乌兰汗’,文学词典里用的是‘高莽’。”
“关于您的笔名,戈宝权先生还闹过一次误会,我觉得很有趣。”我的话匣子打开了。
他解释道:“我的学生生活结束后,抗日战争胜利,我参加了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并从事翻译工作,还当过《北光日报》的编辑。同时我从俄文译过来一些诗歌与随笔等,发表时我使用了很多不同的笔名。戈宝权先生是著名的俄苏文学翻译家、研究家,他对各地的俄苏文学研究现状非常关心。新中国成立前夕,党派戈先生去苏联接收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他途经哈尔滨时,看到本地报纸上有好多人在翻译和评介有关苏联文学艺术的文章。他把这些作者的名字抄下来了,并向当地领导提出要请这些人举行一次座谈会,跟各位交流。我接到通知,早早地赶到会场。戈先生穿一身西装,戴着一副眼镜,面带微笑地和我交谈起来。开会的时间已到,但就我一个人来了。他感到奇怪,对我说:‘你们哈尔滨人怎么这么不守时啊?约好了时间开会怎么没人来?’我也觉得奇怪,就问他:‘还通知了哪些人参加这个会?’他把本子掏出来给我看,把邀请的人名读了一遍。我反而不惊讶了,对他说:‘人都到齐了,因为那八九个人名都是我的笔名。’戈先生明白了原因后开朗地笑了。他没有因为只有我一人出席座谈会而省略发言,而是津津有味地谈了苏联文学现状,谈了苏联作家的创作。我第一次听人专门讲授苏俄文学,讲授如何治学,讲授翻译的重要意义。戈先生很理解我的需要,他把我想知道而没有说清楚或需要知道的事都告诉了我,并指出了我努力的方向。我就暗自思忖,如果有朝一日能在这位学者身边工作该多幸福啊!没想到几年后,我的希望竟变成了现实。我一直把戈先生当作我最尊敬的师长。”他慢慢地说,我们细心地听,很开心。
他女儿为我们沏茶,并问我们到她家走过冤枉路没有。高莽先生对我们说,他的女儿也喜欢摄影,还得过“冰心摄影文学奖”。我将我们拍的多张名人照片展示给他们看,并希望他们提意见,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拍得都挺好,挺好的。”
我抬头看到他身后有一幅很大的肖像画,不禁问:“这画中人是谁呢?”
他边示意我们喝茶,边说:“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插言道:“国际摄影大师菲利普·哈尔斯曼曾受到他的影响。”
“哦!其实他影响过很多人。他的生活多难,经历坎坷,思想复杂,作品深奥。高尔基说,就表现力而言,可能只有莎士比亚能与他媲美。”他转身走近这幅画说道。
“那就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画像为背景开始拍摄吧!”显然我已有为他拍摄的欲望了。
他有些尴尬地说:“这幅画没画完,拍出来可能不好看。”
“这幅画只是个背景,您本身会遮掉这幅画的一些细节的。”我向他阐明自己的想法。
他微笑着接受了我的建议,我哥在一旁拍了多张我为他拍摄的工作照,还不时与他聊天、讲笑话,使他放松。
“您有没有工作室?能不能看看?”我想在更多的环境中拍摄,试探性地问。
“算了吧!我工作的地方不成样子,太乱了。”他为难地说。
这使我想起,前些年在他还未搬进这套房子之时,有一次过生日,苏联大使派人给他送花祝贺,他无法接待,只好跑到紫竹院公园门口接受礼物。想到这里,我默默地为他拍摄着。
“还是到里屋看看吧﹗”他女儿说着带我哥进了里屋,不一会儿,我哥出来了,脸上露出进屋以来难得的微笑,忙说:“到里面拍吧!太好了。”
在他的感染下,我也感到兴奋,估计可拍到多张环境肖像,况且高莽先生是极具国际声望的肖像画家,曾为托尔斯泰、高尔基、歌德、井上靖、博尔赫斯、鲁迅、茅盾、巴金、丁玲、胡风、艾青、萧乾等国内外文学泰斗画过肖像。大幅群像《巴金和他的老师们》、《赞梅图》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其肖像画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法国巴尔扎克纪念馆、高尔基故居纪念馆、日本井上靖文学馆、欧洲及拉美一些纪念馆所收藏。
为肖像画家拍摄,我一直非常小心,因为他们在审视你的照片时会很容易击中要害,更何况为高莽先生拍摄过的摄影家的名气和成就,都大大盖过我们俩兄弟。
说实在的,里面的房间极为拥挤,门对面摆放着他女儿的电脑桌,紧挨门的地方是一张他自制的床。我注意到,床板底部做了几个装书的柜子。床边靠窗子的地方有一张桌子,桌子上堆满了各种资料书籍,上面还有一盏台灯,看来高莽先生每天就在这里看书、写作。书架是用几条木板组合起来的,占据了整个墙面,四壁几乎被书“霸占”着,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难怪高莽先生不想要我们去里屋拍照,确实有杂乱之感,但我们都知道,这正是一位文化名人最真实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您那代人受政治的影响很大,比如‘反右’、‘文革’。”我说着找到一小块难得的地方支起了三角架。
“‘反右’之前,我就受到批判了。我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文艺报》上因漫画受到批判的最早的人中的一个……”他悠悠地说,“建国之后,经受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风暴,我的生活积累比以前丰厚了,对亲情与爱情、对生与死、对酸甜苦辣的感受懂得也多了。”
在交谈过程中,我想起了他双目失明的妻子孙杰。她曾在根据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戏剧《保尔·柯察金》中扮演过冬妮亚,而剧本正是高莽1947年翻译的——他们的爱情因俄罗斯文学结缘。1956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赖莎来中国访问,知道《保尔·柯察金》在中国有这段情缘,见到高莽先生时说:“你应该感谢我,我可是你们的媒婆!”赖莎还送给高莽夫妇一张照片,背面写着:“给高莽、孙杰,希望你们的生活幸福得像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微笑那样迷人。”以后她给高莽写信、寄书,都署名“你们的媒婆”。保尔失明得到赖莎的照顾,没想到多年后,孙杰失明,高莽悉心呵护他的妻子。我们没有见到孙杰老人,但我知道高莽先生每天都给妻子点眼药水。
“您夫人病了,您总在照顾她,使您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了吧?”我边拍边问,哥在一旁用反光板挡光、补光。
“是的。这十几年里,她看不到我,不知我头发白了多少,脸上长了多少老年斑,但我能看到她一天天的变化。其实,我现在也没有能力参加社会活动了。”他慢条斯理地说,“我八十岁了,工作了一辈子,也想为自己留点时间,做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
高莽先生坐在床上,有时严肃,有时微笑,都被我抓拍下来。我不时要他变换方位,说:“这样就可尽量避免您的眼镜反光。”
他反问我:“反光有什么不好?有时别人为我拍照,我还希望把眼镜的反光拍下来。”名家就是名家,太有个性了。
我换了一个话题继续与他聊:“您曾担任《世界文学》主编,我是《世界文学》的忠实读者,那时我虽是个中学生,从中学开始我就知道您了。”
他连声说:“谢谢!谢谢!”接着说:“世界是复杂的,世界文学是绚丽多彩的。每个民族的文学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如今时代大大前进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打破封闭状态,把外国一切优秀的文学成果都拿过来,为我所用。所以,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古代的还是当代的,只要是优秀的或有重要影响的,我们都应当尽力介绍给我国读者。”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在《世界文学》做主编时,就主张文化的多元化,发表过我并不喜欢的作品。这些作品既然在它们本国有很大影响,得到肯定,我们就必须了解。”
“《世界文学》起到了沟通中外文学的桥梁作用,您作为主编立了大功。”我很崇敬地说道。
然而,高莽先生却说出了让我们感到惊讶的话,“我这个人是随着命运走,命运怎么安排我,我就怎么做。其实我不适合当主编,因为缺少工作魄力,办事优柔寡断,不愿意得罪人,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我曾对领导不止一次地表示,最好让我专搞业务。可是领导偏偏让我当什么负责人,我又没有和领导顶撞的抗上勇气。哈哈!”
“您的业务没有丢呀!您翻译过普希金的抒情诗,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的诗……”不等我说完,“还有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他随口补充道。
“您怎样看帕斯捷尔纳克这个人呢?”
“帕斯捷尔纳克掌握英、德、法等语言,除了诗歌、散文、小说创作之外,他还从事文学翻译。他的创作是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中一个复杂的现象。1958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迫于国内的各种压力,他不得不放弃该奖。他沉痛地表示:我生在俄罗斯,长在俄罗斯,在俄罗斯工作。我和俄罗斯是连在一起的。”他似乎在自言自语,“帕斯捷尔纳克一生多难,经历了几次社会变革,经受了文艺界多次批评运动。他的思想有变化,有发展,有起伏,这些因素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所反映。他的身上集结了时代的矛盾与特征。”
“那么,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创作的呢?”
“有机会再谈吧!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字晦涩深奥,联想古怪奇特,流露出他对艺术的唯心主义观点和追求俄国和德国理性抒情的倾向。他的诗,我翻译起来感到吃力,最近我还在译他的作品。”他委婉地说。
“您怎样评价阿赫玛托娃呢?”我对这位诗人的诗也是蛮喜欢的,就继续问道。
他考虑了一下,一只手放在一堆书上,一只手比划着对我们说:“诗——是她的生命,她的一切。阿赫玛托娃相信苦难是人所不能摆脱的经历,她相信天国,也相信人民,相信未来。当厄运临头的时候,她比马雅可夫斯基,比叶赛宁,比法捷耶夫表现出更大的勇气和韧力。她没有绝望,没有自杀。她始终和多灾多难的祖国人民在一起,勤勤恳恳地默默写作。去世前一年她写道:‘我从未停止过写诗,我是以响彻我国英雄历史的旋律为旋律的。我以能生活在这个年代,并阅历诸多无与伦比的事件,感到幸福。’我以为阿赫玛托娃的幸福,在于她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人民心灵的呼声。如今,她的名字已成为俄罗斯语言学中最珍贵的名字之一。如果俄罗斯没有阿赫玛托娃,他们的文学会感到贫乏得多。”他有些惋惜地说,“只是,那个时代对她实在是过于残酷了。”
为了在窗户边拍一张高莽先生坐在书桌前、背景是书架的照片,我在书堆里找不到下脚的地方。他建议我搬走一张凳子。我用广角镜头,手持相机,勉强能拍到心仪的场景。他女儿和我哥为我们两人拍现场照,他女儿站得很高,他提醒道:“小心,别摔下来。”那气氛真热烈。
高莽先生注意到我端详着墙上的一幅画,画面中一个老妇人在做针线活,旁边还睡着一个女孩。他对我们说:“这是我母亲,我画的。”那音调使我感到他的自豪和淡淡的悲哀。他指着画,仿佛在回忆中,喃喃自语:“母亲常对我说,做任何事一定要做到最好,不能留下丝毫的遗憾。”老人家是文盲,但她对肖像画有自己的理解,“女同志要画得漂亮些;男同志要画得年轻些……”对于老人家的绘画理论,钱钟书先生有过评论,他说:“按照高莽妈妈的教诲创作不出好的作品。”杨绛先生听到后,笑眯眯地说:“她的话也许有一定的道理。”高莽先生曾经说过,母亲是他心中的一盏灯,永远照耀着他前行。
结束在工作室的拍摄,高莽先生又带我们返回客厅。我刚坐定,发现高莽先生坐的那地方有很多造型各异的老虎,质地有布的﹑毛绒的﹑泥的﹑玻璃的……他笑着说:“我们家就是老虎多,我属虎,我妻子也属虎,我们现在的住处原来叫老虎洞……”我再次架起三角架为他拍了几张。
拍完后,我发现墙上挂着华君武先生画的漫画《双虎图》,画面中一只老虎拿着药瓶,另一只老虎用双爪把眼睛捂着。画上题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不是害羞,是点眼药的恩爱。”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马上笑起来了,说:“昨天给您打电话时,您答应给我画张肖像画的。”
“对,对。”他说着进里屋拿了个本子。他看了下我,建议我胸前挂上相机,手放在相机上,我哥随手递给我一部相机。那一会儿,他观察我,慢慢地画,整个客厅静极了,似乎听得到心跳声。
过了一会儿,高莽先生问:“像吗?”
大家都看着我,我说:“把我的神韵画出来了。比实际的我年轻,其实我有白头发了。”客厅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晓岚将父亲刚刚完成的美术作品扫描,接着打印出来。高莽先生建议我在上面写几个字,留给他一张。
我随口说:“就写我的摄影观吧!”
“你有摄影观?”他兴奋地说,“那太好了,就写在上面吧!”
“‘以形写心’,就这四个字。”我补充道,“其实我名片反面的那句话也是我对摄影的理解。”
“那就都写上吧!”他女儿在看我写字时说。
我在两张打印的图片上分别写下了“以形写心”和“摄影使我们更加地依恋生命和环绕生命的一切美好;更加地依恋高尚的心灵和心灵的最崇高的创造”。高莽先生看了后非常高兴,幽默地说,日后可以卖钱。
大功告成,高莽先生突然问我们兄弟平常打不打架,我们都说:“不打。”他二话没说,迅速从里屋取出一本书《我画俄罗斯》,不加思索地在扉页上写下了“胡家不打架的两位摄影家兄弟正 高莽 2006﹒12”,还盖了一个小印章。
临走时,我们感到高莽先生依然是精神抖擞。趁此机会我哥问了他一个并不轻松的问题:“您认为俄罗斯民族的性格是怎样的?又是怎样形成的?”
他滔滔不绝地说:“我觉得俄罗斯民族很多地方跟我们中华民族有点相似,长期处于被压迫的状况,另外它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他们开阔的胸怀,俄罗斯的一些大作家多是贵族,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同情心,很强烈的使命感,或者是宗教感。托尔斯泰经过长期激烈的思想斗争,于1910年10月28日,毅然决定摆脱贵族生活,深夜弃家出走,以实现‘平民化’的夙愿。赫尔岑,他从小就恨沙皇,他继承了贵族的头衔,一生反对虚伪的生活。如果他们没有那种经历的话,很难产生感人的作品。”
后来,我把所有拍的有关高莽先生的照片寄给他,不久收到了高莽先生的来信。信中云:
昌群先生:
收到您寄来的几十张照片,让我十分感谢。几乎每一幅拍得都很精彩,足见您的技艺的高超。
我将选出几张寄给您,您放大就可以了,不必装框等。这已经使您破费不少了。
您让我写个条幅,我努力照办,容我好好想句话,再写给您。
向全家及令兄
看完信后,我打电话给高莽先生,他说我拍的都很好,很精彩,只选一张非常满意的感到十分为难。他认真地说:“你如果强行说里面有不好的照片,那肯定是我没有表现好。”
高莽先生在2007年3月3日的来信中写道:“你让我选一张我喜欢的照片,将小样寄给你,以便放大。我觉得你拍的肖像,绝大部分都很成功,扩印哪一张我都没有意见。你为拍摄人像已付出那么多精力与心血,我真不好意思再剥削你,所以一拖再拖。现在选了一张寄上,不知你意如何?”信中还夹有一个条幅,那就是:
我形我影我灵魂
尽在胡郎一摁中
赞胡昌群先生摄影艺术
我打电话给他,感谢他对我所拍照片的偏爱。接着,我问他:“您的学识渊博,年轻时读的是哪个名牌大学?”
他却说:“我没有上过大学,更谈不上什么名牌。我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担任翻译期间,上过一种特殊的大学,它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教授不固定,它不仅给予我各种知识,而且教我如何做人。”
“那些教授是些什么人呢?”我好奇地问。
他在电话那端如数家珍地说:“作家中有茅盾、巴金、老舍、周扬、丁玲、冰心、曹靖华、戈宝权、赵树理、柯仲平、严文井、季羡林、杨沫……画家中有江丰、蔡若虹、华君武、王朝闻、王式廓、艾中信、亚明、朱丹、邹雅……戏剧界中有阳翰笙、田汉、梅兰芳、黄佐临、赵寻、李和曾、陈伯华、陈书舫……音乐家中有吕骥、马思聪、盛家伦、王昆……”他感慨地说,“给这些杰出的文化界代表人物担任翻译,对于我这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是最好的大学,难得的学习机会。他们广博的知识、丰富的经历、高尚的品德、朴实的作风,以及对我国传统文化的阐述和个人的见解,都在充实我、改造我、教育我。我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师长,暗暗地学习他们的作风。”
我听了,羡慕不已,说:“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学呀!美术史论家迟轲说过,‘所谓名牌大学,首先是由著名的教授组成的。所以说,好的教授就是好的大学。’您好幸运啊!还有没有幸运的事被您遇到了呢?”
他深情地说:“我比较幸运,出生在多雪的城市哈尔滨。雪使我迷恋,雪是我的梦。那儿风景绚丽,像一个神秘的黑土世界。我比较幸运,有一个温馨的家。父母、兄长、妻女——性格不同,但都有一颗善良的心,明事达理,善解人意,敬老爱幼,又经受了政治运动的考验,家庭在风雨中变得更加和谐团结。”
我将放大的照片寄给高莽先生后不久,打电话给他,问收到没有。想不到他大加赞赏这幅肖像,我再次感谢他对我所拍照片的错爱。
当我得知他搬家时运了二百四十箱书到新居时,说道:“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爱默生说‘书籍里的道理是高贵的,老一辈的学者汲取了他周围的世界,经过推敲,在心里把它重新整理好,再陈述出来。它进入到他心里的过程是人生,从里面出来的却是真理;进去的时候是短暂的动作,出来的却是不朽的思想;进去的是琐事,出来的却是诗歌。它过去是死的事实,而现在则成了活的思想。它既可以守,又可以攻;它一忽儿忍耐,一忽儿飞翔,一忽儿又给人以灵感。’您认为哪一本书或哪几本书最重要呢?”
他考虑了一下,说:“应该是字典。我觉得字典中没有废话,没有假话,是科学,是事实,它不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
“您离休后的生活怎样?”我换了一个话题问。
他发自肺腑地说:“离休不外是职务的结束,工作才是生命的常青!”
“那您离休后有没有什么嗜好呢?”我接着问。
他坦率地说:“我这个人嘛,不吸烟,不喝酒,离休后逛书店、买书,成了一种嗜好,甚至有些上瘾。”
“有很多书网上可直接看到,何必去买呢?”我不解地问。
他感叹道:“书,如同电源,永远给人补充电力。我是20世纪的人,与网络陌生,总想和书在一起。生——伸手能触摸到书页,死——能躺在书堆里。”
“回溯您的一生,您最值得欣慰的是什么呢?”我又换了一个话题。
他颇为得意地说:“我没有虚度年华,做了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
“您是怎样走上俄苏文学翻译之路的呢?”我想追根溯源。
他回忆道:“早在1943年,我十七岁时,从俄文翻译了第一篇作品,就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小小的年龄,我岂能理解那篇散文诗中深邃的思想和内涵?然而,正是那篇散文诗引我走上了文学翻译之路。这是一条崎岖漫长艰苦的路。”
“您阅读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有什么感受呢?”我想知道得更多。
他激动地说:“我与俄罗斯有着悠久的情结。俄罗斯作家们所描绘的街道、石砌的城市、贫困交加的人物……都深深地震憾着我的心。”
“您的书房就是一片风景啊!很美。”我在电话中赞叹道。
他亲切地说:“你在我书房里感受到的一切,使我高兴!书房里的书像一条无形的线,连接着我的现在与过去,连接着我久违了的师友。阅读他们寄赠的著作时,我仿佛又在聆听他们的教诲,与他们亲切交谈,向他们求教。看着他们书上的题词,想着他们的形象,我似乎听见了他们说话的声音。”他似乎三句不离本行地说,“这条线还把我与俄罗斯连接起来。那广袤的俄罗斯大地,那茫茫无际的雪原,那婀娜多姿的白桦林,还有那众多的文学艺术大家的作品,让我在书中、在画册里重又会晤。”
“您怎样看待中俄文化交流?”
他用有些严肃的口吻说:“中俄两国文字之交和艺术往来,其根不仅深远,而且经历了风雨的考验。”但他没有展开谈论。
“您事业的成功,离不开家的温暖吧!您的家庭很特别吗?”
他惬意地说:“家庭和睦是国家安宁的因子,也是我做了些工作的因素。我的家和千千万万个家庭没什么两样,如果硬要找出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那么只能说,我的母亲比较长寿,活了一百零二岁。我的妻子双目失明,这种悲剧不是每个家庭都会发生的。我女儿比较孝顺,为了照顾我们老俩口,她放弃了国外的生活。”
“您女儿真好啊!”
他夸奖道:“女儿帮我整理文稿,充当我的秘书。她是我们家里的厨师、清洁工、护工……这是我们的福气啊!”
有时候,我把在摄影之余写的关于文化名人的摄影手记寄给他,有时候还专门写信向他求救。
2007年10月18日,他在信中写道:“来函敬悉。读了几遍,很难说清心中的滋味。我国知识分子是物美价廉之辈,不受些苦,岂有成绩可言?!建国以来,我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你或者还年轻,我也不便多讲。我只想说,在痛苦中产生的作品才更有价值。”“你问我对俄罗斯文学的看法,当然列夫·托尔斯泰是最高峰,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无人能超过他。”
时隔一年,2008年11月23日,我收到高莽先生的来信:
昌群先生:
大札及大作都收到了,最近我的身体不好,所以久久未能复信,请见谅。
你写的论述周国桢教授的文章,拜读之后,颇受教益。我对陶艺毫无知识,你的文章让我深有启发,同时了解了周大师的艺术品味,大师的追求美的精神和高深的修养。
你既能拍出出色的照片,又能撰写专题文章,令人钦佩!
祝你在艺术创作上获得更大的成就!
我打电话给高莽先生,感谢他对我的鼓励,聊了一些较为零碎的事情,不知怎的,也聊到了“文革”。
他颇有感触地说:“像我这样长期做翻译工作的,给赫鲁晓夫当过翻译,给刘少奇当过翻译,给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们当过翻译。在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境遇可想而知,我曾想过自杀,多亏妻子一直在身边体贴、安慰,使我对人生充满信心,伴我度过了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唉!”他长叹一声,继续说,“我不愿意谈论那十年浩劫,因为在那十年当中,我见到了太多的黑色事件、黑色人物、黑色心肠……”他自省式地说,“我见到的不止是外界的,也包括我内心的,见不得人的东西。”
我怕提到他感到不高兴的事情而中止交谈,就问他:“有没有值得回味的事情呢?”
他感慨万千:“我关在牛棚里,和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在一间空屋子里相处。我很荣幸,竟然和冯至、戈宝权、李健吾这样的大学者们生活了一段时间。”
“当时叫‘阶级斗争为纲’吧?”我问。
他有些感悟地说:“在牛棚里受审查的人,把祖宗三代、个人历史剥得光光裸裸,如同在洗澡堂里,身上不留一丝一线,更没有任何遮羞布。经过‘文革’我仿佛又长出了一个脑袋,凡遇到什么事精,不再盲从,开始独立思考。”
“那您住过‘五七’干校没有?”我又聊上了。
他茫然地说:“住过。人世间的变化太多、太快了,‘五七’干校在我的生活中是怎样的一个历程,难说清楚,但我无法忘怀。”言及此,他既激动又有些伤感地说,“中国的历史太悠久、文化太厚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什么事都经历过,在大风大浪中成长、壮大。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刚强的一面,也有软弱的一面,做事时,有被迫或违心的时候。”
我对他谈及郑敏先生曾邀我去她家聊一聊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高莽先生毫不含糊地对我说:“我以为深入地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在不同情况下的心态与表现,可以作为专门的学科,因为这个群体聚集了社会的精英啊!”
2009年,我与他只通过一次电话。他对我说:“昌群,我正在创作一幅画,托尔斯泰将在画中与孔子对话。托翁晚年为了寻求真理开始研究孔子,研究孟子,研究墨子。他的研究是寻找人生的真理。到了八十多岁,他竟在夜里乘马车出走了,想彻底改变他贵族的生活。他离开自己的庄园,后来死在一个车站上。我这幅画的内容跨越了两千年的时空。”
在电话交流中,高莽先生多次对我说过,“人——应当不停地完善自我;情——应当在困难中磨炼。”这是何等精辟的言语啊!他一路走来,领略过人世间的沧桑巨变。在一本书中,他这样写道:“我愿将我剩余的岁月和微薄的劳动,继续贡献给巩固人民之间永远的伟大的友好事业!这是我生活经历的需要!这是我艺术创作的追求!这是我心灵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