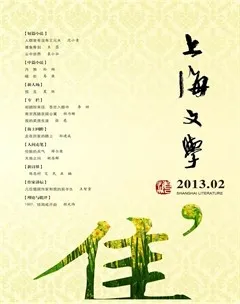走在回家的路上
父亲的追悼会过后没几天,家中收到一份来自台湾的信件。信封上写着“孙宏波先生亲启”。信是台湾高雄的潘胜仁先生写给先父的,内容大意说,他正在想方设法打听我的祖父的下落。
母亲说,这封信要是早几天寄来就好了,你父亲看到一定会安心的……
这就是先父萦绕心头,挥之不去,难以瞑目的心事?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几乎没有与我们说过祖父,没有说过家乡,没有说过他的过去。几十年里,他缄口不语。对我们问长问短,呵护有加,却不说与自己有关的一切。我只知道,我的祖父1952年在家乡失踪,下落不明。几十年里,父亲只有回过老家一次,连祖母去世,他也没有回去。不是他不想奔丧,是上世纪70年代的情势不容他回乡。祖籍浙江永嘉,只是我每次填写履历表时的一个概念。父亲的缄默,我可以理解。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出身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尽管我不了解自己的祖辈,我的人生道路却也被困扰至今。
断层、空白、无根……这几乎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
谁也没有想到,父亲在默默中寻找他的父亲,在我的视线之外。1987年,海峡两岸通邮,也许从那时起,他开始与在台湾的亲友联络。这中间他写了多少信,给了哪些人,现在都无从知晓了。总之,他又多了一条更为直接的寻父途径,而潘胜仁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然而,就在希望初露端倪的时候,他却离去了,没有等到聊以慰藉的那一天。
我代表母亲和弟妹,给远在高雄的潘胜仁老伯写了回信。
潘伯于1990年3月20日回信:
我和令尊宏波君,青梅竹马,永嘉县立一高(瓯江小学)同班同学,他籍楠溪上塘,我家住西溪。在省立福州高中毕业,你父去上海,我到南京升学。1947年我毕业后,晤令尊于上海住所。想不到久别重逢,竟成永诀:我辗转杭州,由浙江省府分派到温州服务,为时甚暂。1948年春到台湾,咫尺天涯,海峡两岸四十多年的隔绝,留下绵绵不尽的千秋长恨,恰如春水东流,再也不会回来了。
又你来信云:祖父孙德馨……我于儿时记得是孙惠民,做过乡长、教员,文笔甚佳。昨天,我走访老乡胡明谆君(律师胡方来子,永嘉中塘人,你祖父与胡氏交往甚厚)。他说,你祖父确来过台湾。我请他在可能的范围内,告诉我你的祖父一鳞半爪、住所、亲属等,以便追查下落。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父亲的点滴过去。高中毕业,他离开家乡,北上求学,至1947年他已在上海立足(我十七岁下乡去黑龙江,二十六岁回上海)。至于信中所语“德馨”还是“惠民”,我想大概是祖父的名和号的分别吧。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线索可以告知潘伯,他知道的远比我们要多。
此后,只知道先祖父曾在台湾,但没有确切的线索。茫茫人海,如何寻找,还是下落不明啊。但于我们心中就此存有了一个希望,期待着祖父浮出人海的那么一天。此间,潘胜仁老伯没有间断过寻人。一年又一年,一日复一日。终于,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七年以后,先祖父终于有了下落。
潘伯1997年1月10日的信:
……孙惠民老先生的下落,经我致台北市温州同乡会刊刊登后,顷接台北市兴隆路二段203巷一号2F孙炎辉先生元月七日来示:
“胜仁先生,今阅温州同乡会刊有关寻人启事一则:孙老于二十多年前逝世于‘云林荣家’(云林荣誉国民之家),并设奠公祭后安葬于云林县斗六市林头里公墓。当时本人及几位乡友参与公祭。至于遗物均由荣家处理……”
随即我写信与孙炎辉先生联系。孙先生1997年4月27日的回信:
关于您的先祖父孙惠民先生来台与去世经过情形大略如下:惠民老早在大陈岛工作,于民国42年即一九五三年随政府军撤退来台。因年逾六十以上自谋生活找不到适当工作,乃向政府申请安置云林荣民之家就养,过着团体生活,衣食住行及日常必需用品均由荣家免费供应,在安置后精神也很愉快。于民国52年间(即1963年)在同乡友好家与我们认识,后来成为我家的常客。每星期日外出看电影后都到我家聊天,用过午餐休息。到下午四时前要回到荣家报到,否则以后不准外出,因为荣家就养荣民有二千多人,采取军事化管理,减少与民众言语不通发生纠纷事件,后来开放管制。我当时在政府机关服务,与惠老认识后因为同乡同宗之谊又是长辈,视为亲人看待惠老。不久得知惠老生病,我与内人利用星期例假日去看过惠老。与我谈话时精神很好,一个人住一房,环境清静,而有医护照顾,当时看起来没有发现有病危之事,不久就去世了。(去世时间已记不清楚。必要时可径向云林荣民之家查证即知)没有留下遗言……
旋即,潘伯于5月4月来信嘱咐:
……查询惠民老伯下落确费尽心思。请记得于二十年前逝世于台湾省云林县荣民之家(组织很健全)公祭后安葬于斗六市(属云林县)林头里公墓,究竟如何处理,何时归葬,请你和令堂暨叔叔们沟通商议决定……
在四十五岁的时候,我终于可以在脑海里勾勒先祖父晚年的生活。可是,他如何去的大陈岛,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留待日后再探了。至于,潘伯所嘱“如何处理”“何时归葬”,其时两岸并未三通,此事咨询无门,一时不得要领,唯久久萦于心中。
1953年,我刚刚出生。先父时年二十七岁。而那一年,父亲的父亲正踏上台湾那一片陌生的土地,进入了他的晚年。
先祖父的下落,如果从收到潘胜仁先生的第一封信时算起,至1997年4月孙炎辉先生来信确认,历时八年。期间,两位前辈在这上面所花费的时间和心血,我等无从想像。个中详情如今已难以知晓,为了同窗之义、同乡之情,他们历经坎坷的搜寻,如今终得善果,得以告慰先父的在天之灵。
将时间再往前推移,自1952年先祖父失踪之时算起,直到1997年得知他的下落,已然四十五年。
漫长的等待和煎熬,成了祖辈和父辈内心无可言说的隐痛。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父亲无法向旁人甚至亲人讲述此事。远在台湾的祖父,又何尝不是欲说还休呢——现在才知道,他写在个人资料上的亲人名字大多掐头去尾,唯恐有所牵连,祸及亲人。如此这般,哪里还谈得上呼号、张扬亲人离散的悲哀。
相比倾诉,隐痛更易于摧残身心。或许,祖父和父亲先后在六旬出头的年纪过早地往生,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从1997年4月27日起,我知道了,先祖父长眠在台湾斗六市的云林荣家的墓地里。自此,台湾与我有了一种亲情和血缘的联络,相伴牵挂,却又遥不可及。
又过了十一年,2008年7月18日,台湾旅游正式向大陆居民开放。
2009年4月,四弟建平随旅游团赴台,随身带上了云林荣家的地址。既然去了台湾,去看一看先祖父当是情理之中的事。
旅游团有既定的行程,并规定不得个人擅自行动。行程中的阿里山景点,离斗六市较近,大约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四弟入驻景点的当晚,便与领队的导游私下商议,第二天一早请假外出。毕竟人伦事大,导游同意了,但限定必须在八点团队出发前归队。
天气微明,四弟打车直奔斗六,六时许找到云林荣民之家。
荣家还没有开门,门卫听了四弟的来意,表示需等至八点,办事人员上班以后,才能帮助查找。四弟等不及了,在问明了墓地的所在以后,便径自前往寻找。他原以为,先祖父有名有姓,只要一一查看墓碑上的文字便可。到了墓地,放眼望去,微明的天色下,荒草连天,阴气森然。他请出租车司机等在墓园门口,自己一头扑进去,拨开齐腰高的荒草,一一查看墓冢石碑上的文字。
辨看了十几二十冢,石碑上青苔覆盖藤蔓缠绕,依稀可辨的墓志上刻着的,全是陌生的亡灵。草叶上的露珠打湿了他的衣裤,泥土的腥气扑面而来,他隐隐觉得,这样漫无目的地搜寻,注定是徒劳的。偌大的墓地,一天两天似乎也看不完全。他站起来,环顾四周,盘算着该如何办才是。晨间的薄雾在墓地上飘浮,四周空寂无声寒气彻骨。他突然感到了害怕,陌生和凄惶弥漫全身。他从草丛中退出来,回到墓园门口,面朝着墓地,跪地叩头,祈祷先祖父和众往生者的亡灵安息。时间已经不早了,他必须赶回阿里山。
四弟虽然没有如愿亲手祭扫先祖父的墓地,但也有了实质性的收获,拿到了云林荣家的联系方式:云林县斗六市荣誉路某号,以及电话号码。
2010年,母亲病逝。至亲的亲人先后离去,让人对生命的传承有了更为切身的体验,对家族概念的认知更为直接和真实。从这一年起。我便开始与荣家电话沟通联络,打听确认先祖父是否确实落葬在其处。幸好荣家数据齐全,承接此案的章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云林荣家确实有孙惠民此人,祖籍为浙江永嘉,且往生之年亦为1963年,现葬于云林荣家忠灵祠内。
直到2011年春,我们兄弟三人去永嘉老家扫墓,看到祖母孤身一人栖息山野,想到祖父在台湾孤身一人,一无家眷二没亲族,两人隔海相望,内心真有无法言说的悲凉。商量以后,我们尝试启动迎回先祖父骨灰的程序。
此后的两年时间里,此案的经办人员三易其人,先是章先生,次为杨先生,最后为陈先生。每次通话,这几位都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的问题,并没有一否了之,也不耍官僚推手,双方交涉始终处于平等讨论的氛围中。即便有时我心生烦恼口出怨言,他们也好言相劝,并不恶语相向。然而,有一点他们始终坚持,即从不主动提供我祖父的资料。也许,他们怕的是当事人进行反向操作,按图索骥,做出不真实的证明来。
按照相关程序,首先要做的是亲属关系的公证。
我无法直接认证祖父与我的关系。在我的人事档案和户籍关系的家庭成员中,没有有关先祖父的丝毫记载,单位里只能出具我与父亲的关系证明,然后再从父亲那儿开始寻找线索。在先父生前工作过的上海房屋设备公司,人事干事从他的档案里,找到了两条有用的证明:
一、父亲于1955年填写的个人履历表中,写有“父亲孙惠民,逃亡在外未回”;二、在他1988年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中,写有“父亲孙德馨,原上海市伪地政局职员”。
据此,父亲的父亲与我挂上了钩。
我们已经知道,先祖父名德馨、字惠民。德馨是家族谱系中的排行,惠民是外人对他的称呼。惠民便是德馨,义同意合,这与旧时名与字的关系相吻合。父亲在他的家庭关系中用不同名字记载他的父亲,当是情理之中,并无错处。令人费解的是,他为什么在1955年写了孙惠民,到了1988年却写了孙德馨,而不是名和字一并写上。这里一定有他的考虑。在我的印象里,只听父亲提到孙德馨,却不说孙惠民。后来,在祖籍调查时,除了族人,别人提到我祖父时,一般都称孙惠民。可见,名和字的用法好像是内外有别的。
所幸,父亲在不同时期的履历表中,分别提到了祖父的名和字,才为日后的亲属关系公证奠定了基础。
循着父亲提供的线索,我来到上海市档案馆,调阅民国时期留下的户籍口卡。这条途径还是一位朋友指点的。但我最初对此并无足够的信心。这套户籍口卡是民国政府1948年建立的,当时只要求市民自愿登记,公职人员登记的为多。
我出示身份证和父亲单位所写的证明,提请工作人员查验。不一会,“孙德馨”的口卡打印出来了:
孙德馨,民前15年8月15日出生,祖籍浙江永嘉,地政局,现居厚德街一弄一号十六区三十六保九甲三十五户……
这张口卡复印盖章后,也成为了身份证明的一个环节。
这份证物虽然在公证环节里显得并不重要,因为有了我和父亲两个单位的人事证明,公证人员也可出具公证书,但于我来说,那却是真正意义上与祖父生平有关的实证,起码是祖父自己的陈述。口卡上记载的厚德街已经找不到了,上海有一条厚德路,不知是否就是那条街;保、甲、户的概念于我也已疏离陌生。这些内容在父亲的档案和乡人的传说都没有提起过,是岁月的风霜把一切打磨得模糊不清,还是刻意的隐瞒?大致可以作这样的猜想:父亲在1955年填表时,不写孙德馨而写孙惠民,也许是不想让人知道祖父的那段经历;到了1988年,那一切已不成问题了,他才用了家族中通用的名字。
我不知道,像户籍口卡之类的老档案,还有多少种类,如果大众能清楚它们的存在,并加以利用,许多与祖辈相关的史实将得以证实,可避免了多少讹传啊。
与此同时,我还请家乡渭石村村委写了我们祖孙三代人的关系证明。
我拿着这几份盖有红泥印章的证明,去了上海东方公证处,办理亲属关系证明。
公证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加上按台湾方面要求填写的“文书验证申请书”,一并用挂号信方式,邮寄至“台北市民生东路三段一五六号十七楼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办理验证手续,随信附上十五美元(正本十美元副本五美元)的验证费用。一个月后,验证盖章通过的证明书回到我的手里。以后,我便用这份亲属关系证明,于2011年9月16日向云林荣家正式提出领取先祖父灵骨的申请。
原本以为,有了亲属关系证明,接下去的手续可以向前推进了。然而,半个月后,荣家返回的公函,像一盆凉水,一下子浇灭了我内心的希望之火:
经查,台端来信检附(2011)沪东证台字第1748号经海基会验证亲属关系公证书,登载孙君之出生年份1897年与本家忠灵祠安厝孙惠民君灵骨之出生个人资料不符,请再查明补正……
我当即电话向陈先生咨询。他的回答较为详细:亲属公证中的内容,除了姓名和籍贯与荣家的档案是吻合的,其余的出生年月、亲属姓名都对不上。
我问他,我该怎么办才好?
他说,凭现在这点证据肯定不行。
我有点恼火:不管有多难,我也要办成这件事,不行的话请律师打官司。
陈先生倒是不愠不火,说,这样吧,你那边再想想办法,多找些旁证,我想办法去陆军那边找找资料。我们一起努力吧。
2011年4月,我和建伟、建平弟兄三人,来到祖籍地永嘉县渭石村扫墓。
年前,堂叔孙宏海托孙宏廉传话,说起修缮祖坟的事,需要我们去商议。孙宏廉与我四十年前同在黑龙江省沪嘉农场下乡,他是下放干部,我是知识青年,他在三连,我在一连。他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向我提及。那个年月,族人的概念并不为社会所公开容纳,加之我祖父的成份是地主,一般人不会主动上来攀亲,当然,我也没有主动向他打听。大家碰到,只是点头打个招呼而已。当年我只知道,他的名字中也有一个“宏”,也是永嘉县人,好像与我父亲同辈,具体的亲疏程度并不清楚。
前几年,村里的孙氏族人修家谱,来信告知,并收了每户二百元的修谱费。这次回乡,看了家谱,我们才彻底搞明白宗亲族人的关系。
事实上,宏廉叔与我们是未出五服的叔伯亲族。他的祖父和我的曾祖父是亲兄弟。那一辈有弟兄四人,我的曾祖父是老二,他的祖父是老三。这弟兄四人,同心协力,盖房置地,读书求仕,在当时村里也算是闻达富裕人家。所以,他们的后人在土地改革划分成分时,不是地主就是富农,房屋田地大都被没收。至此,孙氏弟兄四人这一脉在村里日渐衰微。
孙宏海与我们则更近一层,他的父亲德棠与我祖父是两兄弟,德馨老大德棠老二。两兄弟父母的墓址,还是祖父生前在家乡时选定的。曾祖父母的墓地以下,预留了儿子孙子辈的墓穴,一层一层阶梯似的排列。此时,这片墓地已有了一定的规模。宏海叔的意思,两家合力将墓地作一些规划和修缮。
这次回乡,村里盛传着祖父在台湾的故事,言之凿凿地说,祖父在台湾当了官,建立了新家。由于闭塞,乡人的信息大多是口耳相传,每一个传播者有意无意会在某一点加入自己的臆想。传说经过无数遍的改造和猜想,与事实差之千里。说故事的人也不认真想一想,如果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两岸开放这几年了,祖父的后人怎么的也该回家认一认祖宗吧?我们没有着力去纠谬,因为一旦为传说注入新的故事,很可能会演绎出更大的谬误。
在族人的记忆里,先祖父孙德馨曾当过乡长、小学校长,兼擅歧黄之术,常以医生之职随渔民出海。以常识而论,先祖父当年应该算是一位读过点书的乡绅,经常出头露面为乡人做点事,族人所说的那些事迹,当是他日常应尽的义务。至于那些旁人所冠的名号,大多是世道轮回以后的口耳相传,并无书面文字佐证。
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祖父出走以后,并没有减轻家人的“罪孽”。作为“地主婆”的祖母,在每次运动中都要承受冲击。为了躲避无妄之灾,她曾一度来到上海,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依稀还记得她的模样:高高瘦瘦的个子,说一口很难听懂的永嘉话,一对缠裹过的小脚,走起路来身子的上下两截会错位摇摆,可以用四个字“摇曳婀娜”加以描写。20世纪60年代期间,“四清运动”开始后,村里的公函追到了上海,把她当作逃亡地主“揪”了回去。从此,她再也没有离开过渭石村。
祖父和祖母共有六个子女,三男三女。我父亲十来岁就外出求学,从瓯江高小到福州一中,抗战时间学校迁往金华,毕业后来到上海,在立信会计学校勤工俭学,后进入上海市房地局任会计。虽然身处外地而未承受正面的冲击,但作为内部控制的对象,他的仕途全然中断。二叔宏治,在家乡念完小学后也来到上海,由我父亲供养,读了高中。他就读于上海市南中学,学习成绩出色,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高考志愿为清华大学。临考前,家乡一封举报信投到学校,说他是地主的儿子。就此,他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被分配到安徽芜湖港务局。他生性孤傲,自信会出人头地,工作之余就读皖南大学夜大学数学系,成绩出众。教授曾有意招他为婿,“文革”始,这段姻缘无疾而终。他一如中学时那般热衷社会活动,“文革”后期被抽调到地区行署,参与整顿工作。人生的起伏波动,使他对政治产生了幻觉,最终臆想成病,患上了幻想偏执症。此后二十余年,他奔波于上访之路,人生婚姻无着,衣食居所无定,身体日渐衰败,终因心脏病发作,殁于家乡。三叔自幼失学,因在家乡倍受歧视,独自一人外出各地游荡。有人说,他跟随养蜂人随四季迁移,有人说,他当了弹花匠,走街穿巷,为人翻新棉花胎。无人知晓他的确切下落。偶尔,他也会在家乡出现,倏忽又无影无踪。
三个姑妈也因为成分不好,在家乡竟无有好人家愿意迎娶。大姑60年代来到上海,住在我家,躲在亭子间里,终日绣花为生,中年后嫁了一个四处漂泊的水手,五十出头,便得了胃癌离世,无子无女,连葬在哪里都无人知晓。二姑和三姑,因家庭成份不好,只得将就着,嫁给了祖母那一族里的亲戚。
这次回乡,我们去探望了三姑妈。她已神志痴呆不明人事。知道我们要来,表弟家人已给她换了整洁如新的外衣。被春日的阳光照着,她木木地坐在自家门口的廊檐下,因为我们的到来,有点浮肿的脸上浮现出木讷的幸福感,眼神却是虚浮着。她的手,温暖却无力,捏上去像一团棉花。不管问她什么,她都答以“啊……”我走进她身后的住处,昏暗的房间里,弥漫着潮湿的土腥味,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床上的被褥凌乱地堆放着。一只硕大的老鼠沿着墙边从容地游走而过。半年后,三姑妈便去世了。
老家的祖屋如今已荡然无存。从宏海叔的口中得知,祖屋如他家现存的旧屋相似——当年先祖父兄弟俩各盖置了一套。典型的浙南民居:一个四方的院落,由门台、厢房、正房组成。三级踏步的院门,围墙用青砖砌筑。迎门五间正屋,东西各两间厢房,上下两层楼,都为传统的木构建筑,柱下有青石鼓形柱础。土改后,祖屋在十几年中先后搬入了六户人家,祖母被挤出家门,到两个女儿家中轮流居住。她老人家于上世纪70年代病逝,为她送行的人中,三个儿子均没有到场。随后,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把莫名的大火把祖屋烧得只剩下一堆砖块瓦砾。一户乡绅人家,就这么完全彻底地在渭石村消失了。
墓地上,堂叔指着祖母边上的空穴说:这是你祖父的地方。你祖母身前受尽了苦难,身后还是孤苦伶仃。如果你祖父能回来,一家人团聚,也可以给她一点安慰。
祖父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人孤魂空悬,寄居他乡。
这一次上坟,陪同我们的还有一个年轻人孙功德。一直以为他是堂房里的一个族人,没想到,在去坟山的路,他略带神秘地自我介绍说:你们的祖父也是我的祖父呀。我以为他在开玩笑。谁知,他见我不信,加强了语气说:真的,我父亲就是祖父最小的儿子。
这么说来,先祖父除了三子三女外,还另有子女。
为了明白地确认,我问:是亲生的吗?
他说:亲生的,只是和你爸爸同父异母。
我更为惊讶,从前并没有听说过这回事。经过宏海叔的介绍,这才理清了其中的来龙去脉。
原来,祖父在家时,曾与祖母的随身女侍暗通款曲,生有一子。事情暴露以后,祖母不愿接纳这对母子。女侍带着孩子另嫁了他人,祖父舍不得孩子,便将儿子收回,过继给同族的兄弟,延续了别人家的香火。这母子俩从此不再认祖父这一门人。此事家里人都讳莫如深从不提及。收养的人家也不愿让人知道孩子是别人的骨肉,尽量甚至禁止提起这层关系。如此,便疏远隔膜了。时至今日,祖父外室的儿子也有了三个儿子。
时过境迁,如今上辈子的人先后过世了,毕竟血浓于水,自己的亲祖父还是要认的,只是尽量低调,避免收养人家的难堪。乡里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对于人伦次序还是很讲规范的。
从他们的嘴里,还听到了星点祖父的消息。据说,祖父出走前夕曾回家偷偷与家人告别。他从祖母手里拿了家中仅有的三块银元;随后又去见了二祖母,她也给了他三块银元。与亲人告别以后,他趁着晦暗的夜色,和其他两个人会合,来到海边,租了一条小船,不顾风急浪高,直奔大陈岛而去。
在此之前,我们一直以为,祖父是以随船医生的身份,在随渔民出海途中,被国民党军队劫持,去了台湾。
两种说法,孰真孰假,或是真假掺半,由于当事人的缺失,无法确认此事的真实性。家乡的人事缺少书面记载,大多口传,许多想当然的猜测结果往往被当成了现实。
不过,我还是宁肯相信确有其事。唯其如此,祖父才显得有血有肉,不然的话,他连亲人都顾不上见面,就踏上了遥远的不归之途,不免太过残酷了。
这一次回乡,我们带了相机,拍下了墓地上曾祖父和曾祖母的墓碑:
孙公懋栋 元配谢氏 德馨陈氏 德堂陈氏 之墓 公元二○○六年春月 吉立
随后,我们又去了家谱持有人那里,查看了相关的记载,并拍照留底。
当时,拍下这些资料,只是想为记忆留下一些佐证。没有想到,日后向云林荣家确认身份时,家谱和墓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实际上,无论在我们孙辈还是云林荣家,在亲属关系公证书出示以后,都认可了孙惠民就是我们的祖父,因为姓名籍贯都对上号了,证人的证词也都指向明确,况且在荣家没有第二个永嘉人孙惠民。问题是出生年月等细节上对不上号,他们不敢贸然认可。
第三位承办此案的陈先生,曾在电话里谈到过荣家的难处:一旦将灵骨移出台湾,如果日后再有人来主张权利,他们会因失察而被追究责任。到那时,有多少钱也赔偿不起啊。
为了充实资料,我将手头所有关于此案的书证,一并汇总寄给了荣家。这些书证包括:
一、亲族关系公证书(原件);
二、渭石乐安孙氏宗谱中相关页面(复印件);
三、先祖父父母墓碑照片(影印件);
四、先祖父在上海时的口卡(影印件);
五、台北孙炎辉先生的来信(复印件)。
然而,这些佐证除了加深了荣家对此案的印象,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却未能最终解决问题。因为,在关键点上的分歧始终无法消除。在随后的日子里,我隔三岔五与陈先生通电话,但案子还是搁置在那里,没有进展。
2011年春,在家乡扫墓后回到上海,为迎请先祖父回家一事,我打电话给高雄的潘伯伯,想听听他的意见,并请他代为联络孙炎辉出面作证。自1997年以后,我们便断了联络。所幸他在信上所写的电话没有变动,接电话的人是潘伯的大女儿潘阜萍。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半年前,潘伯伯往生了。
真是人生无常啊。我曾想过,将来有一天到台湾祭祖,到那时一定去探望潘伯伯。他帮我们找到了祖父,我们一定要报恩的。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天即将到来的时候,他却撒手西去了。此情此景,让人情何以堪。
那种痛是彻心透骨的。年轻时,总以为还有将来;中年时,更多的是看顾眼前;等到意识到已时不我待了,一切都已悄悄离去,再怎么做也无法弥补了。
潘阜萍女士是屏东县东港高中的英语老师,快人快语,豪爽热心。她委托在台北的同学——一位加拿大籍华人,去寻找孙炎辉老先生。九月,那位同学回台北,即去拜访老先生。孙炎辉已搬离原址,住到女儿家中去了。台北的同学打听了地址,辗转找上门去。老先生九十多高龄了,听人问起孙惠民,马上说有这个人,民国五十二年就去世了。她的女儿为了避免父亲过于激动,没有让谈话继续下去,也不愿告知电话号码,说是她父亲没办法听电话,只给了一个通讯地址。得到这个信息,我随即给老先生写信,信寄出以后,石沉大海,渺无音讯。
迎祖父回家的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却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这种绝望是幽昧无助而又无可奈何的。对此,高雄的潘老师曾经在信中这样安慰过我:“有时我心里猜想会不会孙爷习惯台湾生活,也有好兄弟在这里,所以没想要回大陆……”有时想想,冥冥中有些事是命中注定,说不上是祸是福。设想当年如果祖父没有逃亡台湾,也许不会有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他很可能早早地被动荡的政治运动吞噬了。许多像他这样身份的人,大多在当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抹去了,筛孔之密,几乎无一漏网。乡村尤甚于城市。逃亡台湾固然凄惶,好歹还保全了一条性命。他的晚年孤身一人生活在荣家,还有闲情与忘年之交孙炎辉下棋聊天,可见已经习惯了云林的生活。
不过,故乡和亲人肯定会在祖父的睡梦中不时地出现,或许还梦到了子孙绕膝一派家庭和睦气象。醒来以后,孤灯长夜,与梦中景象形成强烈的反差,陡添怅然,老泪湿襟,悲摧心痛。天长日久,死神便提前到来了。
我还是不甘心放弃,与云林荣家保持着联络。
2012年3月,荣家的陈先生提出了一个解决此案的途径:从荣家存档的资料中发现,写信给我告知孙惠民下落的孙炎辉,就是当时先祖父丧事的家属方,身份是“侄子”。荣家需要孙老先生的电话,获得到他的亲口证言,便可定案。
虽然孙炎辉的信中也提到了,他和我祖父交往的细节。可这个关节,我还是头一回知道!可以想像,他们两人当年来往的亲密程度。好在他还在人世,可以证明祖父的身份。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3月6日,我写信给潘老师,请她帮忙,烦劳她的同学再去找一找孙老先生。
3月10日,潘老师回信说:她和她的同学,讨论以后,认为孙炎辉久病卧床又严重耳背,接听电话作证言有困难,不能寄予太大的希望。她们提出了另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她们两位愿意在必要时,共同做担保,证明某些行政程序,或亲自跑一趟云林,代为处理事宜。
回想一年多来和荣家的来往,我发觉,除了一纸正式的公文,几乎每次都是我去电话,他们从没有主动和我联络过。而同样是这件事,台湾的公务人员和百姓之间就会有来有往,充满信任。个中原因,也许要追究到两岸间的隔膜,加之鞕长未及,万事还是小心谨慎为好。
3月14日,我将手头现存的潘、孙两位伯伯来信扫描影印,电邮传给潘老师,以为凭证。
即日,她就给云林荣家的陈先生发了信函,以后,高雄潘家与云林荣家开始直接电话往来,有事也是他们之间先商量。潘老师和陈先生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且同门同派,两人在这方面有共同语言。
潘老师的同学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第二日(15日)中午,带着由她拟定的认定书,前往孙炎辉家,想让老先生作个书证。
不幸的事再一次呈现:孙炎辉先生已在同年的一月份往生了。
为时已晚,时间正在抹去一切。无数人间的憾事,就这样铸成了。人生就像在和时间赛跑,输家永远是人生。偶尔的胜利,便是人生的功德。
然而,所有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由于我们锲而不舍地追寻,加之台湾潘女士和她的同学的出面担保,荣家那边也在积极行动。先祖父在荣家属自费养老,相关证据匮乏,无法与我们新提供的证据相对比,承办此案的陈先生便将之报陆军核实档案。
4月19日,在与云林方面通电话时,陈先生告知我:从陆军那边的证据看,相符的地方还是很多的。比较有力的佐证,是先前永嘉渭石孙氏家族的谱系,先祖父的母亲谢氏和他的弟弟孙德棠,都在资料中对上了。他正在根据陆军的资料向上级写报告,办理审批手续,可能还要两三个星期。这期间如有疑问,他会打电话给潘老师询问相关事宜。
听到这个回答,我是又高兴又惶恐,一方面事情终于向前进了一步,另一方面审批会出现何种结果,实在没有把握。
5月16日,接高雄潘老师电话,说荣家陈先生已通知她,批文很快就会寄出。
第二天,我不停地给云林方面打电话,直到下午五时,才接通云林陈先生的电话。他所说与潘老师相同,并说将相关的表格寄我,办理手续。陈先生热心助人,亦有担当。由他接手这个案子,用他的话说是一种缘分。通话的最后,他说个人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内心“咯噔”了一下,唯恐案子又横生枝节。
原来,他的请求是希望我们能念诵《普门品》经,回向先祖父,以求菩萨保佑。
这哪里是个人的请求,实在是施于我们的好处。
我从网上下载了经文,并向同为佛教徒的潘老师请教如何念诵才是正途。
我平日虽入乡随俗,礼佛敬佛,但不谙佛法,平日听人说起流行的佛经,大抵是《金刚经》、《心经》、《大悲咒》,学问深一点的会说到《法华经》、《楞严经》、《圆觉经》,很少有人提及《普门品》。第一次接触《普门品》,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比较那些释义的经文,它更倾向于直接的诉求,更接近宗教的原始执意。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爱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实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如此而下,列数人间苦难,皆因念“观世音菩萨”而得解脱,夫复何求。
有无宗教信仰,在处理问题时,就会有不同的行事方式。
2012年6月,上海、北京、广州三地率先开放台湾自由行。7月14日,我们兄弟三人,从上海启程飞台湾,迎请先祖父的灵骨回家。
7月16日晨,在高雄的佛光山,我们由潘老师陪同,拜谒了潘胜仁伯伯的灵位。他面带微笑地注视着我们,清朗的脸庞上并没有丝毫责备的意思,而是透出一种欣慰。为了儿时朋友的嘱托,他努力了近二十年,终于迎来了今天的圆满。在我的内心,却是满心的愧疚:这一天哪怕再早一年到来也好,那时他还一如往常的健康。病魔是突然来临的,仅仅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便阴阳两隔了。从他以往信里那些充满悲怆的言词中,我已隐约感到,他有很多很多的话,要对我们说。有些话他深藏于内心,等着有一天说给家乡的亲友听。
可是,我们来迟了。
潘伯伯留在台湾,是大时代对渺小个人的一个不经意的嘲弄。1948年,已在温州当了警察的他,到台湾旅游度假,留恋于山水海天之间。不想,还没等他起程回家,海峡两岸已势同水火,划水为界了。身不由己的他,只得在台湾留居下来。原以为世事还有转圜的余地,隔几年战事平定或许就可回家,与亲人团聚。三年五年过去了,局势不但没有转圜,反而变得完全隔绝,让人彻底断了回家的念想。他只得从长计议,娶了苗栗县的一位客家姑娘为妻,从此在高雄安下家来。
从结婚的那一天起,他瞒去了在温州老家还有妻儿老小的事实。在填写家庭成员时,他还将父亲的名字潘金岩改为了“潘锦严”。
潘老师在描述父亲的心情时说:“我父亲经过烽烟四起的年代,常避重就轻地叙述他的故事,一直压抑他的情感,不敢表达对家乡的思念和关心,‘擅改’我祖父的名字(潘金岩改为潘锦严)……命运造化由不得人,他们都在卑微无奈地承受……”
直到两岸三通以后,他才道出了真相。原来,他在家乡浙江永嘉本溪乡外垟村还有妻有儿。在得知这一实情后,现在的潘妈妈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大度地安慰他,错在时势而不在他。她不但认了远在永嘉当农民的大儿子,还陪潘伯伯回家省亲。老俩口在商量将来归宿的时候,潘伯伯表示了留在台湾与潘妈妈在一起的愿望。
对潘伯伯来说,他在台湾已扎下了根,六十年的人生经营,一女两子,儿孙满堂。永嘉成了祖籍地,高雄已是故乡。这是命中注定,再也难以割舍。
7月18日,潘伯伯的大儿子潘南城开车,陪同我们来到云林荣誉国民之家,领取先祖父的灵骨。
直到此时,我对台湾的荣民之家才有了直观的认识。这个机构实质上是一个军队养老机构,规定六十岁以上无家眷无亲属可依靠的退役军人可申请入住,荣家负责养老送终。这样的机构在台湾共有十八家,分散在全省各县。荣民之家极盛时期,与散布各地的眷村一起,成为台湾特有的社会现象。随着岁月的流逝,荣家也逐渐淡出世人的视野,居住其间的大多是八旬以上的老人。这些人的祖籍虽然大多在大陆,然而时间抹去了无数曾经的印迹,他们也年迈得无力再去寻亲。家乡的一切都留在记忆里,只有在明月当空长夜无眠的时候浮现,慰藉一个孤独飘零的心灵。
云林荣家的忠灵堂,祖父这个案子的承办人陈先生已在等待我们。这是一个多层塔式建筑,绿瓦黄墙红柱,远远望去富丽堂皇。塔里面安放着近千座“荣誉国民”的灵骨。我跟随陈先生的身后,走进底层的灵骨安放室,在一排排如蜂窠似整齐排列的灵位里,找到了先祖父栖身的格子。再次确认无误以后,我们取出了黄色鼓形的大理石骨灰罐。
祖父的灵骨罐供奉在灵塔正门大厅的长案前,我们三兄弟长跪三叩头,然后用黄布包裹起来,双手捧着,离开了他栖居多年的地方,开始了返乡之旅。
临行前,我们还在忠灵塔前焚化了纸钱和锡箔,送给多年与祖父为伴的亡灵。当年,随国民党退据台湾的六十万士兵,现在有几人安在?他们中除了至今还健在的和成家的,多数人已作古成灰,寄居他乡。想像一下,遍布台湾十八家荣家的众多灵塔,数十万无家可归的亡灵,景象可谓惊心动魄。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中的大多数势将成为永远也无法回家的孤魂,成为骨肉离散历史大灾难的见证,永远地驻留在台湾这方土地上。
亲历寻亲过程,每每想到这些,泪水就会盈满眼眶。两岸开放已有多年,早日让那些被时代挟裹的个体回到故士亲人的怀抱,让一个个在亲人眼里只是几个冰凉的汉字的先辈,成为鲜活的真实存在的生命,似乎不应只是民间自发的行为,也应成为两岸当政者优先考虑的问题。人伦为大,时不我待啊!再也不能让那些被时代大潮裹挟的百姓,身前受尽背井离乡之苦,身后留下有家不能归的无尽遗憾。
h7d5HsQKpsEvn5MBqqHo8xXYd+l34EEaKz1pNxU8Or8=在办理相关手续时,我看到了先祖父存档的资料,才发现了两岸之间证据上不相对称的地方。正是这些不相符合的地方,造成了云林荣家办事人员的困惑。
祖父的户籍誊本上写着:
孙惠民,男,出生年月:民前十七年八月十五日。
斗六镇林头里拾邻公正街四号。
民国四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由台北县内湖乡紫阳村二十邻后陆八号迁入。
父:孙国栋 母:谢氏
教育程度:浙江省立师范毕业。
职业:云林县税稽处临时雇员
本籍:浙江省永嘉县
民国五十二年五月十九日死亡。
首先是关于祖父的出生年份,在上海1948年的户籍口卡上写的是“民前十五年”(即1897年),而在台湾的户籍上写的却是“民前十七年”(即1895年),日期都是八月十五日;其次是我的曾祖父在家谱上名为“孙懋栋”,到了祖父的笔下,“懋”字换成了“国”字。两相对照,差错是如此的明显,难怪行事严谨的官方机构难以定案。然而,错得又是这样的有“章法”,改了年份对了日月,姓名中间动一个字,其他的信息依然固定,以正常的逻辑便可推出这是同一个人。
祖父在世时,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改动,内在的动机已无从核实了。不过,联想到潘胜仁先生也有同样做法,将自己父亲的姓名改动了音同字不同的两个字,大致可以推测,这是当年这些从大陆来到台湾的人一种自我防范的手段。他们既怕连累家乡的亲人,又怕断了自己的根,处心积虑,左右为难,才有如此流行的做法。老百姓连父辈家人的姓名都不敢明示,可见那年月的世事动荡是何等诡异。如此易姓换名,又加剧了社会的混乱,以致延祸至今。
综合孙炎辉伯伯的信和云林荣家的档案,先祖父在台湾踪迹,可以大概梳理如下:
1952年随渔船到大陈岛,第二年随国民党军去台湾。在台北曾居住于台北县内湖乡紫阳村二十邻,工作单位待查。1959年12月迁往云林县,居于斗六镇林头里拾邻公正街四号。曾在县税稽处当过临时雇员,后以自养身份入住云林荣民之家,军衔为准尉(最低一级士官)。1963年5月19日因脑溢血不幸去世,安葬于林头番子沟公墓。1979年,遗骸火化后安放于荣家忠灵堂内。在台湾共计六十一年。
然而,还有众多疑点没有释然,诸如:先祖父离开大陆,是自愿流亡还是在海上被抓了壮丁?在台北期间,他从事何种职业?晚年为何要迁居云林?等等,都有待日后探查了。或许,这些疑问将永远成谜,和他的灵骨一起深埋于地下。
这是一个平民在乱世中被注定的命运,坎坷、屈辱而多舛。
2012年7月17日,先祖父的灵骨离开云林,7月18日经台北回祖籍地浙江永嘉渭石村,7月20日安葬于群山怀抱的祖坟中,与他的父母以及妻子儿子弟弟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