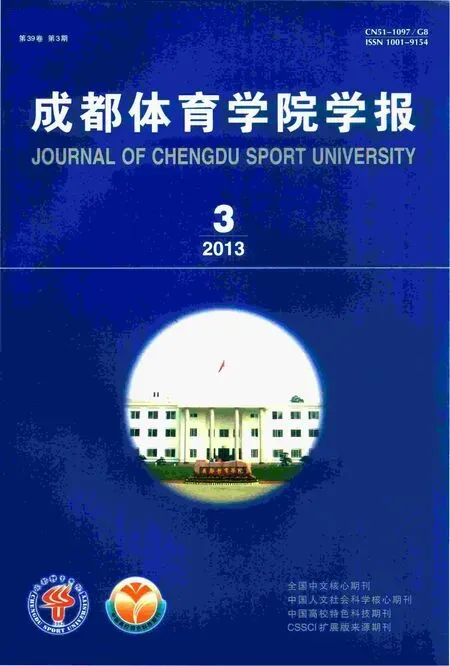中国古代击壤文化初论
张宝强
(咸阳师范学院体育系,陕西 咸阳 712000)
据魏晋时期学者、医学家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该老人所玩的游戏叫做击壤,所唱的歌叫做《击壤歌》。击壤是中国目前文献所记载的最早的游戏,被称为“中国游戏之祖”,《击壤歌》被称为“中国最早的诗歌”[1]。“击壤”一词中,“击”意即“打击、投掷”,“壤”即“打击、投掷”的目标或工具。通过对最古老游戏——击壤的全面解析,可以管窥中国古代游戏的基本特征及其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有助于了解和发掘中国传统的游戏和体育文化。
文化圈层理论认为,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器物层、制度层、精神层三个层面[2]。器物层是文化的物质外壳或载体,制度层是文化的组织、规范或人的行为方式,精神层是文化所蕴含的观念或思想。以下按照这三个层面,对我国古代击壤文化进行初步解析。
1 击壤器物文化
器物层是文化的最外层部分,是构成文化的骨架。击壤所用的器具及其材料,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辞海》中说:“壤,泥土的通称。”远古人们在地里劳动,在劳作之余常用土块进行抛掷、嬉戏。因此,击壤游戏最初采用的器具可能是普通的土块[3]。另外,东汉刘熙撰写的《释名》中说:“击壤,野老之戏,盖击块壤之具,因此为戏也”,也揭示了击壤开始可能是打击或投掷土块。至于后世用各种材料制成的“壤”以及各种玩法,则是击壤这种游戏继续发展的产物。
汉代的击壤主要以木棍(或木板)为材料。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人完成的《太平御览》对此给予了记载(《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五·工艺部·十二》)。该书在“击壤”部分引用了东汉邯郸淳《艺经》中的一段资料:“壤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四,阔三寸,其形如履。”大致反映了汉代时期击壤的用材情况。
以砖块、瓦块或石块为器具的击壤。古籍《丹铅余录·卷九》(明·杨慎著)中记载:“宋世寒食有抛堶之戏,儿童飞瓦石之戏”。这里的“堶”,据专家解释,是指儿童抛掷游戏中用来抛掷的砖、瓦、石等小块物[4]。可见,宋代时流行于寒食节、清明节前后的“抛堶”“飞石”等,是用砖块、瓦块或石头玩的,是击壤游戏的发展形式。
以木棒为器具的击壤。明清时期,又出现了木制的击壤器具——“棒”。明人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中记载:“二月二日龙抬头……小儿以木二寸,制如枣核,置地而棒之,……曰打柭柭。古称击壤者耶。”表明所用的是“木”、“棒”两种木制用具。清代周亮工的《书影》一书介绍了当时南京儿童玩的“击棒壤”:“长尺四者,盖手中所持木;阔三寸者,盖壤上所置木……”表明击壤的工具分别是“长尺四者”“阔三寸者”两个长短不一的木棒。这和近现代在我国部分地区仍流行的“击打”“投掷”类游戏(如打梭、打缸、打尜等)所用器具十分相似,也与西方的棒球用具相差不远。
由此可见,击壤所用器具大致经历了土块、砖块和瓦块、木棒等形式的演变,形状大体由“块状”向“棒状”进化,变得愈益规则、美观,材料也更加轻巧、讲究。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所用材料、工艺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游戏器具也随之发生改进。
2 击壤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是文化的中层部分,是构成文化的血脉,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区别的主要特征之一。分析一种游戏或民俗,应对该项活动的时间、场地、人群、玩法以及奖惩等情况予以全面揭示。在分析了击壤的基本器具后,下面通过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进一步解释其游戏规则。
2.1 击壤游戏的早期玩法
关于早期“击壤”的玩法或规则,《太平御览》给予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该书关于“击壤”的这段史料,现原文辑录如下[5]:
《释名》曰:击壤,野老之戏也。
玄晏(皇甫谧,号玄晏先生)曰:十七年,与从姑子果柳等击壤於路。
《逸士传》曰:尧时有壤父五十人击壤於康衢。或有观者曰:“大哉,尧之为君!”壤父作色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风土记》曰:击壤者,以木作之,前广后锐,长可尺三四寸,其形如履。腊节,僮少以为戏,分部如掷博也。
《艺经》曰:击壤,古戏也。又曰:壤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四,阔三寸,其形如履。将戏,先侧一壤於地,遥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为上。
吴盛彦《翁子击壤赋》曰:论众戏之为乐,独击壤之可娱。因风托势,罪一杀两。
《释名》是我国东汉刘熙撰写的一部专门探求事物名源的著作,其撰书目的是使百姓知晓日常事物得名的原由或含义,是汉代四部重要的训诂著作之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释名》中“击壤,野老之戏也”一句,说明击壤的游戏者一般是乡村老人。
“玄晏”是皇甫谧的字号。皇甫谧(215-282),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魏晋时期医学家,撰有中国针灸学名著《皇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以及《逸士传》、《高士传》等多部文史著作,在医学史和文学史上都负有盛名。皇甫谧“十七年,与从姑子果柳等击壤於路”,表明当时开展击壤游戏的场所是在路上。皇甫谧《逸士传》中又说:“尧时有壤父五十人击壤於康衢”,表明击壤较早出现的时间、人物和地点。“尧”(前2377-前2259年),史称唐尧,远古圣帝之一,生活年代距今至少四千余年。“壤父”即传说中尧时的田野老人,即《释名》所谓“野老之戏”中的“野老”。“五十人”说的是游戏者的人数之多,说明该游戏是集体活动项目。“康衢”即四通八达的大路,进一步说明了游戏场所是指平坦广阔之地。皇甫谧在其《高士传》又说:“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馀而击壤於道中”,反映了游戏者的年龄高达八十余岁。
《风土记》是西晋周处编撰的一部记述地方风俗的名著,《太平御览》中所引的这段资料,说明了击壤的材料是木质的,形状为履状,时间是在“腊节”,即大约在冬令时节,游戏者是“僮少”,即少儿等未成年人。
《艺经》是东汉邯郸淳编撰的一部记述当时流行的各类游艺项目的著作,现除《投壶赋》外,大部已佚失。《太平御览》中所引的这段资料,除了描述击壤的形制以外,还较为详细的说明了当时击壤的玩法:游戏时用两个“履”状木,一个立于地作为目标物,一个握于手作为投掷物,游戏者离目标约三、四十步远,具体玩法是用手中物投向目标物,击中者获胜。显然,这是一种比试“击准”的游戏。
“盛彦”,字翁子,三国时吴国人,官至吴国中书侍郎,年少时有异才,擅长诗赋(《晋书 ·卷八十八·列传五十八》)。《太平御览》引用了盛彦《翁子击壤赋》中的资料:“论众戏之为乐,独击壤之可娱”,表明当时的击壤比较有趣,较为流行。“因风托势”一句说明玩时要借助风力和身体的姿势或力量,揭示该游戏与力量有关。“罪一杀两”可能是一种惩罚措施,由于材料所限,具体含义暂不得而知。
《太平御览》中关于“击壤”的史料,大体反映了我国古代早期(两汉至两晋时期)击壤的基本规则:时间不限或者在冬季;场地多在路上;人群以老年人为主;人数不限,多为集体玩耍;玩法是使用木质器具投掷,以“击准”论胜负;可能有一定的罚则,如“罪一杀两”。
2.2 击壤游戏规则的发展
随着古代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击壤的形式、玩法又有了变化。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暂能了解到明清时代的击壤游戏的大体规则。
明代与击壤类似的游戏叫做“打柭”。明朝末年刘侗和于奕正编撰的《帝景景物略》记载[6]:
“小儿以木二寸,制如枣核,置地而棒之,一击令起,随一击令远,以近为负,曰打柭柭,古所称击壤者耶。其谣云:杨柳儿活,抽陀螺。杨柳儿青,放空钟。杨柳儿死,踢毽子。杨柳发芽儿,打柭儿。”
《帝京景物略》是一部集历史地理、文化和文学三者于一体的著作,它详细记载了明代北京城的风景名胜、风俗民情,是研究中国古代都市不可多得的资料。从该书的这段资料来看,游戏者是儿童,应是两人以上玩耍;所用的是一短、一长两个木棒,短者两头尖,形如枣核。具体玩法为:短棒置地,长棒在手,用长棒击打短棒两次,第一次把短棒击起,趁短棒还在空中时再击打一次,以击远者为胜。著者还认为“打柭”游戏是来自于古代击壤。从当时的歌谣“杨柳发芽儿,打柭儿”可以看出,该游戏大约在春季。
明末清初的学者周亮工编撰的《书影》有类似的游戏,叫做“击棒壤”。书中对该游戏的方法进行了最为详细的说明,并对其名称进行了解释。原文辑录如下[7]:
秣陵童谣,有“杨柳青,放风筝;杨柳黄,击棒壤”之语。《风土记》曰:击壤,壤以木为之;前广後锐,可长尺三四寸。《博艺经》曰:长尺四,阔三寸;将戏,先侧一壤於地,遥於三四十步,以手击中壤敲之,中者为上。《释名》曰:野老之戏具也。元晏曰:十七时与从姑子果卿等击壤於路。吴盛彦赋曰:以手中之壤,击地下之壤。
所言皆似是而非。壤字属土,何因是木!不若童谣中只杂一棒字,使显然易辨。《博艺经》所云长尺四者,盖手中所持木;阔三寸者,盖壤上所置木。二物合而为一,遂令後人不知为何物矣。阔三寸者,两首微锐;先置之地,以棒击之,壤上之木方跃起,复迎击之,中其节,木乃远去。击不中者负,中不远者负,後击者较前击尤远,则前击者亦负。其将击也,必先击地以取势,故谓之击壤云。此是少年有力者所为,必非老人所宜……
周亮工(1612—1672),明末清初的文学家、篆刻家及收藏家,其《书影》一书内容宏阔,涉及经史典籍、小说诗文、戏曲绘画以及奇闻异事等。上面所引的这段资料分两部分:前半部分讲述了击壤的早期发展情况,除个别地方有误外,其余与前文所引《太平御览》“击壤”条大致相符;后半部分是作者个人的评论。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当时的南京(南京古称“秣陵”)童谣“杨柳黄,击棒壤”,点出了该游戏的时间大约是秋季,用具为“棒”;游戏者为“少年有力者”,即力气较大的少年儿童。这段文字与前人不同的地方至少有两点:一是对“击棒壤”的玩法做了最为清晰的说明,该玩法与明代刘侗和于奕正《帝景景物略》中的说法十分相似,不再赘述,只是胜负标准有了变化——“击不中者负,中不远者负”,意即既要击远,又要击准;二是对“击壤”一词的含义做出了独特的解释:“其将击也,必先击地以取势,故谓之击壤云。”意即游戏者用棒敲击地上的“木”之前,先击打地面(壤),以准备出击,就像现在的赛前练习、热身一样,所以叫做“击壤”。第一点给我们廓清了当时击壤的具体玩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第二点仅为一家之言,还需要史料的进一步佐证。
清代类似的游戏叫做“打尜尜”。清代潘荣陛在其《帝京岁时纪胜》中关于正月的“岁时杂戏”一段资料说道[8]:
“博戏则骑竹马,扑蝴蝶,跳白索,藏蒙儿,舞龙灯,打花棍,翻筋斗,竖蜻蜓;闲常之戏则脱泥钱,蹋石球,鞭陀罗,放空钟,弹拐子,滚核桃,打尜尜,踢毽子。京师小儿语:“杨柳青,放空钟。杨柳活,抽陀罗。杨柳发,打尜尜。杨柳死,踢毽子。”
《帝京岁时纪胜》是一部岁时风土杂记,记录了清代北京的岁时令节、风土景物以及民风民俗等,对民间流行的技艺游戏的记载尤为生动具体[9]。据现代资料解释,打尜是我国汉族民间传统的游戏娱乐活动,是上古时期击壤活动的变异形式[10]。从《帝京岁时纪胜》这段资料可以看出,该游戏的参加者是儿童。该游戏记录在《帝京岁时纪胜》正月部分的“岁时杂戏”中,可以看出是在冬季玩耍;再从资料中的童谣“杨柳发,打尜尜”来看,春天也开展这项活动。
通过对上述历史文献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古代击壤游戏规则的大致发展、演变情况:第一,在活动时间上,开始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后来多在冬春季节开展,尤其是岁时节令。这反映了我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特征——在冬季或节令等农闲期间,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老百姓才有机会休憩、娱乐。第二,在活动场所上,起初在路上进行,后来不加限制,但应在开阔地带活动。第三,从活动人群来看,为集体类游戏,开始多为老年人,后多为少年儿童。这一方面是因为一种游戏的发明需要一定生产生活经验和思考认知水平,成年人或老年人无疑在这方面具有优势;另一方面少年儿童本身活泼好玩,对成年人的活动又多具模仿性。因此,击壤从老年人的游戏后来发展为以少年儿童为主的活动。第四,从游戏的主要规则来看,游戏的胜负标准大致经历了“击准——击远——既击准又击远”的演变,体现了击壤游戏的形式向趣味性、丰富性发展,方法向规范化、科学化演变的特点。第五,与其它阶层和人群相比较,击壤游戏多在冬季、节令期间和室外、旷野之地进行,而其它阶层和人群(如士、工、商等),并不受游戏时间、空间的严格限制,这是由人们的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其上的生活方式决定的。第六,与西方的游戏相比,击壤的“击准”规则与现在的地掷球或保龄球相似,其“击远”玩法又与现在的棒球或垒球相像,但其对抗性性、激烈性又与西方的竞技运动迥异。这也体现了世界体育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特征。
3 击壤精神文化
精神、思想是文化圈层结构中的核心,是构成文化的灵魂所在,对器物层、制度层具有一定的主导和制约作用。中国古老的击壤游戏能够长时间延续着,一方面与其器具的发展、规则的完善以及玩法的有趣等有关;另一方面,击壤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社会心理等也起着关键作用。
3.1 击壤文化体现的人类游戏精神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由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构成的。只要人的自然属性存在,人就有游戏的需要,这是以击壤为代表的游戏产生并千年不衰的生物学基础。中国击壤文化起源于茹毛饮血、穴居巢处的原始时代。那时生存环境十分艰苦,但在饱食食物、天气适宜的时候,人们会进行各种无意识的嬉戏,这是在动物生理机制驱动下的“娱乐原欲”。所以,中国古籍《毛诗·序》中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诗歌、音乐、舞蹈的产生是由某种激情所致,同样,娱乐游艺也源于人的生物性[11]。因此,击壤文化的产生,不是一种“矫情”,而是人的本性的真实流露。
游戏由于其独特的作用而成为社会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德国著名学者席勒曾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12]他认为游戏状态是一种克服了人的片面和异化的最高的人性状态,是自由与解放的真实体现。荷兰著名学者赫伊津哈进一步指出:“文明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真正的文明离开游戏乃是不可能的。在某种意义上,文明将总是根据某些规则来游戏,而真正的文明将总是需要公平游戏的。”[13]35-36由此可见游戏在人类文化中的重要性。
游戏与闲暇、休息一样,是人的神圣的权利。据说耶和华在西奈山向摩西传十诫,其第四诫是:星期天必须休息,守为圣日。他甚至下令,凡星期天工作者格杀勿论,由此可见闲暇与休息的神圣。当然,周内的工作同样是神圣的。无所作为的懒汉和没头没脑的工作狂是远离神圣的两极。创造之后的休息和游戏,如同创世后第七日的上帝那样,这时我们最像一个神,其中的快乐感受是不可名状的[13]302-303。
游戏是人的本质属性的体现,是人的现实需要,是人的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这是古老的击壤文化带给我们最基本的启示。
3.2 击壤文化蕴含的土地崇拜情节
前文已述,帝尧时代,“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老人边击壤,边歌唱。该传说实际上是奉献给土地神的祝颂。
古人以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为“春社”,以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为“秋社”。春社祈神,而秋社谢神。这个“神”就是社神(或“田祖”、土地神)。“击壤”是对土地神的献歌或献乐。《诗经·小雅·甫田》中有“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句,描述的是以娱乐的方式祭奉土地,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昌。因此,“击壤”同“击鼓”相类,也是一种动态的乐神行为。不同的是,击壤是一种季节性的民俗活动,它以斗量计数的方式进行“酬神谢土”,同时对生活的安定和来年的丰收寄以希望。例如,“击壤”之戏在20世纪50年代的南京仍十分盛行,是当时小学生们热衷的一种游戏,名叫“打梭”(因短棒被击中时如飞梭穿过,因此得名)。打梭一下称“斗一”,打两下称“斗二”,打三下称“斗三”……从南京儿童的“打梭”游戏中,能察觉其包含着俗信的成份。这是一种变相的亲土祈社行为,以“斗一”、“斗二”、“斗三”的量数,表达万担归仓、谢土报社的喜悦。或者说,谢土报社的俗信活动所具有的欢怡气氛致使该活动由娱神向娱人的转化,形成了季节性的游戏[14]。
击壤文化反映了我国古代习俗发展的基本规律——“初因淡化”规律[15],即某一民俗产生以后,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远离了其产生的动因或初衷,形成的“名不变而实有变”的现象(“名”即节俗名称,“实”即节俗内容)。击壤是一种产生于土壤、游戏于土壤的游戏,其流传几千年,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农耕文明的真实写照。英国一位研究希腊神话的学者曾说过:“宗教的冲动单只向着一个目的,即生命之保存与发展。宗教用两种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一是消极的,除去一切于生命有害的东西;一是积极的,招进一切于生命有利的东西。因此,全世界的宗教仪式不外乎这两种:一是驱除的,一是招纳的。饥饿与无子是人生最重要的敌人,这个他要设法驱逐它;丰稷与多子是他最大的幸福,这是他所想要招进来的。”[16]在古代农业社会,风调雨顺、丰衣足食是人们的现实需要,也是人们的基本追求,击壤游戏正是这一观念的反映。
古代击壤文化反映了人们对土地的崇拜,即对土地的依赖、对农业的倚重以及对丰收的期盼,这是击壤长久存在的文化心理因素。
3.3 击壤文化寄托的太平盛世理想
在远古帝尧时代,天下太平,百姓们安居乐业,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耕作之余,一群年老的农夫玩起了击壤游戏。他们一边玩,一边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就是古人游戏时唱的《击壤歌》,也是一幅远古时代闲适、恬静的农夫休憩图。清代沈德潜在《古诗源》中把《击壤歌》列为古诗第一首。该诗采用白描手法,文字通俗流畅,没有任何斧凿痕迹,仅仅二十几个字,便勾勒出一个囊括时空的理想世界以及该世界中的全部生活,真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那是一个古朴、自然、和睦的时代,人类自由自在,社会公平合理。每个人都依靠自己的劳作获得温饱,平等来往,和睦相处,没有敌视,更无斗争。《击壤歌》前四句表现人按照自然规律起居活动,在自然赋予的范围之内适当地汲取生活资料,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协调的,正是古代思想家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之境界;末一句表现人的精神面貌,那个世界里的人自豪而满足,连帝王也不必恭维,其原因就是他们的生活是完全依照自然的法则运行的,社会制度就建筑在这法则上,人与人之间也是协调的。在这个社会里,老有所养,无忧无虑,所以老人心情愉悦,态度安详,有余暇和兴致去游戏或歌唱[17]。
《击壤歌》所描绘的,无疑是人间的一种向往。它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历代文人墨客在诗词歌赋中对此进行了讴歌,表达了对这种太平盛世的向往,如“玄龆巷歌,黄发击壤”(晋·张协《七命八首》)“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声”(南朝·谢灵运)“候时勤稼穑,击壤乐农功”(唐·薛存诚《膏泽多丰年》)“承平玉烛四时和,处处惟闻击壤歌”(宋·晁公溯《次刘机将仕韵》)“请君画作风调雨顺图,共乐太平歌击壤”(元·王冕《赠杨仲开画图引》)“白屋朱邸亘原野,黔首击壤歌年丰”(清·魏耕《湖州行》)等。如今,“尧民击壤”“击壤而歌”“鼓腹击壤”“凿饮耕食”等词已成为耳熟能详的成语,成为人们心中美好社会的代名词。
击壤及《击壤歌》既蕴含着浓郁的现实感,又充盈着丰满的理想性。击壤是一种游戏,是一首歌,更是一幅社会蓝图。风调雨顺、轻徭薄赋、和睦相处是世世代代百姓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击壤游戏凝结着人们对个体间和睦、民族间和谐、全人类和平的期盼,这是我国古代击壤文化所蕴含的社会学价值。
4 结语
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和发展,击壤游戏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风情和生活气息的表现形式,在器物、制度、观念等方面表现出特定的内涵,形成了丰厚而独特的击壤文化,并在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方面发挥着自己的价值,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击壤文化,对发掘和保护行将消失的中国传统游艺、体育活动,丰富和发展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以及尊重和保障百姓的游戏、体育权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韦明铧.闲敲棋子落灯花:中国古代游戏文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372.
[2]张宝强.体育专业留学生与中国体育发展研究(1903-1963)[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1:93.
[3]王宏凯.益智愉心的中国古代游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1-5.
[4]黄金贵,唐莉莉.辞书误解古代训诂语三例[J].古汉语研究,2011(2):53-58.
[5]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3351-3352.
[6]明·刘侗,于奕正.帝景景物略[M].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66-67.
[7]清·周亮工.书影[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129-130.
[8]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M].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10.
[9]王灿炽.燕都古籍考[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5:320-321.
[10]博闻网.打尜[EB/OL]http://entertainment.bowenwang.com.cn/facts-game-daga.htm,2012-10-14.
[11]王宏凯.益智愉心的中国古代游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1-5.
[12](德)席勒著,徐恒醇译.美育书简[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90.
[13]赵庆伟,朱华忠.游戏风情[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35-36;302-303.
[14]陶思炎.风俗探幽[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5:223-225.
[15]胡戟,张弓,李斌城,等.二十世纪唐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906-907.
[16]韦明铧.闲敲棋子落灯花:中国古代游戏文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330-331.
[17]陈咏明.从击壤歌谈儒道会通[J].世界宗教文化,1995(4):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