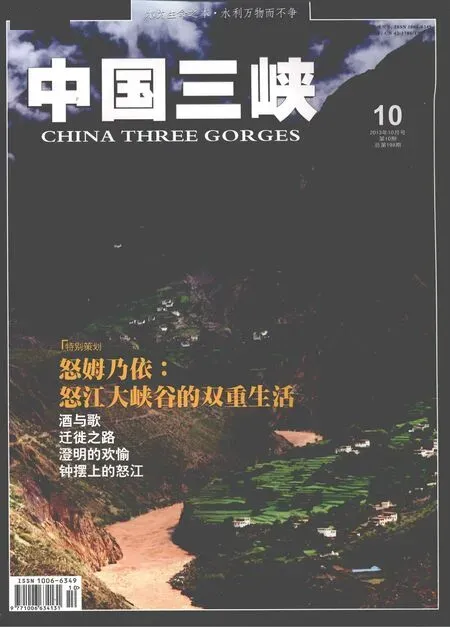澄明的欢愉
图、文/周 伟 编辑/任 红


教会学校课前的祷告。云南怒江,木尼玛,2007年1月。
清晨7点,老姆登教堂的执事约翰敲响了教堂广场上那个用废喷雾器做成的钟,钟声清脆而悠远,伴随着峡谷阴凉的微风,传遍整个村子,余音在峡谷之中久久弥漫……渐渐,朝阳从背后的碧罗雪山喷薄而出,把对面高黎贡山的积雪映成金黄,天空中红色的云雾一扫峡谷的清幽,教堂却在这冷暖的对比间俯视着奔腾不息的怒江,显得格外宁静与平和。
这一天是平安夜。
而教堂的伙房里,义工们早已忙得热火朝天,他们从凌晨四点就开始忙碌了。老姆登是匹河怒族乡中一个较大的村子,今天里全乡的教徒们要齐聚这里,度过为期三天的圣诞节。
在遍布云南怒江两侧的山坡与河谷中那些大大小小的教堂中,老姆登是原碧江县的第一座,它始建于1930年。据村中长者回忆,当时教堂建了三次才成,前两次刚刚建成就被设置局派兵给拆毁了,甚至还把教会的三位负责人也抓了起来,后来在外国传教士的干涉下才放了人,教堂也终于落成。此后,这里一直是碧江县教会的培训基地和圣诞节活动的举办地——圣诞节是怒江基督教徒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当年全县的教徒都会集中到一个教堂过节,而从1930年落成到1957年的20多年间,老姆登教堂先后八次承担了这种荣耀。
遗憾的是,旧教堂在1958年的运动中被拆毁了,直到1979年恢复宗教自由,老姆登教堂得以重建,在后来的20多年中,教堂又先后重建三次,从木草房到到土砖房,规模不断扩大。1984年的12月圣诞节前夕,一个能够容纳千人的大教堂在峡谷傲然矗立。怒江的基督教堂,基本和民居相识,没有太多的装饰,它实在算不上雄伟,但在怒江峡谷当中却是最大的一个教堂,更是最耀眼的建筑,加上他特殊的历史地位,老姆登教堂逐渐声名远播。
午后,从怒江两岸的崎岖的山路上,成群结队的怒族人背着蔬菜,大米甚至铺盖,女人用背篓背着她们的孩子,像是听从了一个统一的号令,往老姆登的方向前进。居住在河谷公路沿线的人们因为交通便利,也许会成群地挤在一个拖拉机上,“突突突”地向着半山腰的的老姆登爬来,而那些生活在对岸的人们,则要踏着摇摇晃晃的悬索桥,或者把自己挂在一根钢索上飞过冬季清澈碧绿的怒江,再沿着山坡的老路蹒跚而来。那些鲜艳的怒族服饰也定然在午后的阳光下熠熠闪烁,这一刻,假如从天空俯瞰,怒江的绿水,和彩色的人流一定交织成一幅神奇的景观。
当一队人马抵达村口,会有组织者招呼大家排着队,一个接一个从教堂前悬挂着傈僳文“庆祝圣诞”横幅的“生命之门”下走进,而老姆登教堂作为东道主,则会组织十几个教徒在“生命之门”边高唱欢迎曲,并且和来者一一行握手礼。他们神情肃穆,举止庄严,让你不敢相信这是在西南边陲还相对闭塞和贫穷的小村落。
当夜幕降临,在峡谷漆黑的天幕中,被昏暗的光芒勾勒出来的教堂似乎就是浩淼世界的一个天堂。顷刻间,从教堂中传出宏大而富于层次的歌声,层层叠叠冲向云霄,一首接着一首——初到怒江的人,没有不被那些散落在峡谷两岸大大小小教堂中飘扬出来的赞美诗所震撼的,而这平安夜的宏大歌声更是无与伦比。怒江,再一次用声音牢牢地把我俘虏。
平安夜里除了正式的祈祷活动以外,主要就是唱赞美诗,先是集体的合唱,再就是匹河乡9个村,37个教堂分别上台表演,而表演的内容也仅是赞美诗。这样的平安夜似乎太单调了,但当圣诞节在都市已经退化为购物和狂欢的节日时,如此朴素的内容与方式恰与这峡谷自然融合在一起。

左上:圣诞节聚会人群中的一个少女。云南怒江,子楞河。2005年12月。

左下:元旦,基督徒在梯田中举行迎新聚会。云南怒江,马底。2007年1月。

右下:聆听祷告的男人们。云南怒江,古当。2006年12月。

右上:圣诞节聚会上,聆听祷告的三个少年。云南怒江,子楞河。2005年12月。
此后的两天中,教徒主要是聆听布道和表演赞美诗。第三天的下午还在玉米地里开展文体竞技活动,诸如爬杆,绑腿跑步,蒙眼敲锣等,这些都是原来怒族人新年的娱乐活动——唯有这一点上,让人看到某些文化上的融合。
第四天的上午,在最后一次聚餐结束后,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刻。教会的几位负责人站在“生命之门”的一侧,与所有的信徒一一握手,每个的口中念叨:“花花(平安)——”上千人的告别仪式,嘈杂而有序,人们的脸上一扫宗教原本的肃穆,洋溢着节日的喜悦,很多老人、妇女,还有一些不常出门的男人,在行握手礼的刹那都会显得局促或羞涩,这让我坚信:他们虽然贫穷,但澄明而欢愉。
很多素不相识的人上前来与我握手,那些能说些汉语的立即就邀请我去他们的村寨做客,我彷佛是他们久违的一个老朋友,是和他们团聚在一起的一分子。是啊,圣诞节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峡谷里,联络沟通都需要艰难跋涉的人们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团聚,是身体的,更是心灵的——峡谷的生活是单调的,但身体的团聚,可以感受温暖;心灵的团聚,可以抵御寂寞。
两年后,我从繁华的都市逃离,再次于圣诞节前抵达怒江。这次匹河乡的圣诞节是在位于谷底公路旁的子楞河村举行的,这个村只有一个仅容二三十人的小教堂,人们就在冬季撂荒的稻田里临时搭建了一个露天教堂。这个平安夜,天空不时飘起蒙蒙细雨,上千人的混声大合唱《哈里路亚》冲破雨雾,在漆黑的峡谷中久久回荡,当赞美诗在峡谷中升起又落下,即便是高山峡谷般跌宕起伏的心绪,亦能被这纯净之声所抚平。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被抚平的首先是一百年前怒江人的心——能够抚平这些刀耕火种、狩猎捕鱼的剽悍民族灵魂的,往往只是一些人、一些事。

已经80岁的布道员亚居拉。云南怒江,老姆登。2003年12月。
1944年4月的一天,位于怒江西岸的里吾底村笼罩在一片悲伤的气氛中,人们围拢在教堂前的平地上,一首接着一首唱着宁静平和却蕴涵着炽热情感的赞美诗,人群中不时传出阵阵哭泣。通往里吾底的路上,傈僳族和怒族人从几里、几十里外的村落急急赶来,他们步履急切,心情沉重,妇女们眼含着热泪,不时仰望传来哀歌的地方,呼喊着“阿子打——阿子打——”。山路上,还有一位西装革履的西方人,他头戴一顶盔式礼帽,行色匆匆,面色凝重。他便是当时的中华基督教内地会在碧江的负责人阿兰·库克(Allyn B.Cooke)牧师,汉文名字叫杨思慧。
“阿子打”便是阿兰·库克牧师的妻子伊丽莎白(Leila R. Cooke),生活在怒江的人们记不住来自遥远国度的人长长的姓名,朴素地用自己的语言称呼他们——牧师叫“阿依打”,意思是尊敬的大哥,而“阿子打”的则是尊敬的大姐。现在,被他们尊称为“阿子打”的女性,宁静安详地躺在担架上,被人们安放在教堂前的空地中央,悲伤的人群一层一层围绕着她。当阿兰·库克终于抵达教堂,俯身匍匐在妻子面前,整个里吾底刹那间沉浸在一片无法抑制的恸哭之中。
人们哽咽地向牧师讲述他的妻子生命最后时刻的情形:就在前几日,阿子打徒步去江东的南安甲村教堂布道,走到半路上就感觉肚子不舒服。南安甲村在里吾底江对面,须下到江边然后溜索过江,再往山上爬。那一日许是下着雨,路途越发艰难,就在阿子打抬手拿起雨伞的刹那,刚刚做过手术的刀口破裂了,人们急忙将她搀扶回里吾底村,但丈夫阿依打正好外出,阿子打没有得到很好的照料,刀口持续发炎,没几天便离开了人世。
人们抬起阿子打的遗体,缓缓走向教堂上方不远的一棵核桃树下,那里正是阿兰·库克夫妇的菜园,现在却是妻子最终的归宿了。赞美诗伴随着恸哭再次潮水般响起——而阿子打已经无法再听到这些曾经是她亲自教唱的歌曲了,她也不知道丈夫此刻已回到自己身边,正为她做最后的祷告。阿兰·库克神情肃穆却没有流泪,也许在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好了把生命留在这里的打算,但他的内心定然充满内疚,在妻子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没有能够陪伴在她的身边,而眼前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妻子,却在20多年里一直陪伴自己在中国,在傈僳人当中,在这偏僻荒蛮的峡谷中履行他们神圣的职责,并且成为自己传道事业最为得力的助手。

上:在天主教堂前玩耍的男孩。云南怒江,秋那桶。2006年5月。

下:在教堂的伙房门口练习吉他的少年。云南怒江,古当。2006年12月。
六十一年后,2005年的年末,我站在了这位至今仍被傈僳人尊敬和怀念的女性的墓前,其实,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坟墓的痕迹了。我的身旁,清瘦颀长的老人友付夺对我说:“文革的时候,阿子打的墓据说被挖开,头骨被扣在一根木桩上接受批斗,我当时在五七干校,后来听说的……上面一点就是阿依打他们的家,坐北朝南,地面和墙壁全部是木板的,还有天花板。西边房是卧室,中间是客厅,也是他们平时工作的地方,东边是厨房和医药室,客厅通着阳台,下面就是菜园子,四周用木板围成栅栏。”依着老人的描述,我可以想见那曾经的木屋,但如今已灰飞烟灭,原来的地方虽有一栋房子,但模样和格局显然不是当年的了。墓地还是菜园,几根玉米秸秆东倒西歪,核桃树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棵茶树墨绿油亮。
老人少年时代曾跟随阿子打学习傈僳文字和圣经,对于杨思慧夫妇的许多事情仍然记忆犹新,他告诉我:杨思慧夫妇一直保持着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他们自己烤面包,吃小米,极少吃大米,自己养了20只羊,只为了挤羊奶喝,他们带来很多豆种和果树,至今当地人还称一些豆和果为“传教士的豆”和“传教士的果子”。
阿兰·库克1896年出生于美国旧金山,毕业于洛杉矶圣经学院,1919年他作为中华基督教内地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1920年在云南大理按立为牧师,1922年开始在中国的西南边疆傈僳族聚居区从事传教事业,先后在木城坡和临沧地区耿马县福音山传教了10多年,之后于1933年和妻子一起来到里吾底村。第二年里吾底落教堂落成了,这座由四根粗壮的栗木支撑起来的高大建筑在着实震撼了傈僳人,它四周均为冲土墙,顶上还覆了杉木板,据说可容纳千人。这里自然成为基督教内地会在碧江传教中心。对于大多数傈僳人来说,杨思慧夫妇的到来,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不再喝酒赌钱,不再因为从天而降的病灾而杀牲祭鬼,以至于不堪重负,他们开始学习洗脸、洗脚,学习以握手的方式表达问候……尤其是阿子打,用友付夺老人的话说,“她是我们的老师、是卫生员、接生员,还是裁缝……”从并不翔实的史料和口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阿子打应当是一位和蔼可亲、多才多艺的女性。她穿傈僳人服装,多数时间都在教孩子们学习傈僳文字,给病人看病,为妇女接生。
阿子打亲手接生的史富相,少年时代也跟阿子打学习,解放后成为国家干部,他回忆道:“阿子打是位和蔼可亲的女牧师,也是一位救死扶伤的好医生,能说一口流利的傈僳话。每到礼拜天,是阿子打最忙碌的时候,信徒群众因病要药的人特别多。但她从不急躁厌烦,总是耐心地为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看病,给药,打针。平时群众患有疾病或妇女生小孩只要喊到她,不论白天黑夜,她都去病人家看病。她对小孩子怀着一片慈母之心,每年都主动召集家长,为他们的小孩种牛痘或打天花预防针……她还经常举办妇女培训班,传授妇幼卫生常识,包括如何操持家务,如何待人接物等方面的内容,使当地的傈僳妇女受益匪浅。”

胸前挂着十字架和弹弓的儿童。云南怒江,害必洛。2007年1月。
传教士们都有不凡的音乐修养,每到星期天或者闲暇的时候,阿依打演奏小提琴,阿子打弹奏风琴,另一位叫贾牧师的吹圆号,组成了一个小型乐队,他们既自娱自乐,也给傈僳人带来新鲜和愉悦。事实上杨思慧夫妇在音乐上都有非凡的造诣,杨思慧熟谙乐理,对圣乐尤其精通。当他们还在木城坡教会时,得知有两位擅长傈僳族调子的老妈妈,便主动上门请教,并一一记录。在搜集整理傈僳族歌曲过程中,他们发现傈僳族调子中的句式和《旧约全书》里“箴言录”及“大卫诗”的句式很接近,于是他们就按照傈僳人的对偶句式把赞美诗填进去,并创造了与汉文简谱不同的傈僳简谱。经过十多年的积累,终于在四十年代编辑出版了傈僳文的混声四部的《颂主歌曲集》,300多首歌曲中,除了杨思慧的创作,还有许多改编自苏格兰民歌、美国民歌和西方圣乐中的经典作品。
和阿子打善于和傈僳人打成一片不同,杨思慧则近乎一个学究,他一向西装革履,严谨有序,这种气质帮助他完成了传教生涯中最具历史价值的事情——他继承前辈初创的事业,在妻子和傈僳族助手摩西等人的协助下,将《新约全书》全部翻译成了傈僳文。
生活在傈僳族和怒族历史上并没有文字,当上世纪初,内地会在云南滇西的总负责人傅能仁牧师开始在傈僳族地区传教的时候就萌发了创制傈僳文字的念头,1912年他与缅甸籍的巴东牧师商讨决定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方法创制傈僳文,他们各自设计了一套方案,在傈僳人当中进行运用试验,最终于1919年定稿。这套拼音文字,运用原有的26个拉丁字母和14个倒置或翻写的拉丁字母作为拼音基础,具有单音节多、易读、易写、易记的特点,很快就为傈僳族人所接受。
这套文字创制成功后,傅能仁和巴东就开始联合试译《约翰福音》,到1939年在杨思慧手上完成,前后历经十七年,在最后定稿的时候,杨思慧夫妇邀请傅能仁牧师来到里吾底一起进行审定。遗憾的是,此后不久,摩西和傅能仁牧师先后去世,都没有能等到它最终出版的那一刻。阿子打在自己的回忆录《傈僳人旺丽和傈僳文圣经》中写道:“我们离开南方福音山,来北方怒江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北方傈僳族地区信教人数逐年增加,他们要求我们传授圣经知识,同时还未入教的人也很多,还需要做宣传布道工作。另一个原因是北方傈僳族聚居区能学到真正的傈僳语,因为那里是地球上傈僳族聚居最多的一个地方,没有住着汉族,他们所说的傈僳语中没有夹杂着汉语,这对我们圣经书的翻译工作来说是很重要的……”傈僳文《新约全书》和《颂主歌曲集》凝聚杨思慧夫妇共同的心血,而这两本书也是以傈僳文字为载体的巨著,至今仍然被傈僳族人使用。那教堂中的布道和歌曲也正是我在怒江旅行中听到的最纯净和神圣的声音——这文字,这歌声,毫无疑问融为傈僳族民族文化中最为精彩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