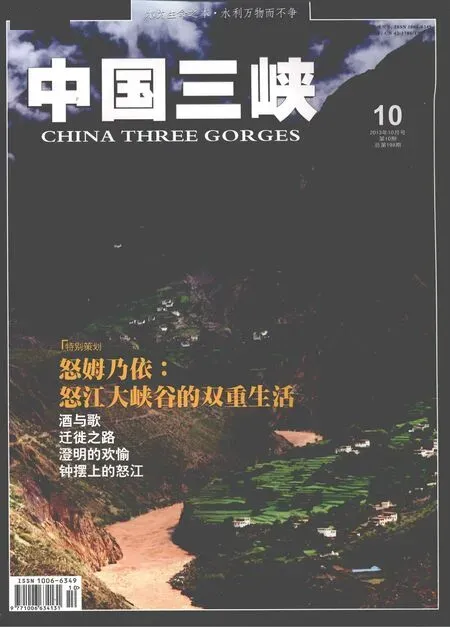钟摆上的怒江
图、文/周 伟 编辑/任 红

“嘭、嘭、嘭”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唤醒,听到阿周在外面喊道:“走啦!已经晚喽!”我听得出来,阿周并没有停下脚步,话音未落已经推开隔壁自己的房门进去收拾东西了。
我看了看表,正是凌晨六点半,整个怒江还沉浸在睡梦之中。前一天晚饭的时候,我听说阿周要下山买猪,兴致一来便决定和他同往。阿周是我在怒江最早相识的朋友,几年来,每次重返怒江都会在行程中安排到知子罗,常常只是为了来看看这位老友。说实话,这位少我几岁的男人,长得还真像个杀猪的,五短身材,黝黑皮肤,浑身鼓胀着坚硬结实的肌肉,说话走路干脆利落,总是洋溢着一股朴素的、用之不竭的热情。阿周为人豪爽,也不乏精明,而给我最为震动的是,他是我在怒江众多熟人中最不认命的一个年轻人。
阿周夫妇都是教师,这样的职业连同他们稳定的收入在当地足以令人羡慕到眼红。但阿周并不因此满足。记得初次与他相识的那天晚上,他邀我到他家里聊天,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盼望着挣更多的钱,盼望过上更好的生活。“像你一样,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说,“所以我要努力,我相信我一定会成功的!”他的语气坚定,不容任何人怀疑。他的比方显然不恰当,但着实能表达他的思想,而他所说的努力是有所依据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请了一帮人在村头的一片空地上垒围墙,那一年他从村里租下了这块地,打算建一个养殖场,当时万事还在开头,他乐呵呵地说:“我现在很穷,今天请这些兄弟干活的工钱也是欠的,不过我会还的!”
那一次,我按计划在认识他的第二天就离开了知子罗,但阿周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隔了5个月,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养上了三只羊,他说要先试验试验,积累一些经验后再扩大规模。之后我才逐渐了解到,十多年来阿周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并且还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经历。
那是90年代的事情了,知子罗迎来了自碧江撤县以来又一次繁华,这次的繁华是因为开发碧罗雪山的森林资源,大批来自云南、四川等地的伐木工人进驻知子罗,一时间这个沉寂多年的“废城”再一次恢复曾经的熙熙攘攘。街道两侧店铺林立。阿周是个善于抓取机会的人。他从小本做起,直到最后开了一家饭店,一家卡拉OK厅,还买了一部微型面包车做客运生意。然而,天有不测风云,90年代末,国家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知子罗的喧嚣又在一夜之间沉寂,阿周的饭店和歌厅就此歇业,恰在此时,他的父亲病重,花去了阿周所有的资财。直到最后,阿周的妻子分娩需要做剖腹产手术,阿周再没有现钱了,不得已将心爱的汽车也卖了。阿周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出乎意料地兴奋,并没有任何沮丧的情绪,言谈间便把电视节目调到中央七台,收看致富信息。

左:放学后,在家看动画片的小学生。云南怒江,古当。2006年12月。
阿周的确不是杀猪的,可这两天恰恰因为杀猪的事儿忙得不亦乐乎。他在敲醒我之前,刚刚忙碌了一个通宵,杀了三头猪。
所谓机遇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当我第三次见到阿周的时候,他试养的羊并没有成功,但养殖场却产生了不菲的效益——一个电力工程队正架设穿越碧罗雪山高压线,工程队租下阿周的养殖场做材料供应站。施工将持续半年多,阿周便在这桩生意中改变了一直以来的困境。他还把山上工程队伙食中的猪肉生意揽下,隔三岔五杀几头猪送到山上去。这一个通宵,圈里的猪都宰了,他必须赶紧再补上,以备后需。
拖拉机在黑漆漆的峡谷中轰鸣着蹒跚而下,从知子罗到江边的简易公路已经年久失修,加之摸黑行驶,阿周开得很慢,但很稳。阿周卖掉汽车后,买了这台拖拉机,他对驾驶有着浓厚的兴趣,说起拖拉机、汽车的事儿头头是道,修理也是自己动手。他一边紧握方向盘,一边撤着嗓门对我说:“有个汽车多方便啊!”
阿周的梦已然走在了路上,但对于大多是生活在怒江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来说,找寻一个梦想都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右:抽烟喝酒的少年。云南怒江,空通。2005年12月。

浓雾笼罩的怒江大峡谷。云南怒江,古当。2006年12月。
2006年的春天,我再次来到怒江,在一个名叫欧鲁底的小山村小住。我在抵达那里的第二天参加了基督教徒的“受洗”仪式——每年申请入教的村民都要经过洗礼才能成为正式的教民,才有资格参加教会的一切活动。这次有23名年龄不一的村民接受洗礼,大多数是年轻人。仪式在村子旁边的山涧中举行,事先已经有人筑起一个水坝,围出一个较深的水塘,每一个新教徒都被几个男子托着,整个身体没入水中,老教徒们则在岸边唱着赞美诗将这一刻铭记。
这天夜里结束了教堂的礼拜,我跟随教堂的执事四富恒来到一户村民家中,这家的老人生病了,他应邀去为病人做祷告。竹楼很宽敞,里外两间的火塘边都已经坐满了人。四富恒坐定,和大家寒暄几句后,人们便拿起歌本开始唱赞美诗。里间的火塘边,席地卧着一位银发老妇人,一直紧闭着双眼,偶尔有人问话才虚弱地吐出几个字。四富恒为她做了一次长长的祷告,最后他走上前去和老人握手,那一刻,平躺在地上的老人将手高高地举在空中,寻找着四富恒的手,当她的手终于被四富恒握住,她微微地摇晃着手,而我感受到了老人内心无限的感激与满足。歌声再次响起,冲出竹楼,冲进峡谷绵延的雨雾中……人的一生如此短暂,当在病中,在痛苦的时刻,乃至面临死亡,总是有这样的歌声陪伴着你,单就心理上便可获得极大满足和喜悦啊。
天主教和基督教从19世纪末开始进入怒江,经过100年的坎坎坷坷的传播之路,终于在傈僳族、怒族人当中扎下了根,尤其是基督教,已经成为怒江大峡谷最主要的宗教信仰。当然,并不是所有传教士都像杨思慧夫妇,献身于纯粹的宗教事业。传教士进入怒江初期所发生的数次教案,无不说明任何一个民族在任何时代都首先需要被尊重和理解。那些历史上有所记载的传教士,如今的傈僳人对他们有惊人客观和感性的评判,即便是杨思慧,里吾底人还是有一个不解的心结:阿子打去世半年后,杨思慧便从重庆娶回第二个妻子——这与傈僳人的传统是不合的,为此里吾底人颇有些酸涩的滋味。
而怒江人最终接受基督教也有深刻的文化和经济因素,包含了浓重的功利色彩——基督教宣扬的生活方式帮助信众摆脱了酗酒、赌博的生活方式,摆脱了买卖婚姻和杀牲祭祀所带来的沉重的经济负担,提高了文化知识水平。这些都给当时仍处在原始状态的民族以深刻的影响。
只是,100年后的今天,怒江正面临着一场彻底的变革,生活在峡谷里的人们已经隐隐地有所感觉。
祷告结束后,人们并未散去,有的继续唱着圣歌,有的则轻松地作围炉夜话。一群年轻人围过来,这些人憨厚、腼腆,一个劲地给我添茶,渐渐开始用生硬的汉语向我问起许多问题,大都是关于峡谷生活以外的事情。那个负责教堂财务,他们称作“财经”的小伙子出乎我意料地问我道:“听说下边鹿马登要建电站哦?我们江边的水田要淹没掉了吧。”——欧鲁底虽地处海拔1800米以上的半山腰,但水田都在山下临近江边的坡地上。
我顺着他的话问道:“如果让你们移民,搬到其他地方去,愿意吗?”
几个人都摇头说道:“不愿意啊,前几年有移民到思茅去种咖啡的,很多人不适应,气候不一样,有些人最后还是跑回来了。”
我再追问:“这里条件这么差,种稻谷都要走半天跑到山下,为什么还不愿意走呢?”
他们微笑着,不知怎么作答,最后还是四富恒说:“毕竟在这里生活长了,习惯了。要是真的建起了大电站,或许我们的生活也能改善吧。”
“真的建电站,我们肯定可以有工做,不用跑很远也能挣钱吧,姑娘们也不会往外跑啦——”那个叫“财经”的小伙子乐呵呵地说道。
众人用笑声对他的话表示的认可,纷纷议论他们村子在高处,也许不用移民,甚至公路改道上移或许会经过欧鲁底,这时他们脸上洋溢出隐隐的企盼和欣喜。
我知道,众人言语中的“姑娘们往外跑”是有所指的,近年来有很多东部农村青年常常到峡谷里面来买媳妇,据说价格已经飚升到一两万,很多家庭就依靠这样的收入盖新房或让儿子娶上媳妇。这些峡谷中的妇女走出去以后,由于语言不同,生活习惯迥异,少有幸福美满的,很多妇女因此被迫回到峡谷中。这样的“婚姻”遍及怒江两岸的村寨,简直又是一次迁徙,一次自发的移民。
和峡谷外面的世界相比,他们的生活变化得太缓慢了,尤其是那些远离公路,赶一次集要花上一天时间的村落,他们太需要某些外在的动因来改变他们静若死水的生活了。怒江干流建坝的事情在峡谷之外已经争论得沸沸扬扬,建与不建的争论其实就是一个保护与开发永恒话题。几次的怒江之行让我深切地感受到大峡谷的生态极其脆弱,和30年前相比怒江的植被已经完全彻底地改变了。据1946年的记载:“怒江两岸,丛山绵亘,且林木总类繁多。树龄数十年至数百不等,均系原始天然林。”即使到80年代以前,怒江两岸的森林在很多地方可以连亘将江面遮蔽,在江边根本看不到峡谷的V字形状。这样的生态显然需要生息、需要保护。
但是,谁又能够剥夺这里的生民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与企望呢?在环境与发展间永恒矛盾中寻找一条出路,找到开发与保护的一个平衡点,以现代科学的水平应该不是一个难题,难就难在如何在现实利益间取舍与平衡吧。那些已经被砍伐殆尽的原始森林,是和怒江人一同生长繁衍起来的,当被一车一车拉出峡谷的时候,却并未给他们带来多少利益,并未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改观,这样的历史假如轻易被重演将是最可怕的事情。
无论是新形式的买卖婚姻,还是即将面临的水利开发,作为迁徙之民的傈僳族、怒族人已然迈上了新一轮的迁徙之路,白天肃穆的洗礼和夜晚对于现实生活的憧憬都震慑着我心,这便是怒江最真实的一面。
每一次离开怒江的时候,我都会回到向阳桥头。“女大王”一年一年变得苍老,但她总能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我来,她依然会盛情邀我喝酒,可是我的内心却再没有当初的喜悦和兴奋,我的心中充盈着怒江的风景,充盈着许多面孔,充盈着太多的酒歌和赞美诗。时间如江水不会停滞,在浊了又清、绿了又黄的流转中,怒江却依然在时代的钟摆上摇晃——寻找平衡,企望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