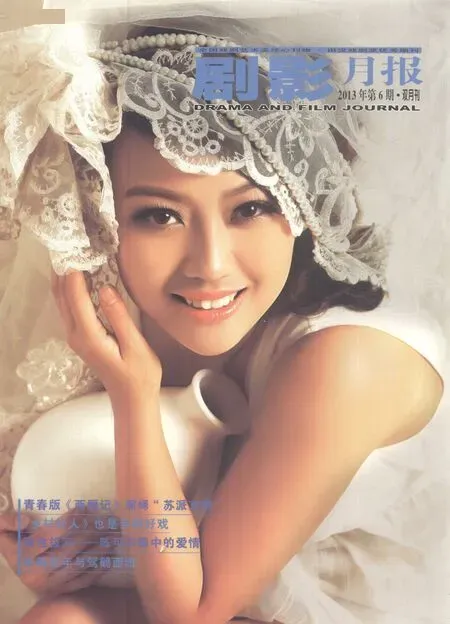论荆浩的山水画艺术观
■李燕
论荆浩的山水画艺术观
■李燕
一.荆浩的笔墨观
五代时后梁山水画家荆浩(约850—?)在他的《笔法记》中以大量的文字对“笔和墨”的应用与效果作了重要而广泛的推断和论述。有着鲜明的思想性和艺术创造性。他提出了绘画的“六要”,并加以阐释:“图画之要,与子备言;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仪不俗;思者,删拨大要,凝想形物;景者,制度时因,搜妙创真;笔者,虽依法则,运转变通,不质不形,如飞如动;墨者,高低晕淡,品物浅深,文采自然,似非因笔”。荆浩认为,山水画“用笔”要遵循一定的法则,这种法则不单纯从用笔自身的规律来确定,而更多的注重“形”和“质”的变通转换。他对气的解释为“心随笔动,取象不惑”,深刻阐明了“心”和“笔”和“象”的艺术关系。这种心、手、物的有机结合,是使绘画达到“气韵生动”的有效保证。用笔虽然要依靠“法则”,但还得必须突破法则看到“物象”形质的区别和限制,做到“运转变通,不质不形,如飞如动”这种取象生动的画面效果。是对用笔重要性的阐释。
荆浩对“墨”的解释也非常明确,“墨的高低晕淡”是对“物象”的深浅表达,在水墨画的表现中,唯一对物象的表达方式也只有用墨色的深、浅来表现其面貌,用笔和墨的法则来勾画显示物象的阴阳向背,来做到“有笔有墨,水墨晕章”这一高超的艺术特点。
董其昌曾对中国山水画进行过很深的艺术研究,并提出了中国画“三变”说,指出荆浩时期为第二变也,的确,无论荆浩的绘画观和他对山水画艺术的创造发展都是非常有贡献的。他“水晕墨章,兴我唐代”的艺术观点影响至深,对后世的绘画发展起着显著的作用。“吴道子笔胜于象,骨气自高,树不言图,亦恨无墨。”这是对吴道子的“有笔无墨”作了有力的批评,并对吴的用笔给与了高度评价说明吴道子在用笔表现上是非常有能力的。他能把物象的“形质”“神彩”表达得非常到位,使绘画表现形式中的物象具有很高的品格,把握用笔对物象的骨气表现,与谢赫的“六法”之“骨法用笔”相对照,符合“六法”法则。荆浩在吴道子对树的描绘上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艺术观点,画树不能只靠笔的勾勒,还要加强墨色的晕染,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水墨晕章”这一最高境界。《图画见闻志》中记载,荆浩曾说:“吴道子画山水有笔无墨,项容有墨无笔”。唐代山水画以水墨的形式代替了青绿着色山水,正是由于有一批和荆浩同样“水墨”观的画家,才形成山水画的又一变革的主要形式。唐代是“水墨”画成熟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代表画家有吴道子、王维和张璪等。他们突破了隋唐时期的展子虔、李思训及李昭道的青绿着色山水。而荆浩的艺术观是对唐时期“水墨”山水画发展的总结。
二.荆浩的“神、妙、奇、巧”论
在《笔法记》中荆浩还对他的另一艺术观点“神、妙、奇、巧”作了充分的论述。“神者,亡有所为,任运成象。妙者,思经天地,万娄性情,天理合义,品物流笔。奇者,荡迹不测,与真景或乘异,致其理偏,得此者亦为有笔无思。巧者,雕缀小媚,假合大经,强写文章,增邈气象。实不足华有余。”这里我们可把荆浩的“四格”来对照宋朝黄休覆的“逸、神、妙、能”“四格”说,从年代上说荆浩的这一艺术观点早于黄休的“四格”说,并能确定“四格”说是继荆浩观点之后的再深入。这里荆浩把“神”作了深刻的解释,乃“亡有所为”,人死之后的一种“灵魂”,这种“灵魂”可以对于貌相在符合常理的状态内,根据画家的意识形态进行任意“挥洒成象”。显然荆浩的这种阐述已上升到韩非子“鬼魅容易,画犬马难”这一重要理念上来了。因“神灵”没有常形,而有常态。故画家们容易表达自身情感中常态化的那种意象美。更容易使人们对物的情感进行选择性的美化,契合画家的意识形态。使在作画的过程中随心成画。
他把“妙”作为经天合地,也就是符合天地间的自然规律性。画家所表达的自然万物既要归附于物体自身的本性,又要顺应它们的“理意”。荆浩根据对以上两格的提出和阐释等于把绘画的意境作了标准化的确立,而又指出了画家在创作中误入了“奇”途,搞些“巧”琢,会使画面出现大的错误。严厉地指出了实质性的一些问题。奇者,他认为就是放荡迹形,使人无法对照其画作的面貌,更不能与“真景”相对照,使绘画作品不符合“常理”。荆浩把这一类的作品看成“有笔无思”,也就是只存在笔墨上的形式表达,而没有经过严格的思考,没有使作品和自然规律相对照。更加有力地批判了“雕缀小媚”的“巧琢”画家,虚假的物象不结合天地自然,不掌握万物的规律性,强行把物体相结合,按插装配,这样就形成了华而不实的病态。荆浩对“神”“妙”的解释和对“奇”“巧”的批判更加鲜明地呈现了他的正确艺术观和审美观,这种观点对我们后人具有深远的影响。
这里我们不再对荆浩的“六要”观和“四势”观一一进行论述,而应把不被人注意的“二病”观进行阐释。“夫病有二,一曰无形,一曰有形。”
《笔法记》中荆浩也作了个别的提示,对于“有形之病”他举例为:花木不符合时间常规,房屋小人物大,树木比山高,桥梁没有搭在岸上。他以绘画实践中的方法认为这些毛病都是“可度之形”。这些问题都能在绘画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就是现代艺术家所说的“制造了矛盾,再去解决矛盾”。当时的荆浩已经能在绘画过程中领悟到了这种矛盾的相对性,而并非是不可修改的病态。这也说明荆浩的绘画能力是非常强的。他认为“无形之病”是不可删改的,他把这种绘画病态首先从“气韵”加以对应,把没有达到“气韵生动”这一根本性艺术表现形式作为第一大病态,不符合自然规律。虽然用笔墨对物象进行了一番表达,但所画出的物象如同“死物”,没有“灵性”,“僵蛇”一般。认为这种绘画面貌不能对其进行修改,更没有修改的必要,因为整幅画面没有精神,在表现物体上,笔墨没有畅快、游刃有余的情感之笔,不具备灵动性。我们按荆浩的解释可以对此“二病”作一个定论:那就是有形之病可改,无形之病不可修。可见,荆浩在《笔法记》中的艺术观点是丰富而又鲜明的。
(聊城市财政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