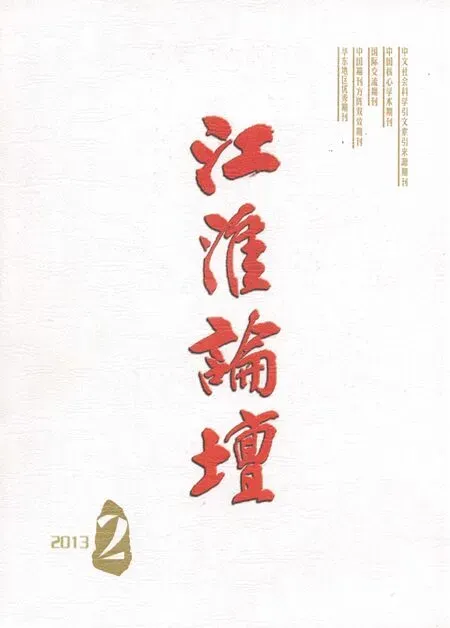“自我”与“他者”:文化政治与儒学复兴*
廖永林 卞程秀
(内江师范学院政法与历史学院,四川内江 641000)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几年,儒家文化在理论界的复兴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从大型儒家文献“儒藏”的整理到各种儒学出版物的发行,从国家形态上的中国孔子基金会的成立到各种民间儒学(儒教)社团的活跃,从各高校的儒学院成立及儒学专门人才的培养到民间的各种尊孔读经运动,无不表明儒学在理论界的复兴已经成为实事。对儒学复兴的时代语境、儒学复兴的具体路径问题的探讨也已成为理论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当代儒家文化复兴有着怎样的时代语境?儒家文化复兴在这种语境之下又有着怎样的发展路径?
一、“自我”与“他者”:世界历史语境下的文化政治及儒学复兴
对儒学的复兴原因,诸多学者已经从不同的侧面展开了研究。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崛起会导致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文化认同的加剧,如龚鹏程认为儒学的复兴与经济复兴上的 “中国崛起”的文化身份认同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学者认为,上个世纪末期政治意识形态的退守使得各种理论得以发展,且儒学内部的某些价值亦为执政者提供了对现实的解释力,如高瑞泉认为“文革结束以后,教条化的意识形态步步退守,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新秩序以后,重建意识形态成为了许多政治势力关注的问题。儒学的某些价值再次被发现”。还有学者从现代性的角度对西方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和弊端进行反思,以此提出儒学复兴的必要性,如汤一介认为西方现代化中的主客对立的二元观使得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造成了自我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之间的不和谐。
对于儒学复兴的语境的探究基本在中国现代化的视阈之下,学者们致力于现代化中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以及现代化所导致的各种问题的研究。这种将儒学复兴置于现代化背景下的打量方式,符合现实的语境。但是,现代化同时是民族的现代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间的民族现代化。
那么,民族国家及民族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与儒学复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在前现代,儒学的发展极少遭遇来自其他国家的影响,而近现代在民族国家纷纷建立的背景下,近现代儒学的发展始终面临着一个外在“他者”。在早期,这一“他者”的形象始终是以政治、军事及相关因素表现出来的,如政治联盟、军事斗争等;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他者”的形象由显明转而为隐晦。具体到文化领域,这一隐晦的“他者”就形成了文化政治。
所谓文化政治,是指力图塑造一种同质文化这一群体公共意义系统,以谋求民族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文化与政治相结合的政治。这一术语曾在不同学者的不同著作中以不同的表达方式被提及,如赵汀阳曾在《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中提出了“文化政治化”。
文化政治作为诉诸文化因素以寻求政治利益的文化与政治相结合的政治,其产生有着文化和政治本身的原因和外在的现实原因。
第一,文化政治形成的基础,在于各民族文化本身的想象和塑造的一个与“自我”相对立的“他者”形象。
文化作为基于生活方式而形成的一套心理、行为的群体公共意义系统,天然赋予了某一群体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模式和价值系统,它与异质文化之间相互区别,存在于某一文化系统中的存在者由于文化的影响天然具有一种“自我”和“他者”意识。
在西方,古希腊人将外族人称为“barbarian”。这一称谓在早期并无价值判断,但是在公元前五世纪时,该词逐步具有了“野蛮的”和“没有教养的”含义。这种对于外族“他者”的称呼证成了古希腊人在文化上的“自我”与“他者”的分离,并确认了“自我”的优越感。进入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时代后,“自我”与“他者”的界定又因宗教文化分化为正统的基督徒和异教徒。而与“自我”相对应的“他者”如伊斯兰世界则被异化为“邪恶、丑陋和令人恐怖的他者”。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率先进入现代化,他们构建了一个“他者”的东方世界。李慎之在评论《文化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时就将亨廷顿称为“西方中心主义的遗老”。
文化上的天然“自我”与“他者”的区分也表现在中国文化中。虽然《说文解字》中并无“他”字,但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认为“他”为“它”的假借字。“其字或假佗为之。又俗作他。经典多作它。犹言彼也。许言此以说假借之例。”许慎《说文解字》对“它”的解释为:“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凡它之属皆从它。蛇,它或从虫。”在华夏文化传统中,与“自我”相对的“他者”类似于没有教化的虫类。这也就不难解释,早期文献中对少数民族皆以戎、狄、蛮、夷称之。黄玉顺在《中国传统的“他者”意识》一文中认为“他”字在早期为远指代词,既可指人又可指物,更多的是指非人的物。因而,他总结说:“从存在论的角度来说,他者乃是异己的在者;如果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则‘他’或‘它’那是邪恶不正的东西。 ”
第二,文化政治的形成基于政治及其利益的诉求。
如果说文化上的“自我”与“他者”的分割来自于文化天然和文化群体承袭中的无意识的结果的话,那么政治上的“他者”与“自我”则是有意识取舍的结果。
卡尔·施米特试图超越道德的善恶、审美的美丑和经济的利害,将“朋友”与“敌人”这一特殊划分作为政治及其内容的简明标准。但是,这一划分始终无法摆脱现实的政治中的权力和由此而来的利益因素。
马基雅维里将现代政治科学聚焦于权力,荀子提出从人之欲、势不能容、物不能赡。虽然他们基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目的,但是其后都隐藏着权力以及由权力所导致的利益问题。在现实政治中,“自我”总是有意识地将“他者”想象和打扮成危及“自我”利益的“敌人”。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主体都是理性的参与者,即使是在群体无意识的政治参与中,其目的都与利益相关。为了保全或最大化“自我”的利益,主体与主体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才成为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有意识选择的“自我”和“他者”形象。
第三,文化政治的形成有着现代世界历史所形成的民族国家这一现实原因。
在前现代的区域历史中,由于交通与信息交流的限制,使得政治上的直接利益诉求也局限于区域范围之内,所以文化上的“他者”与政治上的“他者”相对分离。以佛教为例,东汉末年佛教东传,到唐代形成儒、佛、道并存的局面。虽然如韩愈等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力辟佛老,但是并没有导致文化政治的发生。
近现代随着西方率先现代化,在工业和科技的推动下,历史也由区域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与此同时,基于对传统历史、语言和文化等的认同,王权国家逐步退出舞台,在文化认同上的民族国家纷纷建立。民族国家的建立为文化和政治上的“他者”与“自我”意识相结合提供了现实的条件。
就文化而言,民族国家的建立本身奠基于共同或相似的文化心理。文化上的同质与相似,为其铸就了一个摒离“他者”的藩篱。就政治而言,民族国家本身如何有效地获得和拓展 “自我”的权力与由此而来的利益,是民族国家的主要目标。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的政治》中言“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
至此,文化政治的形成就成为了必然。汉斯·摩根索认为帝国主义有三种手段: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军事帝国主义是最为明显的却难以预估结果的手段,经济帝国通过隐性手段支配和控制他国,而文化帝国主义“他的目的不是征服领土和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赵汀阳也认为文化天生就具有权力因素,文化作为一种“不能独占而不得不分享”的物品“越被公共开采和使用,储量就越变越多,利用价值就越来越大,权力也就越来越大,它就控制着越来越多的心灵和行为”。
在文化政治中,文化交往的过程实质是文化政治展开的过程,是隐藏在文化之后的政治进行权力规则和权力系统的建构过程。通过文化中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公共舆论的操纵、日常交往的影响,政治将文化中的异己的“他者”赋予“野蛮”、“落后”、“无知”等标签。伊斯兰世界将政治与伊斯兰教结合,并积极倡导伊斯兰教的优越性;欧美世界将民主、自由与基督教结合,并积极倡导一种普世主义。正如萨义德所言:“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
当政治以文化的形态表现出对“他者”的拒斥时,民族国家间的格局与关系就表现为文化的斗争。在文化政治格局下,国家之间的冲突就成为了 “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文明的冲突”,即一种文化冲突。“在这个新世界里,最普遍的、最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
因此,如何有效地在民族国家体系中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从文化本身对文化政治的拒斥来看,儒家的文化复兴就是必然。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60多位学者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要求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异质文明、保护各国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他们或从多元主义、或从本民族中的普世主义寻求对文化政治的应对之方。
问题的关键是,对于异己的“他者”无论是强势的“自我”抑或“弱势”的“自我”,应当持允怎样的一种态度?或者就儒学而言,儒学在复兴中应当采取何种方式和路径对文化政治中的 “他者”进行回应呢?是在民族国家视阈之下的非此即彼的“自我”坚守,抑或是超越民族国家的“自我”、“他者”发现一些更为公允的原则?
二、“自我”与“他者”的坚守与超越:当代儒家文化复兴的两条路径
对于最近几十年来的儒学复兴,已经有学者对其形态、特质等进行了分析,如李承贵将当代儒学划分为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和生活儒学。而立足于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间的关系来进行分析的较少。
这十几年中,继港台新儒家和海外新儒家之后,涌现出了一批致力于儒家传统与现代生活相结合的一批学者,如蒋庆、陈明、黄玉顺、干春松、秋风、康晓光等。他们或是致力于某特定范畴的研究,或是致力于儒学体系化的建设,学界一般将其称为“大陆新儒家”。在大陆新儒家内部,以何路径来对西方文化政治的“他者”进行回应也各不相同。大致而言,大陆新儒家内部已经分化为以蒋庆为代表的立足民族国家和以黄玉顺、干春松为代表的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两个不同路径。下面简要以蒋庆和黄玉顺、干春松为代表分析之。
1.“他者”的拒斥:民族国家视角下蒋庆之儒教政治
作为当代大陆新儒家的代表,蒋庆无疑是起步较早也是最具争议性的人物。1989年他在《鹅湖》上即发表了《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一文,提出儒学复兴的必要。截至目前,无论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儒学界内部,都对其评价不一。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从思想的基点而言,他试图从坚守民族性和民族国家的立场,对以西方为主要对象的“他者”予以拒斥;从途径上说,他诉诸宗教——儒教这一复古形式以期保持儒家文化的纯粹性。
从民族国家角度对中国文化“自我”的坚守是蒋庆儒教体系的逻辑起点。蒋庆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本,文化亡则民族亡、国家亡。“依中国人的历史观,亡国不可怕,亡国可以复国,社会生活依然存在;亡天下亦不可怕,亡天下可以复天下,社会生活依然存在;中国人最怕是亡文化,亡文化即意味着亡价值,亡价值则使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可能,是人类万劫不复的灾难。”
为保持中国文化的“自性”,蒋庆形成了中西文化“自我”、“他者”的判然二分,认为在中国,任何政治建构只有符合相关的中国历史文化才能具有正当性,而脱离了中国历史文化或是从中国历史文化中开出了“他者”的文化都是不正当的。
以“三重合法性”为例,蒋庆认为“王道通三”,中国政治只有具有了天道、历史与民意的认同才能将“国民的服从变成政治的义务”,才具有合法性可言。“政治权力必须同时具有‘天地人’三重合法性才具有政治统治的正当理由。‘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地’的合法性是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 ”
以此,他对西方进行了批评:“反观自由民主政治,在合法性问题上只具有‘一重合法性’,即只具有‘主权在民’法理原则下的民意合法性,并且一重独大,排斥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与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使‘三重合法性’不能实现‘政道制衡’,从而使所谓的宪政制度安排只局限在为民意一重合法性服务的偏狭格局中。”
蒋庆简单地认为民主只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产生的,所以秉承“自我”文化优越论,认为西方政治只具有民意合法性。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而分析蒋庆之三重合法性,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合法性并不在于数量上的累加,三重合法性与一重合法性之间并不能仅从数量上就能决定其优劣。
第二,从中国政治思想的本意而言,所谓天道合法性其实是民意合法性的一种外在表现。汤武革命之后,周初统治者面临着如何以天命解释和确立周代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周公等一方面敬天法祖宗,另一方面又提出 “惟命不于常”(《尚书·康诰》)的观念。这种天命的转换实质上表现出来的就是民意。《尚书·康诰》中周公与康叔言“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应当说周公这里的主张一改周代之前的天命观,将民情赋予天,使得周代的天走出了神秘主义,并被赋予了民本主义色彩。自此之后,儒家的天、君、民的关系其实是:民意体现天命,符合民意天命而为天子,天子统治人民。所以,天的合法性实质就是民意合法性的体现。
第三,从合法性的历史文化因素而言,蒋庆将历史文化存在者化。在其观念中总是认为有一个凝固而物化的历史文化在那里,而实质上历史文化是不断更新和被诠释、赋予新的意义,并非历史文化中没有的东西在现实中就没有合法性。在儒家文化圈中,台湾、香港的文化也属于儒家文化,但台湾等相关的“政府”并没有产生来自历史文化方面所造成的合法性危机。
在具体的政治建构中,蒋庆诉诸宗教——儒教形式,以期通过复古宗教的形式保持中华文化的纯粹血统,从而与西方文化相区别。
蒋庆将儒学置于儒教之下,并从时间和超越性上认为儒教是“五千年中国人所共奉之超越神圣价值”,而儒学只是在汉代政制设计过程中超越了儒教。“在政制设计时降低儒教在历史形成之独尊地位,有否定六千五百年中国人共同同意之虞,于民主原则亦有所违背矣。 ”因此,在他看来,中国未来的政治设计必然以儒教为尊。
在具体的政治设计中,蒋庆依照三重合法性设置了通儒院、国体院、庶民院。通儒院,由儒者组成,以四书五经与天道为依据,体现的是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国体院,由历代帝王君主圣贤忠烈后裔推选,代表着国家历史性的承续,体现的是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庶民院则由单子式的个人和团体组成,体现的是民意的合法性。
蒋庆认为,通儒院和国体院都是“善的制度性力量”,对于民意之恶能够进行有限的钳制。这种“善”的力量,或者仅仅因为与圣贤有血缘关系,或者娴熟于圣王经典,实质上是在一种文化无意识之下对于“自我”有限性缺乏反思的表现。
2.“他者”的消解:世界体系视角下黄玉顺与干春松的儒家哲学
与蒋庆立足于民族性和民族国家的基点不同,在大陆新儒家的内部以黄玉顺和干春松为代表的一派,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立足于天下体系以消解“他者”。
黄玉顺在中西比较哲学的视野下提出了其生活儒学,目前积极致力于中国正义论的具体建构;干春松在近代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儒学,并于最近出版了《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
黄玉顺从民族性和现代性双重角度对儒学发展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现代化是中国未来的必然方向,特别是在民族国家的体系下,只有现代化才有可能保种保国。现代化也是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因为西方经济、政治现代化,“先行的事情是观念的现代化”,而观念的现代化则必须对传统进行新的阐释。
“我们的民族国家的命运一定离不开儒学的复兴。因为民族国家同时具有两个相互涵摄的维度,缺一不可:一个是现代性的维度,另一个就是民族性的维度。民族国家是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如果只有民族性的表达而没有现代性诉求,就是原教旨主义;反之,如果只是现代性诉求而没有民族性表达,就是自由主义西化派。”
在具体的正义论建构中,他提出了正义论的两条原则:正当性原则和适宜性原则。所谓正当性原则即要求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具有公正性、公平性。适宜性原则要求制度建构的空间性和时间性适宜,这种适宜性既涵盖了自然空间也涵盖了历史文化空间,它所要求的是“历时性的文化传统被收摄于共时性的生活方式之中”。黄玉顺试图在民族国家体系下寻求一种既是普遍的,又应允多元民族性的正义论体系。
干春松将儒家文化置于全球化背景之下,以民族国家解释全球化背景下的冲突,并以“世界”为基点积极建构一种世界秩序。
干春松认为现有的民族国家体系是建立在利益和私欲上的政治体系。在这一体系之下“对利益和效能的追求促使国家之间并不真正寻求一种互利的秩序,任何国家都谋求成为强大的国家,只是在逼不得已的情形下,国家之间才寻求合作的可能性”。 以美国为例,美国没有一个“世界价值观”而有“美国利益至上”原则。因此,寻求一种“为人类提供一种表达人类共同价值的处理平台”是对“他者”的有效的消解方式。
基于此,干春松提出了儒家王道秩序的观念以期超越民族国家基点上的仇恨。其核心就是要推崇“天下一家”以情感消解敌意,使得每个人认识到除了个人、国家公民之外,又有一个新的身份,即全球公民的身份。在这种儒家的王道天下体系中,干春松认为应当首先“引入全球利益维度”,“反思启蒙以来的人类发展模式”,“建立以个人和全球利益为基准的政治、法律体系”,“削弱各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建立以自主公民为主体的自我管理的社团和组织”,“改革联合国体系”,“通过协商建立一个议政机构”等。
三、余论:文化政治语境下的文化无意识与有限理性
文化作为基于历史承续的意义系统,与个体生活紧密相连。实质上,个体作为存在者,当其被抛入这个世界之时,就处于一种文化的无意识之中。生活在特定的地区、特定的时间的人们将文化当作“现成之物”而缺乏反思。所以,在每一个族群观念中都具有一种“自我”、“他者”的观念,当这种文化的中心主义与政治相结合,“自我”与“他者”的对抗才变得越来越尖锐。
如何走出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文化与政治结合的文化政治,所需要的是各个族群走出这一文化无意识,谨持一种有限理性对其文化进行反思。面对多样而复杂的世界,我们并不能自信地认为:仅仅以某一个族群的文化或观念就可以彻底解决一切问题。不仅仅是对于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亦是如此。正如港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所谓的“我不认为仅仅中国文化,便可以解决中国今日的问题。并且认为若仅仅肯定中国文化,且将无以防止中国文化本身所发生的流弊”。只有秉持如此态度,儒学才可能超越民族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焕发生命力。
注释:
(1)这里所谓的儒学复兴主要指的是儒学在理论界的复兴,而并非社会意义上的儒学的普遍复兴。虽然目前社会上流行各种祭孔读经活动,但主要是以开发旅游资源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正如彭永捷所言,儒学的复兴仍然是研究界小圈子的热闹,“儒家文化的处境可谓门庭冷落”。(彭永捷:《现代化背景下的儒学复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蒋庆儒学体系虽然内容很多,甚至他本人称之为“政治儒学”,但以主要内容而言称其为 “儒教政治”更为可行。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文章[M]//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