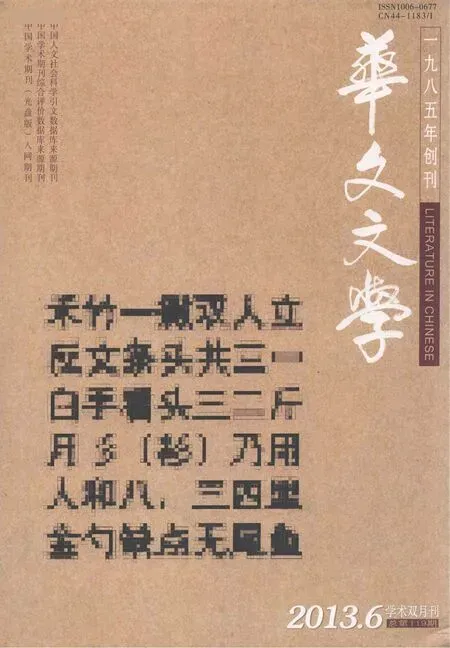求新,求变,求美——纪弦现代诗的美学追求
梁燕丽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
纪弦先生生年百岁,作为一个世纪诗星,自始至终求新、求变和求美,所以他的诗总是鲜活和新颖的、富于审美特质的,贯穿着现代诗的创生历程和美学追求。在《纪弦精品》的序言中,先生自言:“我的题材是多种多样的,我的手法是千变万化的。或为象征的,或为写实的,或为抽象的,构成的,超现实的;或为相对论的,采取什么样的一种表现手法,要看所处理的题材如何而定。”由此,从题材内容角度,一般把纪弦诗创作分成三个时期:大陆时期(1948年前)、台湾时期(1949-1976)和美西时期(1977—),体现出“我的诗生根于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决定了我的诗”。然而,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我们将从纯情和反叛,现实和超现实,以及现代诗的散文化等方面观照纪弦诗的美学追求。这些追求在各个时期,甚至在一首诗中往往是交织、交融在一起的,整体上显示出纪弦现代诗的审美特征,本不能在时序上或逻辑上分门别类,分开来说仅仅是论述的需要。
一、从纯情到反叛
无论“摘星的少年”,还是“槟榔树”和“半岛之歌”,纪弦都有许多“纯情”的诗作,包括爱情诗、饮酒诗、怀乡诗、植物诗、山水诗、宇宙诗等,表达一种真实、纯净、简朴、客观的美学意蕴,也追求一种现代诗的“散文价值”。然而,纪诗有时又会在单纯的底蕴上腾空而起,表现一种观念或美学上反叛、创新的决绝、复杂,这种探索在1950年代中提倡现代派之后或许成为主流,但亦时有漩洄。正如《半醉》里那个“对于那些顽固世俗的见解,/我抛出了挑战的手套”,仗着酒(酒神精神)而如此勇敢的挑战者;又如《个性》一诗:“在我的路上,/你掘了一步一陷阱;/在我的酒中,/你下了极毒的毒药。/但我举杯一饮而尽;/我大踏步向前走”,事实上,经过现代主义洗礼的诗人是最难归类的,因其最想追求的是创新、变化和个性。
纪弦一些极为动人的情诗和一些关注现实的即事题诗,可能在美学形态上是较为单纯和虔敬的,如那首感天动地的《你的名字》:
用了世界上最轻最轻的声音,
轻轻地唤你的名字每夜每夜。
写你的名字、
画你的名字、
而梦见的是你发光的名字。
如日,如星,你的名字。
如灯,如钻石,你的名字。
如缤纷的火花,如闪电,你的名字。
如原始森林的燃烧,你的名字。
还有,那首玲珑剔透的《恋人之目》中“恋人之目,黑且美”的醇美诗句。虔诚者则莫如《独行者》:
忍受着一切风的吹袭
和一切雨的淋打,
赤着双足,艰辛地迈步,
在一条以无数针尖密密排成的
到圣地去的道途上,
我是一个
虔敬的独行者。
看似简简单单的诗句,纯粹中有深味,轻盈中见重量,令人回味。又如写于1952年的《现实》:
甚至于伸个懒腰,打个呵欠,
都要危及四壁与天花板的!
匍伏在这低矮如鸡埘的小屋里,
我的委屈着实大了:
因为我老是梦见直立起来,
如一参天的古木。
这里颇有鲁迅野草中“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的愤慨,又有纪弦式幽默机敏的表达方式。“现实”如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纵然你是大材,在逼仄狭隘的困境中,也只能匍伏着生存,参天古木的生命伸展只是天才的梦想。一些从个人的地平线走向众人的地平线的诗作,如对于草根普罗大众的关怀,以及社会变革和社会反抗的关注,青涩青春的政治抒情,使沉滞局促的生涯也有激越的想象。如《贫民窟的颂歌》:“我住在贫民窟,/我是贫民窟的桂冠诗人,/故我作贫民窟的颂歌。……无数的穷人!无数的穷人!/无数的穷人!/无数的被欺骗与虐待的潮澎湃着。”作为贫民窟的苍白的众生物之一的我的血澎湃着。又如《穷人的女儿》:
穷人的女儿坐在垃圾堆上,
用她的天蓝的眼睛凝视着街的远处。
她是那么庄严,那么高贵,那么美,
像一个有许多王子在追求她,
有许多骑士向她宣誓效忠的
古城堡的公主
坐在垃圾堆上的穷人的女儿,变成高贵庄严的古城堡的公主,这是纪弦式的浪漫唯美想象,再增添上一些乌托邦明丽浮想。而《记一个酒保》:“我所永远忘不了的/是那小酒店的阿胖,/他心仁厚,/他的灵魂善良;/没有一点儿俗气,/在他那纯粹的平凡里”,却又是用朴素、平易来提炼“平凡”,使之成为通向不平凡的感情去的钥匙,仿佛举头三尺有天使。更有那些回望大地的怡然自得之诗,如《昔日之歌》:“昔日我住在一座小城里,深而幽暗的古老之家很难忘,日子如小城市的单纯,而古巷的晨昏是多诗的……”还有《构图》:“寂静的十字路口/满载着甘蔗的牛车/迟缓地行过,/一辆,二辆,三辆……/像活动的图案。/……岛上/诗一般的黄昏。”如此散文化的亲切、明净,不矜持、不夸张地侃侃吟述一种自然、古朴的生活感受,昔日小城的晨昏与今日岛上的黄昏,乃是重复出现的诗意栖居的构图。纪诗中还有更多关怀深广、情意绵密的诗作,如《爱云的奇人》、《今天》、《狂人之歌》、《命运交响曲》、《狼的独步》等代表作,客观生活经过主体的情感化,深深打上个人情结的印记——关乎生死、生命、命运的诗性哲意。形式上的变化从四行一节、凝练纯情,到大量运用散文体长句、第三人称叙事的小说笔法,夹以第一人称的内心独白,显出现代派的色彩;内容上亦从轻柔善感、普世关怀,转向对生活、爱欲、命运、存在的内心激辩,呈现出骚动反叛的灵魂。纪弦命定要扛起现代主义的大旗,在理论和创作中不断求新、求变,引领现代诗的炼狱:新的挑战接着新的挑战,新的启发接着新的启发,新的战栗又有新的战栗。然而,从纯情到反叛的诗风,在纪弦身上又是辩证统一的。
二、现代诗的散文化
纪弦是现代诗的点火人。他在《纪弦精品·自序》中写道:“什么是我对诗坛最大的贡献呢?曰:文字工具之革新,散文主义之胜利。”现代诗反传统,“就是反它那传统的‘韵文即诗’之诗观,乃系置重点于‘质’的决定”。也即,现代诗是内容主义的诗,而非形式主义的诗。现代诗舍弃“韵文”之旧工具,使用“散文”之新工具。现代诗不仅舍弃传统诗(即旧诗)的形式拘束及文字的袭用,而且,纪弦在1950年代中围绕《现代诗》杂志创立的“现代派”,更直截了当地提出“新诗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如果说传统诗以重感性的“诗情”为根本,那么现代诗则以重知性的“诗想”为根本。总之,纪弦倡导谱写全新的诗。这种除旧布新的胆识与决绝体现在《一间小屋》一诗:
……
当我提着一大串的钥匙,
走入这间堆满了线装书的小屋,
好不容易才找到那珍本,
而正在一页页摇头摆脑地朗读着时。
“咦!怎么搞的?眼睛花了不成?”
一股子陈腐的气息钻进了我的鼻孔来,
而珍本,已化为灰烬。
如此对待旧传统,即使今天看来也不无偏激之处,在当时必然引起诗坛的大辩论。纪弦、林亨泰与覃子豪、余光中等展开了“现代主义论战”,这场论战历经1956年和1957年两年,双方大战三百六十回合,结果无论胜负,所幸整个诗坛终走向了“现代化”。自此而始,现代诗的命运,无有格律依傍,无有必定遵从的规训规则,没有写下来就被认定为诗的形体格式,像传统的诗词那样。那么每首现代诗或许都是一个邀请,或者一个挑战,每首诗都有自己的面貌,在别人的世界里遭逢它自己,在读者的阅读理解里实现,或不实现它自己。诗人也必须完全敞开自己,等待读者发现和参与,在阅读中创造属于自己而不必是作者的理解与体会,推衍文学的潜在价值。于是,接受美学及其阅读的动态过程备受关注和强调,只有读者的释读、赋形,诗才是一首诗,一切都是邂逅,正如帕斯所言:“每一个读者都是一首诗,每一首诗都是另一首诗”。而读者的口味会变,息息在变。现代诗创作也在变,求新,求变,读者的口味因诗人的诗而变,一触即变。诗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再也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
三、现实和超现实
现实的诗和超现实的诗都代表纪弦的一部分追求。一些诗写得清澈浅显、简洁明快、毫不晦涩,当然其中也有用“简单”去传达“不简单”的,然而,另一些诗表达更为广阔、复杂、错综、鲜明、多变化的意象,要表达的应是潜意识的、意识流的、多面的,甚至在字面上不连贯、非逻辑的,所谓超现实主义,如《时间之歌》、《时常我想》、《在地球上散步》、《黑色之我》、《我,宇宙》、《足部运动》、《无人岛》、《失去的望远镜》、《火与婴孩》、《午夜的壁画》等现实与超现实。请看《在地球上散步》:
在地球上散步,
独自踽踽地
我扬起了我的黑手杖,
并把它沉重地点在
坚而冷了的地壳上,
让那边栖息着的人们
可以听见一声微响,
因而感知了我的存在。
一个踽踽独行的老人,用手杖点在地上,发出微响,这是“现实”,在现实的基础上开展的“超现实”想象:则是具有“魔幻”色彩的黑手杖,“沉重”地点在“坚而冷了的地壳上”,“让那边栖息着的人们”,“感知了我的存在”。阴阳相隔一点即通,这种生死界限的突破,此岸与彼岸的感应,可说是“现实”中的“超现实”。诗者即巫,诗想象的翅膀可以上天入地,可以通灵,结尾完全超越技巧,一种由“诗想”油然而生的诗意,形神自然自在。《预感》中“自杀的太阳一轮”,《火与婴孩》中婴孩梦里的“火”:从炉火、火柴到火山、火灾,都是自动生成的神奇图景,暗示着人神秘莫测的潜意识。再看《午夜的壁画》:
一盏灯,柔和地
亮在一间小小的木屋里;
三个一模一样的沉思着的影子,
构成了一幅午夜的壁画。
午夜的壁画,
是即我之三位一体。
午夜的壁画,
是即三位一体之我。
修长的我,
不可思议的我,
和破碎了的我。
……
我从何处来?
我往何处去?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而我知道的是:
纵有春风拂过,止水呀也不扬波的了。
故我投修长的影在壁上;
投不可思议的影在壁上;
那个破碎了的我
也投影在壁上。
此乃灯之杰作,
还让灯去欣赏。
灯是美的,
小小的木屋是美的。
午夜的壁画也是美的,美的。
“不可思议的我,和破碎的我”,“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这些天问似乎出诸客观的角度,但却集中主观的抽象,超现实的意喻所描摹的无非现实情况。现代诗,就像现代画中包含了各种解释一样。看现代画时,观者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感受去领会,不一定有特定的解释;同样道理,读者可从某种表达中去推想、体会诗意。也即,欣赏的方向没有特定角度,或许你今天这样理解,这样看,但一年后,可能又有另外的理解,不同的看法。现代艺术与古典作品不同的地方或许就在于此,也该如此。“午夜的壁画,是即我之三位一体,午夜的壁画,是即三位一体之我”,欣赏现代诗该像如此多面性。现代诗也不同于朦胧诗,现代诗中的“朦胧”不过是一种程序,不是要令读者不明所以。创作是内容决定形式。“灯是美的,/小小的木屋是美的。/午夜的壁画也是美的,美的。”纪弦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或一个颓废派,他说:“我的文字,有时明朗,有时朦胧,但我总会展现一幅画面,让你可以看得见;指示一种境界,让你可以走进去。”他的现代诗虽然求新、求变不遗余力,但首要的是求美,因为美是诗艺的灵魂。
陈寅恪先生自述教学三大特点:书上有的,他不讲;别人讲过的,他不讲;他自己曾经讲过的,更不会讲。香港诗人饮江联想到超现实主义诗人,或许会说:“这世上有的,我不会讲。”也即,现实和超现实的诗,既要和存在着的东西相关,更要与非既存的东西相关。存在着的东西前来打招呼,可能就是寄望于诗人去和不存在的东西打交道。列维勒斯在《上帝,死亡与时间》中说:“古远得无法记忆者对不可预见者的敬重”。诗人不恨古人之不见,应恨无由对无法记忆者和不可预见者的入思和敬重。先祖、先人、先行者、先辈,和后来者、后辈、后死者,不可预见者,轮回于此于彼者,于今生于来世者,其中包含诗人对于超现实一点点领会,正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说:“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也是爱因斯坦所说:“努力学习,等待启示”。超现实的诗作,既是技巧又超乎技巧,神附体,灵感眷顾,上穷碧落下黄泉,会有不可知的东西降临,或者到来。但超现实并非等于神话,现代诗人永远倾向于人或人性的价值。人不需要神打造,如果生命有意义,是人创造出来的意义,一切与神无关。如果真有神的存在,人也要与神划清界限,各有各的造化。然而,超现实的古代神话和现代宇宙,都是现代诗创作灵感的源泉,诗人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另一个投影。
生年只满百,却怀千岁思。直至晚年,纪弦写下不少超现实的未来诗和宇宙诗,如《悲天悯人篇》、《有一天》、《给后裔》、《梦想》、《二十一世纪诗三首》、《无题之飞》、《玄孙狂想曲》、《籍贯论》、《人类的二分法》等。纪弦不老,因为纪弦诗超越时空,永远不老。《有一天》这样写道:
有一天,我重返地球老家,
看见我的同类还在自相残杀。
我就唉的一声叹了口气,
说道:像这样的野蛮、无知,
你教我怎能邀请人家
前来访问、参观?
……
总有一天,我们的子孙,
是要乘坐超光速的宇宙船,
飞到那颗蓝色的行星去,
向那些文明人学习的。
这首写于1989年的宇宙诗,不仅具有地球人的宇宙意识,而且颇有理想主义精神。超光速的宇宙船,乃是岛宇宙与岛宇宙之间的交通工具,纪弦相信在今后五百年至一千年以内,这个梦想,是一定可以实现的。纵然这是诗人说梦话,也能使我们顿然心胸开阔,顿时与营营役役、同类相残的生存状态拉开距离。“蓝色的行星”指地球,地球是太阳系中水星、金星之外第三号行星,远远看去,是蓝色的,一种蓝色矢车菊一般的蓝色,非常美丽。可是美丽也只是一种梦幻,当外星人向往着子孙后代将乘坐超光速的宇宙船,来造访美丽的蓝色地球,向文明人学习,地球人不能不深感惭愧和反讽意味。在《给后裔》中:
我的孙儿的孙儿的孙儿,
立个志,去做太空人吧!
去访问仙女座的大星云吧!
那涡状的,多美丽呀!
她是我们最近的一位好邻居。
而当你们超光速的太空船
登陆在那边某一太阳系
之某一类似地球的行星时,
请回看一下自己的家乡银河系,
究竟像不像一个车轮?
诗人的想象力超过孙悟空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到达未来的宇宙世界,超越时空回望来处,银河系不过是一个车轮,而人类的自由与开阔已无可限制,种族、肤色、籍贯、偏见都显得渺小而阴暗,当“我一下了碟形的宇宙船,就看见广场上那么多的儿童”,白人、黑人、红人、黄人、棕色人、非洲人、欧洲人、亚洲人、阿拉斯加人,他们在唱印度歌、日本歌和台湾民谣《阿里山的姑娘》……诗人“没有省籍、没有国籍,也没有洲籍,/……而只说我是一个‘地球人’,/这也未免太委屈了,今天。/至少,你们应该承认:/我是一个‘太阳系人’”。如此看似漫无边际的超现实想象,亦是针对今天许多依然尖锐的现实问题,用“一点也不难懂的”散文化的诗句,表达出现代人的普世情怀和宇宙意识。谁说现代诗不可以这样写呢?谁说现代诗一定该怎样写呢?形式没有限制,想象没有边界,求新,求变,求美是纪弦永恒的追求,也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启示。
①②④⑤纪弦:《纪弦精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第3页;第5页;第3页。
③莫文征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弦精品》,分成“摘星的少年”、“槟榔树”和“半岛之歌”三个部分,对应大陆时期、台湾时期和美西时期。
⑥王良和:《打开诗窗——香港诗人对谈》,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