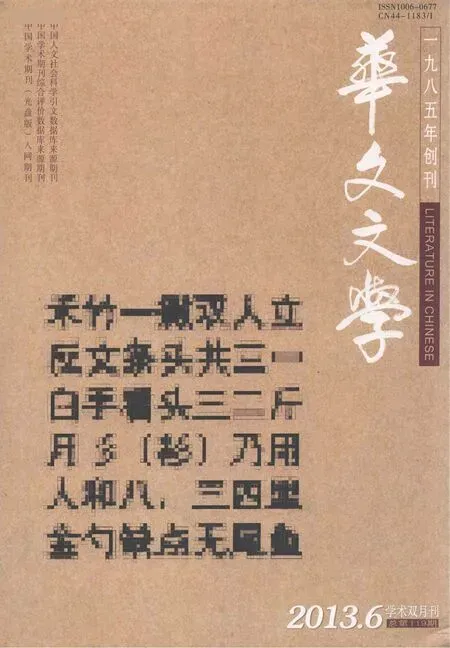小黑的历史修辞与小说叙事
[马来西亚]林春美
一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在马华境内发表的以马来亚共产党为题材的小说中,小黑的几个中短篇小说极为论者所重视。有人视之为标志着他展示其反思“以意识形态的对立为中心的包括战争与经济的这一世纪史现象”的力量与水平之作;有人更认为那是他九〇年代初的“扛鼎之作”,甚至“也应是马华小说史上极为难得一见的杰作”。
小黑原名陈奇杰,1951年生,六〇年代末即开始创作。他早期小说多在展示人生的荒谬性;自八〇年代中期始,则主要关注族群与政治议题,以及家国与社会之变异。小黑的小说创作量虽不丰,然其富探索性的表现方式,与对现实课题敏感神经的探触,已足以使他成为八九〇年代最重要的马华小说家之一。
1989年,原本任教于吉打州的小黑因工作升迁,举家迁往霹雳州实兆远的邻近小镇。那年年底,马共与政府达致和谈,结束双方近半世纪的武装对抗。实兆远是马共总书记陈平的出生地,小黑自言,他初到此地时,常骑自行车到新村走走,“仿佛在寻找共产党人的足迹”;而就近游览据说为马共活动基地之一的山洞,亦让他感到莫大震撼。在历史转折的时间点上迁临此处,使他感觉书写共产党的故事,仿佛是命中注定的一般;更巧合的是,他其后再经擢升、最终出任校长的南华中学,竟然就是陈平的母校。空间与时间的双重刺激,或许是推动小黑创作以马共为题材的小说的重要原因。1990年,他发表短篇《细雨纷纷》;1991年创作中篇《白水黑山》。这两篇小说与较早几年发表的、写得较为隐晦的短篇《树林》,一起收录于《白水黑山》一书,于1993年出版。2006年,他在《南洋文艺》为他作的一个特辑中发表短篇《结束的旅程》,以此作为他《白水黑山》阶段的结束。
小黑在上述特辑的访问中表示,《白水黑山》系列小说意在“检讨一段让我们华社困扰、痛苦的历史”。其与书同名的小说尤为学者所激赏,认为它根本就在“质疑历史的真实”。诚然,其叙述者在故事发展中屡屡现身,提醒读者“虽然事实就是历史,历史却未必是事实”(134);可是,这并不表示他全然否定历史的“真实”。
实际上,作为书写材料出现在小黑的虚构文本中的,与其说是一段“历史”,毋宁说是一段“过去”。“过去”(the past)和“历史”(history),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指“各处从前发生过的事”,而后者则指“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换言之,“历史”乃有关“过去”的书写。而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体,与历史编撰确有某些共通之处。新历史主义学者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如此指出:
没有任何随意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本身可以形成一个故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事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别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
小黑此类的书写固然如郭建军所言,“无意于(将笔力)放在对历史场面比如某次战斗的所谓‘如实’描绘上,而专注于开掘历史参与者在精神理想上的对照与冲突”;然而,因历史书写的过程如怀特所言,必然牵涉书写者对事件与描写策略等的选择,因此,我们应该可以说,以历史——抑或“历史参与者”——为素材的小说,亦诚如历史,“不论历史的可验证性多高,可接受性或可核对性多广泛,它仍不免是个人的思维产物,是历史学家作为一个‘叙述者’观点的表示。”小说家小黑在其对历史的“检讨”中,其实未尝不也极力主张一种他观点中的“真实”,并反复申述他自己对于历史的一套解释。本文要探讨的,就是这位小说家如何通过叙事去编撰他的马共“历史”,及其修辞方式如何建构他对“过去”的解释。
二
马共的故事,往往从他们走进森林开始,至他们走出森林而告一段落。“森林”或“山”,是小黑小说中的重要意象。他以马共为题材所写的第一篇小说,题目即为《树林》。叙述者虽然表示有阳光的树林是美丽的,然而小说中渲染得更多的,却是其反面。阳光被抽走的树林,阴森可疑,风吹草动都传播着不安,令叙述者感觉惧怕。其深邃的黑暗,足以溶解人的身影,让叙述者看不清父亲是否归来;它甚至是“一堵黑色屏障”(22),永远阻隔了叙述者与父亲。
吞噬了父亲的树林,散发着“阴郁”、“黑暗”、“凄凄惨惨”(17)的气息,予人一种压抑之感。而在小黑的另几篇小说中,山的意象,无一例外皆如是。在《细雨纷纷》中,抬头即见的绵延不绝的山脉,让叙述者觉得是“一种没有指望的姿势”;“飘渺的薄雾经年笼罩山巅”的景色,看在他眼里,“徒然增加挥洒不去的沉悒感”(38)。在《白水黑山》中,叙述者则有意以一望无际的稻田与峰峦起伏的山色为对比,前者让他感觉“眼界突然变得很辽阔,更有乘风而去的豪情”,而后者只能带来“黑压压的黑山横卧眼前的压迫感”(68)。在他与父亲的对话中,父亲说在黑山镇“可以看见大山把太阳一寸一寸地吞下去”,可是叙述者却说,在稻米之乡“可以看见太阳从地平线上一寸一寸地升起来。”(168)父亲口中的太阳,无疑隐喻自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而为抗英而斗争的马共,则被喻为立意要吞没太阳的大山。父亲给大山的精巧寓意,在儿子赋予太阳另一内涵时,产生了变异。在后者所述画面中,太阳是以升起的姿态出现(相对于被吞没),且升自稻米之田,因而充满朝气,象征希望。两者比照之下,稻田洋溢的是生机,而大山释放的,则是仇恨。
树林的意象营造,暗示了小黑对走进森林的马共的看法:那意味着对人伦的背弃,与对社会的隔离。《细雨纷纷》中,父亲“投奔森林”(34)一事让叙述者最不可接受的,倒不是其父作为“政府努力剿灭的恐怖分子”(37)的负面形象,而是他认为,即使为了理想大义,但“如果对于妻子儿女都可以放弃,父亲真太恐怖了。”(45)父子至亲,然而父亲却隐瞒动向,并且不告而别,导致他在警方盘问时对其行踪一无所知。父亲对人伦关系的轻侮与背弃,令他“除了彷徨,还感觉羞愧”(36),以致事隔二十年依然认为父亲不可原谅。
在《白水黑山》中,叙述者的父亲坚持不随儿子举家搬迁他处,而情愿孤独地留在那个对他而言已失却意义、而且“简直找不出一个值得(他)正眼一看的人”(170)的黑山镇。实际上,他坚守的不是镇,而是黑山。更确切地说,他坚守的其实也不是黑山,而是黑山所象征的他与马共英雄杨武共同的过去,以及他对杨武的崇拜与怀念。对于父亲“坚守黑山”之举,叙述者以一个矛盾语评价道:“时代进步了,只有父亲偏要停留在他那个暗淡无光的辉煌时期。”(171)黑山,或许确曾经历抗敌卫国的辉煌过去,然而其光芒已随时代的“进步”而消失。父亲耽溺于过去的记忆,因此不仅是逃避现实、自欺欺人,而且还是一种偏激的表现。其偏激性格让他在现实世界中无所适从,以致必须“从市中心热闹的南园茶室退出来,愈退愈远”(171),终究远离人群,孤立于社会。
山,象征父亲的理想与追求。对他们而言,随着时代的改变,“了解山的人愈来愈少了”(178)。可是对叙述者这一辈人而言,这理想却如前所述,是“一种没有指望的姿势”(38)。“没有指望”,不仅因为不得民心,还因为其本身就是经不起考验的,一如《树林》中的易碎的玻璃樽。《树林》里被暗示为给游击队传送信息的父亲,疑将“东西”藏在玻璃樽里。他收集的樽子叠得像一面墙那么高,这面玻璃墙在叙述者兄妹为寻找一条怀疑躲进其中的蛇时,被翻弄得倾塌了一半。无心者的“杯弓蛇影”尚且足以使其“理想”倾塌,警察所象征的执法力量的介入,当然更是轻易地就让“玻璃碎片溅得满地都是”(22)了。偏执于此“没有指望”的理想,正是一种不与时并进的固执,这恰恰是小说的叙述者们所不苟同的。《白水黑山》的叙述者赞赏母亲的灵活,因为“母亲不止一次说:‘时代变了,我们坚持的未必永远不可以改变。’”(105)母亲跟父亲一样深深崇拜二舅,可是,母亲却因有了这层领悟,而免于像父亲一样长久落寞地活在二舅“赴义”的阴影里。叙述者甚至也赞赏被父亲斥为没有原则的大舅。父亲的恶评无阻叙述者对大舅的亲近,在他看来,大舅豁达得没让历史成为包袱,并且在经历无数打击之后,“不但屹立不倒,而且能够从崭新的环境寻找到缝隙做为落足点,吸收日月精华,渐渐凝聚成一股强大的政经力量”(177-178)。相较于他对父亲的批评,他对大舅总是能够适应环境的圆滑性格的描述即使有一丁点调侃,但更多的恐怕还是真诚的赞叹。这与作者在书跋中述及自己不少作为“当年的强烈的理想主义追随者的后裔”的学生,一毕业即远走他国“追逐更多繁华的好日子”时所发出的慨叹:“时代变了”,如出一辙。《细雨纷纷》中那个忙于捞取台资、招待客户到边界嫖妓的叙述者,虽说其经历与作者相去甚远,然而他“一向不喜欢回溯过去”,认为“人是向前瞻望的。过去已是挽不回来的辛酸与沧桑,缅怀往事徒然增加愤懑与悲恸”(29)的价值观,却与多篇小说的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相一致。他通过这些叙述反复强调,马共的斗争如果不是不切实际,也至少是不合时宜的。拒绝看到时代的变化而偏执于这种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理想,毋宁是一种人生路向的迷失。一如《树林》迂回透露的:父亲未必是坏人,但却走错了路,尽管没有理由会迷失在他所熟悉的树林里,却终究永远回不来了。如此的下场给读者的警戒,或如小说中一个没有署名的声音所说的:“这是人民的一个教训。”(23)
小黑的这几篇小说,只有《树林》一篇从少不更事的孩童视角,对人物走进森林的行为呈现出有限的理解与模糊的揣测。这篇较早期的小说在叙述历史方面刻意委婉,甚至是隐晦的表现方式,一方面合乎叙述者的年龄条件,另一方面也是马共尚属于政治禁忌的时代氛围的反映。在其余几篇写于和谈之后的小说中,小黑则选择了成年人——而且都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为叙述者,并以第一人称“我”向读者直接讲述故事的方式,表达他对马共所主张的制度与其斗争方式的不认同:“我想父亲是有理想的。但是他也太不实际了。他怎么可能在这种环境实现他的理想?他想要靠谁的支持?”(45)、“父亲说的没有错。穷人的命运是要改变的,但是父亲的斗争方式令人惧怕,还没有正式接触,已失去大半民心。”(46)其中《白水黑山》及其姐妹篇《结束的旅程》的叙述者,更与真实的作者颇为近似——都是小说家,都姓陈,都是潮州人,二者母亲极为相似。这些成熟、理性、有反思能力、且带着作者身影的男性叙述者,无疑增添其所述之历史观点的可靠性,对读者而言具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
三
1989年的合艾和谈为各界开启总结马共历史功过的契机。走出森林的马共人物,其数十年来的变与不变,则是小说家对他们本人进行评断,甚至是对支撑着他们展开那场漫长斗争的意识形态进行检验的依据。
《细雨纷纷》大概是最早让走出森林的马共在小说中正式露面的作品之一。在与阔别二十年的马共父亲的初次会面中,叙述者就按捺不住地诘问他是否与多年前K镇某戏院的爆炸案有关。我们从他的责难得知,有十几个无辜的人在爆炸中身亡。父亲坚决否认,并说:“我们这一线从来不干懦夫的行动!”(51-52)然而在之后托人转交母亲的信中,父亲承认那起事件乃他一手策划,目的在于除掉害群之马,为牺牲的同志复仇。虽说“伤及无辜,实非所愿”(58),可是为了复仇而无视其他无辜群众的生死,毕竟也暴露了马共残暴的一面。父亲的说谎,更是证明了他不敢直接向儿子承认的凶行,其实正是他自己也觉得可耻的一种“懦夫”行径。隐含作者在此借马共本人的曲折作出的招供,让读者“看见”其暴政之手段,解释了叙述者觉得“父亲的斗争方式令人惧怕”的原因。
除了由下山的马共亲身供认,《细雨纷纷》其实也从其巧妙的情节编排(emplotment)凸显了马共之暴力行径。叙述者陪同母亲到勿洞(小说中细雨纷纷的山城)与刚下山的马共父亲会面,是小说中一个重要的情节。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共分16节、不按时间顺序叙述的小说中,分别与现时空中等候父亲出现和父亲终于亮相两节紧密相随的,是叙述者记忆中十多年前戏院炸弹爆炸事件。爆炸事件第一次出现在小说第一节:叙述者离开戏院为女友雪儿购买零食,闻爆炸巨响奔回戏院,所见只是慌乱逃窜的人潮,及横陈地上的残肢断臂与面目模糊的躯体。作者以此事作为开启他故事的第一个情节,既突显了爆炸事件在叙述者人生经历中的震荡效果,其毫无预告的血肉横飞的场面亦对读者造成一定程度的震撼。此节以设问结束:“血泊之中,雪儿呢?”(26)其答案肯定是读者在阅读中期望寻获的。然而作者却不急着揭示谜底,他的第二节故事将时间拉到十多年后,在细雨霏霏的山城等待与马共父亲会面这个事件上。父亲在这一节没有出现。可是过后几节讲述的父亲神秘性失踪事件及叙述者对其斗争方式的非议,却让我们将爆炸案与父亲联想在一起。待父亲在小说第十二节终于现身,叙述者(跟读者一样)迫不及待要他证实他与爆炸案之间的关系,可是对于真相的探究却在母亲的干预下被迫作罢。紧接着父亲扬长而去后出现的下一节故事从“歇斯底里的尖叫”(52)开始,尖叫声将读者拉回第一节的时空,回到当年的爆炸案现场,揭晓雪儿的下落。叙述者“站在人群中鹄候良久,终于看见了雪儿”(53)——那是雪儿的残骸,左脚失落,身首异处。叙述者“鹄候良久”获见女友惨死的真相,与他在勿洞“茫然鹄候”等待获见父亲(凶手)的修辞之一致,有意无意的都是一种讽刺。
怀特认为,“如果我们把历史事件当作故事的潜在成分,历史事件则在价值判断上是中立的(value-neutral)”。有关事件的性质如何,“全取决于历史学家把历史事件按照一种而不是另一种的情节结构或神话组合起来的作法”。换言之,“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组合”。在上述小说中,把父亲之亮相与女友之惨死这两个事件系列紧密编织在一起,其实已透露了隐含作者对于马共历史之阐释:这是一段与恐怖袭击、血腥暴力摆脱不了干系的“让我们华社困扰、痛苦的历史”。
而小黑对马共党人的理想与人格作出最严正审问的,恐怕还在他最受肯定的小说《白水黑山》。故事中的每一个人都以为早已在黑山瀑布壮烈牺牲的二舅杨武,四十年后竟从广州风光归来。叙述者第一次目睹的二舅是:“一个雍容华贵、气色红润、脸颊圆滑、眼睛锐利的老人”(185)。这个印象之“客观性”,从二舅旧日的战友及崇拜者——叙述者的父亲——的眼中大致得到验证。二舅对久别重逢的父亲说:“四十多年来,我们都经历了无尽的辛酸。”(188)可是父亲对二舅说:“你看起来年轻了许多,并不像经历沧桑呢。”(189)小说人物一句不经意的话,未尝不是隐含作者对二舅之言的“真实性”的婉转挑战。在叙述者的判断中,二舅此语是“轻描淡写”地说出的。“不像经历沧桑”,正解释了其“轻描淡写”地可能,也印证了通过叙述者眼睛所呈现的二舅形象之可信。二舅的气色与气势,在排除他确实经历沧桑的同时,也使其革命性——其传奇性英雄光环之来源——成为可疑。二舅当年从瀑布坠下后的故事无人知晓,但按他作为“广州有身份的人”(184)衣锦荣归的现状推测,他应该是在大难不死之后逃到了中国。四十年来,昔日战友为他的牺牲而耿耿于怀、落落寡欢,“在摧枯拉朽的岁月中渐渐缩小变成一个枯瘦偏激的糟老头”(178)。两相对照,二舅的意气风发、神采奕奕很难不让读者相信,他在众人与之失去联络的几十年间不仅没有历尽辛酸,而且还可能长时期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
杨武的境遇与马共总书记陈平有些类似之处。作为最高领导的后者,自马共于四〇年代末再度走进森林展开长期的游击战之后,其大部分时间不是随部队驻守在战斗基地的深山老林,而是安居于远方的中国,并且获得中共“兄弟党”的照顾。自华玲会谈之后就不曾公开露面的陈平,终于在合艾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上亮相。小黑在《白水黑山》的跋里透露,他当时从电视上看到陈平,对他的印象是:“脸色红润,闪耀富贵的光泽”。(203)他选择1989年电视上外貌富泰的陈平,作为荣归的杨武形象之原型。因此,当杨武出现在叙述的现时空中时,这个在众人认知中原本早该慷慨赴义的“烈士”不仅未曾牺牲,而且竟然还像个“富贾”一般活着归来,“烈士”与“富贾”形象的巨大落差,就形成了对他曾经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的莫大嘲讽,也暗喻着他对其昔日追随者与同志的莫大背叛。
另外,小说叙述者富含深意的措辞,亦蕴藏隐含作者对这个历史参与者的评价。叙述者说,二舅回来之后“一直都抽不出时间与父亲见面”,大舅的商业伙伴大摆宴席庆祝他的荣归,“夜夜轮流轰炸,一口气把个二舅俘虏了三天,七荤八素,炸得二舅晕头转向,乐不思蜀”。(186-187)众人心中何其神勇的二舅竟为手无寸铁的商贾所“俘虏”、为美酒佳肴所“轰炸”,作者寄寓其中的讽刺不可说不尖刻。其后,在叙述者从旁见证二舅与父亲终于重逢的关键情节中,只见欲言又止的父亲最后“好像下定决心做一件大事”,提出要与二舅旧地重游,再看一次象征他们革命事业的“森林之火”。可是二舅的反应竟是“有些愕然”。他委婉推辞了父亲,表示次日一早还要飞往都门拜会“对内陆投资很感兴趣”的几个“老朋友”。(190-191)这个情节所揭穿的“真实”是:父亲对二舅景仰依旧,可是曾经被二舅托付以其革命“遗志”的父亲,如今在二舅心目中的分量,已远远不及其商业上的朋友。都门“老朋友”的存在更是戳破二舅无情寡义的真面目:当家人与至交都被蒙蔽在其虚假的牺牲之中而悲伤时(父亲更是因以为二舅舍身救己而一直活在耻辱中),他其实一直都完好地活着;他没有联系家人,却跨国织起了商业网络。在瀑布事件中生还的马共斗士,其当年的理想已阵亡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诱惑中。
然而,《白水黑山》对马共革命理想之虚伪性质批判得最得力处,还不在作者精彩的措辞,而在于作者“双声”的叙述策略。《作为修辞的叙事》一书的作者指出:“作者声音的存在不必由他或她的直接陈述来标识,而可以在叙述者的语言中通过某种手法——或通过行为结构等非语言线索——表示出来,以传达作者与叙述者之间价值或判断上的差异。”《白水黑山》正是如此。这篇小说的叙述者与他在小说中所写的小说,从一开始都不断地在渲染杨武的英雄特质与传奇色彩。叙述者直接道明他父母与杨武之间的深厚情谊令他深为感动,并表示自己在书写杨武故事时前所未有地为小说人物掉泪,在写杨武赴义前的情节时甚至激动得必须紧锁房门不让妻儿干扰他的情感。他的叙述引导读者相信:英雄杨武值得他们——以及作为读者的我们——投入许多情感。他对真相必须辨识之自觉,及知晓对过去的理解会因人而异的理性表述,使读者对其所述内容的可靠性充满信心。然而,在其所述之故事层面,因人的理解而有所歧异的历史,主要指向杨武遇难是否白猴所害之事件:父亲与母亲坚信是白引兵伏击杨武,大舅却力证白与此无关。叙述者为此思忖:“谁也不相信谁。谁说的才是真实的历史?每一个说故事的人都相信他自己才是真正的目击证人。历史就有得看了。”(177)可是,他却显然无意追究当中虚实。其对故事的讲述,将读者对历史真相的思考引向对杨武——而非对白猴——的理解。在小说中,众人对杨武原本是最无异议的:抗日—反殖—牺牲,这几个重大事件构成他的“历史”,继而决定众人对他的崇高评价。尽管陈立安(即父亲)在英国人重建马来亚社会秩序时曾质疑过马共继续森林游击战的必要性与价值,然而杨武的“牺牲”不仅迫使陈之质疑因内疚而失效,亦使战斗者的道德与理想因其牺牲而变得无可置疑。如果杨武的历史完结于此,则他“舍身取义”的真诚/真实性将无可疑议——这正是叙述者从父母的口述/诠释所建构起来的对杨武及其表征的那段意识形态斗争历史的认知。可是历史还有其后续的发展,瀑布遇难并非事实之全部。数十年后,以“富贾”形象归来的杨武、对内陆投资比对“森林之火”更感兴趣的杨武,一方面让读者惊觉我们对革命者的期待落空了,我们先前投入的情感被背叛了;另一方面亦暴露作者的弦外之音:对过去并不全面的了解,将影响人们对于历史的正确认识。杨武及其意识形态斗争的正面历史,显然是以局部事实为材料建构而成。从他牺牲至归来的数十年时间,从来都不曾存在于“历史”。“归来”的事件,成为作者用以修正杨武的“历史”的重要因素。在此事件中,他让说故事的人本身(带领读者)成为杨武富贵光泽的“目击证人”,迫使读者必须去正视与追究杨武那不曾曝光的过去。杨武沧桑阙如的外表与商人气质,顿时成为新而可信、且暗示性极强的材料。据此“编撰”的他那空白的数十年历史,就很难不如作者在其跋中所说,是以这个历史参与者——或他所影射的“某一个人”——“修正了又修正他的思想(以致乖离了当初诱人的口号)”(201)为主要内容的。
在对《白水黑山》故事进行后设创作的《结束的旅程》中,“归来”依然是作者审视经时光洗礼的马共的主要设计。故事中,二舅被置换成了三叔。在叙述者带领三叔回白水镇的整个旅途,三叔只在两处展露了笑容。第一次是在黑山观看瀑布时:“三叔终于露出这许多天来的第一个笑容。那朵微笑是那么诡异,让我摸不清楚真正的含义。”第二次是黑山下来,三叔明知故问地问叙述者是否知道他当年如何逃过军队的围剿,随即又“不无得意地”抢着说出当年的瀑布逃生记。当他表示曾从叙述者的《白水黑山》中阅读被他掉包的故事时,脸上又再出现了“奇异的笑容”。这些“诡异”、“奇异”的笑容里,尽是洋洋得意,充分反映三叔极度个人英雄主义的心态。不管是136部队登岸的海湾也好,马共集训的山洞也罢,对三叔而言已没有任何意义。他像香客一样来“朝圣”,所朝拜的不过是自己当年的英雄历史。这终究是他的“结束的旅程”。所以故事的最后,三叔说“幸好要回去了”。这句话让叙述者十分感慨:“三叔本来是白水镇的孩子,如今却说‘幸好要回去’,我默默地咀嚼,一时间也不知怎么形容”。《白水黑山》也有类似的一笔。叙述者原本说:“二舅回来了。”(183)可是又马上自我纠正:“不。二舅是出国到南洋访问移居海外的兄弟。”(184)三叔与二舅身份有所变异,然而他们最终的归属没有改变:回到中国。“归来”,竟成了他们早已“回去”的明证。隐含作者对此的“咀嚼”,是否有意暗示读者:马共的革命——虽然也有如《细雨纷纷》中的对其他族群的阶级关怀,然而,终究也还是以华人为中心的族群—民族主义的革命?
四
小黑小说的叙述者饶富意味地指出:“每一个说故事的人都相信他自己才是真正的目击证人。”(177)作为说故事的人,小黑本身未尝不也如是。
然而,一个人能目击的过去到底有多少?《历史的再思考》一书的作者说:“自来便没有任何历史学家的记载,能与过去确切地对应。单是过去的庞大,便使得全面和完整的历史成为不可能。”对历史资料的掌握与认知固然决定了小说家对过去的看法,然而小说家个人的观点与思想倾向,却也同样决定其对历史资料的取择。虽然这些都无阻于他以其精彩的叙事技法建构“真实”,然而,它终究更应被视为是——对真实的一种解释。
①[11]郭建军:《世纪末回首:论作为南洋反思文学的小黑小说》,《华侨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第94页;第97页。
②⑦陈鹏翔:《论小黑小说书写的轨迹》,见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编:《赤道回声:马华文学读本II》(台湾:万卷楼,2004),第431页;第436页。
③所游之椰壳洞(Gua Tempurung),后来即是其小说中“黑山”的原型。详阅苏燕婷整理:《从黑与白之间回到小说的传统》,见《中文·人》第2期,第8-9页。
④苏燕婷整理:《从黑与白之间回到小说的传统》,第9页。
⑤⑥张永修:《前夕与今夕:访问小说家小黑》,见《南洋商报·南洋文艺》2006年2月7日。
⑧本文所引《树林》、《细雨纷纷》与《白水黑山》,均出自小黑:《白水黑山》(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3)。此后仅注页码,不另说明。
⑨[12][20][英]凯斯·詹京斯:《历史的再思考》,贾士衡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第96页;第95页。
⑩[15][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见张京媛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163页;第164-165页。
[13]小黑在《白水黑山》跋中写道:“日子久远,我已渐渐忘记,书中的母亲是不是我的母亲。不过,当我在叙述母亲时,的确有那么一个母亲在我心中。”(205)他在接受苏燕婷等人访问时,亦承认此处的母亲与他自己的母亲有七八分相似。见《从黑与白之间回到小说的传统》,第7页。
[14]小说中诸如“这是我在大学三年一直思考的问题”(46)、“我长大以后分析”(101)等句,都有助这种形象之建立。
[16]陈平于1960年12月开始“北撤中国”,1961年抵达。详阅《我方的历史》。
[17]小黑在《白水黑山》跋里说,1989年出席采访的现场记者形容陈平“像一个富贾更甚于隐秘四十年的政治人物”(第203页)。
[18][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19]本文所引小黑:《结束的旅程》,皆见于2006年1月31日及2006年2月4日的《南洋商报·南洋文艺》,不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