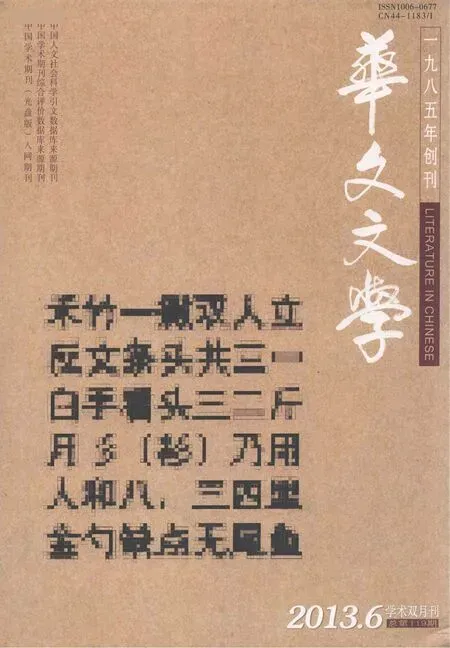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论陈铨的文学批评观
曾一果 季 进
(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最近几年,中国学者就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价值和地位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尤其是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尖锐批评,更是引发了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学存在价值的思考。中国文学对于世界文学到底有没有贡献?西方文学是否比中国文学更高级?我们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看待中国文学?这些问题困扰着不少中国学者。当然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五四以来的学者也都一直在探讨、思考。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战国策派”的主将陈铨便就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价值和地位进行了深入讨论。陈铨曾在德国留学,深受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和尼采思想的影响,他借鉴康德、黑格尔和叔本华等人的思想,深入考察了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特征,并站在“文化主义”的立场,重新评估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世界价值,提出重构中国诗学的四种尺度,并指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应走的“新方向”。但由于各种历史因素,陈铨对于中国文学批评诗学的建构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一、“文化主义”的批评观
1943年陈铨以唐密的笔名,在《民族文学》上发表了《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一文,论文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文学到底有没有世界性?陈铨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其实这是他针对1917年“文学革命”以来的中国文学现状的思考。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化氛围为一股怀疑和反叛精神所笼罩,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进步的,而中国传统的一切都遭到了怀疑。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使许多人产生了一种“文化焦虑”,古典文学被认为是腐朽没落之物,跟不上世界潮流,它们对世界文学已毫无意义,中国文学只有全面抛弃旧文学,引进西方文学思想和价值观念,才能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学。中国文学难道真的缺乏“世界性因素”?到底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呢?陈铨的这篇文章就是想解决这样的文学问题。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和文化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早年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的胡适等人也开始“整理国故”,重新审视中国的文化传统。陈铨的一系列文章也是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认识,这些文章一个很大的贡献是较早地站在“文化主义”的立场,重新评价了中国固有的文学和文化。在《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中,陈铨上来就提出要判断中国文学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学到底有没有对世界文学作出贡献,就必须有一定的“批评标尺”,如果没有一定的批评标尺,每个人自说自话,自然无法认识中国文学的价值。为此,他对世界范围的文学批判类型进行了深入考察,认为世界范围内的文学批评类型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修辞式、内容式、天才式和文化式。他认为有些民族的世界价值在于修辞或者内容,也就是艺术价值高,但绝大部分民族文学的价值却不能用修辞、内容和天才去考察,而应该拿“文化的标准”去衡量,因为文化才是一个民族许多人思想习惯的“结晶”:
一个文化是一个民族许多年代许多人物生活思想习惯的结晶,经了种种方法地熔铸陶冶,结果成了一个民族共同对人生的态度。他们有他们特异的世界观人生观,同旁的民族迥不相同。
在陈铨看来,就是天才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特殊的文化环境中产生,“在这一种特异地世界观人生观的空气中,有天才的文学家会去创造他的文学,不知不觉也就受了影响,结果他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发表他个人的思想感情,同时一方面他也是一个文化的代表。如像歌德的浮士德固然是歌德对人生的启示,而同时也就是全德国文化对人生的启示,因为浮士德不但代表歌德个人同时也代表德国全民族。拿文化式的标准来衡量文学,就是去研究某一种文学里面表现出来某种文化对人生的启示。因为我们的标准是从文化上着眼,所以凡是愈能够代表某种文化的作品,我们愈认它为伟大。”陈铨虽然受到尼采影响,强调“天才”的历史作用,但他和尼采不同的地方是,他强调天才是在一定文化环境中产生,缺乏了这种环境,也就没有了天才。
至于那些缺乏艺术性、天才性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在陈铨看来也并非没有价值,只要它能够代表某种文化,不管它有无艺术成分,都是“伟大的”,他认为中国戏剧就是这样,尽管艺术成分不高,“大部分的戏剧本都俗陋肤浅”,但却具有“文化的性质”,“代表中国文化的力量却非常之大”,因此具有很高的价值。陈铨指出,“文化标准”的文学批评,和修辞、内容以及天才标准的文学批评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文化标准”的批评者并不注重一个作品或一个诗人在艺术上的成功,而注重代表整个文化的文学。
陈铨的文化思想其实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著名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观点很相似。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它的内涵随着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总体来说,人类文化可以分成三种文化类型:1.理想的文化,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按照这种定义“文化分析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或作品被认为构成一种永恒秩序、或与普遍的人类状况有永久关联的价值的发现和描写”;2.文献式的文化,文化是理性和想象作品的集合,主要是指一些历史典籍和文学经典,这些作品集合以不同的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3.社会的文化,文化是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as a way of life)的描述。雷蒙·威廉斯肯定的是第三种,强调文化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而陈铨实际上也是把文化看作一种整体的实践行为和生活方式,在这种文化观念下,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无论它是高雅的,还是通俗的,无论它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代表了某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所以是有价值、对整个世界文学也是有贡献的。
尽管陈铨本人身上具有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但他的“文化主义”批评观,却不是精英主义式的,相反,他颠覆、突破了以审美和道德为准则的精英主义文学批评传统。他认为那些存在于底层的各种通俗、浅陋的民间文化并非毫无价值,从文化角度看,这些民间文化具有较高的文化和历史价值,这些低俗的民间文化为世界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样式。由此可以看出,陈铨的文化主义文化观,其实为人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学和文化,乃至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学和文化的价值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二、中国文学的世界性
而在其批评的实践过程中,陈铨即以一种“文化主义”的文化标准考察中西文学。1933年,陈铨用德文完成了博士论文《德国文学中的中德纯文学》,1936年,商务印书馆将此博士论文以“中德文学研究”为题目出版。在这篇博士论文中,陈铨运用文化主义的批评标准,仔细考察了《赵氏孤儿》、《西厢记》这些中国文学作品在德语世界的传播过程,并重新评估《赵氏孤儿》和《西厢记》的文学价值。
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中国学者,大多从事西方文学典籍的翻译,很少反过来研究“中国文学”在西方的传播情况。主要原因便是像陈独秀、胡适等五四先锋深受西方进化论思潮的影响,觉得在世界文化潮流中,中国文化已经落伍,西方文化是“先进的”、“高级的”,代表着未来文学的方向。陈铨却是一位较早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学者,这本身就反映了陈铨具有很强的“文化意识”,他不因中国其他方面的落后而认为中国文学和文化也毫无价值,因为他认为从文化主义的立场去看,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价值都是一样的,提供了不同的人类生活方式和文化样态。陈铨仔细地梳理了从1763年(即《中国祥志》)以来二百年间,“中国文学”在德国的翻译和介绍情况,考察了歌德、莱布尼茨等人所受到的中国文学的影响。在仔细的考察中,他发现由于中德两国之间的隔膜,德国人对于中国文学并不了解,以致他们翻译中国文学时产生了许多错误:
如果我们再去翻一翻阅在德国最负盛名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一部卫礼贤(Wilhelm)一部是格汝柏(Grube)。看见他们讲中国文学家名字同作品的稀少,我们也会同样地失望。至于德文里大部分的翻译,都是从英文或者法文转译出来,英文法文的译者已经就不高明,德译本的可靠性更可想而知。一般译本里的绪言,大都是乱七八糟地瞎说。
陈铨的批评研究无疑提醒国内学界,不要什么都以西方为是,他说从十八世纪以来,即使最负盛名的德国汉学家,也经常误读中国文化,因而才把中国二流作品《灰阑记》、《好逑传》当作中国经典。陈铨认为如果从“文化”角度就很容易理解这种现象,欧洲人学习汉字本来就很困难,要了解中国文学经典,那就更要耗费很长时间,《灰阑记》和《好逑传》之类的中国二流作品却能够简洁明了地提供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和思想,所以就容易被西方的学者和大众接受。
除了站在“文化的”文学批评立场考察中国文学在西方的传播情况,陈铨也用“文化的标准”审视中国古典文学,与梁漱溟等学者的看法一样,陈铨也认为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早在孔子和老子之前,就已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从那时中国这个民族对人生的态度就基本固定了,而伟大人物孔子、老子等的作用是固定了这种文化,结果形成了三种基本形态:合理主义、返本主义和消极主义。孔子代表合理主义的人生态度,老子代表返本主义的人生态度,外来的释迦牟尼代表消极主义的人生态度。而政治和文学作品只不过是三种基本文化形态的具体演绎,譬如有的作品表现的是孔子思想,有的作品表现的是道家思想。陈铨还详细地分析了三种文化所代表的具体思想,他认为孔子思想的特点在于强调人生的明白性,一切都清清楚楚,而站在这一种文化观的立场来创造的文学,不会有“伟大内心的冲突”,“激烈感情的震荡”,“丰富的想象”和“神秘的思想”。他说中国的散文和史书大多受到孔子思想支配,这些文章的技术达到了很高水平,令其他民族难以企及。“我们只消想,英法散文的历史,也不过三四百年,德国不过二百年,再想中国二千多年以前散文,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就很可以自豪了。”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朱熹的《通鉴纲目》,都有一贯的儒家精神,史料和文章的本事,具有很高的水平。他认为从文化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中国文学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同样,陈铨认为道家和佛家文化也深深地浸透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之中,并且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陈铨虽是“尚力文学”的代表人物,但他却从文化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强调柔弱文化的老子大加赞赏,他说《道德经》“是一部奇书,可以算全世界哲学诗里最伟大的著作。他长不过五千言,但是这五千字所表示出来的哲理,别人五百万字也表达不出来那样丰富。”他认为《道德经》显示了中国文学在深刻性方面也丝毫不逊于任何其他民族的文学。如果不了解陈铨的文化主义立场,就很难理解“尚力文学”的代表人物陈铨会如此褒扬老子,而在“文化主义”视角下,陈铨还看到老子与西方近代哲学的关联:
第一个有胆有识,激烈反抗的人,就是尼采。他看见世界的危机,他恨极了肤浅的生活,他想要重新去维持人类的尊严,他想创造一个新的神话,新的宗教,新的文明。二十世纪的初期,在哲学界,黑格尔复兴运动,生存学派,渐渐普遍,从新康德派的“理性哲学”变成了近代哲学的“精神哲学”。在文学方面,自然主义,渐渐消灭,最时髦的,却是新浪漫主义,表现主义,西洋文化的趋势,是从外形到内心,从物质到精神,从枝叶到根本,从分离到统一,是有目共见的事实。老子的哲学,因此在欧洲也发生了相当的影响。就好像十八世纪欧洲光明运动者,崇拜孔子的合理主义,欧洲不满意现代文化的思想家,也回头研究老子的返本主义。
如果不是本着“文化主义”的立场,陈铨是看不到老子和尼采之间有关联的,正是“文化主义”批评立场使得陈铨对西方文化有着清醒认识,使他意识到不同民族的文学各有千秋,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他希望《道德经》可以变成“现代人到东方的桥梁”,他甚至希望通过交流,把中国文学带进“与全人类相关的世界文学”中去。
三、重建民族本位文化
“文化式”的批评观,其实亦是陈铨后来努力建构“民族文学”的理论依据,“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事情。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列强的入侵之下,中国不断遭遇失败,这直接导致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产生,五四运动就是在民族危机中爆发。在民族存亡的问题上,无论是左翼文学组织,还是右翼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均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思考中国问题,推行各自的“民族主义”主张。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处于战争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化和民族文学的思考就更深入了,沈从文、费孝通、周扬、胡风、老舍、茅盾等人关于“大众文艺”、“民族文学”等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此时,陈铨也站在“重建本位文化”的学术立场上,提出建构“民族文学”的口号。
陈铨肯定了文化是文学的决定因素,文学只是文化的具体形态,具体而言,是民族文化的具体形式。他说当一个民族“到了文化相当的程度,大多数人渐渐有一种或他种共同对人生的态度”,这就形成了民族文化,而一切的政治宗教道德风俗哲学美术,都直接间接接受这个标准的影响。由于民族文化决定着“民族文学”,所以他认为在“文化的标准”下,建立“民族文学”是必要的,民族文化需要一些作家把它“充分表现出来”:
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来说,一个民族对于世界文学要有贡献,必定要有一些作家,把他们的民族文化充分表现出来。一位作者,在世界文学史上要占一页篇幅,一定要有写作品,代表他民族特殊的性格。英国文学史里面,不需要一个中国人,勉强加进去也没有多大的意义,王实甫和曹雪芹的戏剧小说,在世界文学上,自然有他们很高的地位,然而他们决不是莫利哀和托尔斯泰。他们都是中国人,《西厢记》《红楼梦》真正的价值,就在于他们表现中华民族特殊的文化。
陈铨强调,一个民族的文学要对世界性有贡献,必须是表现自己,而不是模仿他人,他认为如果一个文学家成天仿效外国,那么他的文学,也不值得世界上的人尊重和欣赏。陈铨激烈地批评了五四以来的“拿来主义”文学倾向,1919年的辛亥革命为中国带来了民族主义意识,使得人们第一次认识自己民族,而新文化运动打破了旧文化传统,带来新的文化气象,这一点是为陈铨所肯定的。但是陈铨认为新文化运动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没有创造出新的文化,相反盲目崇外的风气造成了一种“古人不要了,外国人神气了,打倒旧偶像,崇拜新偶像,名义上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外国旧文化运动”的现象。他认为这种“新文化”是可怕的,得不偿失,不仅没有带来新的文化,最终会连中国文化的根基也丧失殆尽。
自然,陈铨并非要借民族文学反对西方文化,他试图区分文明和文化的概念,以说明学习西方存在着不同的层面。他认为文明可以全部搬过来,文化却不能够全部搬过来,努力是白努力,定夺不过摧毁自我的发展。陈铨眼中的文明显然与科学技术相关,他认为可以移植和仿效,而文化则与精神结构关联,不能完全照搬。而在陈铨看来,新文化运动的失误就在于混淆了文明和文化的概念,全盘照搬西方。而要改变这种现状,在他看来就是要重新建立起本位文化的民族文学来。
但是本位的“民族文学”的内核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复活中国古代的文化就行了?显然不是,陈铨并不像其老师“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吴宓那样过分迷恋中国传统文化,而认为五四新文化一无是处。相反,他受了黑格尔的“时代精神论”的影响,特别强调文学的时代因素。他认为新文化必须要由新文学来表现,旧文学不能表现新精神。陈铨批评了中国古代文学缺乏“时代意识”,盲目崇古,不思创造,导致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数千年没有发展,他认为个中原因就是“时代精神”没有演进,文学不能摆脱古人。所以陈铨提出重建本位的“民族文学”并不是“复古”,而是重新寻找民族文化的思想资源,并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展出新的中国文化。
当然,这是陈铨的一种设想,在实际的建构过程中,他仍然是采取了“拿来主义”态度,将黑格尔、康德、尼采的理论杂糅在一起,作为自己建构中国“民族文学”的理论根基,他特别强调了文学的主体性,甚至大胆地提出以“权力意志”为中国文学批评的新动向。
四、文学批评的新动向
1943年,重庆正中书局出版了陈铨的著作《文学批评的新动向》,这本著作中的许多文章都曾经发表在陈铨、雷海宗等人主编的《战国策》上。这些文章的核心便是建立“民族文学”,前面已经指出,陈铨其实是用康德、叔本华,尤其是尼采的主体思想作为其重建“民族文学”的理论资源。
陈铨认为西方近现代文学批评和古代文学批评最大的不同,就是现代文学批评发现了主体(人)的价值,他说,“文艺复兴”之前的希腊悲剧和希腊哲学以亚里士多德的批评观为代表,都相信自然中有一定的规律,这种思想统治西方思想二千年,而文艺复兴打破了这种观念,把文学批评的对象由自然转到了人身上,确立了以人为主体的文学批评体系。陈铨称赞康德是西方文学批评转型中最伟大的批评家,他认为正是康德动摇了西方传统的基石,“假如人类是一切事物的中心,世界上一切规律都不是自然事物的本身,乃是人类心灵的创造,那么在文学方面,从希腊以来一脉相传的文学批评家所认为天经地义的规律,就时时刻刻有动摇的危险,因为规律是人类心灵的创造,人类心灵有变化,文学批评的规律自然也就有变化。”陈铨认为近代西方文化就是“从外在到内心,从物质到精神”,越来越张扬“精神主体”,永恒不变的外在规律不复存在,一切随着主体意志的转移而转移。
普通个体的内心世界已够丰富多彩,不受规律约束,天才就更不用说。陈铨接受了康德、尼采的天才观,极力宣扬天才的价值。他指出天才不但不受一切规律束缚,而且能够创造规律,“仿效不是天才,天才一定有与众不同的贡献。规律不能束缚天才,天才随时可以创造规律。一位天才艺术家的作品,我们能够就它本身的规律来说明它,不能够用旁人预定的规律来指摘他。”他还抄录了康德的大段原文称赞“天才”,他把天才看成自由心灵和崇高精神的体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陈铨强调主体和天才,这与其文化主义批评观并不矛盾。“文化的标准”是陈铨文学批评的基石,而文化在陈铨看来,不仅与物质相关,更联系着精神世界。所以天才代表精神,也就代表着一种文化,具体地说,代表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且在文化的前提下,陈铨在盛赞天才的同时,并没有否认那些艺术性不高的一般文学作品。在陈铨看来,尽管一些艺术性不高的文学作品可作民族文化的典型,但天才所创造的文艺作品,往往更能代表某一民族文化,要想认识德国的思想和文化,自然要去阅读歌德作品。西方近现代文学批评实现了由外部世界向内部世界的文化转向——强调个体精神和自由意志。这一文化转向被陈铨认为可以借鉴过来,解决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问题:
人类的自我已经发现了,世界已经转变了;天才,意志,力量,是一切问题的中心,创造发展,是全世界人类共同努力的方向,我们再也不要任何“外在”的规律,来束缚我们自己,我们要根据“内在”的活动,去打开宇宙人生的新局面。
陈铨认为中国的民族文学要想发展,也应该强调个人主义和主体精神。他认为新文化运动轻视主体性,因此没能把握“文学批评的新动向”,具体而言,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犯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严重错误:即“把战国时代看作春秋时代,把集体主义时代当作个人主义时代,把非理性主义时代当作理性主义时代”,他说五四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忽然发生了转向,把本来强调主体性的文化活动变成了崇尚客观性的科学活动,导致了科学至上、阶级斗争等思想的泛滥,中国文化走上了重视形而下的物质主义道路,陷入了盲目的科学、机械和阶级信仰,忽视了个人和社会的精神建构。结果,不仅个体自由失落了,而且整个民族从此丧失了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要摆脱这种现状,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光靠科学和机械文明是不行的,还必须创造自身的精神文化。
而作为进一步要求,尼采的信徒陈铨希望中国文化也应有在世界大战的时代环境中求生存的“权力意志”。所以,在重庆出版的《文学批评新动向》一书,陈铨把“意志哲学”作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将来方向,他说在将来社会里,“意志哲学”才是中华民族进步最合适的良药,中华民族要在大时代中生存,必须追求“权力意志”。
通过上面论述可以看出,陈铨吸收西方文学中关于主体性的批评理论,提出以“文化的标准”考察中西文学的价值,颠覆了以审美为中心的精英主义文学批评模式,让人们重新认识了中国文学和其他民族文学的世界价值,对于我们思考当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也具有重要启示。而且,他提出的“民族文学”主张,强调个人意志和主体精神,弘扬民族主体意识,更是对“现实主义”的批评主流的反拨。
当然,陈铨的“民族文学”仍然有很大缺陷,虽然他试图建构中国文化本位的“民族文学”批评体系,可其“民族文学”的批评体系的核心观念却依然源自西方哲学话语,其文学批评观只不过是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人哲学思想的杂糅,并不完全适合中国文学,尤其是他对尼采“权力意志”思想的大力宣扬,更是步入了批评的歧途;而且在实际的文学创作实践中,陈铨所创作的《野玫瑰》、《蓝蝴蝶》等戏剧文学作品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重建“民族文学”的主张最终成了一纸空言。
①②③⑦⑧⑨⑩陈铨:《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民族文学》第2卷第1期,1943年7月。
④⑤[英]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文化研究读本》,罗钢、刘象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⑥陈铨:《中德文学研究·绪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1][12][13]陈铨:《民族运动与文学运动》,《文学批评的新动向》,正中书局1943年版,第20-21页;第35页;第34-35页。
[14][15]陈铨:《文学批评的新动向》,昆明,《战国策》第17期。
[16]陈铨:《五四运动与狂飙运动》,《民族文学》第1卷第3期,1943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