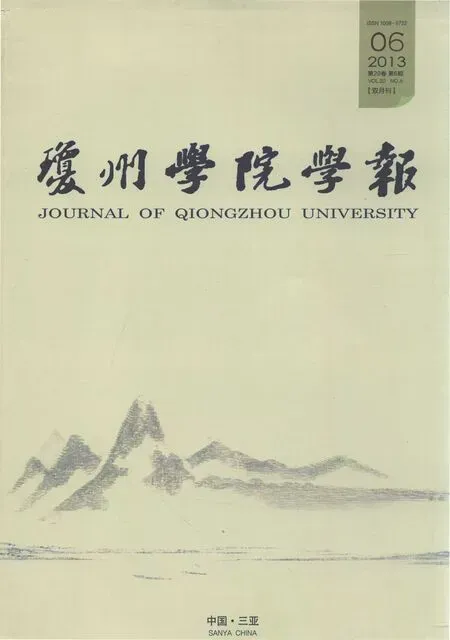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抉隐探微
侯海荣
(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吉林四平136000)
《古诗十九首》集“三百之性与离骚之情”,以不足二十首的诗歌集萃,凭藉极高的魅力指数堪与《诗经》比肩论剑。与其他文学经典历史上褒贬轩轾的接受起伏相较,《古诗十九首》锦心绣手,位隆声远,从齐梁刘勰赞其“五言之冠冕”肇始,至清已降千余载盛誉空前,独领风致。由是以观,此组“风余”“诗母”绝非等闲之辈率性草成。在学术史上,文本作者及创作年份作为《古诗十九首》研究的重中之重,因无断语遂呈“悬置判断”状态。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问题,计五种说法:枚乘说、傅毅说、曹王说、张衡蔡邕说、文选学士删减说。关于创作年代,大抵有三种结论:两汉说、东汉末年说、建安说。何真何伪,木斋先生直面这宗千古谜案,覃虑精思,奋发垦拓,历十载之功,成一家之言,言之凿凿地指出:《古诗十九首》作者乃“曹王说”之曹植,缘此“建安说”自然成立,但仅以建安作结过于笼而统之,具体应该定位在“建安十六年后”这个特殊的时间之窗。木斋先生这一敢于“吃螃蟹”的领先行为,使得“人代冥灭”的《古诗十九首》拨云见月,其古诗解蔽路径无疑具有方法论的学理意义、启发意义、指南意义。
一、小言詹詹:基于《古诗十九首》的靶点考察
木斋先生集中火力,将学术视点聚焦于《古诗十九首》,从诗本体、诗客体、诗主体三个层面发覆正谬,抉隐探微。简单地说,“诗本体”即回到了诗本身,“诗客体”即回到了文本身,“诗主体”即回到了人本身。
(一)诗本体的原生视角
何为诗本体?本文着力点非在阐论古典诗歌本体论之“言志说”“缘情说”“实义说”等多元姿态,也不在中西异质文化背景下比较中西诗歌本体论之反差及合流,更非在形而上层面陷入哲学追问的本质纠缠。笔者赋予“诗本体”的内涵是:某一文学样式自诞生起,就具有了“一种可以称作‘生命’的东西”,[1]诗的形式构成本体之后即拥有了独立的、本己的、排他的生命代谢规律,拥有了一个自给、自足、自律的本然生存逻辑机制或说是生态系统。诗歌有其自身萌蘖、成长、因革、式微到淡退的生命历程。
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即从十九首的五言体式发端,把探究视角返璞到“诗本体”自身。《古诗十九首》作为五言诗,与建安诗歌是什么关系?汉代的五言诗,还仅仅是五言诗歌长河的涓涓细流,处于五言诗的发生期,“十九首”乃是建安诗歌的重要组成。进一步讲,两汉的五言诗与建安的五言诗有何不同?前者言志,后者抒情。整个汉代诗学以五经为祖祢,以圣贤为准则,诗歌担当了道德取向的超额负载,作家抒情意识受到极大捆缚;“五言诗”与“五字诗”有什么不同?并非每句五个字即为五言,汉代五言诗不具有“为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之审美属性,五言诗本体尚未形成;五言诗的本质特征是什么?穷情写物;五言诗缘何到了建安时期在诗史上横空出世并蔚然大观?因为,以建安十六年为界碑,开始了五言诗群体写作的新时期,曹操此前对于五言诗的探索、变革、奠基的使命基本完成;五言腾踊的彬彬盛况是一蹴而就的吗?五言诗的真正成立,历经二十余年的漫长史程,可细化为三个阶段,等等。木斋先生抓住五言诗发生、成立、转型、成熟几个关键词,全程展示了《古诗十九首》的“生命个性”,并回溯到五言诗的生命源头,由滥觞到流衍再到勃兴,“塔式”搭建起五言诗发生学意义上的递进层级结构,从而决定了抵达文学史、诗歌史生命自身的深度。
(二)诗客体的立体释读
诗客体,即诗文本,是作者心魂的外化与物化形式。歌德指出:“一般地说,我们都不应把画家的笔墨或诗人的语言看得太死、太窄狭。一件艺术作品是由自由大胆的精神创造出来的,我们也就尽可能地用自由大胆的精神去观照和欣赏。”是否擅长运用数种方式阐读文本,这是衡量文学研究者学术能力的标尺之一。木斋先生对诗文本采取全方位解剖加感悟的释读模式,即从生物学角度将诗当作生物标本般细致,精心地进行“组织切片”,再对每一个“细胞”或部件加以个别或联系地研究,同时从心理学维度与文本进行心灵的“对流”和感应,直观、主观地洞见文本的美学特征和整体意义。诚然,解剖不是机械或单向地操作,不仅有合理的规程和路数,还有一定的目的和指向。在具体探析过程中,不断质疑,不断设问。问题的提出及对问题的回答既是起点亦是终点。感悟虽为霎那间的审美方式,却是以研究者的心理准备、艺术体验、联想能力作为基础的。刘勰云:“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文心雕龙注·知音》)披文入情是文学消费者、研究者的“二度创造”。概之,解剖是从部分到整体,感悟是从整体到部分。局部的解剖最终能否遥契整体的感悟?整体的感悟又能否最终得到微观解剖的检验?此乃衡量文本细读效果的圭臬。
1.旁采故实,佐以正史
木斋先生认为《古诗十九首》乃曹植散佚之作,并且九成以上是抒露其芳馥悱恻的“曹甄之恋”。面对这样一个惊悚之论,诸多学者难免产生“八卦”之嫌。为了证无讹传大忌,木斋先生力图“从史实蒸馏出观念,从抽象过滤出理路,是思想归证后的文史”[2],以期达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文史互证。中国人最发达的思维两翼:一为“诗”,一为“史”。“文史一家”,形成整个民族文化的优势。文史互证由20世纪学术大师陈寅恪倡立并付诸实践。“以诗证史”,即因文学存在于历史之中,或者说诗歌是具有文学意味的历史。尽管真正的历史无法复原,秉笔直书的正史往往为亲者讳,为尊者讳,最多不过一种文化想象或学术期待,但文学置身于较大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氛围当中的“历史性”却永远无法击碎。譬如,《古诗十九首》作者非是汉人,因为《汉书》《后汉书》艺苑人物中只字未提;其内容缘于曹甄的一段情案、冤案,并非演义戏说,王沈《魏书》、鱼豢《魏略》均有记载;曹志曾言家中有曹植手作目录,见于《晋书》;甄妃死因蹊跷,《三国志》曾录“隐奥难窥”等等。
第二,系年索骥。木斋先生擅于考索诗歌的历史背景,或从作品中寻绎历史,使诗歌发挥裨补史阙的功效,再将诗歌的意旨坐实。沿建安十六年这个关捩点顺藤,推断《今日良宴会》《涉江采芙蓉》作于建安十七年,《西北有高楼》作于建安二十一年,《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树》《行行重行行》作于黄初二年,《青青陵上柏》作于太和六年等等,并且分别为曹植作于邺城、鄄城、洛阳等不同的地理空间。按此次序加以排列组合,编年出十九首目录的原序。诗史合参,双向连璧,能够杜绝鲁莽、枉牵的偏差。史料是判断的依凭,史论是判断的参考,史鉴是判断的关键。在“史实”与“史识”之间,不纯仗自己的想象驰骋,不臆测、武断、固执。只有逻辑上讲得通,历史上站住脚,据此在文化平台上登临望远,方能步入诗歌情感审美的自由王国。
2.杂取意象,提摄要旨
诗歌是一种感性的审美存在。意象乃寓“意”之“象”,即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简单说来,就是主观之“意”和客观之“象”的结合,是赋有某种特殊含义和文学意味的具体形象。研究古诗绕不过意象。“十九首”中,芙蓉作为曹植和甄氏爱恋的媒介,是曹植一生不断回忆追恋的意象,“采遗芙蓉的意象,几乎贯穿于曹植的一生”。[3]芙蓉,即荷花,曹植《九咏》起就用芙蓉来为甄氏为车:“芙蓉车兮桂衡,结萍盖兮翠旌。四苍虬兮翼毂,驾陵鱼兮骖鲸。”《九咏赋》后出现两人首次倾诉衷情的场景:“寻湘汉之长流,采芳岸之灵芝。遇游女于水裔,探菱华而结辞”。木斋先生认为,“采芳岸之灵芝”,正是对“涉江采芙蓉”和《离友诗·其二》中“临绿水兮登重基,折秋华兮采灵芝”景况的再现。采撷芙蓉在曹丕作品中亦屡次提及。这一说法的另外实证是元代《河南志》提供了魏晋宫城中的“芙蓉殿”“灵芝池”的存在,可资佐证此前论证的甄后对芙蓉、灵芝的偏爱。这样的资料是十分可贵的。此外,对胡马、越鸟、游子等木斋先生均作以细致考论。意象相当于符号编码体,它与特定感觉信息表征相对应,作为诗歌文本高级的信息载体,对于诗歌主题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3.还原语境,详考词汇
一方面,此处语境包含历史语境、文化语境、诗歌语境。诗有古今因袭,不定之中自有定法,格律技巧又存历史的界阈性。木斋先生指出,汉、魏五言诗为两种不同的诗体。“两汉五言诗并不具备‘指事造形’‘穷情写物’,‘一诗止于一时一事’的意象诗写法,仅仅是‘五字诗’”。[4]先秦两汉诗作,就其外部特征而言,皆以单音为主体,五言诗出现大量的双音词,并构建了每句三个音步的基本节奏。换言之,两汉五言诗虚词、单音词使用较多;建安时代的五言诗逐渐摆脱散文写法,虚词渐次退出,句式由单音词为主转向双音词为主,五言音步初步形成。音韵、雠校、训诂现代学者大多视为畏途,木斋先生爬梳廓清这些语法、诗律层面的“硬知识”,无疑将十九首研究上升到语言学领域的又一高度。
另一方面,诗人主体受到创作条件、个人秉性、生活阅历所辖,往往会出现大量的雷同作品,这一点或许与“风格”有些混容。曹植到底能否写出十九首那样的作品,曹植总集的其他诗作又水平如何?经验告诉我们,即便是巧夺天工的匠人,也不会突然产生撼世骇俗的杰作,所谓的“鸣必惊人”,映示的仍然是某一阶段的现实当量。木斋先生通过俯拾曹植五言诗与十九首中大量的如出一辙,浑然一体的相似语句,进一步奠定了十九首作者为曹植的学理自信。因为,语汇、词句的使用是一个时代的文化产物,诗人很难脱离时代的语言局限和个人的语言习惯,这一点无由驳难。
4.疏证同作,发皇心曲
诗歌“意境的创造与接受是矛盾统一的整体,诗味则是整体信息输出的反馈”[5],欲为《古诗十九首》为曹植所作立论,务必对曹植的其他作品高度熟稔。木斋先生或循文理,或依句律,力求内在具足的“内证”,通过数理统计曹植诗与“十九首”中的相似语句,从语汇角度考量十九首与曹植诗集的关系,进一步勘察心迹,平行比较,新见迭出。我个人以为,如此搜觅二者之间微妙的“蛛丝马迹”并非穿凿蔓引,而是具有学理上的可操作性与合理性。
(三)诗主体的通盘考量
侧重“诗主体”即以诗人为本位,自古“知人”多艰,列曹植作为“十九首”的真正执笔人,可信度到底有多大?首先,汉魏时代是贵族享有文化特权的时代,能够写出惊心动魄的“十九首”,其作者不可能是社会下层或没有教育权利的无名小卒,“一字千金”的“十九首”与才高八斗的曹植高度匹配,曹植具有“言出为论,下笔成章”的绝佳禀赋;其次,温厚缠绵的“十九首”若没有曹植亲历的凄婉爱恋作为素材难以成为千古绝唱;再次,通过文学音响能够回放时代声讯,其他诗人(如刘桢、王粲等)不具备创作“十九首”的自然条件、艺术条件,其他时代(如两汉)也无法提供五言诗的成熟土壤。
二、大言炎炎:由内向外的宏阔视野
对“十九首”的研究,事实上牵一发动全身。《古诗十九首》深刻地影响了整个魏晋诗歌的发展,也直接为盛唐诗歌的巅峰起到铺垫作用。据木斋陈述,“十九首”的研究,来源于他的整体学术计划,是一部相续相禅的《中国诗歌演变史》整体课题的重要组成。
(一)寻根:从“十九首”推扩到整个汉魏古诗谱系
木斋先生由对“十九首”的研究,将研究对象扩展为汉魏遗失作者姓名的全部古诗,主体为文人五言诗。这并不是五言诗研究带来的副产品,而是木斋先生一以贯之的大文学史观使然。他对待词的学术眼光亦是这样,皇皇巨著《宋词体演变史》“打破了板块式思维惯性的断层限宥,从而把拼盘式的、凝固的、扁平的词史,还原为网状的、圆通的、运动的词史。不仅如此,作者在其每章中还以论文的体式著述词史,积微言细,自就鸿文,其几何级的学理内存潜蕴了更多的学术生长点与不可穷尽的春潮带雨的继发效应。木斋独特的学术操作模式,消弭了词史研究的困惑、焦虑与危机。它真正实现了词史的‘认知完型’,并高度契合了词史的文化品格与历史真相。”[6]木斋先生一如既往,心无旁骛,由“十九首”之冰山一角,擘画出了诗峰演进的宏大脉络,受众体会到的是情在诗外、状溢目前的生动诗学解读。[7]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如此视界,倘无熟参中国艺术精神,必有短绠汲深、举鼎绝膑之绌。
(二)回归:曹魏时代的文化现场
历史是凝固的现实。文学是“面对无法发声的历史的唯一见证”。[8]对古代作品的考证,最终势必落点于孵化孕育作品的特定的历史时空。木斋对十九首的考索既能“出乎其外”,以宽阔的视界凭轼而瞻,又能“入乎其内”,从诗作的残章衔续历史碎片,寻觅作品挟带的年份信息与镌刻的时代“胎记”。
第一,政治文化的转型。“诗虽有‘镜子’‘历史’等外向功能,但这也不是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因而从根本上讲,我们更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有限的镜子’或一种‘具体的历史’”。[9]首先,建安时期的政治文化渐次转变为一种审美文化,士人的生命价值重心亦转移到追求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愉悦;其次,曹操在思想上实现了对经学传统的结构与通脱思想的建构,这样的“易代革命”势必影响到文学品格的铸塑,诗歌的主情思潮到此时段已然堂庑渐阔;再次,文学的自觉,准确而论,要在曹操之后。他既是“收束汉音”的终结者,又是“振发魏响”的奠基者,以上思想解放运动与文学蜕变态势为古诗十九首确立了栩栩欲出的前提。
第二,文学观念的嬗递。“建安诗歌的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完全摆脱了汉代诗歌那种‘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想的影响,完全归之于抒一己情怀。”[10]曹魏时代铲除了经学的牢笼与桎梏,为崭新的五言诗歌拔地而起扫清了道路,否则不会产生“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约束”的恣肆放纵;不会产生“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行乐贪欢;不会产生“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为伊憔悴的相思体验;不会产生“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刹那芳华的情爱感伤;更不会发出“荡子行不归,空房难独守”的内心呐喊与生理袒露。
第三,曹植情感的曝光。对曹甄隐情的跟踪并非猎奇。穿越历史的丛林,甄后赐死、曹植获罪、曹叡生怒、曹诗阙略,将这些扑朔迷离的事件与“十九首”内容加以绾和,那么曹植就成了最大可能性的首选作者。杀戮时代的血雨风云,情感世界的愁情别恨,使得十九首“婉转附物,怊怅切情”,此种暗合、吻合很难以仅为一种巧合作罢。(具体可参见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第11-16章)廖俪琪从时代风气、阻抗理论、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多重角度剖析,认为“情诗乃曹植诗与古诗的基本属性”。[11]缘此,“木斋学说不仅是在思考方式、研究方法上的革命,更是一种对于社会、政治、人性精神上价值观的思想革命”。[12]
(三)跨界:文学史、音乐史、思想史、文化史的多维向度
研究本身是开放的,汉代王充曾把“知今不知古”讽讥为“盲瞽”,把“知古不知今”奚落为“陆沉”。木斋先生将“十九首”的研究触角从中国古代诗学向外延伸,包括语言学、音乐学、心理学、考古学、文化学等,皆择善而从,为我所用。文学不是存于真空的绝缘体,某些学科之间具有极强的渗透性与交叉性,凭借学科间的嫁接、融贯、整合、勾兑,能够实现学术节点的突围。疏畅“十九首”盘根错节的内外血脉,势必会遭遇文史通义的挑战。木斋先生通过多学科的杂糅参与,转换视野,扩展视域,共同推进了《古诗十九首》的深入开掘,最后完成了学术积累的集成绽放。
譬如,语言、意象、声律、技巧皆为诗歌的审美要素,其中,声律美是最先作用于读者内听力的音乐美。从音乐史的演进历程看,清商乐是建安曹氏父子开创的新兴音乐,极其重视音乐的抒情作用,“尤其推崇悲伤怨苦之音,认为悲音最能撼动人心”,[13]而清商乐的兴起,正是五言诗成立的条件。铜雀台的建立,标志清商乐和文人乐府创作走向高潮。因此,从音乐角度辅助证明了“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古诗十九首是建安时期的产物。
若全面推阐有汉四百二十六年的文学思想奥区,“汉代经学尚‘志’抑‘情’。儒家经典所推重的政治伦理道德范畴构成汉代经学之‘志’的积极方面,此包含适度情感的‘志’尤为经学文论所推重;汉代经学视域下的‘情’,为情欲,虽然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但过则与‘礼义’构成对立。汉代文学言‘志’亦扬‘情’,文学之‘情’承先秦而来,强调人内心的真实与精诚。”[14]而“由与经学同义向意味着以诗文为中心之创作的转化至汉魏交变之际方迹象明显”[15],在建安时期,“文学并没有被看做是依附于政治道德的东西,相反,他们倒是将文学看作是无益于政治功业的装饰,最典型地表达这种思想认识的是曹植。”[16]看来,将“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的“十九首”著作权落于曹植名下,似乎与情与理不相抵牾。
文化是最宽泛的一个概念和范畴,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所以又被称为大文化。它在人类社会是一个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复杂庞大的综合体系。某一时代的文学生产自然要受到此一时代文化的濡染,浸渍;彼一时代的文化影像也自然会在文学肌体上留痕,投射。《古诗十九首》涉及了汉魏时期民俗、伦理、宫廷、制度等不同的文化侧面。譬如,“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该诗关乎古代的建筑文化。据木斋先生考证,绮窗、阿阁、三重阶,皆表明此高楼非处于市井街面,而是帝王殿宇,曹魏邺城之高楼,非铜雀台莫属,从而进一步证明古诗并非民间无名氏之作,而有宫廷文化背景。元代《河南志》记载:“明帝御阿阁士众”,更证明阿阁是宫廷政治场所。“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与《魏都赋》所言的“殿居绮窗”同一所指,曹植《杂诗·其六》中的“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飞观”和“双阙”,应是同一建筑的不同说法。这些新见确实前人未发。专著还对婚姻、器物、服饰等方面皆进行了文化观照,通篇形成了一种圆融的柔性机制。如图1:

图1 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的学理辐射示略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一切现象都处于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之中,无论刻舟求剑的静止思路抑或盲人摸象的片面思维都是错误的。“不大通,何由得大有!”“真正的文学立场和方法是各种思想张力场的翕动”[17],上述各条门径看似云行雨施,各有所专,实际上紧密体现了“文史哲互根”的大端与宗旨。林林总总的诠解,形成一股巨大的阐释合力,完成了母因素下众多子因素的有理、有机、有序地印证阐发。因为“任何一个真问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逻辑上能自洽;第二,实践中能举证。”[18]封闭的固态的结构考察,必然带来画地为牢的局促或捉襟见肘的尴尬。以此观之,木斋先生的学术态度既是革命的、颠覆的,又是保守的、谨慎的。
三、结语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术方法本质上是一种“对象化”思维的尖端形式。毋庸置疑,借鉴某些相邻学科的研究范式,构建适合本学科特点的话语体系和分析工具,这是学术水平标高的展示,也是人类理性精神的觉醒与学科研究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木斋先生以宏富的学养根柢与笃实的学术品性,既照隅隙又观衢路,规避了文学研究的隔阂肤廓之弊与观天呓语之嫌。其含茹揣摩,咳唾成珠,“爆炸性”实绩使《古诗十九首》的谜底浮出有了指日可待的期许。林登顺认为:“木斋先生对古诗十九首的创见,带来古诗研究的新视野。”[19]江晓辉说:“先生所做的其实是拨云见日的工作,以新方法、新角度发明旧说,还原历史真相。”[20]李孟宣说:“近十年来,木斋先生为汉魏五言诗体及古诗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诠释视角。”[21]李江琪则把木斋与宇文所安进行比较:二人“对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看法,竟不约而同地打破中国文学史从民国以来的认定,他们试图让文本回到当时社会文化发展背景中,进行重新解读与解构,举证历历的梳理与分析,得出一个殊途同归的结论:汉魏五言诗的成熟不在东汉。”[22]要之,若云小言詹詹为“剥洋葱头效应”;大言炎炎则为“多棱镜效应”。通过研究者远近距离的能动“调焦”,重新建立的参照系,不再是仄陋粗糙的框架,因缘和合的纵横考辨归结的最后命题不致蹩脚。“法无定法,道有常道”,庶几木斋先生筑葺的古诗研究长城在当代鸿儒的学术群动下绵亘万里。
[1]韦勒克.文学理论[M].刘象愚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35.
[2]栾栋.文史哲哲学阙略管窥[J].哲学研究,2005(12):100-104.
[3]木斋.采遗芙蓉—曹植诗文中的爱情意象:兼论建安十六年对曹植的意义[J].山西大学学报,2011(5):40-47.
[4]木斋.论汉魏五言诗为两种不同的诗体[J].中国韵文学刊,2013(1):31-38.
[5]何明星.系统的诗歌本体论:评《诗歌美学理论与实践》[J].江汉论坛,1989(2):61-63.
[6]侯海荣.别样的词史:木斋《宋词体演变史》方法论研究[J].天中学刊,2010(3):73-75.
[7]木斋.古诗研究的多种可能性[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3(3):5-11.
[8]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6.
[9]刘士林.中国诗学原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3.
[10]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20.
[11]廖俪琪.论情诗为曹植诗与古诗的基本属性[J].琼州学院学报,2013(4):21-29.
[12]高辛佑.论植甄隐情为古诗背景的接受[J].琼州学院学报,2013(4):30-37.
[13]刘明澜.魏氏三祖的音乐观与魏晋清商乐的艺术形式[J].中国音乐学,1999(4):68-81.
[14]侯文学.汉代经学与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29.
[15]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2.
[16]陈顺智.魏晋南北朝诗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37.
[17]栾栋.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立场和方法[J].文学评论,2001(4):146-149.
[18]劳凯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学理意识和方法意识[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1):5-15.
[19]林登顺.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带来新视野[J].琼州学院学报,2013(4):18-20.
[20]江晓辉.木斋古诗曲词研究的时代意义[J].琼州学院学报,2013(3):21-25.
[21]李孟宣.木斋甄后研究的学术反思[J].琼州学院学报,2013(3):32-37.
[22]李江琪.论木斋、宇文所安古诗研究对台湾国文教学的影响[J].琼州学院学报,2013(3):2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