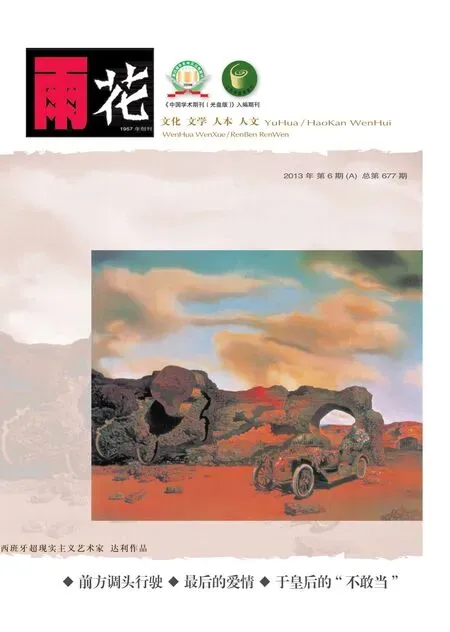走火入魔的“国学热”
● 唐德亮
近年来,“国学热”持续升温。一些大学办了“国学研究院”,设置国学课程,个别地方还开办“读经学校”。更有甚者,有些学校,要求全体师生都穿着古装上学,戴着颇似大清帝国的圆帽子。据媒体介绍,去年成都九月一日那天,天气酷热,三十度左右,某校小学生们穿着汉服,汗流浃背,集体朗诵《三字经》。
这真让人有“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慨!
对此情景,窦文涛说:“一位国学研究专家写文章,说这叫国学虚火上升。”作家王蒙则说:“我看比虚火上升还得难听一点,有点儿走火入魔了。”
国学中,凝聚了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确有不少伟大的思想、哲理与科学,应该学习并光大。但从实际看,国学中也有不少糟粕。我们应该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
譬如说许多人十分推崇的《弟子规》吧。该书确有不少精华,如“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这是教育孩子要孝顺;“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这是教育孩子珍惜光阴;又如“凡出言,信为先,作与妄,奚可焉”,教育人讲诚信,不要欺诈骗人。类似的佳句的确不少。但也有糟粕。如“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意即父母丧后三年,应常怀念悲伤哭泣,这没错,但要戒绝酒肉就不合情理。“居处变”,意即夫妇不同居,就更荒唐了。又如“打闹场,绝勿近”,这话也值得商榷。假如看到一群人打架,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而应当上前劝阻调解,如若见到坏人欺负殴打老人妇女小孩,我们应该见义勇为才对,怎么能“绝勿近”呢?又如“勿厌故,勿喜新”,如针对老友(或旧的好事物)不厌弃是对的,但不能将其与喜欢新友(或新的好事物)对立起来。喜欢新事物,创造新事物,社会才能进步。又如“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意即发现了别人的短处,千万不要揭发出来,发现了别人的隐私,绝对不要去说破。此言差矣!对不良的风气,对坏人坏事,我们就是要理直气壮地敢于揭发检举,让他们无藏身之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一味“莫揭”,“你好我好大家好”,正气能弘扬、邪气能刹住吗?又如“扬人恶,即是恶”,这话逻辑就有问题。
《三字经》里头,好的东西不少,但也有与科学教学相悖的地方。如“头悬梁,锥刺股,勤有功,戏无益”。“勤有功”是对的,但“戏无益”则十分片面。儿童玩游戏能提高学习效率,早已成为教师、家长及学生的共识,怎能说“戏无益”呢?而被古人奉为圭臬的《增广贤文》糟粕就更多了。如“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三十不豪,四十不富,五十将来寻死路”,“先到为君,后到为臣”……这不是赤裸裸地教人虚伪,宣扬宿命论等封建货色吗?
还有人大肆吹捧《二十四孝》。“二十四孝”中荒诞处甚多,如《恣蚊饱血》:“吴猛,晋朝濮阳人,八岁时就懂得孝敬父母。家里贫穷,没有蚊帐,蚊虫叮咬使其父亲不能安睡。每到夏夜,吴猛总是赤身坐在父亲床前,任蚊虫叮咬而不驱赶,担心蚊虫离开自己去叮咬父亲。”
还有“一孝”更加令人毛骨悚然。该“孝”这样写道:“汉代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于是决定活埋三岁之子。(见《郭巨埋儿》)
鲁迅先生说:“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这些“以不情为伦纪”(不讲人情人性的伦理纲常),“实在是把肉麻当有趣”,“教坏了后人”。(见《鲁迅全集》第2卷《二十四孝图》)
一般认为,儒学是国学的重要部分。因此有人提出要以儒学做我们的精神支柱。这又走偏了。儒学有很多合理的,有生命力的成分,应该发扬,但又有许多封建文化的东西。譬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三纲五常”之类。特别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帝王掺进了许多封建专制的东西,统治者不断将孔子神化,使之成了皇权文化的代表。因此,近代社会,要打倒封建主义,解放思想,就必然要向儒学开火。如辛亥革命“马前卒”邹容就把儒学说成“忠君”的“伪学”。陈独秀、鲁迅、李大钊、胡适等“五四”文化革命旗手更是举起“打倒孔家店”大旗,对儒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在古典文学巅峰之作《红楼梦》中,最坚持儒学、精通儒学的是贾政,而贾政不仅当不好官还治不好家,他本人还是个“假正经”(红学家周汝昌语)。鲁迅的经典小说《祝福》中的封建卫道士鲁四老爷就是一个满口“理学”实则心狠血冷的人物。北大教授李零说“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虚火”与“走火入魔”总是应该警惕。
“读书无禁区”,但对懵懂无知的少年儿童来说,教他们辨别是金还是沙,是玉还是石,是蛋白质、维他命还是“三聚氰胺”、地沟油,可是一件重要的大事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