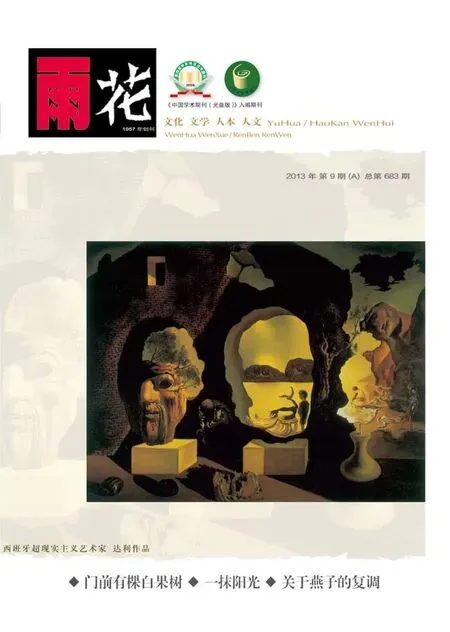淹没在淮剧里的村庄
吴光辉
我认为淮剧表达荣华富贵的欲望,比起其他地方戏来显得更加强烈,这也恰恰说明苏北比起其他地方遭受的灾难更加严重,这个地方的民众更加需要精神上的慰藉。
一
“苦……啊…………”
这“苦”字如千钧之重喷薄而出,在一百多年前大清舞台的上空划了一道弧线,“哇”地一声随着“苦”的惯性滑翔起来,带着泪沾着雨在半空飞旋不散。
当一百多年前淮安清江浦的戏台上,赵五娘一身素衣,头扎白布,怀抱琵琶,满脸凄苦地站在自己丈夫却又是新科状元、相府快婿的蔡伯喈的书房里,哧啦啦地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用“大悲调”唱出那句“苦命人坐书房泪如雨下”时,全场的观众全都跟着她一起泪如泉涌。见到这样的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弱女子,陷入叫天天不应、呼地地无声的悲惨境地,特别是“淮悲调”的以哭当唱,纵使你是铁石心肠,也要热泪难忍,肝肠寸断了。
赵五娘的丈夫、蔡家庄的才子蔡伯喈,三年前赴京赶考高中状元,却入赘相府三年不归。家乡又逢大旱,父母自尽,赵五娘撮土为坟,然后穿着一身孝服苦寻到了京城,来到这相府里蔡的书房,这就由凄婉悲催的板胡扬琴伴奏,引出了这番催人泪下的“拉调”哭诉。
面对着享尽荣华富贵的丈夫,面对着不认亲爹亲娘的丈夫,面对着抛妻另娶的丈夫,她想起自己这些年穿的是破衣烂衫,住的是透风漏雨破草房,吃的是树皮草根度饥荒;她想起自己为了孝敬他的爹娘去借粮,被强盗抢走粮食绝望地去上吊自尽;她又想起公婆双双赴死,自己用五张芦席葬了公婆,从心底发出的悲愤之情唱了一段“大悲调”:“我扒了七天共七夜,麻布兜土立坟堂,狠心的呀你望望,我十个指头还有伤。张大伯劝我把京城上,滴血描起图一张,送我琵琶沿街唱……”
淮剧《琵琶记》演绎的赵五娘悲剧故事,其艺术价值就在于对苏北灾民悲情性格的表达和发泄。从南宋到清代“黄河夺淮”的728 年的漫长岁月里,水灾给苏北带来的经济损失难以计数,苏北经历过数十次甚至上百次的严重水灾旱灾蝗灾。无数村庄屡被淹没,千万百姓流离失所,良田变成盐碱地,水利系统全被破坏,洪泽湖经常倒溢成灾。宋元明清有关苏北水患旱灾的文献记载甚多,有“死徙流亡,难以计数”、“白骨成堆”、“田庐尽没”、“尸骸遍野”、“幼男稚女称斤而卖”、“惨不忍言”等等。清咸丰五年黄河北徙之后,在苏北留下的仍是大片的黄泛区,水系紊乱,土地贫瘠,乡村困苦,经济落后,与汉唐、北宋的盛世繁华相比真是天壤之别,直到民国、新中国,苏北都还处于黄河夺淮的“后遗症”之中。
许多饥寒交迫的百姓为生活所逼,把苏北的劳动号子串编成“门谈词”,沿门逐户,边唱边讨,这就是淮剧最早的起源了。后来外出逃荒中夫妻搭档、兄妹结伴或姑嫂联袂,把“门谈词”发展到两人对唱,再配上胡琴、串板,哭诉灾情,卖唱求施,凄惨动人。他们唱的是自家的苦,讨的是活命的饭。
这就是因为水旱灾害逃荒要饭而产生淮剧的历史源头。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现在传承下来的淮剧里,居然没有一出正面描写水旱灾害的剧本,却又无一出戏没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可同样是产生于淮河下游,同样是产生于灾荒,也同样是产生于乞讨的黄梅戏,却有《逃水荒》、《报灾》、《闹店》、《李益卖女》、《闹官棚》、《告霸》等一大批表现水灾旱灾的戏剧流传下来。所以,我认为淮剧表达荣华富贵的欲望,比起其他地方戏来显得更加强烈,这也恰恰说明苏北比起其他地方遭受的灾难更加严重,这个地方的民众更加需要精神上的慰藉。
二
蔡家庄是一座被水旱灾害吞噬的悲剧村庄,是一座被淮剧的悲伤剧情笼罩着的村庄。蔡家庄的背景是一望无际干枯龟裂的土地,村庄里笼罩着一阵阵无数灾民乞讨时哭诉的“门谈词”的曲调。
蔡家庄一带先是大水,后是大旱,连年饥荒,颗粒无收。赵五娘家锅里无米煮,灶下无柴烧,三餐无一饱,生机无一条,一家人眼看就要被饿死。赵五娘只得外出借粮。这时她将借来的一点米,煮成稀粥端给公婆吃,自己却躲在厨房里吃糠麸,结果反而被婆婆怀疑她在偷吃大米饭。当公婆强行将赵五娘推倒在地,冲去厨房看个究竟时,才发现赵五娘背着他们偷吃的,根本不是什么米饭,竟然是糠麸!公婆这才悔恨交加起来。
“一瓢糠……一碗水……”“一瓢糠……一碗水……”“一瓢糠……一碗水……”公婆止不住愧疚得捶胸顿足,婆婆更是愧疚不已,将赵五娘搂在怀里,痛哭流涕起来:“儿啊,饥荒岁月全仗你,如不然我们早已化作灰呀!你挖草根,摘树叶,不顾双手血肉飞。你晚织麻晨织线,挑水担柴夜少眠,煮粥送到我手里,自己粒米牙未粘,暗暗厨下把糠咽,怎么不叫为娘更伤悲!”说到这里,赵五娘一阵委屈的泪水涌出眼眶,又悲又饿又气又急,一下子晕倒过去。
我觉得淮剧《琵琶记》的“赵五娘吃糠”这场戏,之所以能够催人泪下,其主要原因就是将淮剧的悲情特色,人物的悲惨命运,天灾的悲剧性质,这三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从而将悲剧的艺术效果推向极致,也使《琵琶记》成为淮剧里的经典,传唱几百年经久不衰。
淮剧的悲情特性完全根植于苏北灾民的悲剧命运,淮剧的曲调天生就是为了灾民的悲情发泄。传统的“香火调”就源于苏北求神拜佛以保风调雨顺的香火社戏。“老淮调”源于叙述灾荒,唱起来情绪悲愤,色彩鲜明,大段唱词常常是扣人心弦,催人泪下。淮剧经常使用的“南昌调”、“叶子调”、“跳槽调”、“下河调”等曲调,全都是灾民乞讨时的对唱发展而来。因而,淮剧擅长演绎悲情曲调又被称为“苦情戏”。这是苏北灾民贫困的生活状况和苏北人的悲情性格的直接反映,从而使淮剧成为苏北人区域性格的精神符号。当戏台的大幕一经拉开,舞台上唱的跳的便是一片呼天喊地的血泪控诉。“淮悲调”时而清亮,时而混浊,“下河调”时而平缓,时而激荡,这就难怪许多人将淮剧说成是哭丧了。
当年淮剧作为“门谈词”时,倚门乞讨演唱的是:“叹只叹遭旱荒年有三载,树无枝草无芽水井也干。又谁知发下洪水五月十三,有湖田和土地被水来淹,高岗地被沙压具已不见,低洼田被水打波浪滔天……”试想,他们在唱“门谈词”时是何等的悲痛欲绝,是何等的凄惨悲凉?在这里,淮剧哪里还是在唱,简直就是在哭诉,就是在泣血。
苏北的灾难引发了淮剧的悲情,正是淮剧曲调能够感天动地的根本原因。因而在淮安发生的本土故事《窦娥冤》才能如此家喻户晓,传遍全国。悲剧发展到了杀头的关键时刻,因灾而生的淮剧悲情天性便流露出来了。也正因如此,窦娥在被冤杀行刑之前,这才发了三桩无头誓,其中就有两桩是关于自然灾害的,一是要六月下雪,二是要三年大旱。那出《琵琶记》里的赵五娘吃糠,也是因为天灾大旱,也恰好表现了淮剧曲调的这份悲情天性。在灾荒绝境之下,公婆为了能让赵五娘放心去京城寻夫而双双吞糠自尽,赵五娘眼睁睁地看着公婆噎死在自己的面前,也就悲痛欲绝地唱出“淮悲调”,让观众跟着她一起流泪。
然而,炙热如火的太阳,依旧照耀在蔡家庄的上空,却没有一丝儿被这曲“淮悲调”感动而下雨的迹象,倒是引来了一场蝗灾。只见得一片片成千上万只蝗虫遮天蔽日地向蔡家庄扑来,发出一阵阵巨大的嗡鸣,然后向村庄和田野俯冲下来,很快就落满了村里村外,蝗虫所到之处,庄稼没了,树叶没了,连野草都没了,四处全都是被蝗虫啃噬之后留下的洼坑。全村的男女老少全都拿起叉把扫帚驱赶起蝗虫,又敲起锅碗瓢盆想吓走蝗虫。在千万只蝗虫的飞舞中,全村上下一片锣声,一片吼叫,一片呼号,还有一片哭喊。
我觉得这片声响肯定会合奏演变成淮剧的另一种悲惨曲调。
三
悲情天性与美好向往,贫民本质与拜官情结,是淮剧的双重品格。这是淮剧与其他地方剧产生不同叙述风格的根本原因。同样是《琵琶记》,在秦腔里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悲剧结局。秦腔让赵五娘上京寻夫时,被狠毒的相爷差人用马踩踏,差点丧命。用心歹毒的相爷又请皇上钦赐“贞孝可嘉”皇匾,封赵五娘为弥陀主持,想永绝其俗念。心力交瘁的赵五娘,最终倒在血泊当中,含恨而死。而淮剧《琵琶记》的结局却是一个喜剧,让赵五娘到京城向相府千金备述前情,居然感动了相爷和千金,使夫妻得以团圆,然后又请旨归祭,最后皇上下旨,满门荣封,赵五娘便心满意足地穿戴上一品夫人的凤冠霞帔,与牛相爷的千金亲如姐妹,然后两个女人一起跟随她们共同的丈夫蔡伯喈,前呼后拥,荣归故里,光宗耀祖,在一派欢乐祥和的锁呐声中,吹吹打打地结束全剧。
其实,淮剧这般热衷表现荣华富贵,简直就是给苏北灾民画饼充饥。我倒觉得秦腔的剧情发展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人物性格,比起淮剧的结局更加可信。然而,淮剧的这种双重品格,决定了淮剧的情节发展,也决定了赵五娘历经磨难之后的大团圆结局。事实上,像《琵琶记》一样,叙述一个悲情故事,最后却都有一个大团圆的喜剧结尾,早就成为淮剧情节发展的套路,《莲花庵》、《牙痕记》、《郑元和与李亚仙》等等,这些久演不衰的淮剧传统剧目莫不如此。从本质上看,淮剧这种大团圆的结局,也是悲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虽也能给善良的观众以安抚与慰藉,却是短暂的、临时的,虚构的。因为这仅仅就是一种强颜欢笑,只是一种表达贫苦大众的一种希冀与期望,一旦人们明白这种希冀与期望,其实是一种难以变成实现的幻想,剩下来的也就只能是格外的悲催。
淮剧的双重品格是苏北民众“乞丐思维”的艺术表达,而这种双重品格之所以能够传承至今,是因为今天的苏北民众还是没有真正摆脱“拜官情结”的影响,或者说现在的水灾虽然不复存在了,但现行的体制和经济的滞后,还没有促使百姓真正摆脱“拜官情结”。正因为如此,这里报考公务员的场面异常的火爆,他们期待着能够像淮剧里的秀才一样,高中状元,跳越龙门。
四
一轮六月的烈日徘徊在楚州(现淮安)的城头,一群乌鸦不停顿地在七百多年前的天空盘旋嘶鸣,城外那条被黄河冲涮后的淮河早被炙热,一阵阵惨白如霜的水汽正从浑黄的河面上升腾而起。城南菜市口那个杀人的高台早已围满了人群,高台上立柱顶端悬挂着一面黄旗,旗下系着十几条迎风招展的白色长绸。这时,人们似乎全都听到了大元王朝的阳光射向大地时发出的滋滋声响,似乎闻到了阳光散发的毒辣辣的气味。
高柱下面正五花大绑着一个20出头的少妇,她的背上竖插着“斩”字标牌。随着午时三刻一到,监斩官凶神恶煞地一声怒吼,少妇还没来得及高声喊冤,就被刽子手一刀砍下了美丽而苦难的头颅。一颗血淋淋的头脑瓜子,像西瓜一般,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滚向远处,一腔鲜血居然凝聚起来,一起溅向那白色的长绸,将长绸染成了红色。
也就在这时,乌鸦们全都闭上了嘴巴,烈日被一团乌云层层笼罩,接着就狂风乍起,尘土飞扬,一股冰冷的寒流从天而降,顷刻之间就下起了漫天大雪,淮河水面很快就结上了厚厚的一层冰。那些红白相间的长绸,就在这冰天雪地里飘飞起来,并且发出一阵阵阴气逼人的嘶喊。
这便是七百多年前的那个六月天,因为一位楚州少妇的含冤被斩,而引发的一场雪灾和三年大旱的奇特场景。这位少妇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窦娥,这个著名的场景便是流传千古的《窦娥冤》“斩娥”的外景地。
窦娥被张驴儿诬告毒死公公,楚州太守桃杌是个昏官,严刑逼供窦娥,她坚不屈从。桃杌转而对蔡婆用刑,窦娥为救婆婆,含冤承招,被判了死罪,这就引出了《窦娥冤》“斩娥”这场戏。
值得注意的是,像窦娥这样的贫困女子,到了生死关头,还自然而然地将自己平反昭雪的全部希望,寄托于进京赶考的父亲身上。而这一点恰好表现出苏北灾民比起其他地方更为强烈的拜官情结和皇权意识。试想,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去北京参加公务员的全国统考,如果没有考上或是考上了没有做官,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窦娥的冤案岂不是无法得以平反吗?
生活在现实水旱灾害里的苏北贫困民众,迫切需要通过淮剧去编造美好梦想,让自己达到精神上的宽慰和满足。因此说产生于水灾的淮剧钟情于皇权,崇拜于官员,正是苏北民众这种封建意识的自然流露。
正是因为如此,淮剧搬上舞台后,就将苏北民众的这种拜官情结刻意放大,使淮剧大演特演的“九莲”、“十三英”、“七十二记”,无一没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身影。“九莲”里,《刘全进瓜》中的李翠莲,负气自尽,最后还是唐太宗“还阳”,才让她与丈夫团聚;《吴汉三杀》中的王玉莲,本来就是官宦之女,命运一直被朝廷所左右;《蔡金莲告状》中的蔡金莲,为伸张正义宁愿滚钉板,最后是高中状元并当了两淮王的丈夫王文勇主持公道,这才真相大白;《荆钗记》中的钱玉莲,历经坎坷之后,与高中状元的王十朋以荆钗为凭,重新团圆。所有淮剧演绎的故事全都是悲剧人生,可最后又全都因为皇权官府而有了大团圆的美好结局。
所以,赵五娘当初送夫进京赶考时,便无限向往地唱出了“官人若把青云上,谢天谢地谢皇恩”。蔡伯喈高中状元后,自然春风得意地唱出了:“四杆彩旗马前摆,三杯高酒谢皇恩,两朵宫花头上戴,独占鳌头第一名。”当皇上钦准赵五娘与夫一起衣锦还乡时,便一起感激涕零地唱出了:“先跪拜深谢皇恩浩荡,恩准我蔡家团圆还乡。”再所以,窦娥的冤魂向已经做了“两淮提刑肃正廉访使”大官的父亲告状,窦天章主持公道严正判决:“张驴儿毒杀亲爷,奸占寡妇,合拟凌迟,押付市曹中,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处死。升任州守桃杌,并该房吏典,刑名违错,各杖一百,永不叙用。”最终,窦娥得以平反昭雪,张驴儿得以严惩法办。
沿着淮剧的拜官情结推演下去,窦娥伸冤平反之后,楚州在窦天章的英明领导下,肯定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便是淮剧画给苏北灾民的又一块饼了。这个饼就像那高悬半空的太阳,又大又圆。其实,像哭声的淮剧或是像淮剧的哭声,跟随着凶猛的洪水一起,早已淹没了苏北的所有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