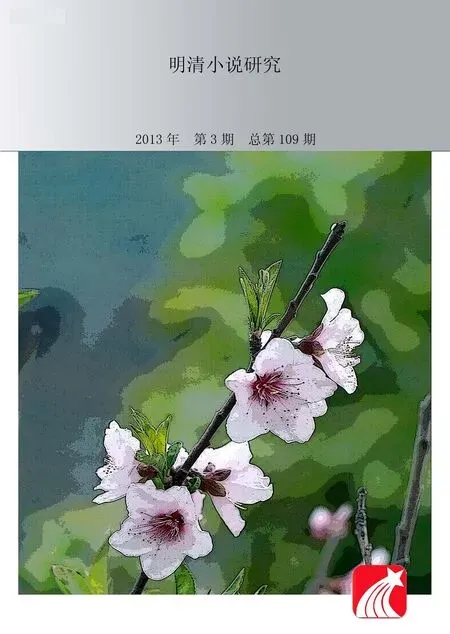从小说文本到诗文批评
——论《水浒传》“点将录”形式的演变
··
文学史上“点将录”形式经历了从小说文本到诗文批评的演变历程,这一富有民族特色的批评形式本身即包含着特有的历史文化含义与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的重要意义。
一、江湖社会座次与诨号:《水浒传》“点将录”的含义
儒家传统尊卑理念深入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核心,日常礼仪座次即与尊卑、权势等紧密相联,不惟以士大夫为主体的主流社会,即使打家劫舍、占山为王的草泽豪杰亦深受此种理念熏陶,效仿基于儒家尊卑意识的主流社会架构,建立江湖秘密组织。《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写“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即突出群体的秩序感,意味着“以武犯禁”的松散的豪侠组织渐渐向主流社会架构靠近,宋江的绝对权威地位得以巩固,在以君主为核心和绝对权威的严密社会组织架构中,个人的英雄豪气常常受到压抑甚至打击,就在“忠义堂石碣受天文”及“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后的梁山泊好汉大聚会中,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场景叙述:
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却冷了弟兄们的心!”“黑旋风”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颠做粉碎。宋江大喝道:“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众人都跪下告道:“这人酒后发狂,哥哥宽恕。”宋江答道:“众贤弟请起,且把这厮监下。”……(第七十一回)
武松、李逵、鲁智深等这些强烈反对宋江招安的好汉身上,更具江湖豪侠气,即英雄气概,为保持这种豪侠之气,梁山好汉大都不近女色,但在梁山江湖社会组织日益世俗化、严密化,特别是在“排座次”之后,在一心主张招安的大头领宋江面前,梁山好汉们多数选择沉默,纵有武松、李逵等人反对,亦以被压制约束,由此,英雄气短,何关儿女?侠客特立独行的英雄豪情终被以儒家尊卑理念为核心的专制宗法社会和文化吞噬,即使游离于传统主流社会边缘的江湖秘密组织亦难逃其网。
“排座次”这一情节是《水浒传》一书的高潮,意味着梁山组织结构的日益严密,即他们的主要交往模式由所谓兄弟逐渐转为君臣,虽然宋江一味要招安,号称“呼保义”,但梁山社会在“排座次”的高潮之后,宋江以及诸多头领的地位得到巩固和保障,实质上已经接近于一个江湖小朝廷了。体现成员间的尊卑高下以及秩序感是为“点将录”、“排座次”的内涵与本质。这也为后来《水浒传》“点将录”演变成一种针对文学群体的批评形式提供了阶序品鉴的模板。
颇有趣味的是,始终不变的是梁山好汉们的诨号,在这次宋江导演的貌似严肃的“排座次”大戏中得到强化。一百零八将的姓名始终与他们的诨号连在一起。一百零八将个个都有诨号,无一例外,并且在宋江所炮制的类似于“天授君权”的忠义堂石碣上,亦或“点将录”中,诨号全部位于姓名之前,诨号之于梁山好汉的意义甚至超过了姓名,若在江湖上没有混出一个响当当的诨号来,是没有资格加入梁山队伍的。这“反映了宋元时代江湖人物的习尚”,从更深层次来讲,这种一个群体全部冠以诨号的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含义,如宁稼雨《〈水浒传〉趣谈与索解》中所论:
这些诨名一旦叫开,便作为其人格精神、个体形象的具体化象征,表明这个人与绿林社会之间的一种相互认同的结构关系,一种身份标识。它一旦产生,便会在其深层人格精神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所以,诨名与其所代表的绿林文化系统是无法分开的,与其他江湖习俗相比,取诨名有更深刻的意味,它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它的内涵所表达的则是整个绿林文化……
诨名主要根据江湖人物的性情、才技、相貌特点等得来。《水浒传》之于人物塑造的成功历来为人称道,金圣叹称《水浒传》“只是贪他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水浒传》在人物塑造上确实较前代或同时期的小说更趋于个性化,一百零八个人即有一百零八个诨号,即是人物塑造向个性化发展的标志,但比起后来《红楼梦》完美地将人物塑造成个性化的典型形象,《水浒传》仍欠火候,虽然每个人物的诨号本身即是这个人物独特的标志,但这些诨号本身的片面性或抽象性亦带来人物塑造类型化的嫌疑,一个诨号可以指向这个人,也可以指向有同样特征或倾向的另一个人,读者不仅可以领会《水浒传》文本中各个人物的神貌,亦可在现实中寻找《水浒传》各类人物的蛛丝马迹,至于那些比姓名更加重要的有意味的“诨号”,不妨可以用来张冠李戴,这大概可以成为后来《水浒传》人物或诨号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原因之一,也为政治野心家或文艺批评家借《水浒传》中人物特别是排座次之后的人物名单即“点将录”来秩序品评某个群体人物提供可能。
二、以正统士子拟于江湖草泽:《东林点将录》的厚黑与东林士子
就“点将录”在后世传播的含义或指向而言,由明末阉党一手炮制的《东林点将录》具有转折意义,它上接《水浒传》“点将录”,下启清代中期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将以江湖草泽为主体的“点将录”诡异地指向了与之对立的正统宗法社会的主体阶层——“士”。
《水浒传》人物诨号在此后的江湖社会中广为流行并被借鉴,《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即有这方面的详细记载,他们中好多人直接把梁山好汉的诨号拿来用,有学者称:“此风一直未绝,直到清末民初,还有燕子李三、大刀王五等家喻户晓的绿林诨名。”《水浒传》以直接文本的方式以及各种水浒戏曲等间接方式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得到广泛传播,这在明清各种文献资料中多有记述,已为学界认可。在士子眼里,《水浒传》终究有着诲盗的色彩,其以武犯禁的江湖人物群体与谨守儒家传统思想的士子群体又怎可同日而语?如果一直谨守江湖与士林的楚汉之界,则就不会有后来一系列的文艺王国里的各种“点将录”批评形态了。《东林点将录》之于后世“点将录”的意义就在于打破了看似不可逾越的江湖与士林的界限,而这种突破在常规之下似难以想象,偏赶上了明末阉党乱政的非常态的极端环境,政治斗争的残酷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樊树志《东林非党论》不无感慨地这样描述晚明的政治环境:
在晚明党争日趋激烈的政治氛围中,形而上学的门户之见盛行,凡是敢与当政者唱反调的,一概戴上“东林党”的帽子,而予以摈斥,“东林”二字成了整人的手段。
明天启初年,魏忠贤的亲信王绍徽、卢承钦先后作《东林点将录》、《东林党人榜》,前者仿北宋末年《元祐党人碑》309人体例,后者仿《水浒传》108人体例,将异己之士搜罗起来,列入黜汰的黑名单。《东林点将录》中人员大都为士林精英,他们或为官、或讲学,多半进士出身,为一时士林翘楚,在专权者那里,俱被扣上了犯上作乱的帽子,并以《水浒传》中108个犯上作乱的盗侠相拟,魏阉虽不太识字,但王绍徽、卢承钦俱出身士林,且都为进士,他们大概深知,对于正统士子来讲,犯上作乱的罪名不仅威胁到人身安全,更是士的耻辱。
阉党在这里“实际是袭用了讼师、恶吏借绰号以整人的老谱”,鲁迅在《华盖集·补白》中这样论述:
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名,——或谓之“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张三李四,倘只说姓名,本很平常,现在却道“六臂太岁张三”、“白额虎李四”,则先不问事迹,县官只见绰号,就觉得他们是恶棍了。
可见,诨号虽然在中国古代民间被广为应用,但诸如传达狠猛或武力之意的诨号,典型的如《水浒传》中的诨号,确实其本身即带有犯上作乱的江湖意义,被冠以类似诨号的人在世人的印象中也绝非善类,即使《东林点将录》中诨号不取于《水浒传》,依然具有杀伤力。晚明文人许自昌曾引明末文学家钱允治之言,略论当时《水浒传》的传播情况,称:
《水浒传》,成于南宋遗民杭人罗本贯中……上自名士大夫,下至厮养隶卒,通都大郡,穷乡小邑,罔不目览耳听,口诵舌翻,与纸牌同行。吁!可怪已!
《水浒传》一百零八将人物甚至被付诸纸牌,流行之广,可想而知,《东林点将录》以东林士子群体拟于《水浒传》中的江湖盗侠,一方面方便坐实他们犯上作乱的“同党”之罪,另一方面,实在便于魏忠贤等阉党检索记忆。
在恶性党争的背景下,被统治势力排为异己的精英士人群体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失去了士之所以为士的基础,被拟到《水浒传》108人的黑名单中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摒弃政治的厚黑因素之外,《东林点将录》第一次将《水浒传》108个江湖人物诨号与精英士人群体相连,客观上促动了之后《乾嘉诗坛点将录》的生成。
三、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的隐而不传与诗文批评“点将录”之创体
至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水浒传》中“点将录”形式经《东林点将录》的党争变态演变为文艺批评形态,以诗国拟于江湖,以诗人拟于豪侠,无论就批评思想亦或批评形式而言,《乾嘉诗坛点将录》都堪称《水浒传》“点将录”形式在文艺批评领域的创体。此种创体之孕育在明末《东林点将录》之后跨越了近两百年,直至清代中后期,始与世人相见。
明亡之后,清代以异族入主中原,自清初开始,就大兴文字狱,文禁森严,乾隆和嘉庆两位皇帝始终没有放松对《水浒传》蛊惑人心、犯上作乱的警惕,对此书一禁再禁,据《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乾隆十八年癸酉七月壬午·上谕内阁”文:
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甚至以满洲单字还音抄写古词者俱有。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至,不可不严行禁止……将原版尽行烧毁。

与之相对的是,乾嘉之际《水浒传》在各个阶层中广泛传播,乾嘉时期朴学领袖钱大昕深感自明以来通俗小说惊人的传播能力,称:



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正是在这种非常微妙的政治和小说传播背景下产生,此书不署真名,只以其斋名署之。叶德辉光绪丁未刻本所录蓝居中《〈乾嘉诗坛点将录〉抄讫记后》云:

另有金丝玉壶斋主人抄本题记云:


舒位一生穷奇潦倒,无力刊刻自己的著作,其《瓶水斋诗集》等均有赖他人资助刊刻,初刊成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之后于光绪五年(1879)、光绪十二年(1886)等均有刻本,这些刻本均未收录《乾嘉诗坛点将录》,却普遍在诗集之后附录舒位《瓶水斋诗话》。《瓶水斋诗话》主要针对同时代诗人及诗歌品述议论。存诗话而不存“点将录”,其中自有深意,据苏州名儒王汝玉(1798-1852)《梵麓山房笔记》卷四云:

从整体上品秩当代的诗坛及诗人并非易事,而模仿《水浒传》人物及“东林点将录”,以化贬为褒、皮里阳秋的游戏笔法,品秩当代诗国人物,就更觉难上加难,一方面拟诗人于不伦,另一方面座次难排、下品难书,即使评得恰到好处,亦难免招致有些诗人的不满。舒位另有《瓶水斋论诗绝句》二十八首,亦未收录集中,主要以入清之后的近代诗人为评骘对象,自称:

凡涉品评鉴定,一定含有客观乃至主观褒贬之义,将褒贬一一加之于近世或当代诗人,若没有较高的社会和诗坛地位,没有相当的识鉴,对当代诗人群体“雌黄月旦”,虽痛快直陈,却暗含隐忧,其间难免意气相加,有如明代王世贞这样的诗坛领袖人物亦难免“自悔”其作,儒家讲“忠恕”之道,大概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作者对于诗人的同情理解之心亦会加强,舒位对于自己于少壮时期即“雌黄月旦”的顾虑在后来得到验证,据舒位儿子舒昌枚等在《瓶水斋诗话》卷末所记:

从中可见,舒位对于当代诗坛的诗歌品评创作仅限于青壮年时期,正如他在创作《瓶水斋论诗绝句》时所疑虑的,不惟王世贞,舒位亦自悔少壮艺林品评之作,于《瓶水斋诗话》、《瓶水斋论诗绝句》既复如此,更遑论创体不经的《乾嘉诗坛点将录》了,“因游戏之笔未免略肆雌黄”,他竟然连自己姓名也不明白标示,只以斋名示人,从篇首题词看,仅在诗友圈内传播,这一诗坛“点将录”因为没有及时刊刻及作者的有意隐讳,仅以传抄的形式流传,它在当时的传播及影响极为有限,如上述所引蓝居中《〈乾嘉诗坛点将录〉抄讫记后》所记咸丰初年抄本传录仅在有限的诗人间进行,当时《录》中惟一在世的“通臂猿”太仓毕子云先生,似并不知有此诗坛“点将录”。
《乾嘉诗坛点将录》篇首自序,透露出作者创作的动机、方法和意义:
夫笔陈千人,必谋元帅;诗城五字,厥有偏师。故登坛而选将才,亦修史而列人表。遂觉星辰可种,借其说于九百虞初,将使风月常新,和其声于三千雅颂……爰效东林姓氏之录,演为江西宗派之图……此则汝南之评,不遗孟德;元祐之籍,未列欧阳。岂曰以下无讥,实乃于斯为盛。文章千古,玉帛万重,盖惟善将将者始可与言诗已矣!


舒位创作《乾嘉诗坛点将录》以后,直至清季以前,再也没有一个作者去尝试以《水浒传》“点将录”的形式对当代文艺进行描述和品评,这固然与《乾嘉诗坛点将录》极为有限的传播状况有关,但也更突出了舒位在乾嘉时期的创体之功,在传统宗法社会及封建文禁政治尚未真正解除以前,文人学者以《水浒传》“点将录”形式创作和传播各种文艺“点将录”,始终是一个不可言说的禁区,直至清末民初,传统的宗法社会以及文禁政治渐被打破,叶德辉方能毫无顾忌的取《乾嘉诗坛点将录》抄本付以刊刻,《乾嘉诗坛点将录》得以重见天日,文人士子竞相阅读,一些有影响力的文人学者如汪辟疆、南社文人并着力模仿借鉴,以之描述品评当代文学,形成富有民族特色的独特的“点将录”批评形式。
四、近代以来“点将录”批评形式的兴起与诗歌谱系的多元化
清末民初,诗人或文学批评家意识到“点将录”批评形式之于建立一代诗歌谱系的诗史意义。

然而,就批评形式的角度看,汪辟疆以“点将录”形式为“同光体”诗派张目,柳亚子则以之树帜南社“革命文学”,他们显然俱已意识到“点将录”的文学批评形式之于建立和巩固文学谱系的重要诗史意义。源于《水浒传》“点将录”的批评形式虽然传达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文统体系,但“点将录”之牛耳若为多方所执,面貌多样,则表明在新旧文学交替之际,文坛谱系建立的话语权不止于一家,标示着近代文学及批评打破传统的一元文统框架,正向多元化发展。
小 结
《水浒传》“点将录”之“座次”体现了儒家尊卑高下的社会理念,而“诨号”则蕴含了深刻的江湖文化意味并带有类型化的特征,这些都为后来“点将录”形式由小说文本向诗歌批评转变提供了可能。就“点将录”在后世传播的含义或指向而言,明末阉党《东林点将录》具有转折意义,在极端政治环境下,以正统士子拟于江湖草泽,客观上启发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的创作。清代中期,舒位以赞美之情、理性之笔,创体诗国“点将录”,受儒家宗法社会理念以及封建文禁政治、“自悔少作”等因素的合力影响,《乾嘉诗坛点将录》仅以抄本形式流传。直至清末民初社会新变,“点将录”的文学批评形式才得以发扬光大,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柳亚子《南社诗坛点将录》俱以“点将录”形式自觉地为某一个文学流派或团体树帜,彰显出“点将录”一体之于建立一代诗歌谱系的诗史意义,而打破传统一元文统框架的多元化文学发展方向及专业严谨的“点将”态度正可为当今“点将录”批评形式提供借鉴。
“点将录”形式经历了从小说文本至文艺批评的演变历程,文化的、政治的以及文学自身的因素,俱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这一批评形式自身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含义与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的意义即是我们值得总结与反思的。至现代,“点将录”的批评形式已涉及诗歌、棋艺、书法、学术等多个领域,因其形式自身所包含的相对封闭的统序含义,如何保持“点将录”文艺批评形式的水平及纯粹性,则其创体之人舒位“自悔少作”之心理或可警惕后人,舒位后继者汪辟疆创作《光宣诗坛点将录》之严谨多识亦可借鉴,执“点将录”之牛耳者不仅当为某一领域之专家,更应秉持公心、如履薄冰,在发挥“点将录”一体的谱系统序功能的同时,亦重视文学话语权的多元化开发,使源于古典小说名著《水浒传》的“点将录”一体常青常新。
注
:①④ 王同舟《地煞天罡:〈水浒传〉与俗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114页。
② 宁稼雨《〈水浒传〉趣谈与索解》,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页。
③ [清]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清]金圣叹著,周锡山编校《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上,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5页。
⑤ 按:潘建国《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提出通俗小说的读者分为直接读者和间接读者,小说传播亦从这两个维度展开。见《复旦学报》2001年第1期。
⑥ 樊树志《东林非党论》,《复旦学报》2001年第1期。
⑦ 李乔《笔挟风霜的点将录》,《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
⑧ [明]许自昌《樗斋漫录》,北京图书馆藏明刊本,转引自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页。
⑨ 《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二百六十三,转引自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457页。
⑩ 《钦定学政全书》卷九,转引自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第4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