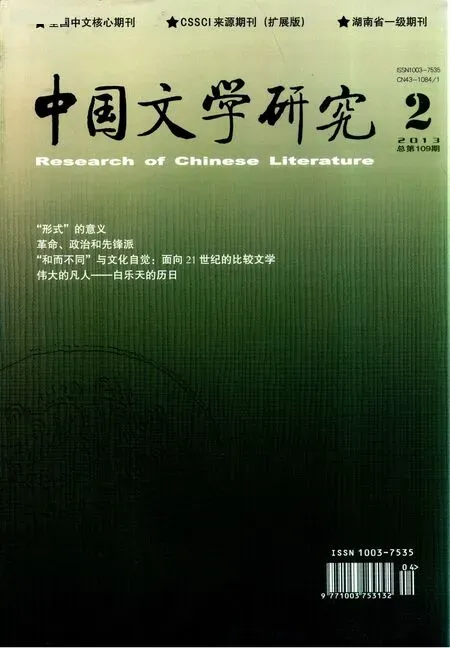论作为“边界文化”的文学
马大康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在谈到文学活动中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时,巴赫金说:“审美文化就是边界的文化,所以,它要求有拥抱生活的充分信任的温馨氛围。而为了自信地又有据地创造和加工人的内外边界,他所在世界的边界,前提是要有外在于此人的坚定而可靠的立场;处在这一立场上,精神能长时间地驾驭自己的力量而自由行动。”针对以往美学界注重“移情”,巴赫金特别强调了文学活动中“外位性”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作者要从审美上完成文学作品及作品主人公,就必须要处于作品世界的外位,处于主人公的外位,也就是说,处于作品世界的边界和主人公的边界,他的行为和内心世界的边界,只有这样,才能够赋予作品以完整的形式和价值内涵。巴赫金着重阐述的是文学创作和欣赏中跟审美移情相对应的“外位性”,而对文学作为“边界文化”的特征尚未深入分析,因此,也就留下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空间,有待我们去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一
在巴赫金看来,文化领域本身充满着纵横交错的边界,它不存在内域疆土,那么,作为“审美文化”的文学,是否仅仅因为它从属于文化领域而兼具文化自身的边界性,只不过体现了文化领域的一般特征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文学作为文化中的一个特殊门类,作为审美文化,它有自己的独特性,较之于一般文化领域,“边界”有着远为重要的意义。
作为审美文化的文学,它与其他文化领域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独具审美形式的。审美形式是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正是审美形式构成文学以区别于其他文化领域的独特性,赋予文学令人心动神移的不竭魅力。如果说,形式是物理对象和一般文化对象普遍具有的时空特征,是对象的边界,它将对象从现实的时空连续体中区划出来,赋予其特征,申明对象的身份,然而,又让对象仍旧处身现实时空关系之中,不将对象与时空连续体分隔开来并独立出来;那么,审美形式则不同,它不仅具有一般形式的边界区划功能,而且具有马尔库塞所说的“专制的力量”,它将文学作品从现实时空连续体中“间离”开来,超脱出来,升华为一个虚构的审美世界,从而获得审美独立性。原先来自现实的质料和素材因审美形式的专制,失却了原有的现实性质而成为文学虚构世界的组成部分,成为另一迥然而异的审美要素。因此,文学的审美形式所造就的边界,就不仅仅是物理对象或一般文化对象的边界,它同时毗连着两类不同的活动:日常现实活动与文学想象活动;毗连着两个不同的世界:现实的生活世界与非现实的虚构世界。审美形式构成的边界,区分着两类活动,同时又连接着两类活动;区分着两个世界,同时又连接着两个世界。
正如巴赫金所强调,在文学活动中除了移情作用,同时存在着外位性,即作者或欣赏者处身主人公的边界之外和文学虚构世界之外,来观照和完成主人公及他的世界。外位性是审美活动不可或缺的另一重要方面,它和移情一样共同构成审美活动整体。审美与游戏不同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它需要旁观者,即观众、听众和欣赏者,需要一个外在于主人公及他的世界的立足点。文学创作也一样,作者如果不取得外在于主人公及其世界的立场,也就不可能从审美上最终完成作品。没有外位性,文学活动就丧失了必要的心理距离,蜕变为游戏或仪式了。这也正是戏剧需要“第四堵墙”的原因。既然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活动,它同时包含着移情与外位性这两极,那么,作者或欣赏者就必定处身边界之上,他们立足边界,穿越边界,往来于两个世界,即现实的生活世界与非现实的虚构世界之间。移情让人深入作品虚构世界,与主人公相认同,融合一体,同悲共喜;外位性则又强调人自身的独立立场,他外在于主人公、外在于作品虚构世界,处身边界来观照主人公及他的世界。整个文学活动中,人就立足边界,不断超越边界,并因此交织着复杂多样的意向性关系。可以说,没有任何活动具有文学活动那样一种独特的边界,并因其区分且沟通着两个相异在的世界而构成如此广阔深邃的视野和巨大的张力。文学活动的基本特征就源于这种独特的边界文化之中。
一方面,移情令人投入文学的审美世界,与主人公相认同、相融合,与主人公一道去经历同一事件,人就生活在这个虚构世界而与现实世界相隔离。历来所谓文学独立、审美自律正源于边界的区隔功能,源于文学的虚构性。作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隔离的虚构世界,它已不再受制于现实法则而独自奉行着审美法则。虚构之境中,现实的固化秩序也业已化解。在这里,人可以超越等级界限,成为任何角色而又不受角色规范的制约,不必承担责任和风险;他可以潜入一切境域,追索他的所想、所爱,可是又因目标失去现实性,致使追求改变了性质,即便是热烈的性爱也转换为精神之爱、心灵之爱;他体验着所经历的一切事件,细细品尝人生况味,却因事件的虚构性而使体验失去重量和压力,他翩然超升,终于获得自由和灵性,并真正成为“我自己”。进入文学之境,人常常不由自主地变身为其中的人物:他成为情人又不是情人,成为律师又不是律师,成为士兵又不是士兵……他是个具体的人,有着具体的角色身份,却又只是“人本身”,因为虚构之境解脱了他所有的现实束缚,让他自由地成为自己,自由地发展自己。这样一种向“我自己”或“人本身”的生成,也正如人们所说的“审美还原”。因此,文学活动必定是与“真性情”、与“赤子之心”联系在一起的。在此需要指出,恰恰由于移情活动的同时又存在外位性,才可以让欣赏者维持着对虚构的意识,将文学事件中的体验与真实生活事件中的体验相区分,在体验过程中同时发生了“审美抑制”,从而跟现实事件、现实行为划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维护了文学事件的心灵的和精神的维度。
一旦人深深陶醉于文学虚构世界,以致他的自我意识也因此失去,又一种变化发生了:他与人物完全融合、同一,进入了无我无物之境。这种混沌境界就是阿多诺所说的“震撼”和罗兰·巴特所说的撼摇、恍惚、迷失的“醉”和“销魂”。
另一方面,外位性则让人重新处身主人公之外、处身文学虚构世界之外,他立足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的边界来观照文学所创造的审美世界,也即观照主人公及他的世界。但是,这种观照绝非日常生活中的观看或观察。他所观照的“对象”是非现实的,纯粹是虚拟的,是英加登所说的“意向性客体”,一个由他自己亲身参与构建的虚构的想象世界,实即自我的延展,因而无法掺杂功利目的性。功利目的因想象性、虚构性而消解了。因而事实上,他的观照已无法将所观照的“对象”对象化,更不可能将其工具化;他自己则因功利目的的悬置,转而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主体。于是,观照“对象”也转化为“另一个主体”,一个与文学活动中之“我”比肩而立、相互独立又相互交往、对话、生成的“你”。这,正是审美活动中的“主体间性”。
由于审美观照需要维持一定的心理距离,也就为理智的渗入提供了条件。只要离开边界,稍许增加心理距离,主体间性关系就解体了,审美观照即刻转换为对象性活动,转换为认知活动或伦理活动;而他本人则已经重新立足现实世界了。当人离开文学虚构世界的边界,重新返回现实生活世界,置身现实之际,他势必成为沟通现实与虚构两个世界的桥梁。现实的经验、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制约着他的认识活动和伦理活动;同时,他所经历过的虚构世界又曾令他蜕变为“我自己”,一个独立自主的主体,一个类似于马尔库塞所说具有“新感性”的人。他受到两股力量的牵扯,不能不从中重新确定自己新的立场:一个不同于原有的现实生活立场,且对现实权力有所超脱,对成见、偏见有所突破的新立场。世界于是在他的视野中展示出新的面目,那些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现象则第一次受到质疑。正是基于文学活动这种复杂性和多变性,布莱希特才利用“陌生化”手法创造心理距离,来实现戏剧的认识批判功能。
移情与外位性两种倾向的活动并非截然分开。巴赫金说:“审美观照的一个重要(但不是唯一)方面,就是对观赏的个体对象进行移情,即从对象的内部,置身其间进行观察。在移情之后接踵而来的,总是客观化,即观赏者把通过移情所理解的个体置于自己身外,使个体与自己分开,复归于自我。只有观赏者复归于自我的这个意识,才能从自己所处位置出发,对通过移情捕捉到的个体赋以审美的形态,使之成为统一的、完整的、具有特质的个体……移情与客观化两个因素是相互渗透的。”审美观照绝不可能纯粹外在于审美客体,特别是文学活动中的观照,因为观照者必须首先将语言概念转化为审美对象,给予具体化,并填补空白,这就是说,他必须参与创造,才有可能观照。而创造活动则已经注定将观赏者卷入到文学的虚构世界,将他与主人公及其世界相结合,也即发生移情了。审美观照处于一种不即不离、又即又离的活动状态之中。可是,当欣赏者在审美观照中受到深深的感染和陶醉,他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和审美对象融合为一,和一种永恒的生命境界融合为一。
移情与外位性相互融合的状况正如尼采所说的酒神与日神的结合。尼采认为,悲剧观赏过程中既存在酒神状态的迷狂,它毁坏人生日常界限和规则,将个人和他过去所经历的一切都淹没在恍惚的激情之中,试图摆脱个体化而成为世界生灵本身,回归存在之母,回归一切现象之彼岸的历万劫而长存的永恒生命。同时,又需要日神状态的无意志静观,它令我们迷恋个体,用个体来满足我们渴望伟大崇高形式的美感,激励我们从中领悟人生奥秘。“酒神魔力看来似乎刺激日神冲动达于顶点,却又能够迫使日神力量的这种横溢为它服务。悲剧神话只能理解为酒神智慧借日神艺术手段而达到的形象化。悲剧神话引导现象世界到其界限,使它否定自己,渴望重新逃回唯一真正的实在的怀抱,于是它像伊索尔德那样,好像要高唱它的形而上学的预言曲了。”正如没有外位性,没有心理距离,就没有审美观照活动;没有移情,也就没有审美体验,甚至会失去审美创造的重要动力。人处身文学作品的外位观照着,同时又因观照而移情着。外位性与移情是水乳交融的。因此,文学的审美活动就只能发生在文学虚构世界的边缘,发生在现实生活世界的边缘,在两个世界的交接处。文学是边界的文化。
二
作为边界文化的文学,由于留滞于现实生活的边缘和文化的边缘,它一方面仍然处在权力和意识形态笼罩之下,另一方面又因被边缘化而为逃脱权力和意识形态掌控提供了可能。
文学作品的素材和语言都来自现实生活,它们都渗透着社会意识形态;而且文学也必须以现实的经验和价值来充实作品,才能使作品具有现实感,才能对人产生亲近感和亲和力,才能吸引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虚幻之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不会令人产生真正的兴趣。罗兰·巴特说:“意识形态之体乃是虚构……每种虚构都受某类社会专用语、社会语言方式的支撑,它们与之同化:虚构,是在那一致黏稠的程度上,触及到语言,此际,它异乎寻常地凝结起来,且找到一个司铎阶层(classe sacerdotale)(僧侣,知识分子,艺术家)去普泛地言说它,传播它。”语言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它不可避免地体现着权力关系,负载着社会意识形态。对话语权的争夺,以及如何运用话语,运用一种什么样的话语,实际上就潜藏着权力纷争,隐含着的意识形态问题。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较之于其他种类的艺术,必然有着更为显著的意识形态性。
在《后现代主义诗学》中,哈琴指出后现代批评话语重视意识形态和权力问题这一倾向,并认为,这种现象根源于对自由人文主义的反对,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学艺术阐释为永恒和普遍的东西,压制其中的历史、政治、物质以及社会因素,而后现代理论则质疑这种压制行为。他们认为:“意识形态是产生意义的一般过程。换言之,一切社会实践(包括艺术)都凭借意识形态,也存在于意识形态当中,如此一来,它就成了‘我们的所言所思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方式’。”后现代理论一反自由人文主义对永恒和普遍的热忱,转而垂青于文学活动的历史性和政治内涵,力图揭示文学叙事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他们通过话语分析和叙事策略分析来揭露作品中存在的不平等关系,彰显缺席者和被遮蔽的声音来质疑压制的权威性,以此证实文学本身即各种权力交集的角力场。
文学并非躲避意识形态的避风港,作品实即权力的角力场,人在文学活动中就经受着各种力量的争夺和影响。在分析洛里·穆尔作品《如何》的修辞效果时,詹姆逊·费伦说:“‘在我们(读者)身上所发生的’一些事取决于我们在虚构内部采取的双重视角,当我们走进和走出表述对象的位置时,我们仍然处于观察者的位置,并发现了叙述者就我们作为表述对象时的认识和信仰所做的假设。进言之,担当表述对象的角色意味着我们进入了理想叙事读者的角色——叙述者告诉我们该相信什么、思考什么、感觉什么、做什么,而在担当观察者的角色时,我们评价我们所处的理想叙事读者的位置。”在此,费伦所说的“理想叙事读者”即一位完全听命于叙事策略,与叙事者积极配合并实现其意图的读者,因而它实即叙事者在作品中为读者设定的位置,是叙事者行使话语权力,意图迫使读者顺从的一个视角。当读者与理想叙事读者相重合,进入作品的虚构世界,并随叙事策略的指引,以特定叙事所确定的方式与表述对象相关联、相融合,这实际上就已经处在叙事者权力的掌控之中了。他按照叙事者的意图去相信、去思考、去感觉和行动,而这一切又是他于无意间自愿去实现的,他已经掉进意识形态陷阱了。可是,一旦读者处在表述对象之外而成为一位观察者,他也就可能摆脱叙事者的控制,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并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来评价理想叙事读者及其位置,也就是说,叙事者所具有的权力和所提供的视角已经处于读者观察的前景位置而受到了质疑。阅读欣赏过程中的“双重视角”正代表着不同权力之间的纷争较量。
费伦颇有说服力地阐述了文学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学作品总是以特定的话语方式和叙事策略预设了某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它们暗中引导着读者,不知不觉间诱使读者就范,偷偷将特定意识形态灌输给读者。而读者则坚持着自己的权力,从自己的权力和视角出发与叙事者相抗衡。事实上,文学作品中的权力纷争可能更为复杂,因为作者或叙事者并非始终能够控制作品整体,甚至是作品主人公及其他人物都可能逸出作者或叙事者的掌控,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由此构成“多声部”,构成各种因素间的角力。不过,这只是进一步说明文学与政治的关联。
问题的关键在于,费伦的论述忽略了文学作为审美文化的边界性质,他将文学虚构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相混同,忽略了文学虚构世界中人的生存状态与现实生活世界的差异。在文学的虚构世界,任何强制都必然受到抵制和唾弃。固然,叙事者可以通过种种手段诱使读者进入特定位置、调节读者与表述对象的关系来实现目的,令读者自己落入意识形态陷阱,受到意识形态影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文学虚构世界毕竟是个感性的世界,它激发起欣赏者的感性力量,让欣赏者的生命和激情得以充分展开,而这恰恰又构成冲决意识形态牢笼、维护生命本身的有效机制。马尔库塞就十分重视文学艺术跟现实相区别的“异在性”,他说:“升华要求较高程度的自律与包容;它是意识与下意识的中介,是初级过程与次级过程之间的中介,是理智与本能之间的中介,是不合作与反抗之间的中介。在其最完善的方式中,诸如在艺术作品中,升华成为在向压抑屈从的同时挫败着压抑的认知力量。”文学艺术正是通过升华跟现实生活世界相区分,而成为独立的虚构世界,成为居于现实生活世界边界、文化领域边界的审美文化。在文学的虚构世界里,现实法则、现实秩序已失去其权威性。文学只遵循审美秩序,也即感性生命的秩序来重建自己的王国。即便叙事策略诱使欣赏者进入特定位置,迫使欣赏者按照叙事者的方式来看待世界,而处在这一位置的欣赏者仍然不会轻易屈从于权力和意识形态,他总是从自己的感性生命出发展开活动,感受世界。
甚至当欣赏者与作品主人公融合一体时,也不是简单地受到操纵。一般认为,在文学活动过程中,欣赏者与主人公相同一,也即欣赏者为主人公所同化,实现了视界融合,不自觉间接受了主人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其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在文学活动中,欣赏者与主人公相互接触的过程就是一个交往对话的过程,这期间,两者的思想观念发生了碰撞、交换和影响。当欣赏者与主人公之间思想观念差异很大时,融合是很难发生的,主人公往往只能处在被欣赏者评价的位置。只有当两者间存在某些共同点或相似点,才有可能相互吸引、相互接近,进而发生融合;而且这种融合也不是欣赏者将主人公的思想观念据为己有,不自觉地受到作品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掌控了。“融合”只能是想象的融合,它发生在虚拟情境中。当文学虚构世界悬置了现实法则和现实秩序,对处身其间的欣赏者来说,现实压抑已不复存在,意识与无意识间的隔阂也被撤销,一个浑融的生命境界开始了。只有在此时,欣赏者与主人公的融合才有可能。“物我合一”只能发生在“无物无我”之时,也即发生在自我意识消解而沉入生命底层的浑融境界之时。从这个角度看,文学活动过程中欣赏者与主人公的同一,并非发生在观念意识层面,而主要发生在感性生命层面。这是生命对生命的呼唤和认同,是生命之间的共鸣共振,而不是一方被另一方所属的意识形态所俘获,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已经被悬置了。感性生命的自由活动始终是非意识形态和反意识形态的。这种回到生命本身、对生命的发现和认同,恰恰构成对抗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力量。因此,文学活动中,欣赏者与主人公相融合的过程,固然存在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最终又激发起对意识形态控制的反抗。
对罗兰·巴特提出读者阅读中的“狂喜”,约翰·费斯克做出这样解释,他说:“狂喜,可以翻译成极大的快乐(bliss)、喜极忘形(ecstasy)、极度兴奋(orgasm)。它是身体的快感,发生在‘文化’崩溃成‘自然状态’的时刻。它是自我的丧失,也是控制与治理着自我的主体性的丧失——自我是社会性建构起来的,并因而受到控制,它是主体性的场所,并因而是意识形态生产与再生产的场所。因此,自我的丧失即是对意识形态的躲避……这身体蔑视着意义或规训。”当读者(或作者)沉浸于文学活动的高峰体验之中,当自我意识在这种体验中瓦解,当他沉入生命的本然状态时,意识形态操控势必显得软弱无力了。
在谈到解释活动时,伽达默尔说:“我们站在他人的面前,甚至在他人开口回答之前,仅仅是他人的存在就帮助我们打破自己的偏见与狭隘。”在文学活动过程中,人总是面对叙事者、主人公或其他各式人物,不断与叙事者、主人公、其他人物相遇、对话、交流,因此,不能不受到种种权力和意识观念的挑战和影响。另一方面,文学活动又有其特殊性,它发生在生活和文化的边界,与一般理解活动不同。在日常生活中,“一切熟悉的东西都被遮蔽了”。“因此,理解艺术品向我们诉说的内容就是一种自我遭遇。但是,作为同真实性的遭遇者,作为一种包含着惊奇的熟悉性,艺术经验就是一种真实意义上的经验,而且必须不断重新掌握经验所包含的任务:把它整合进人们对世界和对他们自身的自我理解的定向整体之中。”日常生活中,我们或忙于筹划,孜孜以求;或自暴自弃,浑浑噩噩;然而,却总是处在必然性的掌握之中,处在意识形态笼罩之下,以致自我的真实生命被遗忘了、被遮蔽了。唯有文学艺术才让人重新面对自我生命本身,发现生命的真谛,那既熟悉又令人惊异的生命的真实。正是这一发现赋予文学艺术以不朽的魔力,使它有能力对抗外在权力,破除意识形态的遮蔽。也正因如此,当人们阅读古典作品并陶醉于作品世界时,并非重新受到已经作古的先人们的蛊惑和操控,竟然不自觉地落入早已逝去的意识形态陷阱;与此不同,在实际阅读中,那些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已经失效了,与读者十分隔膜了,真正构成对话的是双方的心灵。那是心灵与心灵的沟通,是对生命的启迪和激发,对人性深度的发现。
马尔库塞曾深刻阐述了文学艺术与革命的关系,他说,对于诗歌来说,即便政治缺席的地方,也存在着革命。从这个角度同样可以说,只要是真正的文学艺术,即使最具意识形态性的作品,也仍然持存着抗拒意识形态的力量。从终极意义上说,文学只认可真实的生命和生命的真实,它从根柢上是反对任何控制,包括意识形态控制的。这,正是对文学很难断然做出“进步”或“反动”等简单判断和区分的缘由,也是文学经典历经时代变迁、社会意识形态更替而仍然魅力长存的缘由。作为一种处在现实生活边缘和文化边缘的边界文化,它为人提供了边缘化的生存;然而,也正因为是边缘化的生存,才让人能够据有一种理想的自由生存,一种真正属人的生存。
〔注释〕
①游戏和仪式都可以没有观众,所有人都可以直接参与其间,并且需要全身心投入;而审美活动则不同,一旦失去旁观者或外位性,就失去审美所必需的心理距离,就没有审美观照,也就不成其为审美活动了。
②韦尔南认为:戏剧、悲剧在公元前5 世纪创建,其时,正是“虚构的意识”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因此,需要对戏剧做出规定:它不能谈及城邦的现在。韦尔南讲述了一个例子,公元前5 世纪初,曾有一出悲剧上演了一场当时的灾难——米利都陷落事件,结果引起观众的震惊和骚动。这就是说,在虚构的意识刚刚形成之际,戏剧还需要有更多限制,如时间距离、非凡的英雄等,以帮助维持观众在戏剧观赏中的心理距离和外位性。(让-皮埃尔·韦尔南.神话与政治之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434-435 页。)
〔1〕巴赫金.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A〕.钱中文.巴赫金全集(第1 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巴赫金.论行为哲学〔A〕.钱中文.巴赫金全集(第1 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3〕尼采.悲剧的诞生〔A〕.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4〕罗兰·巴特.文之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詹姆逊·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赫伯特·马尔库塞.对不幸意识的征服:压抑的反升华〔A〕.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8〕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9〕伽达默尔.文本与解释〔A〕.严平.伽达默尔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
〔10〕加达默尔.美学与解释学〔A〕.哲学解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