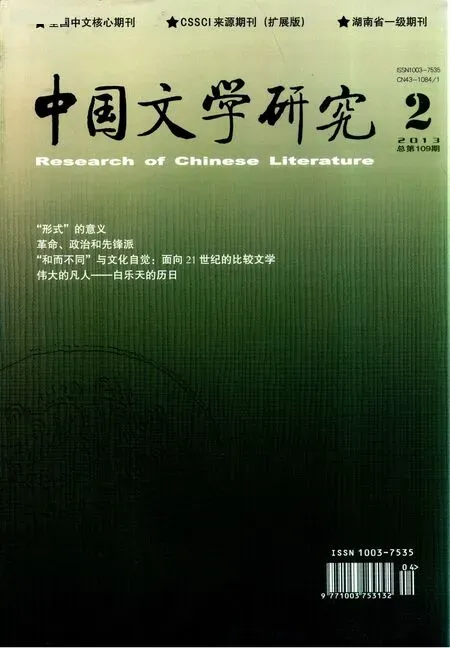革命、政治和先锋派——论中国当代先锋主义文学思潮的转向
姜玉琴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 上海 20083)
也许自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先锋文学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了艺术形式和审美表现范畴之内,而对先锋文学中的文化意义虽有一定程度上的探讨,但却甚少谈到政治。即便是谈,也是从“反政治”的角度来谈的——把先锋文学与政治设置成对立的两极,先锋文学似乎就是一种与政治势不两立的文学。可能是出于对这种研究倾向的一种反拨,近几年的先锋文学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向:有些研究者开始从激进的“革命性”角度来强调先锋性,即把先锋与政治性紧密地联系到一起。
这个转向值得注意,它不但关系到对先锋派文学的理解,也牵涉到对整个20 世纪中国文学作品的再评价问题。换句话说,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下,如何定位先锋派,也就如何定位了中国新文学。这样说决非是哗众取宠,而是因为中国20 世纪的文学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二者同步发展,休戚相关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该如何评价文学的历史与社会历史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评价将会直接影响,甚至颠覆了对文学作品的认识。通俗地说,如果把文学的历史与社会历史分开来看,所得出的结论将是以文学为中心的;而把文学的历史与社会历史合而为一的话,占主导地位的则就是社会历史。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文坛上的一些现象来加以分析。如目前就有学者这样来论述中国的20 世纪文学:
“在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如早期和中期乃至更晚,中国的艺术家们虽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像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给人类那样“拿来”西方的种种“主义”,但却很少提及或使用“先锋”(或其他译名如“前卫”)一词。他们可能采用先锋主义的某些具体思想或主张,或者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文艺行动上可能已经完全称得上货真价实的先锋主义者了,但却并没有自觉或明确地竖起先锋主义旗号。取而代之,他们索性把自己的先锋行为统合到其他主义、尤其是声势浩大的革命主义之中。”
显然,作者是从“文艺行动”的角度来指认先锋主义的,即先锋主义在中国“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和革命主义基本是同一个概念。或者干脆说,在很多时候,它就是借着革命主义的面貌出现的。
把先锋主义纳入到革命主义轨道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新文学的秩序要发生改变,即原本是先锋的,现在变得不先锋了;原本不是先锋的,现在变成先锋的了,如发生于20 世纪20 年代包括诗歌在内的“革命文学”就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先锋主义文学,这在过去是从未有人这样来指认的。果然,这样的一种思路流通开来了,就有学者进一步指出,40 年代的“延安艺术运动”,可以被视为是“20 世纪最为杰出的先锋运动”。“延安的艺术运动”就是一种“革命主义”运动;而“革命主义”运动又是一种先锋主义运动,故而“革命性”、“政治性”就成为先锋主义的关键词了。而且在这些学者的言说语境中,这种“革命性”和“政治性”是丝毫不带有贬义的,它是和“杰出的先锋运动”连接在一起的。
当“革命性”、“政治性”上升为文学领域中的一种合法性标准时,就意味着评价文学的标准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果然,又有学者语出惊人:“存在的政治性决定批评”。这句话的意思无非是说,“政治性”是第一的,文学批评要服从于政治。既然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借着先锋主义的框架得以重新调整与确立了,那么以往的一些文学观点必将会出现颠覆性的变化。确实如此,就有学者以此为基准,来重新解读与定评了“十七年文学”:
“十七年的文学,要从中国现代性激进化的特殊道路去理解。毛泽东在文化上的设想,也并不是“政治专制”可以完全概括的”;“政治与文学之间并不是可以简单等同的,政治也并不能完全压垮文学。十七年文学作品,始终存在着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那些政治起作用地方,文学也会以它的方式确立自己的存在”,不可简单地把“十七年文学”看成是“一无是处的政治压迫。我们还要看到,这些问题,也是中国创建社会主义文化尝试用文学来回答重大的紧急的现实问题”。
显然,以上诸位学者都是从“革命”和“政治”,甚至“创建社会主义文化”的角度来肯定40 年代的延安文艺和“十七年文学”的。往前推十多年,这些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不讨人喜欢的,并且屡遭人们的质疑与批判的。有意思的是,质疑、批判的原因与现在肯定它们的学者一样,也是因为“革命性”和“政治性”。面对同样的创作现象和同样的文学作品,甚至就连使用的批评术语也有互为重合的地方,所得出的结论怎么却是截然相反的?
问题出在了哪里?出在了批评者所操持的理论话语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当年批评延安文艺和“十七年文学”的学者所操持的主要是启蒙主义理论,那么肯定这些文学艺术的批评者使用的则是先锋主义理论。以往由于我们没有把先锋主义与现代主义很好地区别开来,所以往往把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些特征当成了是先锋派的一些特征,所以对先锋派作品的研究往往都是聚焦在其艺术内部,以探讨其美学本质为主的。近几年来,随着一些学者注意到先锋派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要具有革命性的激情和革命性的行动,正如西方学者所总结的那样:“先锋派艺术家并不仅仅以一种厌烦、焦虑、愤世嫉俗(weltschmerz),以及其他一些有关灵魂的伪存在主义的激情来反抗社会。……他们并非要使自己孤立起来,而是要将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艺术与生活重新结合起来。……先锋派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艺术‘体制’攻击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摧毁这个体制,而且也在于使这个体制的存在和意义变得显而易见。”所以,他们评价先锋派文学的眼光也随之改变与调整了。
的确,西方的先锋派除了注重艺术的自律性之外,它还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加关注文学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问题。如果说现代主义诗人是用沉醉于文学艺术的方式来消极对抗社会与体制,那么先锋派艺术家则不然,他们选择主动出击,并对其采取革命行动,这是它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问题在于,当我们意识到了先锋派的这种“激进性”以后,应该怎么来对待文学中的这种先锋性?无疑,前面所提到的诸位研究者都是因为窥见了先锋派中所包涵的这种激进性因子,而改变了对以往那些并不待见的文学作品的态度。换句话说,那些作品还是那些作品,它们丝毫也没有改变,改变的是研究者,即他们观察作品的视角发生了改变。
这种改变是理论站位的改变,即由过去的文学性立场转换到了现在的政治性立场。如果说过去在评价一部作品的优劣时,看的主要是其艺术性,那么现在则是把政治性置于更重要的位置的。对中国新文学而言,这种转变是巨大的,同时也是值得深思的。我们到底该如何认识、评价国内这几年来所新兴起来的这种先锋主义思潮?毫无疑问,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先锋派文学的文化和政治意义,是一件颇有价值的事。它可以丰富我们对先锋派文学的理解与认识。但是在把这种理论运用到具体的文学批评中去时,我们有必要问一下自己,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文学为政治、革命开路还是为了让文学更好地成为文学?
实事求是地说,在任何的一部可以称之为文学作品的作品中,都是能或多或少地分析出一些“文学性”来的。如果缺少了这一点,也就不能冠名为文学作品了,而只能算是宣传资料。所以沿着“文学以其自身的字词力量,以其自身的书写历史的传承,总是有超出政治的东西存在”4〕(P72)这样一个思路来为“十七年文学”,包括延安文艺辩护是没有太大价值的,因为这无助于解决文学自身的问题。归根结底,评价文学作品优劣的标准有若干种,可唯独不可能把是否“超出政治的东西存在”作为评价一部作品的标准。用新知识、新方法来阐释老问题、老作品,的确能在某种程度上产生出新意,问题在于这种“新意”对文学的发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假若研究者们仅仅想把文学当作是一种纯粹的社会武器,那不是我这篇文章要探讨的内容。我所关心的是这样的一种思维转换,即把政治性重新搁置到文学性之上,会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些什么样的后果,毕竟中国20 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状况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学。
西方的20 世纪文学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艺术自律传统。20 世纪文学是一个庞大的概念,不好笼统而论,我们可以以诗歌为例。
就诗歌领域而言,强调艺术至上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经过了充分的开采与发展,隐喻、象征、暗示等纯艺术技巧都发展得异常娴熟,并收获了像艾略特、瓦雷里、马拉美、里尔克、叶芝等一大批堪称世界大师级别的诗人。相比之下,中国自“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则是瘦弱与单薄的。对中国新诗发展了解的人都知道,新诗的传统不止一个,但成就最大的还当属是现代主义诗歌传统。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统,其发展也是异常艰难与缓慢的。艰难、缓慢的原因有两个:一、这原本就不是新诗的自身传统,需要从欧美诸国引入与学习,这是现代主义在中国新诗中发展缓慢、艰难的客观原因;二、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中,一直与“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处于对立的状态。确切地说,它始终受到以“正统”自居的“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的排斥与批判。如臧克家在1956 年受中国青年出版社之托编选《1919-1949 中国新诗选》时,不但把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相决然对立,而且还把“新月派”、“象征派”称作是必须批判的‘时代逆流’,并说直到“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才解决了文学艺术上的许多原则性问题,诗人才真正找到了写作途径:“许多诗人继承了民歌的优秀传统,写出了新鲜活泼的民歌体的新诗来。”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现代文学时期没有发展、壮大起来的内在原因。也许有人会说,不能过于低估中国40 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九叶诗派”中的穆旦岂不就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师?
穆旦的确算得上是中国现代新诗中成就最高的现代主义诗人,可作为现代主义诗歌大师则可能还是有所欠缺的。穆旦的诗歌单独看一两首,三五首,还是颇有现代主义特色的——无论是思想上还是技巧上,但是如果阅读了他的全部诗作就会发现,他的创作中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的创作观念与其美学思想不够统一。这一点表现在他的诗歌中就是,他的诗作可以分成不相关的两大类:一类是有着相当明显的,甚至一眼就能分辨出来的西方现代哲学观念为其创作思想的胚体,如《诗八首》、《我》等就是如此。即使在那些没有明显哲学思想所渗透的诗中,也能较为明显地看出西方现代诗人对他在谋篇、造句方面所发生的影响,如《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从空虚到充实》都能看出艾略特等西方现代诗人的身影晃动在其中;而在穆旦的另一类诗中——这类诗所占的比例更大,则又能鲜明地体现出以艾青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歌所固有的时代特征,如《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赞美》、《控诉》、《给战士》等诗就代表了这一创作倾向。
离开特定的历史背景来苛刻穆旦的诗是有失厚道与公平的,穆旦所生活的年代毕竟不能令他心无旁骛地创作,但在同一历史时期中出现了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创作倾向,的确也折射出穆旦的艺术思想在当时还没有走向成熟:他对西方的现代主义诗歌,包括现代主义哲学都是异常喜爱的,可这种喜爱还基本处于模仿的阶段,并未达到深入骨髓的程度。其标志是,当其环境、心境,甚至阅读范围发生转换时,他的诗歌内容与风格也就随之转变了。这就决定了他可以写出几首非常漂亮的,充满现代意识与生命感觉的诗歌,但却不能保证其所有的作品都能达到相应的高度。
作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领头羊的穆旦,尚且没有在中外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找到自己的坐标点,很好地完成两种文化的转换,其他的诗人就更可想而知了。通过穆旦的这个例子想说明的是,中国20 世纪以来的文学环境与西方20 世纪的文学环境完全不一样,西方有彰显政治意欲的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但与此同时也有以艺术为上的象征主义、意象主义等。就流派自身的发展状况而言,后者的势力和影响是要远远大于前者的,这一点即便是从我们的接受情况中,也能明显地反映出来:西方先锋派中所包蕴的革命性和政治性要求,直到近几年才被我们的研究者所觉察。而在其之前我们所认识的先锋派也罢,现代主义也罢,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是从艺术的实验性角度来加以理解和接受的。
这种在无意识中所形成的接受模式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西方20 世纪文学中的审美传统是要远远大于其政治传统的,至少在我们的目击之内,首先带给我们冲撞的是文学的审美要求,而不是政治要求。
反观中国20 世纪以来的现代诗坛,则会发现,除了“五四”初期有大概不到10 年的自由发展空间之外,其他时间内对诗人的创作都是有着明确要求的,即要求把“诗的前途”与“民主政治的前途”联系到一起。重要的是,这种要求在诗人们的身上贯彻得还颇有成效。如郭沫若是“五四”以来第一个高举为艺术而艺术旗帜的诗人,他说:“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之纯真的表现,生命源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之颤动,灵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可是刚一转身,这个把诗推举为“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的诗人,就又说出了与此完全相反的话:“我高兴做个‘标语人’,‘口号人’,而不必一定要做‘诗人’。”文艺就是政治的“留声机器”。他之所以如此大幅度地掉转了头,是因为他皈依了“革命文学”。
一个诗人的一生自然不是只能服膺于一种艺术观念,他完全可以根据对艺术的不同理解与追求来适度地调整其立场,但一个诗人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能毫无痛苦与挣扎地从一个立场跳到了另一个立场——一个截然相反的立场,就有些不那么正常了。也许这可以从个体者的性格方面来寻找原因,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他缺乏一套成熟而坚定的艺术信仰和美学追求——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改变,他都能始终不渝地坚守住内心世界中的那片净土。这当然不是郭沫若的个人问题,整个中国现代文学都没有像西方20 世纪文学那样搭建起一个崇高而不可侵犯的审美殿堂:有些诗人在某个阶段、某些环境中可以成为艺术之美的疯狂信徒,可一生能沿着这个轨迹走下来的却少之又少。
强调中国现代文学中没有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审美传统,并不是说文学就截然不能与政治相兼容,曾有那么多的学者花费了那么多的笔墨来证明文学与政治是不可分的。这其实是一种偷梁换柱的做法,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压根就不是与政治分开分不开的问题,而是中国的文学、中国的作家离开了政治以及与政治相关的国家、人民等概念的时候,就变得茫然失措,不会讲话了。正像一位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中国文学谈社会的大问题、国家或人类的命运的时候,总是从国家大事开始(茅盾的《子夜》是典型的例子),谈身边的事情则很难飞跃到社会、人类的大问题。为什么呢?在日本(我相信西方也包括在内),我们看到,从非常小的事情——个人的生活、个人的幻想、脑子里面的世界——等等出发,想通人类的命运、社会的命运等大问题的文学作品,觉得很好,很激动。”
这段话可能带有一定的偏激性,但倒也把存在于我们创作观念中的“弊端”给揭示了出来:中国作家的创作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探讨“大问题”的。而所谓的“大问题”都是与“社会”、“国家”等相关的,而这类作品的写法是大同小异的,都是“从国家大事开始”,即作家自己的叙事必须要借助于“国家”这个喻体才行。否则,就变得无所适从了;一类是“谈身边的事情”的,而这类的创作往往与“大问题”是接不上茬、对不上话的,通常仅与一己的悲欢相联系,因此这类的作品常常遭到人们的轻视。
以上两方面的问题,说明我们的国家情结、政治情结是远远大于个人情结、内心情结的,我们没有建立在“个人的生活”、“个人的幻想”基础上的个人叙事话语,有的只是“国家大事”这套公共话语系统。作家的创作只要沿着这条既定的线路走,就会有“伟大的作品”、“史诗”之类的头衔降落下来,而一旦偏移了这套系统,作品也就自动降格了,成为了“小我”的代名词。
这种现状表明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个人”,也就是“小我”根本就没有上升到与“国家”这个庞大概念相对等的地位,充其量只是其身上的一棵螺丝钉——动还是不动,怎么动,都是要取决于这个庞大机器自身的。这套用“国家”来压制“个人”的话语体系,在90 年代的反“宏大叙事”思潮中曾有所松动——“个人”渐渐脱离开“国家”、“人民”的轨道,开始以独立的面貌出现。遗憾的是,“个人”的意识刚刚觉醒,还没有成长、壮大起来,随之而来的“个人写作”,即发生于先锋诗坛的“个人写作”又重新把“个人”置于“国家”和“人民”之下了。
“个人写作”是90 年代先锋诗坛上的一个怪胎。它的名字叫“个人写作”,喜欢顾名思义的人自然就会把这种诗学与“个人”联系在一起,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个人主义诗学。翻阅一下相关研究文章和所出版的相关专著,就会发现有那么多的学者都是从个人化思想情感和个人化话语的张扬及维护角度来为“个人写作”唱赞歌的,这可能是90 年代诗坛,包括进入2000 年后发生在当代诗坛上的一次最大错误的对话。因为如果仔细阅读一下那些身体力行倡导“个人写作”的人的相关诗学文章,会发现,“个人写作”的倡导者不过是与你开了一个玩笑:“个人写作”中的“个人”非但不“个人”,相反它就是历史、时代、现实、责任、道义、承担等系列名词的代称。如果非要把这种诗歌理论中的“人”称之为“个人”,那也是被道道绳索捆绑起来的,完全没有自由的“个人”。一个明明强调诗歌与政治、国家关系的诗学,为何偏偏要用“个人”来命名?一个明明不可能有个人立场的人——个人的立场必须要让位给国家的立场,正如诗人西川的惊呼:“诗歌写作走向了政治之途(比赛谁更能使人震惊)。真正的,货真价实的创造力还有待于开发。”把这样的一种政治性的写作,为何偏偏要释说成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的写作?
有人倡导这种完全“不个人”的“个人写作”,还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诗学主张,哪怕这种主张漏洞百出、荒谬不堪,那也是他的自由。令人不能理解的是,这样一种打着“个人化”的旗帜,借着历史、时代、国家的名义来讨伐多元创作的诗学潮流,竟然搏得了一片又一片的喝彩声,还被某些研究者推捧成是90 年代以来最有价值的诗学理论等等。
这种诗学理论果真具有如此价值?对所谓的“个人写作”权威版本稍加研读,就会发现这种诗学理论异常陈旧,几乎不涉及对形式、语言的认知以及修辞技巧方面的心得,其核心内容——当然是绕着弯子说出来的——就是诗歌要反映时代、历史和现实,个人的命运要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经过了一番波折才终于从政治的坐标回归到艺术本位的诗歌研究界,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挣扎就纷纷地选择站到了“个人写作”的旗帜下,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个诗学理论的内容虽然异常陈旧,但却借鉴了一些解构主义等术语,包裹上了一些新名词,所以不细读文本的话,容易被理论的外表迷惑住。这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不会所有追捧这个理论的人都不读文本的。读了,依旧觉得亲切、有道理,就说明这个建立在时代、社会、国家、政治等基础上的诗学理论是符合于绝大部分人的心理期待的。换句话说,新时期文学尽管经过了30 余年的所谓艺术回归的洗礼,但是蛰伏在人们心底的依旧是那个陈旧的叙事模式,其内在的魂魄依旧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和俄苏文学的那套东西做班底的。只要看一下与“个人写作”理论相伴而来的,是些什么所谓的底层诗歌写作、诗歌必须要承担起社会的道德与责任等,就会明白我们这些年来的艺术观念并没有取得什么突破性的进展,一些原本都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又被义正言辞地重新搬了出来。而且说得与听得都觉得真理在握,丝毫也没有觉得这些低级的问题是根本无须再讨论的了。
好不容易从政治的囚笼中挣脱出来的20 世纪中国文学,在进入到了90 年代,特别是2000 年的门槛后,又自发地朝着政治的方向去了。这种转向无疑有来自于现实方面的刺激,但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我们的艺术审美传统的确是太过薄弱。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让人们纷纷放弃艺术,而集体走向政治。
在西方20 世纪的文学传统中,由于有一个强大的艺术传统在暗中发挥作用,所以即使有些文学流派向政治敞开了心怀,也依旧改变不了文学的总体流向。而在中国这种政治性原本就大于文学性的文学语境中,如果完全用先锋派中的革命性、政治性来取代了先锋派中的艺术自律性的话,就会使当代诗歌重新陷入到“非诗”的窘况之中。包括新诗在内的中国新文学的最惨痛经验教训之一,就是不要再重蹈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救亡压倒启蒙的悲剧了。
从这个角度说,研究者们对先锋文学思潮中的革命性、政治性因素是应该持慎重态度的,否则中国文学又有可能失去独立的艺术身份,而再次成为政治、革命的附庸。
〔注释〕
①在诗歌领域内谈论“个人写作”的人很多,但王家新是最典型的一个,这不但是说他发表的这方面文章多,态度最坚决,而且其他谈论“个人写作”的人也常常以他的观点为观点,所以本文把他的相关诗学视为权威版本。
〔1〕王一川.现代性的先锋主义颜面〔J〕.人文杂志,2004(3).
〔2〕参见唐小兵.试论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中的先锋派概念〔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3).
〔3〕张旭东.当代性·先锋性·世界性——关于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对话〔J〕.学术月刊,2009(10).
〔4〕陈晓明.再论“当代文学评价”问题〔J〕.文艺争鸣,2010(4).
〔5〕彼得·比格尔,高建平译.先锋派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6〕臧克家编选.1919-1949 中国新诗选〔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
〔7〕艾青.诗论〔A〕.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编)〔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8〕郭沫若.论诗三札〔A〕.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编)〔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9〕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A〕.郭沫若论创作〔C〕.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10〕郭沫若.留声机器的回音〔A〕.文艺论集续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1〕千野拓政.当代性·先锋性·世界性——关于当代文学的六十年对话〔J〕.学术月刊,2009(10).
〔12〕西川.深浅—西川诗文集〔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