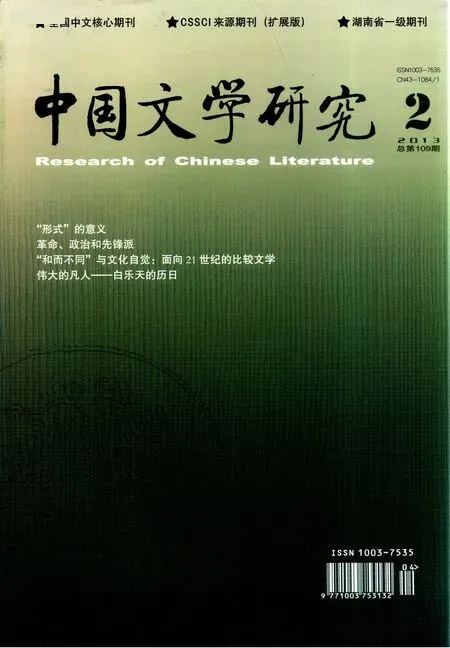《玩偶之家》的“中国化”阐释与新文学聚焦的“解放”
陈传芝
(宜宾学院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 四川 宜宾 644007)
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知识界痛感中国现实问题重重,亟需从思想、文化、文学、科学等方面进行思考,加以解决,于是,对易卜生作品提出的社会、家庭和妇女解放等问题有一种不可遏制的认同欲。”因此,始自“五四”的易卜生社会问题剧译介,一直渗入新文学的话语建构。
易剧中,译本最丰富、演出最频繁、刊载量最大、评论与争议最深广的是《玩偶之家》。检索易剧的接受阐释可发现,其问题剧凸显为《玩偶之家》,而《玩偶之家》又集中于“娜拉”问题。胡适依易剧所阐释的写实主义与个性解放,逐渐演变为追寻“娜拉答案”和求解社会解放的言说。
“对社会束缚的觉醒和从中解放出来,这二者的汇合似乎是《玩偶之家》在中国受欢迎的根源。”《玩偶之家》参与中国社会解放而生成的“解放”话语,正是新文学聚焦的关键词。伴随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批判与革命吁请,娜拉逐渐演变为“解放”的话语符号。而易卜生立足于娜拉个体意志分析创作的审美品格,却成为“解放”背后的阴影。实际上,易剧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证明:自我意志分析与社会分析并不存在选择上的对立。然而,由于译介接受批评发生于新文学革命之际,批评的现实需求常等同于创作的现实要求,成为指导中国新文学的创作论,而创作上的审美探究却一直难以深入下去。因为历史依然影响着当今的文学判断,并在当下纷繁的文学理论建设中体现出来,所以,通过《玩偶之家》的个案接受分析,回溯译介接受生成的新文学话语,并不失其现实意义。
一、生成易剧接受批评的社会“解放”
“五四”文学革命的迫切性肇自现实的民族危困。新文学聚焦的“解放”,是社会解放的现实要求。
易剧译介发生于新文学革命之际,始自《易卜生主义》的嬗变之旅,真实地再现了新文学的关键词——“解放”话语的生成样态。
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称:
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
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
胡适认为:“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出于民主主义和社会改良的政治观,胡适通过东西文化对比,发现麻木昏睡的国人需要兴奋剂。易卜生“专研究社会种种问题”的问题剧,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尤为看重易卜生的怀疑精神和叛逆品格,主张引进易卜生戏剧来激励“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的国人,呼唤拥有自由意志和责任意识的“维新革命者”。他说:“社会国家的健康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球,方能有改良的希望。”通过坚持自我主义,实现社会改良,正是易卜生的创作宗旨。他曾在致勃兰兑斯的信中说:
我首先希望你具有真正强烈的自我主义,这种自我主义一时会促使你把同你自己有关的东西看成是唯一有价值和重要的东西,而把其他一切当作是不存在的东西。不要把这个看作是我的兽性的一种表露,要对社会有益,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自己的本质。”
鲁迅亦独赞易剧坚守自我,冲击社会弊端的“白血球分子”,他说:
其所著书,往往反社会民主之倾向,精力旁注,则无间习惯信仰道德,苟有拘于虚而偏至者,无不加之抵排。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则常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已也。
伊孛生之所描写,则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迕万众不慑之强者也。
虽“迕万众不慑之强者”等同于“白血球”分子,但鲁迅从中国现实出发,关注“强者”命运。《娜拉走后怎样》,立足于娜拉这一“强者”形象,拓展了“易卜生主义”的社会使命。
1923 年5 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公演《娜拉》失败。在5 月11 日至18 日的《晨报副刊》上连续刊登了演出评论,或归咎于观众素质,或致诘于演员、剧场条件和舞台设计,《娜拉》一时成为学校与社会争论的焦点。戏外议论引起了学生、知识界和剧作人对《玩偶之家》更为深入的社会思考。针对剧演反响,1923 年12 月26,鲁迅在女高师以《娜拉走后怎样》为题进行了演讲。他说:
娜拉走后怎样?……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 ……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
鲁迅指出的两条路,冷峻地揭示了娜拉无路可走的现实处境。他将娜拉置于中国社会舞台,将其现实处境的社会问题抛给国人,唤起思考与求解的注意。虽对《玩偶之家》作如此阐释,鲁迅却并未将易卜生定格于“社会改革家”,他说:
(娜拉)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
鲁迅认为易卜生是歌唱着的诗人,不是解决问题的导师。但他却依然拿易卜生的自我主义,来阐述国人问题: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易卜生剧《国民公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 多幸运!
鲁迅肯定“个人自大”,相信新思想、新改革定会“从他们发端”。易卜生的“自我主义”,被赋予了启蒙大众,造就独战庸众之士的期许。而这正是文学自身变革的动机,1928 年,他在《语丝》上撰文说:
何以大家偏要选出Ibesen 来呢?……因为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的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事已亟矣,便只好以实例来刺激天下读书人的直觉,这自然是确当的。
在鲁迅看来,追求解放的新文学:就戏剧言之,旨在建设新的戏剧,散文戏剧;就文学言之,是为了真的文学和白话文学;就思想性和艺术性而言,则是“以实例来刺激天下读书人的直觉”。他择其要义,单就“刺激性”来做文章,拿中国实例来“刺激天下读书人的直觉”,“真的文学”、“白话文学”、“新剧”也就置于启蒙意旨的附属地位。
在《易卜生主义》和《娜拉走后怎样》的易剧阐释中,我们发现“解放”话语的趋向:胡适赋予“易卜生主义”的写实功效——改良,鲁迅则倾注易剧形象以社会斗争的期待。当人生自救与社会变革作为新文学话语建构的宗旨时,“解放”的言说就担负起了人生信仰和社会使命的职责,被赋予了进步文化和世界观的特权。
二、娜拉归属的追问与社会“解放”的言说
1934 年,《国闻周报》3 月19 日发表了《娜拉走后究竟怎样》的文章。作者鋗冰为了响应国民党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提倡“中华民国固有之德性——礼义廉耻”,批评鲁迅《娜拉走后怎样》为经济权而出走、战斗的思想,提出“仍要中国式的家庭的幸福”,“娜拉走后怎样?”的讨论再度重温。
1935 年初的“娜拉事件”使讨论进入白热化。南京的磨风社公演了《娜拉》,剧中娜拉由南京的一位小学教师王光珍扮演,另有三位女生扮演其他角色。嗣后,校方以“行为浪漫”为由,将师生四人开除。此事当即引起轰动,后被称为“娜拉事件”。茅盾针对该事件写了《<娜拉>的纠纷》一文,他说:
现在似乎更加弄明白些了,单单是不靠男子来养活,还不够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还有比纯粹的经济问题更中心的问题在那边呢!演几次《娜拉》,不会将那更中心的问题解决了的。何况那出走的“娜拉”实在自己也不明白跑出了那“傀儡家庭”以后该到哪里去。不过现在的兴中门小学校长之类委实是神经衰弱,见了一点点就会大惊小怪,所以扮演“娜拉”的王光珍女士还是敲破了饭碗,而其他三位女子受了开除。于是乎应该不会惹祸的“娜拉”,在民国二十四年的开头就惹了一次祸。
针对“娜拉事件”,茅盾以嘲讽的笔触,挞伐了校长拿“浪漫”做文章的政治行径。此后,剧联决定《娜拉》在全国公演。1935 年,全国各大剧团纷纷公演《娜拉》,当时有报刊称:“今年可以说是娜拉年,各地上演该剧的记录六千数十起。”
在《娜拉走后怎样》中,鲁迅打破艺术与现实界限,将思考与行动指向未来,是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的言说。而这次“娜拉事件”,则是戏内和戏外相结合的政治解放行为。表面看来,“娜拉事件”是“鋗冰”与鲁迅的对立,兴中门小学校长与王光珍师生的对抗。而实际上,事件背后是两个阶级和两个政党的文化斗争。剧联兴起的“娜拉年”,意味着“娜拉”的胜利、新思想的胜利、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的胜利。至此,作品与生活、艺术与现实的距离正趋于零。出走后的娜拉,“还有比纯粹的经济问题更中心的问题在那边呢!”“那边”是一个比“经济”更中心的政治问题,同时“那边”是一个与“这边”阶级分明的立场问题。“当文学艺术统一于革命斗争和现实政治立场的阐释时,由于追求文学的政治思想性,致使“创作主体在政治思维定势的作用下,格外倚重政治功利性而相对轻视客观真实性”。
《玩偶之家》的“中国化”阐释,是新文学声音与现实社会问题的回应。1941 年,郭沫若给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答案。他在《娜拉的答案》中说:
《娜拉》一剧是仅在娜拉离开家庭而落幕的,因此便剩下一个问题,娜拉究竟往哪里去?我们的先烈秋瑾是用生活来替她写出了。她是四十三年前不折不扣的中国的娜拉,她不愿意“米盐琐屑终其身”的先觉姿态,大彻大悟地突破了不合理的藩篱,为中国的新女性、为中国的新性道德,创立了新纪元。她并不是纯趋于感情的反抗,她的革命行动有深沉的理性为领导。她知道女子无学识技能,总不能获得生活的独立,所以她便决心跑到海外去读书。她也知道妇女解放只是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中的一个局部问题,要有民族的整个解放、社会的整个解放,也才能够得到妇女的解放。……脱离了玩偶之家的娜拉,究竟该往何处去?求得应份的学识与技能以谋生活的独立,在社会的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在社会的总解放中担负妇女应负的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牺牲——这些便是正确的答案。这些答案,易卜生自己并不曾写出的,但秋瑾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替他写出了。
“娜拉的答案”由中国秋瑾来做答,由个人解放、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内在逻辑性而生成的革命信念,毋庸置疑。自此,响应时代需要,筛检、嬗变中的娜拉问题,似乎得到了圆满解决。从《玩偶之家》或“娜拉”的中国化旅程来看,其“解放”话语呈线性发展。胡适阐述的是“救出自己”、“保卫社会健康”的个性解放。鲁迅给出了娜拉问题的多种可能:堕落、再回家、为争取经济权而战斗——“解放”行为的讨论。茅盾直接参与现实政治解放斗争,把多变、多边问题简化为“两边”问题。郭沫若把秋瑾作为“娜拉”样板,总结性地将所有问题归为一个政治行为——社会总解放。娜拉,作为“解放”的话语符号,当再次回到中国形象时,其“中国化”之旅也就画上了圆满句号。而其接受批评却由复杂的个人与社会、现实与历史的问题,逐渐简化为现实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与政治行为——社会总解放。
《玩偶之家》的“中国化”阐释,是其接受性创造和历史性误读的过程。创造性误读的关键词是“解放”,从“解放”的言说到“解放”行为,最终以历史证明的完成式结论。其嬗递在于:娜拉文学形象特质的淡化,社会形象内涵的叠加。然而,娜拉,作为文学形象,是作者立足个人意志分析的形象塑造,其中蕴含的审美品格,作为阐释热情发生的原初,本应成为接受批评与创作理论探索的关键所在,却渐处“解放”的光晕之外。《玩偶之家》的中国化之旅,使我们发现新文学话语建构的缺憾在于:接受批评中,社会现实意义的扩大化,遮蔽了文学意义的探索;社会分析的恣意延伸,阻碍了个体生存意义的深入追问。
三、社会“解放”背后的文学形象
卢卡奇认为,“因为一国文学发现本身出现危机的时候,外国作家才能真正有所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危机”肇自现实社会的困顿,“外国作家”的“作为”在于解决社会问题。因此,从译介作品的文学意义过渡到社会意义,是现实发展的需要。《玩偶之家》的接受阐释,一直游离于文学自身的审美品格之外,纠缠于中国接受主体的是社会意义上的“解放”。作为家国拯救的言说,这是遭遇特定历史时期的合理性解读,又是易卜生写实主义的历史性误读。娜拉与丈夫讨论的法律、宗教、道德问题,是其情感意志觉醒后的反思,既有聚焦过去与当下的现实质疑,也有反观人自身的叩问。其间人物形象的社会分析,是抵达哲学意义和审美向度的桥梁。《玩偶之家》的中国接受,截取社会批判而生成的“解放”话语,是以删汰文学形象的审美品格为代价的。
中国接受者热衷于易剧,是因为他们需要易剧人物所传达的信念和力量。这些形象,对于中国“注视者”来说,是“社会总体的想象物”,注视者创造了形象的文化含义,即“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描述。娜拉,之所以能作为中国注视者的想象物,走出剧本、剧场,走进中国社会,参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成为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代言人,是因为娜拉要求做人的“解放宣言”:
娜拉:这些话现在我都不信了。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托伐,我知道大多数人赞成你的话,并且书本里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从今以后我不能一味相信大多数人说的话,也不能一味相信书本里说的话,什么事情我都要用自己脑子想一想,把事情的道理弄明白。
……
海尔茂:你说这些话像个小孩子。你不了解咱们的社会。
娜拉:我真不了解。现在我要去学习。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
这是娜拉个体意志觉醒的“宣言”,其凌厉气势激发了受众参与社会现实的热情。中国接受者,对此产生了强烈共鸣,将其解读为追求革命解放的激情与坚强斗志。这误读在于译介发生的社会需要。社会需要将娜拉拉出客厅,背离婚姻、爱情,直接进入社会语境,成为现实社会的抗争者。这社会影响力之源正是文学审美的感染力。而文学的审美内蕴则生成于个体意志的人性分析。因此,立足于文学形象敞开的个体生活所阐释的社会“解放”,则不应悬置个体意志分析的审美品格。因为文学形象的个体意志分析,既是社会批评的深入,又是文学理论探索的切入点。
“娜拉走后怎样”是中国接受主体解读的核心。而作品本身的关注点却是娜拉该不该出走,出走的原因是什么。对于娜拉出走的原因,中国接受是“觉醒”与“解放”。而从剧情和娜拉自身来说是因为爱情的“奇迹没出现”(第三幕)。剧中的娜拉根本不关心“社会”,她完全生活在自我的情感想象中。娜拉的生活动力和热情是“奇迹的梦想”。“这种期待把她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圣灵降临的状态,而她本人对生活中的一切悲惨事情变得毫无知觉了。”当“丈夫充当了扼杀她梦想的现实工具”时,娜拉慷慨陈词的“妇女解放宣言”,只是“娜拉的激烈决定和直接的道德说教徒劳地掩饰她内心的空虚”。
《玩偶之家》的社会分析,着眼于娜拉压迫情绪的“觉醒”和“解放”宣言。而其文学意义,则是“这部现实主义的、处理问题的作品中,论及生活中梦幻的力量和它的苦难,而这首‘诗中诗’赋予全剧艺术生命——它的无休止的紧张”。易卜生采用“追溯法”的分析技巧,通过娜拉害怕“奇迹出现”的紧张情绪,艺术地再现了“看清和盲目之间的辩证法”。“他从叙事性的事件出发展示主题,采用追溯往事的方法,将时间聚焦,将事件再现于当下,并跨越横亘在当下和过去之间无法再现的鸿沟,挖掘情节统一的因果结构”,其间的写实主义创作精神表现为:在现实与历史的交错中反观现实问题,历史、现实、未来和社会与个人辩证地统一于情节中。
“拉娜走后怎样”的接受阐释,是参与现实斗争的急切和未来展望的激情使然,省去了过去、现在、未来之间内在节律的发现,把现实的复杂性简化为寻求解放的言说。实际上,《玩偶之家》存在着历史传统与当下、未来讨论的多向度,中间并不存在单方的胜利和价值取向。何况《玩偶之家》由家庭问题延伸到妇女地位问题和社会问题,问题一直处于敞开状态。
易卜生将现实熔铸于历史和哲学思考的写实主义创作,具有整体性和开放性特征。他总是安排戏剧人物在情节的高潮端,思想观念激烈冲突之时,进行问题讨论,并以人物平等性、公开性、参与性的视角,互相辩难,将问题引向深入。对传统道德、法律、社会现象痛下针砭者,是独战多数的觉醒者、民主战士,虽具有未来的预言性和斗争性,却并非解放者和胜利者。结局并没有解决人物辩难的圆满,常以引导受众思考的行为落幕,传统的顽固性与现实、未来的多变性、复杂性,一起向当下与未来敞开。
易卜生并没有沿着“娜拉走后怎样?”的未来问题前行,而是直面该不该出走的现实。继《玩偶之家》之后,他创作了《群鬼》。“《群鬼》是《玩偶之家》的自然的下篇,易卜生在一八八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的一封信里写道:‘继娜拉之后,阿尔文太太就得出来了’。阿尔文太太是被说服后继续呆在家里的娜拉。该剧的题材再次是有关责任和自由的问题。”阿尔文太太一直隐忍着丈夫荒淫无度所带来的痛苦,把寄托希望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良好教育。当得了遗传性病的儿子归来,却又让她回到了从前,生活蔓延着令人恐怖的“鬼”气。针对“这个男人主宰一切的世界孕育着的混乱、疏远甚至疯狂”,易卜生又创作了《海达·加布勒》。作者似乎回避女性参与社会活动,将其放入四墙之内的客厅,居于自我空间经营自我存在。与庸俗社会格格不入的她们,寄予了作者的诗意和梦想,是庸俗社会的牺牲品,并不是解放社会的英雄和奠基者。而这与《玩偶之家》“中国化”阐释的社会分析并不相悖。这也是易卜生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社会改革家,只说自己是个诗人的原因。他运用诗人笔触,生活化地揭示人物形象的“自我本质”与社会冲突,根据人物“自我”选择需要落幕,“对社会有益”的热情并未让他抛开“自我主义”。他将个人融入社会历史的现实批判,“是由人的本性根底酝酿出来的。推开一层障隔,而个人的特性呈露于我们的眼前。再推开一层障隔,而我们可以看到他过去的关系。再推开第三层障隔,而我们已洞鉴这个性的本质……我们须用精神,才能理会剧中事物的关联,如在实际生活一样。”易卜生的创作选择,不存在自我意志分析与社会分析的冲突。易剧人物个性分析与社会分析水乳交融,如同实际生活感受一样。然而,接受者却常抽取社会分析,取向于未来与社会向度的精神探求。这样的接受批评不仅仅发生在中国,正如劳逊所说:“现代戏剧家都钦佩易卜生紧凑的技巧,社会的分析和性格化的方法。但现代作家跟萧伯纳一样地把这些因素大大的变了质……易卜生式的对自觉意志的分析不再出现,代替它的是某些品质的组合。”《玩偶之家》的“中国化”阐释,同样是“变质的品质组合”,即娜拉意志觉醒放大之后的现实社会分析,虽践行了启蒙救亡的社会使命,却经不起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检验。
四、结语
《玩偶之家》的“中国化”阐释,是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接受的主体性选择。而在今天看来,却是急切寻求社会意义的被动接受。易剧人物意志的自觉,在中国冠以“解放”之冕后,直接向社会与未来敞开,其创造性误读虽有有舍本逐末之嫌,却再现了新文学话语建构的历史需要。通过这一个案回溯新文学批评话语,祛魅“解放”神话,我们发现:立足于个体意志自觉分析的《玩偶之家》,并不影响历史选择中的创造性误读,同时又能让我们再次回到作品本身,发现历史和现实。因此,创作上基于个体意志分析的形象塑造,批评上依据个体意志分析与社会分析相融合的生活现实,才能保证创作与批评理论的深入,使文学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最初的英文稿是民国三年在康奈尔大学哲学会的宣读稿;中文稿作于民国七年五月十六日。
②《玩偶之家》的又一译名,本文参照译本是潘家洵翻译的《玩偶之家》。
③最初发表于1924 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刊》第六期。曾署“陆学仁、何肇葆笔记”。同年8 月1 日上海《妇女杂志》第十卷第八号转载时,篇末有该杂志的编者附记:“这篇是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演稿,曾经刊载该校出版《文艺会刊》的第六期。”
〔1〕邵锦娣.《伤逝》与《玩偶之家》:映照中的阐发〔A〕.王宁、孙建编. 易卜生与中国〔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2〕Eide,Elisabeth. China’s Ibsen:from Ibsen to Ibsenism.London. 1987.
〔3〕胡适.易卜生主义〔J〕.新青年,4(6).1918.6.
〔4〕胡适.答T·F·C《论译戏剧》〔J〕.新青年,1919.6(3).
〔5〕卢卡斯.易卜生的性格〔A〕.高中甫编.易卜生评论集〔M〕.崔思淦,译.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6〕鲁迅.坟·文化偏至论〔A〕.鲁迅全集(第1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A〕.鲁迅全集(第1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八〔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鲁迅.《奔流》编校记后三〔A〕.鲁迅全集(第7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鋗冰. 娜拉走后究竟怎样〔J〕. 国闻周报,11(11),1934.3.19.
〔11〕微明(茅盾).《娜拉》的纠纷〔J〕.漫画生活,1935(07),1935.3.20.
〔12〕娜拉大走鸿运〔J〕.申报,1935.6.21.(作者无考).
〔13〕陈咏芹.中国现代话剧的现实主义特征及其历史生成〔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14〕郭沫若.娜拉的答案〔J〕.重庆,新华日报,1942.7.19.
〔15〕(匈)卢卡奇.托尔斯泰与西欧文学〔A〕.见卢卡奇论文学文集(第2 卷)〔M〕.范之龙,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6〕易卜生.玩偶之家〔M〕.易卜生文集(第5 卷)〔M〕.潘家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17〕(挪威)艾尔瑟·赫斯特.娜拉〔A〕.高中甫译,高中甫编.易卜生评论集〔M〕.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18〕(德国)彼得·斯丛狄:《现代戏剧理论》〔M〕.王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9〕(英)J.L 斯泰恩.现代戏剧的理论与实践〔M〕.周诚,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
〔20〕李江、于闽梅.世界戏剧史话〔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
〔21〕(丹麦)勃兰兑斯.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M〕.林语堂,译.上海:春潮书局,1929.
〔22〕(美)劳逊.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M〕.邵牧君、齐宙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