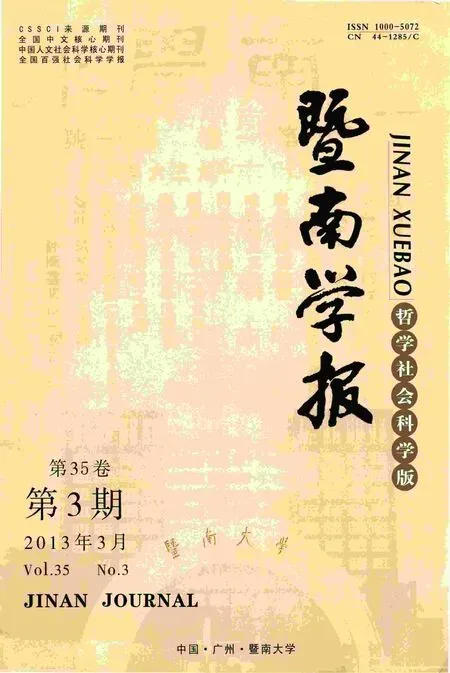行走的景观:宋元话本小说的空间意象
夏明宇
(上海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处,上海200444)
意象是中国古典诗歌本文构成的基本单位之一,这早已为学界所共识。但在叙事文学的研究当中,有关意象研究的论文论著却寥寥无几。近年来,叙事意象逐渐受到学界关注,如杨义在《中国叙事学·意象篇》中阐述道:“中国叙事文学是一种高文化浓度的文学,这种文化浓度不仅存在于它的结构、时间意识和视角形态之中,而且更具体而真切地容纳在它的意象之中。研究中国叙事文学必须把意象以及意象叙事方式作为基本命题之一,进行正面而深入的剖析,才能贴切地发现中国文学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神采之所在,重要特征之所在。”诚然,意象不仅只是诗歌的专利,它也是叙事文学作品必须正视的命题之一,在中国白话小说兴起之初的宋元话本小说中,就蕴含有大量的深具“文化浓度”的意象。
宋元话本小说主要关注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与绮丽梦想,叙述他们的悲欢离合与辗转辛苦,为了生计,很多市民常年奔走于江湖,因而,有关旅行的叙事主题犹能牵动普通市民的心肠。本文拟择取宋元话本小说中旅行者最为熟悉的桥、城门、旅店等空间意象,它们皆为“行走”途中常见的景观,并以之为例,来考察空间意象如何从宋元时代的日常生活进入小说叙事,进而分析它们在故事中的美学体现及其如何参与叙事建构的。
一、桥:空间连通与叙事衔接
宋元话本小说中的“桥”空间意象,主要出现在以两宋都城东京与杭州为背景的作品中,它们同时也是都市空间的组成部分之一。北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一》载录了当时东京的河道与桥梁盛况。河网繁密,桥梁道道,足见北宋都城水运交通一时之盛。南宋都城杭州地处江南水乡,城市更是水网密布,桥梁连绵,《梦梁录·卷七》详尽记述了杭州当时的河道及桥梁布局情况,“小河桥道”、“西河桥道”、“小西河桥道”、“倚郭城南桥道”、“倚郭城北桥道”等条就对杭州多种形态的桥道作了全景式描叙。史料载录可见杭州的桥道远比北宋都城东京为盛,尽显杭州作为江南水乡的地域特色。这些河道与桥道,不仅有江南地理风貌的真实记录,还是江南人生活生产、经商贸易等经济生活的重要交通媒介,同时,它们还是南方人,特别是都市人游赏把玩的去处。因此,宋元话本小说中频频出现桥梁的空间意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宋元话本小说中出现的桥名,属于北宋都城东京的有金梁桥、白虎桥、天津桥、天汉州桥等,属于南宋都城杭州的有众安桥、师姑桥、新桥、断桥等,其他地方城市的桥梁也偶有身影出现。以杭州为背景的小说,其中的桥梁远较东京为多,这是由江南特定地域环境中的城市水系所决定的。宋元话本小说就其所体现的地域特色来说,多具有江南气息,故事中多呈现出南方的水乡泽国与风土人情。话本小说的江南特质,已引起了相关学者的关注,李桂奎认为:“南宋以后,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话本小说在江南得以迅速兴起,并在明代走向全面成熟。生活在江南的话本小说家基本依据江南的地理特点、地质构造以及节日风俗等人文地理状况来构架小说时空;即使写到江北时空,也往往参照江南‘版本’进行。以‘游赏’为主题的江南节日,为话本小说故事的生发提供了带有地方人文色彩的叙事时间刻度。同时,江南水乡又为话本小说提供了别致的叙事空间。其中,作为故事的多发地带和情缘的多生场所,‘桥’、‘船’、‘岸’成为故事得以展开的基本场景。”话本文学作为江南文学,与话本小说所蕴涵的江南水乡文化密不可分,而桥梁等空间意象则是解读其内蕴的代码。宋元话本小说中的桥梁意象比比皆是,尤其是地标性的桥梁,总是出现在以两宋都城作为叙事空间的小说中,对于“行走”的市民来说,这些桥梁是他们忙碌生活的组成部分。如杭州的众安桥就在小说反复出现,《张生彩鸾灯传》中的落第秀才张舜美元宵观灯时艳遇刘素香,后却在众安桥跟踪失散了;《陈可常端阳仙化》中的陈可常三举不第,后在众安桥边算命先生的点拨下,毅然皈依灵隐寺。还有著名的西湖断桥,也先后在《西湖三塔记》、《错认尸》等作品中现身。类似桥梁甚多,此处不再例举。
宋元话本小说中为数众多的桥梁的涌现,不仅是由话本小说“江南文学”的地域特征所决定,同时也与桥梁本身所具有的美学功能有关。“桥梁的美学价值在于,它使分者相连,它将意图付诸实施,而且它已直观可见。在客观现实中,桥梁是联系两岸风光之依据,映入眼帘的桥梁同样是联系两岸风光之同一依据。”桥梁在空间中的本位功能乃是让对立、分离的两岸联系起来,由隔绝走向沟通。因此,桥梁在小说中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其表面价值在于,它将江河的两岸联系起来,跨越了地理环境之障碍,因为桥梁联系着两岸的码头,故江河两岸的桥下、桥边多为人烟繁茂之地,生意多、行人多、故事多,因而很多故事中多取“桥”作为叙事空间,如《一窟鬼癞道人除怪》中的吴洪科举落第、盘缠用尽、旅途困厄之际,只得在杭州“州桥下开一个小小学堂度日”,后得王婆牵线,在梅家桥下酒店里与女鬼李乐娘相亲,就此结成了一段人鬼夫妻。这里的场景空间有两个,其中的州桥是吴洪落魄时教书的地点,梅家桥是吴洪相亲的地点,两个“桥”皆位于交通便利之处,自然也是来往客流密集之所,故而招收学子、相亲碰面都较为便捷,叙述者选择两座桥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显现出桥所附属的经济社会功能对叙事的隐性干预。其深层价值在于,此种联系不仅便利了人世间的交通,它还连通了更深远更广阔的天地,跨越了人、鬼、神三界的空间区隔,如《张古老种瓜娶文女》中韦义方寻访的扬州开明桥,它就是连结人间与仙界的一座桥梁。故事讲述韦义方为了解救妹妹文女,追寻至仙界桃花庄,解救妹妹不成,自己却被逐出了仙界,回到人间后,方知天上数日,人间转眼二十年已经逝去。根据张古老的指引,义方来到扬州开明桥下,找到开生药铺的申公讨取十万贯钱。开明桥下空间实乃嵌入人间的一处仙境,申公和其年少的妻子皆为下凡的仙人,桥下店铺中的时间流逝如同仙界桃花庄一般缓慢,不同的是它与凡俗人间有着沟通交流。此处的开明桥其实就是一处仙人桥,它是人间与仙界相连通的神秘空间,不过凡俗的眼光难以辨识而已。《洛阳三怪记》中潘松进入与逃离妖界空间时所经过的独木桥,就是人间与妖界的连接符号,潘松被素不相识的婆婆骗入一座颓败的花园,误入妖界后险些丧命,后得助侥幸逃脱,“潘松慌忙奔走,出那花园门来,过了独木桥,寻原旧大路来,道:‘惭愧惭愧,却才这花园,不知是谁家的?那王春春是死了的人,却在这里。白日见鬼!’”此处的独木桥是繁华热闹的人世间与颓败恐怖的妖界空间的沟通媒介,巧妙实现了跨时空的叙事衔接。《西湖三塔记》中的断桥与此独木桥的功能类似,一样起到连接不同空间的作用。宋元时期的“三怪”故事同源异流,“同一故事的演说时空发生了改变时,说话人则入乡随俗,作一些因地制宜的改编”,即便故事时空发生较大变异,小说创作者们都自觉地选择了“桥”作为连通虚实空间的媒介,充分显示出“桥”所独具的空间叙事价值。
桥空间意象的介入,除了上述经济、美学等因素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创作者有意让它们来参与叙事的构建,进而形塑出小说中不可或缺的独特的叙事空间。《错认尸》中的新桥乃情节发展的转捩点,也是“错认尸”这出闹剧得以实现的叙事空间。商人乔俊家的佣工董小二,被周氏害死并沉尸于新桥河底。与此同时,程五娘的丈夫失踪日久,恰逢她路过新桥时,看到小二的浮尸漂于河面,错认为是丈夫尸体,便在河边痛哭。后在恶人的举报下,周氏谋杀小二事发,全家皆被拘捕入狱折磨致死。新桥在叙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聚焦矛盾的故事核功能,之前叙述乔俊买妾,嫖宿不归,小妾与女儿皆被雇工小二所奸,后高氏为掩饰家丑,将小二杀死,种种矛盾积聚已久,犹如火山不得不喷发,而新桥就恰如那地壳最薄弱处的火山口,此后叙事急转直下,以乔俊一家走向死亡而告终。《简帖和尚》中的天汉州桥也是促成故事情节发生转折的叙事空间。因恶和尚的挑拨陷害,恼羞成怒的皇甫殿直当庭将妻子休掉,小娘子羞愧难当有口难辩,正当她走上汴河上的天汉州桥时,“恰待要跳将下去,则见后面一个人把小娘子衣裳一捽捽住,回转头来看时,恰是一个婆婆”,正是在桥上,才有小娘子跳水的举动,也才引出了婆婆救人,进而催生出小娘子被劝嫁恶和尚的后续情节。天汉州桥介入叙事,扭转了故事发展的方向,并最终将叙事指向预定的目标。桥梁作为空间意象,深度参与了叙事空间的构成,成为故事情节发生发展的重要关节。
宋代都市中桥梁架设密集,于是在河流两岸便形成了热闹非凡的“桥头市”,它们自然也成为了故事中人物活动的连接空间。“如果唐代小说是‘无坊不传奇’的话,宋代小说可谓‘无桥不成书’!”桥梁在小说中的世俗价值,在于连接两岸、便利交通、促进商贸活动,它是日常生活中行人奔走的交通媒介,也是有情人偶遇、相聚、分手的场所。就其叙事功能而言,它为故事提供了敷衍情节的背景空间,增加了叙事偶然性的质素。“桥”连接着不同的空间领域,连接着不同的人、事、物,连接着不同的叙事环节。很多离奇的故事,往往只有在此空间场景才能发生、展开,各种叙事要素向着“桥”聚焦,各种矛盾冲突同时汇聚于此,进而情节突转,衔接转入新的叙事空间,最终实现了它参与叙事空间构建的功能。就其美学价值而言,桥衔接连通此岸与彼岸,不仅跨越地理障碍联系两岸风光,还实现了人、鬼、仙三界的交流互动,让各种滑稽的、断肠的、愉悦的情感在此倾泻呈现,使得小说叙事空间深情隽永。
二、城门:空间分隔与叙事离合
城门,作为都市城墙建筑结构的一部分,主要起到封闭、隔离、交通、疏散、防护的功能。“与城市中其它部分相比,城门的社会性往往容易被忽略,但实际上,它与城市流动与控制都有紧密联系。”从空间构成层面来看,城门是都市空间限制、分割、联通的关节点。两宋的史料笔记中对城门多有记载,《东京梦华录·卷一》“东都外城”、“旧京城”、“大内”诸条中,详赡地记录了东京城从外到内的三重城墙中的诸多城门,如南薰门、新郑门、新宋门、封丘门以及朱雀门、保康门、新门直至大内正门宣德楼等等,气象森严,等级俨然。相对而言,作为“行在”的南宋都城杭州,城墙的层次与城门的规模远不及北宋东京,《梦梁录·卷七》“杭州”条载录了东、南、西、北诸城门的概况以及城中的几个城门,特别介绍了“旱门仅十有三,水门者五”的江南特色。这些城门犹如都城的咽喉,来来往往的行人皆要由此路过,它是市民们外出旅行、经商、求学时的必经之地,又因为城门的开闭时间相对固定,因而,对于旅行者来说,城门就是一个时空分隔的要塞,是进城或者出城的分割符号。
与百姓生活如此密切相关的城门,必定是故事多发的空间地带,也自然地进入了小说家的创作视野。宋元话本小说中的城门意象频频出现,是两宋都城市民日常生活状态的映射。如《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的暗娼金奴被吴山的邻居驱走之后,因寂寞难耐,就央八老前去求吴山过来,“金奴道:‘可着八老去灰桥市上铺中探望他。’当时八老去,就出艮山门到灰桥市上丝铺里见主管。……八老提了盒子,怀中揣着简帖,出门径往大街,走出武林门,直到新桥市上。……吴山不听,上轿预先分付轿夫,径进艮山门。迤逦到羊毛寨南横桥,寻问湖市搬来韩家。”八老和吴山先后出入艮山门与武林门,这二座城门皆位于杭州城东北,是出入城市的必经之地,作为百姓日常生活中“日用而不知”的交通要道,它们在小说叙事中如同寻常巷陌一般自然亲和,化作进城与出城的一个空间符号。诸如此类的带有地标性质的城门,在宋元话本小说中尚有许多,本文对这些只作为空间标示的城门不予讨论,而主要论述那些既具有空间标识意义又对小说叙事起着建构功能的城门。
随着两宋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时空拘束的唐代坊市制,远远不能适应现实需求,街市制度终于北宋时期应时而生了。在北宋的东京,店铺、酒楼、妓馆等商业活动场所与民居、官署、寺庙交错,而且通宵营业的夜市也成了汴京的特色,如朱雀门外大街妓馆云集,“街心市井,至夜尤盛”,州桥夜市以各类小吃闻名,“车马阗拥,不可驻足”。到宋神宗时,街市制完全取代了坊市制,“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宋代街市制虽已建立,但是城门禁闭制度并没有废止,话本小说中对此多有记载,同时也叙述了因城门的关闭而引发出许多意料不到的故事。《任孝子烈性为神》中老实巴交的任珪在听闻妻子红杏出墙的传言后,痛苦不堪但又苦于没有证据,碰巧某天因夜深城门关闭,任珪无法赶回候潮门外的家,“任珪道:‘便是出城得晚,关了城门。欲去张员外家歇,又夜深了,因此来这里歇一夜。’”不得已只得到岳父家借宿,谁知当夜妻子圣金与老情人周得正在岳父家中偷欢,为防止奸情败露,他们趁黑贼喊捉贼地将任珪乱打了一顿。任珪气急败坏,“开了大门,拽上了,趁星光之下,直望候潮门来。却忒早了些,城门未开。城边无数经纪行贩,挑着盐担,坐在门下等开门。也有唱曲儿的,也有说闲话的,也有做小买卖的。任珪混在人丛中,坐下纳闷。”任珪气头中打算当夜返家,无奈城门依旧关闭,只得与众商贩在一起等候城门开放,让他料想不到的是,这帮闲来无事的商贩们竟然拿他的窝囊事谈笑取乐。任珪怒不可遏,回家的念头迅疾取消了,复仇计划在心中燃烧,“当时任珪却好听得备细,城门正开,一齐出城,各分路去了。此时任珪不出城,复身来到张员外家里来,取了三五钱银子,到铁铺里买了一柄解腕尖刀,和鞘插在腰间。”待到城门开放的时候,任珪却折回了张员外家,取了银子去买了尖刀,从此踏上复仇之旅。正是城门对任珪行程的两次阻断,让他身不由己地来到岳父家而被打,后又意外地走进了商贩群中并听到了各色流言蜚语。一夜之间连续两次的身心羞辱,让任珪的怒火瞬间达到了燃点,复仇的烈焰终于熊熊燃烧起来。
城门的开闭导致都市内外空间的流通与隔断,人物行动也因之而顺畅或受阻,各种悲欢离合的人间故事就此发生,城门也就成了小说叙事的重要转捩点。法国叙事学家格雷马斯在分析民间故事结构类型时,认为民间故事具有三种结构形态,即契约型组合、完成型组合、离合型组合。“所谓离合型组合,包括人际间的聚散邂逅迁徙流离,相会相失等等。许多言情小说都属此类。”话本小说中的城门意象,多发挥着离合叙事的功能,在城门关闭与开放的过程中,往往意外丛生,许多故事由此而改变了情节方向,种种聚散离合的人间故事随之发生。宋元话本小说中,因城门关闭的时空分隔而造成的离合叙事最为激荡人心。前述《任孝子烈性为神》亦属此类,因为城门关闭而导致意外发生,矛盾激化的同时推进了叙事进展。《张生彩鸾灯传》中因城门关闭而引发的离合故事一样动人心魄。故事讲述落第书生张舜美元宵灯夜与少女刘素香一见钟情,偷尝禁果后,二人密约私奔出城。“是夜,女子收拾了一帕子金珠,也装做一个男儿打扮,与舜美携手迤逦而行。将及二鼓,才方行到北关门下。……且又城中人要出城,城外人要入城,两下不免撒手,前后随行。出得第二重门,被人一涌,各不相顾,那女子径出城门,从半塘洪去了。舜美虑他是个妇女,身体柔弱,挨挤不出去,还在城里也不见得。急回身寻问把门军士,军士说道:‘适才有个少年秀士寻问同辈,回未半里多地。’舜美自思:一条路往钱唐门,一条路往师姑桥,一条路往褚家堂,三四条叉路,往那一路好?踌躇半晌,只得依旧路赶去,至十官子巷,那女子家中,门已闭了,悄无人声,急急回至北关门,门又关了。整整寻了一夜,巴到天明,挨门而出。至新码头,见一伙人围得紧紧的,看一只绣鞋儿,舜美认得是女子脱下之鞋,不敢开声。”私奔当夜,素香女扮男妆,穿着男人的衣服及宽大的男鞋,行动极其不便,加之出城时情绪紧张,故而在汹涌的人流中二人瞬间失散。舜美在慌乱中四处寻找素香,从北关门折回十官子巷,待再返回北关门时城门已经关闭,舜美只能在北关门内熬到天亮等候城门开放。待到天明出城之后,舜美发现了一只溺死女子的绣鞋,自以为素香已落水而死,惶恐不已。这段出城故事波澜丛生,寂然无声的城门如同一只无形的巨手,不动声色地将这对有情人分隔在城门的两侧,让他们在城门开放与关闭的瞬间突然失去了音信,本该顺向发展的私奔叙事至此戛然中断。
由城门分隔而造成的离合叙事,是古代小说创作者所惯用的手段。朱玉麒认为,“中国城市的城墙分隔了居民的活动空间,使得城门口相失相遇引发小说情节的曲折离奇成为唐宋小说共同的特征。”这种离合叙事范型,实乃小说家欲擒故纵的叙事技法,为了达到一波三折的叙事效果,他们往往有意让叙事不圆融完满,从而增加了故事的离奇性。这与中国传统诗学中,门的时空意象素来与感伤的美学传统相契合的审美心理相一致。齐美尔认为“门在屋内空间与外界空间之间架起了一层活动挡板,维持着内部和外界的分离。正因为门可以打开,跟不能活动的墙相比,关闭门户给人以更强烈的封闭感,似乎跟外界的一切都隔开了。”如果说桥天然地具有连通之功能,那么城门就具有隔断的功能,在城门关闭之际,小说叙事朝此聚焦,陡增了叙事冲突的偶然性,使得叙事张力弥满。城门开闭的时间规定性,为叙事离合创造了契机,让矛盾冲突显得妥溜自然,大大增添了小说叙事的艺术质感。
不仅如此,城门在小说叙事中的空间设置,还得益于传统诗学的沾溉使然。在古典诗人笔下,“门的诗性意味是指向家园的”,“门在象征层次里把人类生存空间划分成家园与世界两个部分,人们漂泊于世界之中却无时无刻不向往家园。”话本小说的创作者书会才人们,“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他们自幼饱读诗书,积淀了深厚的诗歌素养,他们在创作故事时自然会融汇吸收古典诗歌的神韵,而门的诗性意味也必然会融入叙事之中。宋元话本小说中的城门空间意象所引发出的离合叙事,蕴含着小说创作者们有家难返的深重乡愁。叙事中的城门景观,隐匿着无数历经曲折的旅行者内心深处的情感召唤。被分隔在城门两侧的旅行者,期待穿越时空阻碍早日返回家园,这何尝不是落魄的书会才人们的心灵写照呢?因此,城门意象参与离合叙事,不仅为故事进程布设了重重障碍,它还接续了传统文化的诗性血脉,提升了小说叙事的文化品位,成为小说创作者的自觉选择。
三、旅店:空间栖止与叙事转折
宋元时代商业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大批商人奔波逐利,科举取士连年扩招诱惑天下才俊奔竟功名,战乱频仍生灵涂炭迫使百姓辗转迁徙。众多流动人口的激增,必然推动了宋元时代旅店业的快速发展,“旅舍的业务扩展与‘邸店’的活跃息息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时各城市之间流动着大量的赶考举人、调选官吏、南北行商、各国商胡等流动人口,为了解决他们的食宿和适应其经商需要,旅店业才迅速发展起来。”人在旅途,必然需求大量的旅店来安顿歇宿。不同于桥跨越河道的空间连接功能,也不同于城门的空间分隔功能,旅店是旅行者在旅途劳顿时的栖止空间,这些临时性的寄宿空间,成为了旅途中的一大景观,同时它也是小说故事中极富特色与韵味的叙事空间。
现存的史料笔记中,对于两宋都城中的旅店情况记述颇丰,大抵见出当时的旅店业繁盛之一斑。《东京梦华录·卷三》中对北宋都城东京的旅店记述云,“街西保康门瓦子,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於此安泊”(大内前州桥东街巷)、“自景灵宫东门大街向东,街北旧乾明寺,沿火改作五寺三监。以东向南曰第三条甜水巷,以东熙熙楼客店,都下着数”(寺东门街巷)。从摘引的诸条笔记,大致能够看出北宋东京旅店业的空间布局状貌。与东京相比,南宋都城杭州的旅店业更为兴盛,不仅有官办的旅店,还有很多私人经营的旅店也应运而生。《武林旧事·元夕》载杭州“三桥等处,客邸最盛,舞者往来最多。”《梦梁录·塌房》专门记录了杭州旅店业之发达,“有慈元殿及富豪内侍诸司等人家于水次起造塌房数十所,为屋数千间,专以假赁与市郭间铺席宅舍、及客旅寄藏物货,并动具等物,四面皆水,不惟可避风烛,亦可免偷盗,极为利便。”可见当时已有专门用于租赁的房舍,其中部分即为旅客寄宿的旅店,当时其他地方城市亦有此种旅店。从现存的史料来看,旅店业在两宋时期非常发达,这为旅行者的往返流动提供了方便,宋元话本小说中的旅店意象正是这一生活现实的投射。
作为旅途中不可或缺的驿站,旅店是构成旅行空间的核心元素之一,它是旅行者漫漫苦旅中温暖的栖止港湾。因此,无论是士子、商人,还是赴任官员、逃难流民,纷纷以旅店为落脚休整的临时家园。《赵伯升茶肆遇仁宗》中的赵旭离家赴京,孤身寄宿状元坊,待到考试落榜时,曾经给人带来无限希望的状元坊刹那间变得冷清孤独,这是落榜者孤苦心境的映射。北宋词人秦观“可堪孤馆闭春寒”的叹息,可谓当时天涯流落人的共同心声。“与叙述者视角相比,采用人物视角的空间描写常常倾向于展现人物心理活动。更多的情形是,以人物视角展现的空间,既是人物所处的真实空间,同时又是人物心理活动的投射。环境与心境相互映照。”不错,旅店景观因为叙事视角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旅店空间投射了旅行者当下的心理活动。赵旭栖身的旅店只是提供了叙事的背景,旅店空间基本没有参与叙事活动,但是因为举子的独特心理认知,而让此类空间著上一层凄清孤独的色彩。位于都市里的旅店,既有如举子们寄居的状元坊那样相对平静的安逸空间,也有一些风波不止的邪恶空间。如《计押番金鳗产祸》中的镇江旅店,即为一处危机潜伏的叙事空间,故事讲述张彬和庆奴在害死佛郎后逃至镇江,碰巧庆奴在酒店赶趁卖唱之际,遇到了杀死其父母而流窜至此的前夫周三,三个凄凉孤独又身负罪孽的年轻人在镇江旅店碰头了。此处的旅店空间,不仅只是作为叙事背景出现在故事中,它也参与了故事的情节发展,正是镇江的旅店空间让三人聚拢到了一起,进而推动了小说叙事的突进。
都市里的旅店空间,因其处于文明的中心,故多能维系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即使如《计押番金鳗产祸》中的镇江旅店,虽然牵涉到生死官司,但因那里没有强盗横行、肆意打杀的恐怖场景,相较于荒蛮旅途中的旅店而言,倒显得分外宁静。对于那些行走于荒蛮之地的旅客而言,途中的旅店不只是他们容身的避风港,往往还是事故频发、风烟四起的危机空间。此类旅店空间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景,同时还参与叙事,是故事生成必不可少的环节。《小水湾天狐诒书》中的王臣从江南返归故乡长安,于城外旅店借宿,谁知白日被王臣用弹弓射打的狐精化作人形,来旅店讨要被王臣捡拾的书本,双方就此发生争执,并埋下了王臣日后家业凋零的种子,故事中的旅店不仅呈现出乱世的时局景象,而且参与了叙事进程,夜半狐精敲打门窗索要书本的呼叫,店中旅客的凄惶心态,人妖杂处的世相,隐喻着乱世中人妖难分、群魔乱舞的世态炎凉以及旅行者凄惶无助的生存状态。《皂角林大王假形》中的知县赵再理在新会县任职时,因烧了皂角林大王庙,而受到了皂角林大王的恶意报复。在赵知县三年任满归途之中,皂角林大王假扮赵再理,在赵知县路过峰头驿旅店歇宿当夜,掳走了他的衣服箱笼以及随从人员,并提前返回东京,霸占了赵知县的妻子与家园。峰头驿旅店空间的设置,令叙事节外生枝,并改变了故事的行进方向,使故事朝向悲情复杂的方面发展。旅途中的旅店,既是旅客歇宿的栖止空间,同时也是叙事转向的驿站。类似情形在《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杨温拦路虎传》等小说中也一再出现。此类旅店多位于荒蛮的旅行途中,恶人抓住旅客旅途劳苦、急于修养调整的心理,埋伏在旅店周围,伺机实施阴谋勾当。这些危机四伏的旅店,让旅行者往往横遭匪祸,叙事进程也随之转折,从而牵引出更多新生的情节出来。因此,旅店空间多为故事情节的新变而设置的,从而将故事过渡到新的叙事时空之中。
除了这些公私经营的旅店之外,宋元话本小说中尚有寺庙与妓院等特殊的空间场所,对于部分旅客来说,它们也起到了旅店的寄宿功能。如《张生彩鸾灯传》中的镇江大慈庵,就是素香最温情的旅店空间。在素香与舜美私奔当夜失散后,她幸得大慈庵老尼的善待与庇佑,得以保全了性命,三年后,舜美赴京应试,因故偶然造访大慈庵,在此与素香重逢,破镜重圆。寺庙空间因其具有超越凡俗的社会属性,而与世俗的旅店大异其趣,它逐渐流变为古典文学作品中才子佳人们期盼艳遇的叙事空间,如《西厢记》中的普救寺即为张生与莺莺的艳遇空间。此外,妓院因其为旅客提供了歇宿之便,也兼具旅店的部分功能,不同于寺庙空间的艳遇浪漫,妓院空间的叙事终点是贪色者挥霍享受后的走投无路。《错认尸》中的商人乔俊置家中大妻小妾不顾,羁留东京上厅行首沈瑞莲家达两年之久,期间,家中妻儿老小全部死于狱中他也浑然不知,直到两手空空返回杭州,走投无路而被迫投水自尽,唐传奇《李娃传》中的贪色者荥阳公子的遭遇与其何其相似。不同于普通旅客只是把旅店当做旅途中休憩的临时驿站,旅店中多弥漫着乡愁之痛与漂泊之苦,妓院青楼等淫乐空间却让寄居的旅客乐不思蜀,他们迷失了旅行的目标而只能等候灾厄的降临。
宋元话本小说旅店空间意象的独特内涵,同时也与旅店本身所具有的美学品质分不开。旅店多为旅行者临时性的寄居所在,因此,对于旅客来说,旅店本身即内涵有动荡不安的流动性,正是这种心理感受的不安定感,导致旅行者寄居旅店时的心态是紧张不安的、焦虑的,尤其是在郊野的旅店中,这种不安全感更为深重。但是旅行者多为有着特定目的而离家远行,在没有到达目的地、完成旅行目标之前,他们是不会轻易折返故乡的,因而,对旅店心存不安,但又不得不寄居于此,只能期待早日离开旅店,完满返乡。在这种心理暗示的支配之下,发生在旅店中的故事多紧张压抑、阴郁愁苦,正因此种美学内涵,决定了发生在旅店中的故事,在叙事之初就已注定了未来的大致结局,故而在旅店空间叙事中,思乡成病、不得归去,旅况艰险、横遭匪祸等叙事模式也就应运而生了。旅店空间不仅是旅行者寄居他乡的临时港湾,也让他们体验出有家难返的别离酸楚与人在江湖旦夕祸福的焦灼孤独。旅店所特有的充满流动感的叙事空间,在叙事中多起到情节聚焦之功能,直到旅行者离开旅店,叙事空间切换完毕,这种动荡漂泊感才稍稍释放。而由旅店所引发的种种事端,往往又会牵引、延伸至新的叙事空间。
宋元话本小说中的旅店空间,因地处都市或郊野等环境的差异,而导致了故事发展方向的迥异。都市中的旅店叙事多平静从容,郊野中的旅店叙事则多险象环生,意外频发。这与唐传奇中的旅店空间所呈现出的温情浪漫的精神气质有着较大差异,其中一个因由就在于创作者身份的不同。唐传奇的作者多为风流倜傥的秀才或举人,他们多以小说创作作为彰显才华博取功名的途径,故每能思致缠绵激扬文字,他们还通过隐含作者来驱遣小说主人公,代为传达自己的风流意绪。而宋元话本小说的创作者多为穷苦潦倒流落江湖的下层文士,他们对现实生活充满了担忧与恐惧,其笔下的旅店空间叙事有着自己苦难生涯的倒影,融入了他们凄冷无助、动荡漂泊的人生体验,正如王国维所谓的“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故而宋元话本小说中的旅店空间意象又是指向话本小说主人公心灵世界的生动路标,体现出话本小说“为市井细民写心”的创作旨趣。
宋元话本小说中与旅行相关的空间意象还有很多,本文只着意于旅行途中与行走、栖止紧密相关的桥、城门、旅店等空间意象,并以此为例,来论析空间意象介入小说叙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任何意象的存在都有一定的空间形式。把意象放置于何种时空坐标上,体现着某个诗人的特定心态,也反映着一个民族特定的情感模式和审美模式。”不错,中国古代诗歌创作非常讲究意象的营造,同样地,宋元话本小说中也存在大量的具有“空间形式”的意象,空间意象经过长久的民族审美心理的积淀后,其内涵的美学特质自然也会迁移到小说作品中来,从而参与并影响了小说叙事及审美价值的生成。这种价值实现是与小说创作者——书会才人的奉献分不开的,王水照认为“宋代文学的创作主体是宋代士人,他们不仅是传统雅文学(诗、词、文)的主要作者,也是新兴俗文学(戏曲、白话小说)的重要参与者。”宋元话本小说是在借鉴、吸收、仿拟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创作者“士人”——书会才人们,乃是宋代文化下移的先锋,他们曾经醉心科举饱读诗书,长期浸淫于雅文学与雅文化之中,但却因命运不济而沉沦下僚,不得不以布衣身份流落江湖,在进入俗文学的创作场域时,他们深蕴的文化素养必然会沾溉新生的叙事艺术,让通俗叙事的空间意象载负着传统高雅文化的基因,从而使得古典小说的诗性叙事成为可能,并最终推动了中国叙事文学从幼稚走向成熟。
[1]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4]李桂奎.话本小说时空构架的“江南”特征及其叙事意义[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5](德)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M].周涯鸿,陆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
[6]纪德君.从《洛阳三怪记》到《西湖三塔记》——“三怪”故事的变迁及其启示[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7]朱玉麒.唐宋都城小说的地理空间变迁[C]∥荣新江.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王静.城门与都市——以唐长安通化门为主[C]∥荣新江.唐研究(第1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9]宋敏求.春明退朝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罗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11]傅道彬.晚唐钟声——中国文化的原型批评[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2]罗烨,编.周晓薇,校点.新编醉翁谈录[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3]林立平.唐宋之际城市旅店业初探[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2).
[14]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5]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6]王水照.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J].文学遗产,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