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炳良散文小辑
唐炳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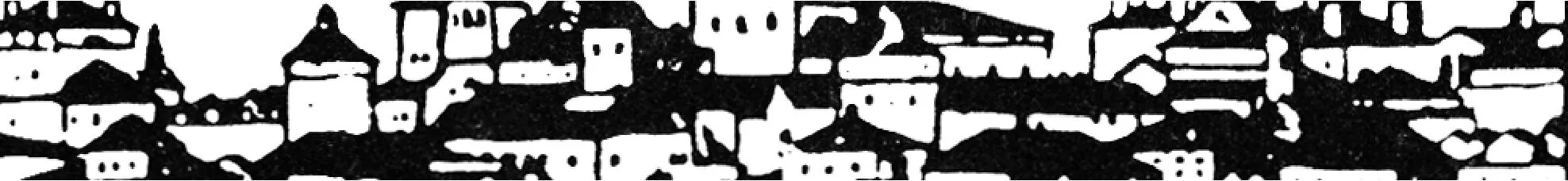
东宫之夜
至今不能忘记,我宿于东宫的那些夜晚。
长长、长长的夜,长长、长长的静。静到这静仿佛不是今天的,是过去的;静到这静即或是今天的,我却仿佛不是今天的人。日光灯仍亮着,我也便要睡了,仍望着屋顶,那青蓝与朱红的绘制,叫做雕梁画栋,决然不是今天的,我却只能是今天的人。
恍如隔世,已然隔世,但还可以识得,东宫的今生与前世。时维公元一九八四年冬,我从乡下上来当一名编辑,一上来就住进“宫”里,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这南京中山东路三百一十三号,俗称“东宫”的这座仿古大屋顶宫殿式建筑,其时是省作家协会的驻地。这里本是南京军区档案馆,被作协租用后,档案馆也还在,收缩到了一楼,故门口依然有士兵放哨。所谓“东宫”也者,以其西侧另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俗称“西宫”,——南京人习惯上是这么区分它们的。
这东宫、西宫,可不是第六代导演张元拍摄的《东宫西宫》呵。他那电影里的同性恋内容,关我们的东宫西宫屁事。
东宫的正面,左右对称,各有石砌的台阶可上二楼。但由于作协也租用了一楼部分面积,为便于上下,也节省空间,作协启用的是背面的台阶。从那里上楼,马上见到一个个“格子”,“格子”里是作协所属各部门,而走廊仍宽余;可见“大屋顶”之大。白天,大屋顶里是很热闹的。
到了傍晚,同事都回家了,大屋顶内骤然一静。我每每下楼,绕着大屋顶转一个圈儿,又转一个圈儿。东宫占地甚富,庭院深深,古柏苍翠。李璟(南唐前主)词:“玉砌花光锦绣明,朱扉长日镇长扃。”可是不对,我们早已把它打开了呀。走到东南墙角处看看,有一块大理石奠基碑,上面刻着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题写,计三十七字的篆文:“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华民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奠基纪念 吴敬恒谨篆”(稚晖是他的字)。我第一次见到这块奠基碑时,心头一惊,这吴稚晖,可是我家乡武进人呀。
还有人告诉我,我白天上班、晚上睡的这间屋子(二楼东首朝南一间),千真万确,就是当年民国政府监察院院长、大书法家于佑任的办公室。
我因而恍兮惚兮,我仿佛夜夜都住在“民国”。
嘁,这都是“前朝之事”了,我何不统忘却了它;我只须有眼前这间屋子,我便可以愉快地工作与生活。但我依然惶惑于东宫的静,即或“夜深人不静”之时,“宫”里还是静。令人难以置信,喧扰的中山东路就在百米之外,一夜间驶过的车辆正不知凡几,而东宫仍能静。东宫之“静”于我,犹之乎一种声音,有分贝,我能“听”到;“分贝”之外的汽车引擎声,车轮滚动声,人的喧哗声,仿佛没有分贝,我总也听不到。则东宫之静,又类乎一个“场”,我之受制于它,是因为我“在场”。
“静”的分贝里,俄尔会爆出哈哈的笑声,便是吴稚晖在笑了。这个吴稚晖,真是太爱笑、也太能笑了,为了随时随地、无拘无束地笑,可以一生不入官门。一九四三年,蒋介石邀他出任民国政府主席,被他推辞,理由是:“我见到什么都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万一我接见外国使节时,也不由自主地笑起来,这可怎么办呀?”蒋也拿他没奈何。是啊,笑也是他的权利啊。
极细微的声响,有点像于佑任在研墨,抑或在书案上铺展宣纸。我猜想他存世的诗文与书法,有一部分是在这间办公室完成。一九八四年,陕西那个叫曾卓(其父当年是于佑任的卫士)的人,为一批于佑任的书法,与政协的纠纷案还没有发生。如果当时有这件事,我也许会听见于佑任说:“吵什么呢?不都是我写废的纸么?——捡就捡了,吵什么呢?”
这便是一九八四年的冬天,我的倾听的东宫之夜。
到了翌年春天,我的东宫之夜不再孤单,苏童也住到办公室来了。我俩都是《钟山》的编辑。我喜杂七杂八乱说,苏童也愿意听,正好挣脱了东宫堆积的静。故我尝言之,“下榻”东宫,宜作竟夜谈。
这年秋天,不知是谁,通过什么办法,给编辑部的人一人弄来一只小收录机。有一盘磁带,不知是汤国弄来的,还是綦立吾弄来的,大家如获至宝,很快每人翻录一盘。一到晚上,我和苏童就打开收录机,放那盘磁带,主要是听其中的一首摇滚,崔健的《一无所有》;直白的歌词,有别于“诗文”,也绝不“斯文”,听来那么高亢激荡: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
我们似乎很快乐了;但也分明感到,一个过程还没结束,另一个过程又开始了。
青衣
青衣二字,使人想起“青花”,明清官窑器的莹澈富丽,和民窑器的蒙翳华滋。使人想起“青丝”,所谓“三千烦恼丝”,“朝如青丝暮成雪”。使人想起“青灯”,遁入空门后的枯寂岁月,黄卷青灯里的晨钟暮鼓。使人想起“青鸟”,李义山笔下的青鸟信使,“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这只是我的不着边际的联想,然而,青衣的莲步轻移与水袖飘洒之间,淹然百媚或者长日幽怨,未见得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青衣的“青”,或许来自于“青素褶子”,一种色彩比较素雅的褶子。青衣虽也有穿女蟒或宫衣的,但在多数剧目中,是穿色彩素雅的褶子。
青衣最通俗的解释,是“良家妇女”;知廉耻,有道德,稳重安详。所以,她说起话来,永远是慢吞吞的韵白(不同于花旦的京白),举手投足,可不像现在的姑娘,利索得很,那是有一套程序的。青衣要开口唱了,先把袖子放下去(袖管荡一荡),长长的水袖,足足拖到地;再撩起来,手腕抖几抖,露出手指(兰花指!有一百种以上不同的兰花指),一肚子幽怨,二黄慢板;可是你别急,她那声“叫头”,有得拖,声音由徐而疾,由微而著,像一道声音的抛物线,高到云里去,再缓慢落下来,落到地上,足足耗时半分钟。然后,板鼓响了,京胡拉起来了。
有人看么?那么严肃,慢性子,还节外生枝的女人。
青衣的规矩真大,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天天见面的夫君,见面也要礼让一番。青衣的青素褶子,只表明她身居闾巷人家,青素褶子本身,仍然好看。青衣的容貌,却是夸不得的,就算她的夫君夸她,她也会立刻羞红了脸,用水袖挡起半边脸(所以,青衣的水袖必须长而又长)。青衣要出门了,衣袂飘飘,去陌上采桑,或溪边浣纱(篮里装着饭与馍)。倘若这时有个打道的军爷问路,要连问三遍,她才用慢吞吞的韵白答道,敢是问我么?倘若这军爷竟起了不良意,故意拿话挑逗她,她便马上正色道,放老成些!因为,大凡青衣,一定也是烈女。
(另一个青衣遇到的是腹中正饥的伍子胥。伍子胥欲往吴国借兵,讨伐无道的楚平王,这青衣便将篮里的饭与馍赠予他吃了。虽然她知道伍子胥是个大大的好人,但仍要求他赶快离开,因为“男女交言是非多”。)
青衣,一如她穿的青素褶子,总而言之有点“苦”(要不怎么还有个名字,叫“苦条子旦角”呢)。怨妇,思妇,要不苦守寒窑十八年。倘若她是个夜夜织布的怨妇,那么必定还有一件比织布更让她焦心的事,她是织几梭子布,就思想一番,托、托!更鼓一声声传来,她从二更一直唱到四更。倘若她是个思妇,则她的所“思”,多半也难有结局,“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你就听张火丁唱吧!“去时陌上花如锦,今日楼头柳又青。可怜侬在深闺等,海棠开日我想到如今。门环偶响疑投信,市语微哗虑变生。因何一去无音信,不管我家中断肠的人!”是啊,这苦日子何时才是个尽头啊!
也有终于熬出头的,薛平贵十八年征战,修成正果,马上要坐金銮殿,王宝钏的好日子到了。可是你看发生在武家坡的一幕,薛平贵竟欺她认不出自己,在武家坡百般调戏她,以验证她这十八年里是否“贞节”。呔,天下有这个理么?
苦条子旦角,是指舞台上,青衣的唱工相当繁重,是苦上加“苦”。
(童年鲁迅和阿发、双喜他们几个,一见到旦角要开口唱了,马上叹气!他们都担心那旦角会一直唱下去,伊伊呀呀,唱到天亮还唱不完。他们是喜欢一个长胡子的背上插着四张旗的“铁头老生”,捏一杆长枪,能连翻八十四个跟斗。)
青衣的“苦日子”里,仿佛埋藏着一座金矿,不仅女演员长年开采它,连七尺男儿也多有属意。梅兰芳年轻时,面貌、身材不要太好;程砚秋可是一米八几的大汉,也能演女人么?建国后拍舞台艺术片《荒山泪》时,程砚秋本人已无信心,不仅高,而且胖,比大汉还要大汉,登不得台了。最后,还是周总理出马,亲自动员,他才答应一试。拍摄时,凡舞台上用到的道具,都放大了尺寸,以尽量显得和“人物”协调。
有人看么?那么大个子的女人,实际还是个大个子男人。
你可以去问问,全中国有多少人不知道“程派”。
艺术是一个原因,艺术之外,还有观赏者自身。
斑马的头、颈、身躯、大腿、小腿,各有十一条花纹,这就是生物学全息(全息码),反映着部分与整体,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全息对称性关系。青衣的青素褶子,也是那“十一条花纹”,反映着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全息对称性关系。人类的伦理和道德,犹如你出门时带的那条狗,有时落在你后头,有时跑在你前头,跑得远了,它会回头看一看你,等一等你。
我想说,我们也是那条回头看的狗啊!
作家班轶事
作家班开学,是在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段宜于相逢的日子里。有一天上完课,几个女同学回宿舍去,走到学校的大操场上。
球场上有人在打篮球(半场)。又是他们,几个年龄比本科生大,再大一点也无妨,小一点却嫌嫩的在读研究生。郑同学入神地看了一会儿,突然说:
“真想抢一个带回家!”
另一个女同学对她侧目而视。
作家班的学员,年龄跨度很大,女学员中年龄最大的和最小的,足可以当母女。郑同学年龄偏小,虽然也做了母亲了,但仍掩不住一脸青春气息。她是写儿童文学的,儿童小说已多次获奖,有一件还得了全国奖。
上课的时候,总共三十八个同学,本可以坐得很宽余的,但总有一个人口密集区,以郑同学为中心,今天在教室的左侧,明天在教室的右侧。我记得这一年过了国庆节之后,天气仍很炎热,男士们不依不饶的架势,把她箍得紧紧的,郑同学不停地擦汗,已多次表示不满,但仍无法改变这一现实。
有一天,几个人走到学校的生活区,一位男士请客,请大家一人喝一瓶酸奶。这年的酸奶是一瓶三毛五分钱。一共七个人,请客的男士扫了一眼,以为是八个人,买了八瓶酸奶。多出一瓶之后,也不退了,请客的男士看一眼郑同学,说:“小郑你多喝一瓶吧。”郑同学迟疑了一下,接过了酸奶,但她说:“你已经请过客了,这一瓶该付你钱。”摸出三毛五分钱,给请客的男士。这位男士大约想挡,但一时想不出合适的话,收下了。郑同学将吸管插入第二瓶酸奶,刚喝了一口,又有一位男士来了,她马上举起手里的酸奶问:“喝不喝?三毛五分钱。”后到的男士说:“喝。”接过酸奶,摸出三毛五分钱,给郑同学。郑同学把钱往口袋里装时,脸红了,她说:“我已经喝过一口了,这一瓶不值三毛五了。”取出一枚五分硬币,不等对方反应过来,塞给了他。
我不是七个人中的一个,也不是后来喝实际价值为三毛钱的酸奶的那个,这件事我是听七个人中有位也写儿童文学的女士说的。这位女士说:“丢不丢人?——精不精?喝过了还卖钱,喝的那口,算出来值五分钱。”我点头。
明白了,纯粹意义的儿童文学,也不是人人能写的。
美国派
据说,美国阿波罗号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除了那句著名的话——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之外,在返回登陆舱的时候,还说了另一句话。而对这句话,阿姆斯特朗在长达二十六年的时间里,却不作任何解释,无论各路记者如何追问,阿姆斯特朗就是不说——不愿作出解释。
阿姆斯特朗说的这句话是:
“戈斯基先生,祝你好运。”
谁也不知道戈斯基先生是谁,以及戈斯基先生住在哪里。人们只能猜测,这句话对戈斯基先生来说可能相当重要,否则阿姆斯特朗不会特地到了月球上才说。当然,至少有两个人知道这句话的含义,一个是阿姆斯特朗本人,还有一个就是戈基斯先生。戈斯基先生不可能不看任何一份报纸,记者已就此事作了广泛的报道,阿姆斯特朗说的这句话,被登在了全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
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是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直到过了整整二十六年,一九九五年七月五日,佛罗里达州的一个记者又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次阿姆斯特朗终于开口了,他觉得他应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因为,戈斯基先生已于不久前去世。换言之,阿姆斯特朗要解释的内容,涉及到戈斯基先生的隐私。
阿姆斯特朗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喜欢玩棒球。有一天,他和朋友在院子里玩棒球,他的朋友把棒球打到了邻居戈斯基夫妇的窗户下面,阿姆斯特朗跑去拣球的时候,听见戈斯基夫妇正在吵架。原来,戈斯基太太因为无法接受丈夫的个性,早已与他分床而眠,虽然戈斯基先生心有不甘,仍隔三差五地去骚扰她,但每次都遭到戈斯基太太的愤怒的拒绝。只听戈斯基太太大声嚷嚷着:“你想跟我上床?除非有一天,邻居家那个小屁孩登上月球!”
“戈斯基先生,祝你好运。”
我们必需明白,戈斯基太太在二十六年前也已闻听此言(她是知道这句话的含义的第三人),就算戈斯基太太从不看新闻,但戈斯基先生不会懒得连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的事也不告诉她吧?
美国佬也爱创作段子,创作的段子也带“色”。但细想想,美国佬创作的这个段子,似乎比咱们国产的段子少了点什么,又多了点什么。
少的是猥琐、狎昵;多的是崇闳、开阔。
麦田守望者
没有风。
稻草人在一夜之间遍布田野,远远近近,疏疏密密,令人想起“撒豆成兵”的典故。麦子快要成熟了,是稻草人登场亮相,忠实地履行职责的时候了。麻雀集结在林间鸣叫着,或者试探性地飞过麦田上空,看看稻草人敌人有什么动静。啾,啾,所有的麻雀都不那么乐观,估不透这个麦季对它们来说究竟是祸是福。
没有风。
稻草人复制头戴箬笠,身穿蓑衣的农人形象,但只有一条腿。它们的脸,是在一张白纸上画上五官,慈眉善目,或者笑逐颜开。这是规模化和装备化的一群,手中的竹竿,竹竿上挑着的一块红布,成为它们在麦田执勤的标志。我看见从前的我,一个身背书包的小学生,和另一些背着书包的孩子开始走近稻草人,试图和稻草人攀谈。稻草人叔叔,你为什么不工作?九岁的我问一个和善的稻草人,你手里的竹竿从不挥动,竹竿上的红布一动也不动,你不怕麻雀会吃掉所有的麦子么?稻草人不答。这时候,一些孩子的脸上开始出现坏笑,他们从书包里取出毛笔,笔尖在唇齿间润润,给稻草人画上胡须或者皱纹。
在后来的几天里,依然没有风,空气灼热,麦穗发出了成熟的哔剥的声响,稻草人却依然没有作为。挑在竹竿上的红布一直静垂不动。看见了吧,它们是稻草制作的假人,不是活的,根本不会工作。一个孩子说。是的,昨天我拿弹弓打中了一个稻草人,稻草人也没有反应。另一个孩子说。由于失望,不满甚至憎恶,孩子们开始作践稻草人,几支毛笔在它们脸上肆意涂抹,使它们轻易地变成了歪嘴,斜眼,酒糟鼻,大麻子。
这一年,麦田里的稻草人呈现出丑陋的面貌,我也是丑化稻草人当中的一个。
麻雀已经不失时机地来到田间,它们发现今年的稻草人像普遍得了肢体麻痹症,那些会移动的红布曾经是它们眼里最恐怖的颜色,现在却静止不动,成为死亡的红色,一点也不可怕。满世界都是食物,可以随意取用,根本不必存有戒心。它们的短喙勤奋而灵巧,一啄一颗麦粒,一啄一颗麦粒,顺便还能去壳。而当它们由于吃得太多,飞行有些困难的时候,它们都选择停栖在了稻草人戴的宽沿草帽上,啾啾而鸣,遗下白色的粪便。有些麻雀天生闲不住,或者认为这是一个报复的好机会,短喙转而啄起了稻草人的脸,一啄一个洞,一啄一个洞。多么奇怪,孩子们留下的墨迹,成为对短喙的指引,它们啄完稻草人脸上的麻子,又啄稻草人的鼻子,嘴巴,眼睛,把眼睛啄成一个大窟窿。
这一年,孩子和麻雀事实上成为了合谋者,成为对稻草人毁容和凌辱的共犯。
我九岁的生命必需穿越一个类似于日全食那样的黑暗时刻。这是一个午后,云层压得很低,黑夜像突然降临,但依旧没有风。麻雀惊慌失措,惨叫声一片,每一只麻雀都想尽快撤离这个是非之地。由于害怕,我在田野上惊慌地逃奔,很快迷路,因为我找不着确定方向的参照物。我看见麦田里的稻草人却异常镇定,像战争打响前的那一刻,屏气凝神,等候一颗信号弹的升起。信号弹升起来了,是天空的一道耀眼的闪电。雷声响了。起狂风了。这时候,稻草人发威了,身体在剧烈地抖动,竹竿在舞动,红布在飞舞。满世界都是狂暴的稻草人。这与其说是一场对麻雀的战争,还不如说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暴动。稻草人被欺负和凌辱得太久了。只有走到具体的稻草人跟前,你才知道什么叫困兽犹斗,什么叫狰狞与恐怖。稻草人已经生不如死,它们的脸整个毁了,但依旧藏着一颗不死的复仇之心。黑暗与狂风持续了有半小时之久。风停的那一刻,暴雨骤然而至,沉重的密集的雨点恰如其分地打湿了麻雀的翅膀,使它们不能飞翔,也像雨点一样落到地上。
它们都死去了,挺着一只只鼓胀的小肚子。
别以为稻草人痛击的只是麻雀,不!无辜的麦子也成为它们袭击的对象。麦子在反叛的稻草人的击打之下,纷纷折断和倒地,成为死去的庄稼。
也别以为稻草人是最后的胜利者,不!战争结束,雨过天睛,麦田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倒下的稻草人,缺胳膊少腿,甚至掉了脑袋,整个麦田里充满了死亡的气息。
几乎和稻草人、麻雀、麦子一样死去的,还有我;当天晚上,我发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