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政简史
梦亦非
梦亦非,生于1975年,布依族,诗人、诗歌评论家、小说家,出版有评论集《苍凉归途》、诗集《苍凉归途》、先锋小说《碧城书》等著作近二十余部,长期在众多媒体等开设专栏。现居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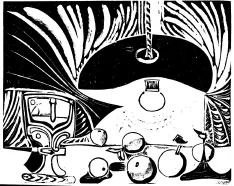
在小说一开始,我们先设计一个任务,比如说这个任务是将A物从B地送达C地,A物的性质须确定,方能设置人物D。为了文本的自指性,我们将A物设定为一份文件,书名《邮政简史》,将文件传递的工作,往往由邮政人员完成,所以人物D的身份是:邮差。
作为小说,须对人物进行形象描写,性格刻划,因为文学被一些王八蛋认为是人学——如此一来心理学或体质学是最本质的文学喽,什么狗屁道理。但在负小说中,人物的形象描写与性格刻划被放弃。人物甚至不应该有名字,我们知道,名字会暗示人物的面貌与性格,比如张三狗——一个鼠眉獐目的无赖,金城武——哗,一个高大帅气阳光的明星。所以,我们不给人物设定名字,只给他一个代号:D(禁止从这个符号联想到胖子)。
D得到一项任务,将《邮政简史》从B地送达C地,D将刻在龟甲与兽骨上的这部书稿装进口袋里,扛在肩上,告别六十岁的老娘和两个孩子,冒着满天的毛毛细雨,出门。在此我们看到D是一个男人,上有老下有小。D步行,甲骨很重,正常人不负重每小时可步行5公里,负重只能步行约3公里,D每天走10小时,30公里。D要行走的距离大约是200公里左右,从一个部落到另一个部落。
按小说的方法,须得在D行走的过程中设计一些意外,他会碰见一些人,遭遇一些事,他要说话,要行动,通过这些语言与行动来体现人性,以及人的命运。任何一个作家都可以想象出D在这200公里之间的所见所做,D作为主人公,必须贯穿整部小说。比如我们可以这样设计:D在第三天天黑时,敲开一户人家的门,门里坐着父亲、母亲、女儿,有几种可能,第一种是D与父亲交谈并饮食,睡下,次日继续行走;第二种是D砍死了其中的某个人,被抓住或未被抓住;第三种是D与这家的女儿相爱……这些设计都很无聊,因为它们不过是故事罢了,小说可以没有故事,所以在本文中我们不做这样的设置。
(杀手总开着皮卡车)
读者一定好奇在这200公里间发生了什么事。如果这是一篇学术论文,读者就不会指望其间有什么传奇性的变数,但作为一篇小说,读者就会指望有些事情发生。
但我们可以在这里让小说发生变化,比如这样写:第二天中午,D坐在路边吃干粮(如果是面食,就是北方背景,如果是饭团,就是南方背景),看见口袋被甲骨磨了个洞,一块龟甲从破洞中露出来,上面刻着一些字:在人类的文明史上,邮政扮演了扩展文明、交流文化、沟通信息的作用,一部邮政史即是一部文明史……事实上D并不识字,他看着那些字符,心想它们怎么这样沉重。
当D抬起头的时候,我们可以设计他看见什么什么什么,故事就有了变化,但负小说要力避“传奇性”,所以,D并没有什么什么,D作为小说中的一个符号,他的命运由写作者所决定。我们可以继续设计:第二天下午,下起了雨,D调转马头进入道旁的屋檐下避雨,跳下马,将那一袋竹简《邮政简史》从马背上搬下来,放在靠墙雨淋不到之处。在此发生变化,D从步行变为骑马,所传递的《邮政简史》从甲骨变成了竹简。事实上我们还可以让继续变化,让D变成了E。在从B地到C地的200公里的路上,人物发生了第一次变化,看起来是要贯穿全文的主人公却消失了,上场的是与D不相关的E(禁止从此符号联想到一个端正的人)。唯一不变的是任务:送信。对于命运我们所知甚少,甚至可能一无所知,命运的设计者可能会中止某个人的使命,也可能突然心血来潮给某个本来无使命的人凭空加上使命,对于命运设计者,我们连它是否存在都不确定,更何况猜测它的意图?这有如文本中的D或E也许不会知道我们在设计他们的境况与未来。
E骑马送信,两三天之内完全可以将《邮政简史》从B地送到C地,他可能在路上碰到马失前蹄而摔伤,被强盗射倒马而被抢走信件等等事情,每一个意外,都可以发展成另外一篇小说。但小说可能不是关于意外的传奇叙事,小说也可以是一种必然性的叙述,所以在负小说中,E一路上并没有出现什么意外,他最多因为天热而流汗,因为下雨而避雨,还能有什么大事呢?当我们设定E在送信的路上不会出现任何意外之后,我们几乎无事可做,等待读者自己在想象中完成即可,我们这样写:E骑着马,从B地将信件《邮政简史》的竹简,送达了C地。这里面有事件,有叙述,但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言的小说,因为它没有变化、高潮,不能表现人性、故事之外的寓义。当小说被认为是这样这样这样之后,那样那样那样就不被认为是小说了。小说因而成为一种矫情的文体。不过我们在这个文本中可以看到,小说可以是真实,而不是矫情的。
(杀手总喜欢开着皮卡车)
我们可以继续在工具上修改,第三天清晨,F驾着马车奔驰在从B地到C地的途中,马车厢里堆放着一卷卷抄在纸上的文件,那文件正是手抄的《邮政简史》,并没有出现多个人物,还是同一个人物,但他不是D,也不是E,他是与前两者无关的F(禁止从这个符号联想到大头瘦子),从马变换为马车,从竹简改为纸卷。因为任务是不变的:从B地将《邮政简史》送达C地,所以这里面的人、文件、赶路是不能改变的,虽然它们可以在形态上改变。这已经不符合小说的套路了,更像一部关于邮政史的影视记录片中的镜头的切换,以蒙太奇的方式暗示出时间的流逝之中送信方式的变化。这很无味,读者肯定愿意去看纪录片而非阅读文本。
但小说仍然可以继续发生变化,我们先让任务消失。于是情景变成:G坐在从B地到C地的火车上,他不知道自己从何处而来,去往何处,坐在他边上的是一位女士,女士说:“先生,你的这个皮包很漂亮。”G(禁止联想到一个啤酒肚的矮胖子)看了看放在自己膝上的包包,说:“这是一个邮政包。”它是洗布了的绿色,磨破了边,包盖上还有一个洞。女士说:“安妮·海瑟薇,很高兴认识你。”G说:“我叫G,我是一个邮差。”海瑟薇说:“你正在执行送信的任务吗?”G看着窗外暮云低卷的天空,和云层下灰褐中闪着白光的沼泽,说:“是啊,我是在送信吗?如果我不是在送信,为何会带着一个邮包呢?可是如果我是在送信,我为何又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海瑟薇说:“先生你真有趣,是不是也研究哲学?”G说:“我不研究哲学,我研究威士忌。”海琴薇说:“我也喜欢威士忌。”G说:“那太好了,不如我们来喝一杯?”到此小说应该出现转折,比如两人起身到餐车去喝一杯威士忌,这才符合常理。但负小说一般不按常理出牌,所以接下来的情节是——于是G打开破旧的邮包,从邮包里取出一瓶威士忌和二只玻璃杯子,倒上半杯,送给海瑟薇,自己也倒上半杯,两人边喝边聊高谭市最近上升的犯罪率,聊蝙蝠侠破产之后再没满血复活。在此,已经胀破了传统小说的边界,传统小说不允许出现从包里拿出酒和酒杯来喝这样的场景,又不是阿拉伯飞毯的故事,更不允许在《蝙蝠侠:暗夜骑士的崛起》问世之前,这部电影中的人物在数百年前谈论电影的内容。
(为什么杀手都喜欢开皮卡车呢?)
但这没关系,因为这是负小说,所以允许这些不符合常理的情节。但这些情节其实都是废话,可以从小说中删除,如果读者跳过这个情节,也不会在阅读中有任何损失。但我们之所以写下这个情节,目的是想说的是,在G从邮包里掏威士忌与酒杯时,将一个纸袋子先掏出来,纸袋子用蜡封上,盖着一个徽章,封面上写着一行英文:邮政简史。克里斯丁·斯图尔特好奇地问:“G先生,你送的这文件是什么呢?一本书稿?”G说:“我想应该是一本打字稿,我此行的任务就是运送它。”斯图尔特说:“可是你不知道你要送给谁。”G说:“是啊,这就是问题之所在。”然后G又说:“女士,你此行的目的地是?”“巴黎,”斯图尔特说,“我去出席2013巴黎春夏时装周。”好吧,按小说的写法,最后斯图尔特没有出现在时装周上,她在中途就和G住到某家旅馆去了,为什么?因为她是劈腿女王”啊。这样写没意思,俗套,但我们的意思是既然小说可以在某个情节上拐弯,那么所有的拐弯都是没有意义的,仅仅是写作者自己的选择,在这种偶然的选择中,人物的生活将发生改变,命运因此也被改变。那些看起来精彩的真实的或荒诞的细节,其实都是写作者的设定,就如同我们的命运与生活其实也是上帝偶尔或不经意的设定。
进而,我们还可以让任务消失,在从B地到C地的第三天中午,在一间苍蝇馆子里,H(禁止联想到一个身材匀称的高个子)坐下来吃午饭,然后又来了一个人坐到他对面,或者那个人先坐在他对面他是后来者。那个人点什么菜都没关系,无关于小说的情节,总之,可以让两人交谈,从天气谈到物价,谈到各自的生活,H发现对方在火车站邮局工作,每上午八点准时上班,与同事从火车站后门进入站台,接收从省城发出来的邮袋,签字;再将交运的邮袋交给押车员。列车中有一间车厢专门堆放邮袋,火车开走,他们将邮袋堆在推车上,运回邮局工作间,将这些邮袋拆开,从里面倒出一堆堆的报纸,杂志,信件,货物,按各乡各镇的分拣。还可以设想这个人在边分拣邮件时边干边唠叨,或者边吸烟,有一天烟头引起火灾——可真无聊,小说总喜欢写些灾难与不幸,因为按叙事学的规定,小说就是从平衡被打破到最后恢复平衡的过程。事实上在分拣室里是不能吸烟的。此人分拣好邮件,封袋,完工时已是中午十二点,他出了工作间到路边的苍蝇小馆里,吃午饭。
(杀手在《极速秒杀》中开着一辆皮卡车,轰!)
这个邮局的工作人员,不知道是男还是女,性别没关系。用了午餐后,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本书,翻开来阅读。I(禁止联想到一个瘦到皮包骨的人)抬头瞄了一眼,看见那是一本《邮政简史》。“我猜,你是拿了一本破损了的邮件中漏出来的书,或者干脆就是因为忘记处理这封邮件,太久了,不好意思再处理,只好将邮件撕开,得到这本书。”I说。或者可以这样写——I说:“你们要考试吗?在看业务书?”
于是,我们可以设置这样的回答:“这是一本短集小说集,没错,我从过期忘记处理的邮件中找到的。”或者这样回答:“这是一本历史著作。”
无论如何设置,所有的情节都是柏拉图所言的理念的分有,没有本质区别,一篇写得精彩的小说与写得失败的小说,本质上是同一,它们都是同一理念的不同分有。只有当它突破原有的小说模式之后,在小说的世界之外,假装成小说,这时,它才是不同的理念,而不再是分有。所以在本文中我们并不重视情节,当同一个关节可以发展出无数种情节之后,所有的情节都只是“意见”,而不是必然的“真理”。小说中的人物J也知道这一点,J并不是一个喜欢翘脚的人,J只是一个符号,它与A D E F J H I是同一个作为理念的主人公的分有,它既是也不是A D E F J H I,J对自己在文本中成为一个暂时性的人物无所谓,没有人可以贯穿整个历史,时间是上帝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没有从头到位都出现的主人公,每个主人公存在的时间比这部文本中每个词存在的位置还短暂,J也知道,自己无非是这部文本中的一个过渡,就像我们知道在时间这部小说中,唯一的主人公不是我们,而是上帝这个写作者本人。
明白这一点,J就好行动了,他现在手头没有邮件,也没有要送信的任务,他知道自己从B地而来,却不知道自己要往何处去,情节发展到现在,与原来相关的只有J从B地来这个细节,除此之外与原来的情节没有任何关系,但因为我们在写一篇小说,在“小说”的这个场域中,这些其实不相干的人物与情节被规范到一个间接的链条里,看起来成为同一篇小说的不同发展阶段,历史也正是这个样子,J当然明白这些,所以他假装成自己就是小说中某一阶段的人物,在那里说话,他换了几种口气说话,他说:“先生,请签收你的邮件。”他搓了搓手,换了口气:“我来的那个地方天气可真见鬼,如果有一小杯伏特加就好了。”他想想不够自然,又说:“兄弟,我继续跑路,这烟留着你自己抽好了。”他假装看见一辆邮差的单车停在马路对面的住宅前,说:“骑单车送信算什么?在中国贵州,邮差们都骑越野摩托车送信……不过他们已经不送信了,只给机关单位送没人看的报纸。”他觉得因为没有目的地没有任务没有道具,这戏没法演下去,当小说的主人公太困难了,于是扬长而去,不干了。
我们得再给这篇小说寻找另一个主人公。寻找?听起来好像有个主人公在某处,我们将他找出来就O K了似的……所以准确的说法是“我们得再给这篇小说设置一个主人公”。可怜的J,才出场没机会干点什么就退场了,像上帝创造亚当之前那些失败的范本。后来上帝觉得所有的人物设计都是失败的,于是就从完美主义者变成了次优主义者,接受了亚当,并从亚当发展出女主人公夏娃,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最后敷衍成了现在这个世界或者说《圣经》。J走了,我们按字母表的顺序,迎来了新的人物K,哗,K可是一个牛叉的名字,在所有黑帮小说中都有这个人,在所有暴力片中都有这个人,在所有神秘的或者侦破的电影中都有这个符号,K的出场引来一片掌声,掌声像浪潮一样汹涌,只见他……得,打住,我们说过不描写外貌不刻划性格的。
(杀手在电影《环形使者》中开着皮卡车,轰!)
K开着皮卡车,请不要想象K戴着墨镜手夹着雪茄之类的庸俗镜头,也不要想象什么颜色的皮卡,没读者想象的硬汉,K在小说中不是来杀人的,也不是来耍酷的,K没有任务,不从B地来,不向C地去,K只是开着皮卡车在贵州的公路上跑,像油价还没涨到每公升8.77元似的不断轰油门,像贵州的公路是足球场似的胡乱拐弯。我们只给K这个镜头,在这篇小说中,他就只能这么出现,消失在上帝的后视镜中,上帝想看见什么,什么就出现,这是上帝的创造。在小说中我们想看见什么,什么就被我们写下,这是小说的创造。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写小说就是创造世界,我们的意思是说上帝创造世界就是在写小说,小说中的正常荒诞真实虚假都是没有终极意义的,只是被设计而已,所以,我们的生活与命运也不外如是。K就深知这一点,所以K不会调转车头追问我们为何只给他一个镜头。就算不停地调头他也看不见我们,就如同电脑屏幕上的鼠标箭头赶不走停在屏幕上的苍蝇一样。
因为负小说有一条规定:9,负小说不整体逃离到诗歌或散文等非小说的领域去。所以这篇小说中的人物都被整合到同一个事件中去,因此形成某种时间链条,时间是上帝不断创造世界的逻辑,唯一的逻辑。我们可能的设计并不是一些不相关的碎片,这些不相关的碎片因为“小说”这个场域,而被整合进一个链条中。当然,我们也可以在显得很无聊的时候将这些碎片联系起来,比如这样设计:K开着皮卡车在从C地到B地之间,抢劫了步行的背着甲骨的D,枪击了骑马送竹简的E,撞上了驾着马车运送纸卷的F,射杀了坐在火车窗后的G,被为G报仇的H打断两断肋骨,又被出场就退场的J给救了,I帮他修好了皮卡车……这样一联系起来,就成了一篇硬汉小说,或者一部公路电影,读者不如直接去电影院看电影,还读小说干什么?小说就是要提供电影所提供不了的东西,小说不是电影的灵感,小说只是小说,上帝只是上帝。所以我们拒绝以上这种传奇性很强的关联,我们声明:所有字母代表的人物都没有任何关系,就像字母与字母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但这篇小说至此为止,仍然有一些固定的元素在维系着叙述的推进,比如人物,比如物件,比如目的地。如果我们将这些全部取消呢?里面没有邮件,没有邮局工作人员,没有车马,没有目的地。那变成什么样子?有时上帝在闲下来的时候,在打坐入定的时候,思想松驰下来,它就不会看见事件,它眼前只出现大片的色彩,于是就有了沙漠、草原、风平浪静的海面、没有星月的夜空……在与小说的关系上,我们也是上帝,现在,这个假上帝安静下来,眼前没有了事件,这意味着小说消失了,虽然小说消失,但文本还得进行下去,因为我们打算要写到一万字左右,这可怎生是好?好了,我们可以来描述,传统小说中描述是不可获缺的,描述人、描述物、描述场景,描述心理,没有描述,从古典小说到现代小说都无落脚之处。这些描述都是为事件服务。但现在我们可以描述与送信无关的事物,让被描述之物与小说没有任何关系,比如我们来描述一个U盘。
这是一只U盘,长4.5 C M,宽2.0 C M,厚0.8 C M,外壳黑色,一面印着红色S A N D I S K字样,另一面用白色印着C R U Z E RE D G E16 G B,M A D EI NC H I N A,外壳呈浅勺状,从中间可以推出红色U S B接口,接口中的金属条是金色,排在绿色的底上。外壳上有一个孔便于穿系带子。黑色外壳底部处理成磨砂的,上面为光面,U S B部分在推拉处设计了三道突起的横纹以增加附着力。
(杀手为什么喜欢开皮卡车?轰!)
读这一段对U盘的描述的文字,是不是将读者的注意力从事件、人物、叙述中转移出来?获得了片刻的宁静,就如同夜空是上帝片断的宁静。这一段文字是非小说性的。当然,也可以将U盘看成是道具。每一篇小说中都有一些道具,在现实主义的小说中,道具都要派上用场,如果开头出现一把刀,最后这把刀就会杀人,如果出现一盒烟,烟就要被吸掉,如果出现一个美女,美女就会被搞上床。多俗气无聊的现实主义小说啊。现实主义小说其实才是最不现实的,因为现实不是它们所写的那样,它们才是真正的弄虚作假的小说。而在后现代作品中,出现的道具不一定派上用场。上帝创造的每样东西,在《圣经》中被认为都要派上用场,其实并非这样,有些东西是上帝在无聊中创造的,并不是为了用上。甚至有些是在下意识中创造的,都未意识到它的存在,更谈不上使用。就在这一篇小说中,我来创造一个事物L,在以后的行文与此前的行文中,我不会用上它。
L不是实有,也不是没有,不是存在,也不是虚无,但又是这些的集合体,L没有名字,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味道,没有质地,但也没有这些“没有”,L不能被用来做什么,不从何处来,不往何处去,不属于谁,不支配谁,没有谁能感觉到L,但L却又不是不存在的,L甚至不是文字或符号,也不是公式,更不是关系……L甚至没有代号,不能用字母来代替或指称它。
在这篇小说中,我创造了L,但我将不会用上L。
(杀手开着皮卡车,轰!)
上帝创造了哪些它不曾用过的事物?
邮政被定义为从B取得A而送达C,邮政简史的意思就是从B取得A而送达C的简单的历史,历史又有两重意思,一重是从B取得A而送达C的一次典范性的过程,另一重是从B取得A而送达C的过程在历史上是如何演变的。这篇小说的标题是《邮政简史》,我们在其中自指性地设置了一份文件或一本书《邮政简史》,无论是出于小说的需要还是学术的需要,我们都必须继续发展出新的情节。
好吧,我们这样来设置新的情节:M(禁止将这个符号联系到作者梦亦非,虽然M是作者名字的首字母,并且作者毕业于邮电学校并在邮政部门工作过,熟悉邮政的每个环节)从B地取得了一堆邮件A,包括报纸、快递、挂号信、平信、包裹,B地是一个投递局,M开着他的皮卡车(不是杀手开的那些牌子,也不是K开的那一种型号),将邮件A送到B地,B地是一条街道,M将报纸与平信塞进一些门槛之后,打开小区中的信报箱塞进去,按门铃进入楼中让人签收快递……M辛苦地派送了一上午,将整条街的邮件A都配送完毕。这只是一种日常性的叙述,并不构成小说,还需要将M丰满成一个人物形象,描述这条街道,M派发邮件的所遇所想所作,处理的一些意外,才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小说。
好吧,我们就俗一次,来一点读者读到现在想要看到的故事,一个没有故事的小说,通常认为不是小说,小说与故事在中国被划上等号,其实故事只是小说的一个元素,小说可以没有故事,只有最俗的最没有创造力的作家才致力于讲故事。我们略微俗一下,给N在派送邮件的过程中碰到的一个情节——
N(这不是一个驼背的邮差的形象)敲响寺贝通津四号的门,这是一座修建于一百年前的别墅式小洋楼,两层,有一个小院,院里种着一些美人蕉,勒杜鹃沿着那株高出屋顶的凤凰树开花,院门开处,出来一个收信人,收信人签收了快递,站在门边折开蓝色的E M S信封,里面掉出一只U盘,并附了一纸小纸条,上写:《邮政简史》电子版。收信人拿着U盘(不是我们上面所描述的那一只,不过并不禁止你将它对等于上面所描述的那一只)哭笑不得,说:“费这么大的劲寄E M S,还不如上网发个E-M A I L给我呢,真秀逗!”
其实这并不是邮政发展的历史的最新阶段,最新阶段要参照梦亦非另一篇小说《环型废墟》,在那篇小说中他写一个邮递员O下乡送信,路上被人告知,邮局早就不往乡下送信了。所以,这篇《邮政简史》可以看作《环型废墟》的前传,也可以将《环型废墟》看作《邮政简史》的续篇。因为一篇小说的完成并不一定在自我文本中,它有可能在另一个文本中才能停下来,就如同白天停止在黑夜里,就如同男人停止在女人里……上帝的心思无可猜测,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只能模仿上帝,并且在模仿中,不知不觉就成了上帝。
小说不过是世界的另一种说法,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