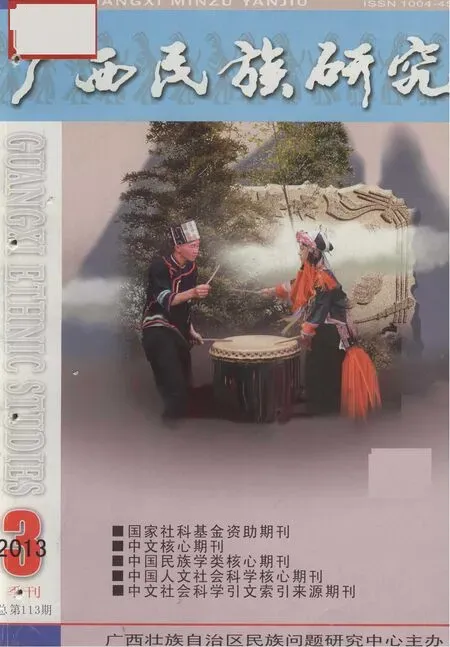转型期侗歌传承场域的多维走向与价值位移*
张泽忠 韦 芳
田野调查发现,转型期侗歌艺术传承场域衍化模式的总体趋势是传统意义上的传承场域聚合要素①侗歌艺术传承场域的时空聚合要素,指侗歌艺术传承、发展、演变的构成因素或组成要素:(1)侗族歌谣艺术的主要内容和形式;(2)侗族歌谣艺术的演唱时间和地点;(3)侗族歌谣艺术的传承人 (歌师、歌者与受众);(4)侗族歌谣艺术的虚拟空间 (网络)传播及仿像性表演、展演;(5)侗族歌谣艺术的经典性歌论:“养心”论。陆士斌:此是笔名或编校出错。综合各方信息,其真名应为陆干斌,男,原是广西象州县高中历史、政治教师,退休后为象州县“象文化”研究会会员。曾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发生了多维走向与价值位移的改变。显然,这是一个颇具现代性特征的“场所化”与“去场所化”②人类学家马克·奥格 (Marc Auge,1995)认为,“场所化”开始的同时,“去场所化”即如期而至,只是由“场所化”到“去场所化”有一个转换点的增殖以及据以和社会空间、世界进程打交道的临时“场所”的不断涌现与扩散。转换过程所带来的变化。
一、民间性与精英性
现代性视角中的民间性,一是指传统传承场域以自发性、自足性和自信性等聚合方式构筑持守自我品格、品质的规整性特性,二是指传承人 (歌师、歌者与受众)这一聚合要素具有多数性、普通大众性和一般性等特征。相对民间性而言,精英性主要指侗歌艺术传承人 (指歌师及歌者,受众不包括在内)及其演唱方式向精英化转变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从侗歌艺术传承场域的主体性角度来看,民间性指侗歌演唱活动“存活”于民间和大众,其演唱主体是民间的和大众的,欣赏主体也是民间的和大众的,因为传统社会侗歌艺术演唱活动大都属于民间自发性表演和展演。以踩堂“哆耶”③“哆耶”(duol yies/thɔε323jiε33),亦称踩堂“哆耶”,是一种集歌舞乐为一体的源于人类原始社会早期艺术样式。参见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侗族文学史》,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8页。注音格式说明:在“duol yies/thɔε323 jiε33”中,前者为侗文,后者为国际音标读音。下同。(duol yies/thɔε323jiε33)为例,亦可看出侗歌艺术演唱活动的这一特性。踩堂“哆耶”是一种集体的歌舞活动,发起人邀请众人参与,歌者与听者在且歌且舞中位置不断地变换,这种全民参与性和角色互换性保证了踩堂“哆耶”的民间性特质和品格。然而民间性在向精英性衍化后,侗歌艺术传承场域演唱主体和欣赏主体大都是“精英”的,或者有一方是“精英”。“精英”的队伍也发生了变化,不是以往人们所认为的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群。转型期的“精英”,一是相对民间自发性即普通民众而言,二是指群体的特殊性和非一般性。后者 (即特殊性和非一般性群体)包括歌师、学者、政府人员、歌舞活动经纪人,等等,他们的能量主要体现在知识文化和技术水平上,或者体现在权力或资金的投放与市场运作上。不过,不管是传统社会或现代转型期,“精英”主体仍指歌师群体。传统社会中,歌师既是侗族文化传承的精英,又是普通大众中的一员。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歌师身份发生了变化,有的成为文化馆干部,有的成为乡镇文化站职员,然而他们在传承场域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担当的责任,与民间歌师没有多大区别。不同的是,转型期歌师的身份明显向“精英化”衍化,包括民间歌师在内,有的身价、地位与普通民众不尽相同,有的可以说已经跻身于纯粹意义上的精英队伍。
调查表明,现代转型期精英队伍的主体是学者、政府官员和民间文化市场运作中的经纪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侗族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涌现出大批的学者型精英人才,他们土生土长,吸收母体文化的滋养,接受高等教育和掌握汉民族文化知识,因此,他们往往能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和视角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审视和研究。他们是侗歌艺术传承场域中当之无愧的精英。而侗族地区政府职能部门官员,由于文化产业运作的原因,也挤入了传承场域精英行列,原因是他们直接管理侗族地区的行政事务,较普通大众和学者有更大的话语权。经纪人则来自于民间,是市场经济时期的新型人才;在民间,经纪人意味着掌握财权,在文化资源市场化运作过程中他们拥有资金投放和财力基础话语权,是一股推动侗歌艺术繁荣和市场化操作的生力军。
实践表明,转型期侗歌艺术传承场域衍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现代型文化精英,其话语权及领军位置并不是生而有之,他们原本是民间普通民众之一员 (从酷爱侗歌艺术这一意义上说,政府职能部门官员除了行政话语权之外,其基础性身份可认同于热心侗歌艺术传承的民间普通民众),在经过一定的人生历练后转变为艺术精英。当他们投身侗歌艺术传承场域并有所作为时,往往以他们所善长的技能,或以他们的知识文化、权力和财富以及市场操作能力去影响侗歌艺术的继承与流布。由此可见,缘于转型期传承渠道的多样性,以及传承活动过程中各项聚合要素发生变异和衍化这一契机,侗歌艺术传承场域民间性与精英性特征发生了诸如同质叠加、异质同构等相互交叉和精彩纷呈的趋势特征。
二、神圣性与世俗性
与民间性和精英性的现代转型相对应的是,神圣性与世俗性也发生了变化。应该说,神圣性遭遇了挑战,世俗性有所抬头,这已成为侗歌艺术传承场域现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另一倾向。与民间性与精英性一样,神圣性与世俗性是一组互为关联对应的概念。当我们对神圣性作界定时,发现这一特色浓郁、意味厚重的概念,旨在传递民族情感诉求中的带有崇高性和神秘性的公共情怀。确切地说,这里所说的神圣性,指侗歌艺术传统传承场域时空聚合要素的自我表征 (Representation)①表征,指原有的形态无法描述与表达,用新的符号形态与方式再度表达。英国学者霍尔在《表征:文化意象与意指实践》中的解释是:表征指“用语言向他人就这个世界说出某种有意义的话来,或有意义地表述这个世界”,“从根本上说,表征一方面涉及符号自身与意图和被表征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又跟特定语境中的交流、传播、理解和解释密切相关”。参见[英]霍尔编,徐亮、陆兴华译:《表征:文化意象与意指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15页。行为,源自世俗性 (民间的诙谐性)又超越世俗性②指特定场域中时空要素的神圣性,譬如时空要素的非均质性 (Homogeneous)、间隔性和可逆性,如节庆日侗胞在“萨坛”旁、鼓楼里演唱《大歌·女神萨岁歌》时,苍穹 (空间存在)仿佛回复到远古,时间存在仿佛从平常序列中逆出或间断,倒流到“当初萨岁七千里路下界来”这一神圣时刻,这时你、我没有尊卑等级之分,只有一个和谐、平等对话的“干道” (gaeml daol,kaem55tao55,即“我们侗人”)在共同体验元初宇宙图景的再度现实化所带来的愉悦、欢乐和神圣。,从而具有充分表达民族公共情感的圣化品格特性;特性的品质内涵意味着崇高性和神秘性。换言之,侗歌艺术传统传承场域聚合要素所具备的神圣性,指神圣性情怀的自我表征行为,源自于民族集体的原发性体验和对宇宙时空的非均质性(Homogeneous)体验,这种体验来自于民间和世俗,又超越民间和世俗,其崇高性、神秘性品格、品质内涵使侗歌艺术传统传承场域模式烙上了圣化特征和宗教意味色彩。具体说来,非均质性体验,指传承场域时空聚合要素与非传承场域时空聚合要素彼此之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和时空上的间隔或中断,正因为这样,崇高性、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区别及差异才成为可能。
事实表明,现代转型期,民间性与神圣性、精英性与世俗性共同构筑了侗歌艺术传统传承场域的存在样式。值得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神圣性,特定意义上与超越性相对应,而世俗性则与现实性相对应;此外,世俗性应该说与神圣性一样系舶来的概念,社会学中指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文化艺术从中世纪宗教桎梏中逐渐摆脱出来所呈现的一种现实性与平民性倾向。我们正是在现实性与平民性的这一意义上,对“神圣性遭遇了挑战、世俗性有所抬头”这一问题作当下性的诠释与分析。我们拟从如下方面展开问题讨论:
其一,关于侗歌艺术传统传承场域的品格、品质特征问题。分析认为,传统传承场域的品格、品质特征既是神圣的,又是世俗的。尽管神圣与世俗是一对矛盾对立的概念,但两者并非水火不相容,恰恰相反,它们往往统一在同一对象上。可以这么说,侗歌艺术传统传承场域要素构成及其所显现出来的情状特征由两方面构成:一者持守神圣,二者拥抱世俗。前者如前所述,在传统传承场域里,侗歌艺术的品格崇尚宗教性情怀和审美性体验,因而它是神圣的,其特点是追求一种超越性,因为宗教意味也好,诗意性与审美性也好,都倚重于对精神性的追求与超越。
后者之所以归属于世俗,原因是在传统社会里侗歌艺术的表演或展演全然是一种全民性的民俗活动。从这一意义上说,侗歌艺术是一种生态性的文化样式,崇尚的是一种人文深度的生存方式,它实实在在地与现实社会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它就是生活本身。从这一角度说,侗歌艺术传承场域当然隶属于世俗。总之,在传统社会里,侗歌艺术传承场域的神圣性与世俗性合二为一,融为一体。
其二,关于转型期侗歌艺术传承场域的品格、品质特征归属于神圣性还是世俗性的问题。田野调查表明,转型过程中的侗歌艺术传承场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神圣性与世俗性依然是矛盾同一体中的两个方面。不同的是,矛盾对立的两方面发生了裂变,从而使侗歌艺术的表演、展演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品格、品质特征,或崇尚神圣,或取媚于世俗。这是一种带有对规整性和根本性品质、品格 (饭养身,歌养心)的裂变。当侗歌艺术的表演或展演从民俗活动中分离出来,变成一种纯粹性的审美活动时,它是神圣的;当侗歌艺术的表演或展演与市场化运作活动联系得过于紧密时,其市场功利目的掩盖了侗歌艺术的审美性和诗意性,那么它就降低品位而取媚于世俗甚至低俗,因而它是世俗的。诚然,两者又可以发生互化,即神圣化趋向世俗化,世俗化趋向神圣化。这里所说的世俗神圣化,与民间自发性试图向精英化靠拢极其类似;不尽相同的是,世俗神圣化注重的是侗歌艺术传承场域的内在品格、品质的追崇,民间自发性向精英化靠拢注重的是表演或展演活动主体的文化地位或话语权与财富目标 (经济效益)如何得以体现及实现。因此,精英性未必就是神圣性,民间性不见得就是低俗和鄙陋。
结论是,现代转型期侗歌艺术传承场域的价值定位与取向发生了位移和变化,位移和变化的过程由原来的对超越性与诗意性的追求,衍化为时下注重对现实性与世俗性的关注。
三、民间精英化与神圣世俗化
以下,拟结合侗歌艺术传承场域时空聚合要素的变化,对现代转型期民间精英化与神圣世俗化衍化模式及其交叉性、互渗性形态特征作简略的描述、梳理与分析。
(一)表演、展演场所的衍化
调查发现,转型期侗歌艺术表演、展演场所实现了由实到虚的转变,其转变轨迹与侗歌艺术发展的三个阶段——作为生产活动产物的原始文化时期、作为观念形态产物的古代文化时期、作为审美对象产物的泛历史文化时期——相对应,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室外演唱 (田间地头、山坡草场演唱)。这一阶段的侗歌演唱场所一般在田间地头,因为人们的劳作多发生在田间地头、山坡草场,男女之间的情感也多在劳动中逐渐培养起来,所以这一阶段的情歌、劳动歌相应地在田间、地头得以表演或展演。
第二阶段,室内演唱 (火塘、月堂、鼓楼演唱),尤其是侗歌大歌、琵琶歌向来以室内演唱为主。这与许多少数民族的山歌风俗有所不同:场所由山坡上移到了寨子的鼓楼或火塘、月堂。如下图例,可说明一二:

(左)鼓楼里的琵琶弹唱 吴景军/摄

(右)鼓楼里的大歌对唱 张清澍/摄
侗歌艺术演唱场所由室外移至室内,与侗族传统社会制度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在侗族传统社会里,鼓楼被当成侗族制度文化的象征,是村寨的心脏,是人们聚集的中心地;因为如此,它最终成为培育侗歌艺术的园地及中心场所,为人们唱歌、跳舞度过劳动之余的闲暇时日提供了可能。由于场所的可能性,这就为侗歌艺术发展的第二阶段 (作为观念形态产物的古代文化时期)——侗歌艺术离开劳作的直接需要而进入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且充当精神统治工具——提供了保障。另外,相对鼓楼的公众性和庄严性来说,吊脚楼里的火塘行歌或月堂坐夜,譬如男女青年的情歌对唱,其教化功能是通过审美性来实现,因而变化了的演唱场所依然充盈着诗意性显得温馨和富有魅力,这一时期的侗歌艺术系作为泛历史文化时期审美对象的产物而出现 (审美性从发端到成形经历了三个阶段)。实际上,表演或展演场所的改变或衍变,经由作为原始文化时期生产活动的产物和作为古代文化时期观念形态的产物以及作为泛历史文化时期审美对象的产物三个阶段后,所有的场所共同创造了侗歌艺术的“黄金时代”。[1]
现代转型期的第三阶段,突出的特点是表演或展演场景的虚拟性 (舞台、校园、电视、广播、电脑、网络、多媒体音像制品)。前两个阶段,侗歌艺术表演或展演场景实实在在地凸显于现实生活和生产活动过程中,全然民间化和世俗化。而第三阶段,表演或展演场景已然由“实”趋向“虚”,其表现形态为:或舞台化,或平移于主题公园、校园,远离了民众的生活实际;或“活态”场景为虚拟世界所取代,譬如,与实际生活隔膜的电视、广播、电脑、网络、多媒体音像制品的出现。当然,侗歌艺术走向虚拟舞台、主题公园、校园、电视、广播、电脑、网络以及为多媒体音像制品取代,未必不是侗歌艺术传承场域现代化变革应走的一条新路子。因为,当舞台、校园、电视、广播、电脑、网络、多媒体音像制品等精英化传承因素经由民间化后,必定趋向大众化。
实际上,转型期侗歌艺术表演、展演场所由实到虚的转变过程,是一个颇具现代性变化特征的“场所化”与“去场所化”(Non—places)的转换过程。从理论的角度看,人类学家从未忽视社会文化“场所”的偶然性,认为因特殊性“场所”而形成的“场所化”规律,体现在行为文化寄居其中的社会空间或虚或实的变化:即“场所化”开始的同时,“去场所化”即如期而至,只是由“场所化”到“去场所化”有一个转换点的增殖以及据以和社会空间、世界进程打交道的临时“场所”的不断涌现与扩散。看得出来,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这一理论说旨在说明“去场所化”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是一本“被无休止地重写”和“涂改得一塌糊涂的稿本”,一方面“可以被解释成一种意识形态,其立场的归属并不比传统的‘空间’少;而固定性、社会关系和文化常规 (群体、神和有机体)可以被认为不断地在这个世界上重构自身。但去场所化要达到的目的是推翻一个地方正常的单一性;因此场所和去场所化代表了相对的形态 (指意识形态、立场归属、文化常规等),前者从未被完整建构过,后者从未完全达到过。去场所化的可能性和经验从未被完整建构过,结果是,任何场所都不完全是它自己,都没有与其他场所彻底分离,也没有任何场所是另一个场所。”[2]378“去场所化”理论说是由马克·奥格 (Marc Auge,1995)提出来的,这里引述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转型期侗歌艺术表演、展演场所由实到虚的转变过程,有如人类学家所描述的“场所化”与“去场所化”的转换过程。即第一、二阶段的室外、室内演唱和第三阶段的场景虚拟性,可理解成侗族社会的行为文化、歌唱场景“不断地在这个世界上重构自身”,其结果是“场所化”和“去场所化”“都不完全是它自己,都没有与其他场所彻底分离,也没有任何场所是另一个场所”。作此描述的目的是为了提醒人们关注这一由“场所化”到“去场所化”的转换点所带来的变化。譬如,变化中据以和社会空间、世界进程打交道的临时“场所”是如何地涌现与扩散的,而我们该如何予以关注,并加以总结和研究。
(二)歌者、受众及表演、展演内容的变化
2004年8月,贵州黎平篙镇晚寨田野调查所获数据表明,寨子里三四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几乎人人会唱歌、人人爱唱歌,而三四十岁以下年轻人能唱歌的,男青年只有1人,女青年过半数。晚寨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寨子,歌唱传统保持较完好,但已是这样一种状况;而广西三江独峒寨作为一个正走向城镇化的开放地区,情况则不容乐观,除五六十岁以上和三四十岁以上有半数会唱歌以外,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只有二成会唱歌。尤其严重的是,侗歌在三十岁以下这一代年轻人中已经失去了市场。原因是年轻人忙于生计 (外出打工)而远离侗歌艺术传承场域,最终荒废了学歌唱歌;即使不出远门,闲暇时聚在昔日作为歌谣艺术活动中心的鼓楼、月堂或火塘,其场景、情形不再是“年老的教歌,年少的学歌,年轻的唱歌”。
又譬如,传统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传说,靠讲古者传承下来。讲古一般在鼓楼讲。调查发现,现在鼓楼里把国内奇闻趣事也当讲古来讲。如讲布什、伊拉克,讲海峡、讲阿扁 (陈水扁)、讲机器人、讲克隆人。而月堂或火塘,昔日是行歌坐夜的地方,如今电视屏幕里的内容取代一切。
案例表明,民众已经在关注“团寨”(Duans xaih/thuan11ai33,指聚族而居的自然村寨)社会以外的事,关注世界性体育赛事,关注国家、民族整体利益得失,认知触角已然由乡民社会的文化“小传统”,向都市大众文化“大传统”拓展。[3]251可见,传统社会的“年老的教歌,年少的学歌,年轻的唱歌”的对侗歌艺术的单一性需求,已发展为包括“去场所化”在内的、不比传统“空间”少的、从内容到形式都得以扩展而带来的变化和衍化。
(三)衍化模式的交叉性与互渗性
转型期,兼容与整合,变迁与再地方化,即衍化模式的交叉性与互渗性,是传承场域聚合要素民间精英化与神圣世俗化的又一表现特征。调查组重点考察的独峒寨,表面看,当下的侗歌艺术表演、展演活动一般按传统习惯、习俗来开展,如“月也”(weex yuev/w31yie53,寨子与寨子间的集体做客)、“月地瓦”(weex deih wakv/we31tei33w k53,意为“种公众地”,即种产权系族群共有的公用地)、鼓楼讲古、演侗戏、讲款活动、行歌坐夜等,都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有直接的关系,可看出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形态下衍生出来的文化产物。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独峒寨社会—经济在转型的同时,民众的文化生产和消费理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在,原来民间自发组织的活动减少,由政府部门介入的活动增多。如2004年“十·一”黄金周,独峒寨的生态文化旅游系列活动以政府为主和民间组织参与相结合的方式来开展,以这种形式举办的传统活动项目除了“月也”、“月地瓦”、“多耶”、“吃百家宴”之外,还举行诸如当下流行的“卡拉OK赛”、球类竞技赛等活动。传统社会的文化活动、歌舞表演或展演,场所相对固定。演侗戏、芦笙踩堂、青年男女行歌坐夜,场所相对固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活动项目的秩序化开始向无序化转变或衍化。
案例说明,转型期侗歌艺术表演、展演场域已然发生聚合模式的交叉性与互渗性衍化的变化。变化的特点可用这样的形态特征来归纳概括:即侗歌艺术表演者、展演者包括受众,已由传统的普遍性、多数性、民间性,衍化或变化为当下的少数性、精英性 (指非民间的自发性,即指政府职员的职能性和民间发起者的组织作用性)。譬如,传统侗歌艺术作为一种审美化生存方式被整个社会集体所接受和传承,其情形是人人学唱歌、人人会唱歌,然而现代转型期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开放性,致使精神消费有多渠道的选择,人人学歌、听歌和唱歌的热情已发生不可抵御的当下变化或衍化,侗歌艺术的表演或展演,逐渐成为少数精英阶层在操作或把玩,传承场域及流布渠道因此变得相对狭小和不顺畅。
与此相对应的另一种情形是,与侗族族群自身的由传统的普遍性、多数性、民间性的变化或衍化为当下的少数性、精英性不同的是,大环境意义上的受众 (包括侗族族群自身的受众)反而由少量的、精英的变成多数的、民间的和世俗的。相当一段时期,了解侗歌艺术的外族人只限于专家、学者和音乐人士,普通民众接触、观赏侗歌艺术表演、展演的机会极为有限。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侗歌艺术传播媒介种类繁多,传播范围广泛,由此,更多的族外民众有机会了解侗歌艺术并学唱侗歌。比如受众这一层面,过去以侗族自身听众为主,如今全国各地包括国外都有喜爱侗歌艺术的受众。这部分受众有普通民众,有精英型的学者,有音乐人。可见,侗歌艺术传承场域衍化模式的不确定性、交叉性及互渗性衍化特征已然形成,并日益凸显。
(四)传播媒介的多样性
侗歌艺术的传播媒介有多种类型及方式:一是口耳相传,即口传心授。侗歌是一种口头艺术,其媒介是言语及音乐,其特点是直接性、易变性、完整性和创造性。二是纸质材料的运用。凡有汉文化功底的歌师都会使用纸质材料来帮助记忆。这是侗歌艺术得以传承的另一个重要保障。调查发现,歌师采用的是“汉字记侗音”的方法记录歌词。汉字读音与侗语不能精确地一一对应,纸质材料只能保存歌词的大致读音。每个歌师选用的汉字记音符号有所不同,相互间不易于交流,只能方便歌师自身的使用。因此这种媒介的使用具有不完整性和相对稳定性。正是这一点,歌师对记忆力的要求被放在技能训练最重要的位置,而纸质材料则只起到辅助性的记忆作用;这样,侗歌艺术口耳相传过程中的个体性、独特性和创造性亦得到了保证。三是借助多媒体材料、网络与电视。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和电视、网络技术的普及,侗歌艺术多媒体音像制品应运而生,并推上了市场,网络因此有了专门介绍侗歌艺术的网站,电视里也不时转播侗歌艺术表演或展演的场景。相对于纸质材料,多媒体材料能储存更多的信息,保存更为久远,传播范围更广,更方便使用,具有可复制性、可转换性。然而正因为具有这样的优势,演唱者对记忆力的要求降低了,其独特性、创造性也降低了,演唱活动也往往出现千篇一律的格局及场景。
三种传播媒介中,口耳相传中的“口”与“耳”,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必备的身体要件,因此,口耳相传模式既具备个体性和独特性,民间性和大众化亦得以体现。第二种方式是使用纸质材料,其前提条件是歌者必须具有汉文化功底,这部分演唱者相对普通民众而言,属于精英阶层。因此,使用纸质材料,是民间化向精英化迈进的第一步。第三种方式是借用多媒体材料、网络与电视,开始属于精英阶层所拥有,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变成或衍化为普通民众所能接受的承传方式。
(五)内容、形式、格调的衍化
侗歌艺术种类繁多,内容包罗万象,有自然知识、劳动知识、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英雄叙事诗、伦理道德训诫,等等。然而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发展过程中,侗歌艺术的阶段性受重视情况有所不同。如前所述,作为生产活动产物的原始文化时期和作为观念形态产物的古代文化时期,对应于农耕文明时期,因此侗歌艺术种类及内容大都反映传统农业社会的劳动生产、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英雄叙事诗。而现代转型期所创编的侗歌艺术及其表演或展演方式,更多地反映、表现改革开放后新农村社会生活,传统侗歌艺术则侧重于对审美品位较高的曲目的传承,譬如对情歌及大歌中的声音大歌 (嘎梭,al suoh,a55suo44,大歌的一种,类似美声演唱的歌,如大歌精品《蝉歌》)尤其青睐。对此,另拟专题论述,这里着重关注侗歌艺术的内容、形式及格调的衍化问题。
田野调查发现,现代转型期侗歌艺术的传承、流布有了新的衍化和变化,表现在传统侗歌艺术比较重内容,当下流行的侗歌艺术则重形式轻内容。这里所说的衍化或变化,不是说形式对传统侗歌艺术来说不那么重要,而是说现在传承场域聚合要素中的作者、演唱者、受众等在创编侗歌、演唱侗歌、欣赏侗歌时关注重心已由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转向现在的垂青形式淡漠内容。
传统侗族社会,歌师对侗歌艺术的创新,多指对侗歌内容的改编或创造,较少指对侗歌艺术的音乐形式比如曲调的创新。原因在于,一是传统歌师一般汉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没有相关的音乐知识,难以对侗歌曲调等音乐元素进行改革或创新。另外,从受众的角度看,曲调的频繁改动或变换,也不适合和不易于口传心授,加之旧有的欣赏习惯偏向或偏好于接受传统遗存下来的带有原汁原味的曲调,因而受众对新鲜东西的出现要求不高。二是侗歌艺术演唱者和受众一般把关注目光放在歌词的内容美和语言的生动美上,形式美往往次而求之。
然而当下精英人士却极力倡导侗歌艺术改革,试图为侗歌艺术的繁荣、发展寻找一条新路,尝试过程中,常常把创新的重点转移到对传统曲调等音乐形式的“刷新”上。田野材料表明,目前有关人士对侗歌曲调的创新基本摸出了路子,创作或改编过的侗歌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由单一、齐整走向丰富、多样,二是由随意、疏落走向严谨、规范及精细。
创新实践中,音乐人士发现,传统侗歌种类曲调变化不大,旋律简单,目的是为了适应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由此,他们另辟蹊径走出一条新路子,即借助乐谱记录曲调、媒体音像材料刻录等手段,为侗歌曲调的花样翻新创造条件。另外,创新队伍中的创作者 (包括受众)一般受过汉文化教育,具备相关的知识以及音乐素养,创作或改编出来的侗歌,形式精美、花俏,品种、花样繁多,为侗歌艺术的传承、流布注入了新鲜血液。总结起来,在传承渠道多样化的趋势下,侗歌艺术方法创新上有如下两方面特色:
1.高雅化
即由俗到雅。这一点在校园传承中表现尤其明显。侗歌原本来自于民间,创作者、受众大都土生土长,因此不管创作者还是接受者,都要求曲目或歌词通俗化,符合大众口味。当侗歌艺术搬上舞台、搬进校园后,精通音乐的精英人士认为传统曲目或歌词土里土气,因此理所当然地进行改造和改编。目前校园里尤其是高等学校侗歌班所教授的侗歌曲目,从众多传统歌曲中选择较典雅的部分,为适应演唱场景需要大部分经过了改编或调整,而改编或调整的标尺定位在高雅化上。事实上,经过筛选、改编过的侗歌确实属于精品创作并流传于国内外大型舞台上,然而这些作品或产品却逐日疏离了民间自发性根基,乡土化、民俗化特色仅仅作为调料、点缀,让人多少还能看出侗歌艺术的身影。
2.俗化
即由雅到俗。这一点在侗歌艺术市场化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传统侗歌文本有其俗的一面,但因审美目标为经典歌论“饭养身/歌养心”(Oux xih sangx xenl,al sangx sais,ou31ji33saŋ31jən55,a55saŋ31sai323)所规范,所以依然不失典雅之品位。传统侗歌的创作和演唱实际上是由精英们 (一代又一代的歌师)来完成的,这就从源头上保证了侗歌艺术的品质和品格。传统侗歌的创作和演唱活动,注重“唱心头”,讲究审美性,因而保证了侗歌艺术的创作和演唱活动的自律性及品质、品格的纯净性。当下侗歌艺术市场化要求,听命于市场指挥棒,加之如前所述的值得商榷的高雅化要求,以致造成一种混杂局面,即高雅化、市场化的同时,侗歌艺术的庸俗化露出端倪。
形式和内容的衍化或变化,必然带来艺术格调的改变或“刷新”。总体来看,侗歌艺术一方面由大众化走向了精英化,即民间精英化;另一方面则愈加世俗化,即“元叙事”中的经典性或神圣性遭遇现代性的挑战甚或亵渎,世俗化或低俗化逐日抬头并有了市场。
(六)功能性衍化
传统侗歌的功能大多是世俗性 (指民间性)和功利性 (指审美性及伦理性),特点是所蕴含的生产辅助性功能、宗教性功能、文化性功能、情感性功能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现代转型期,这些功能性能量有所衰弱和萎缩。这与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有关联。因为当人们不再拉木时,《拉木歌》就会失去演唱的机会,当行歌坐夜、宗教祭祀等民俗活动逐渐消失时,情歌、祭祀歌就会逐渐绝迹;当人们在课堂上更多地关注“大传统”语境中的丰富多彩、系统化的科学知识时,处于主流文化边缘、作为民族文化传承载体的诸如历史故事、英雄叙事歌和伦理歌的演唱机会自然减少。可见,转型期侗歌艺术世俗性或功利性功能发生变化或衍化是必然的事。
总而言之,以“饭养身,歌养心”为规整性特征的侗歌艺术传承场域,传统意义上,持守“民间性”、彰显“神圣性”,现代转型期,则一方面对“民间性”、“神圣性”若即若离,一方面却迫不及待地向现代性“精英化”与“世俗化”多渠道地演进,从而使原来处于本体性源头、具有规整性特质的经典性歌论(“养心”论)发生了价值位移。实际上,如同马克·奥格 (Marc Auge)所说的,这是一个“场所化”与“去场所化”(Non—places)转换过程所带来的颇具现代性变化特征的演变和改变。
[1]张泽忠.侗歌艺术历史分期“背离”模式说[J].百色学院学报,2011(1).
[2][英]奈杰尔·拉波特,乔安那·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M].鲍雯妍,张亚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3]张泽忠,吴鹏毅,胡宝华.变迁与再地文化——广西三江独峒侗族“团寨”文化模式解析[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