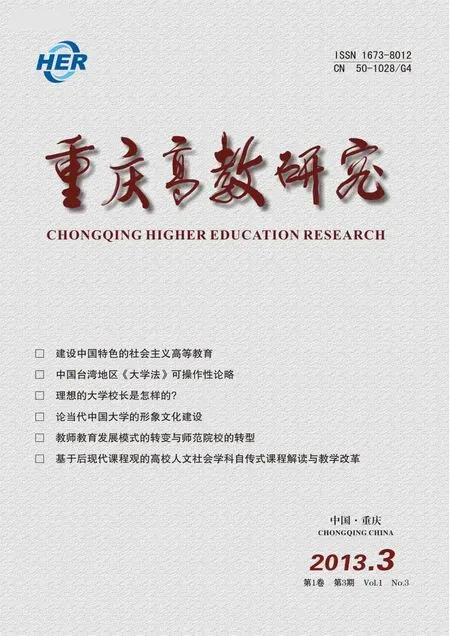基于后现代课程观的高校人文社会学科自传式课程解读与教学改革
——以“中外教育史”为例
杨晓峰
(长江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重庆 涪陵 408100)
基于后现代课程观的高校人文社会学科自传式课程解读与教学,是受美国学者威廉F·派纳的自传式课程理论与后现代课程观启示所提出的课程内容拓展与教学方法改革。自传式课程理论把个体经历的课程视为课程之本质,把课程目标界定为个体的解放,把课程内容视为依据兴趣建构起来的自我经验的观点,[1]对于高校人文社会学科课程解读与教学改革具有启示意义。
一、缘起:基于后现代课程观的“中外教育史”自传式课程解读与教学改革形成过程
自传式课程理论重视“自传”在课程中的意义与价值。“自传”的希腊文由“自我”(auto)、“生命”(bios)、“书写”(graphy)组成,指个体基于生命经历的书写。[2]基于后现代课程观的高校人文社会学科自传式课程解读与教学改革的设想,源自我从事“中外教育史”教学工作的感悟。
(一)教学困境中的理性反思
初次接触“中外教育史”是在2006年。虽然,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教学效果却让我失落与困惑。“知识点”庞杂,理论色彩浓厚,这促使我不断地反思,怎样的课程与教学才能让“历史”与学生之间达成对话关系,怎么才能将我对教育的思考融进课程与教学之中?在思考中不经意觉察到一个现象:很多教师会缺乏理性地在教学中援引民族/国家的伤害历史,即课程与教学中的“创伤历史叙事”——一个民族/国家所遭遇到的战争、屠杀、清洗、迫害、隔离等历史记忆。很多学者都思考过历史的价值,比如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区分了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历史价值观。纪念的历史主义者目光越过现实生活,过分强调历史导引;怀古的历史主义者把历史视为工具,缺乏理性反思。两类历史价值观持有者先验地假定了历史的正面价值,而忽略了历史的负面作用。尼采的第三种观点将历史置于批判视角之下,要求在反思和意义中审视历史。这种观点得到了后现代主义者的支持。后现代历史课程观认为,我们已经走到了一致的、单一的、宏观叙事的历史解释的尽头,认为历史是情境性的、多维的、反讽的、偶然的、非线性的、发展的和自传的,不再简单地把历史看作是纯粹记忆的事实,而是把历史诠释为自传的、局部的、特殊的事实,强调历史的社会和文化建构性。[3]在上述思考基础上,我从人类的宏观与终极伦理关怀角度,对课程与教学中的“创伤历史叙事”进行了初步思考,在《现代大学教育》上发表的论文《如何面对课程与教学中的创伤性叙事》被“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网站的“发展趋势研究”栏目全文转载。文章获得认同促使我在“中外教育史”课堂上,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课程内容进行了拓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后现代课程观的“中外教育史”自传式课程解读与教学理念。
(二)自传式课程解读与教学理念
1.教学目标:以知识促进个体的解放
自传式课程理论把课程目标界定为个体的解放,教学的意义之一是为某个领域生产解放性知识。长期以来,历史教学遵循的是恢复“历史本来面貌”这条线索,对历史的解读只能从具体的历史阶段出发。这本是科学、严谨、辩证的历史态度,但在教学过程中很容易将历史教学过程变成历史学家观点的普及过程,导致“中外教育史”成为“死知识”的传授与记忆,远离鲜活的生活、远离丰富的实践、远离实在的价值、远离现实的意义,不利于学术与思想的解放。感受到传统“中外教育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之后,我开始自觉探索新的教学方法:上课之前仔细浏览教科书及相关资料,并结合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和学生的学习生活工作,将所思所想归纳为一个与当前社会、教育生活、学生实际情况高度相关的观点,再进一步查找资料进行丰富,最后在课堂上以随笔形式将思考结果展示给学生。这些随笔会涉及到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美学、伦理学等各个学科。形式也是多样的,包括诗歌、故事、杂文、流行歌曲等。这样在完成教学计划的同时也扩展了课程内容,触发学生思考的频率明显得到提高,使学生有机会从牢固的、传统的、束缚性的知识观中逐步获得个体的、本土的、现世的意义。
2.教学过程:内在自我的开放与流动
其一,教师的内在自我的开放与流动。自传式课程理论借鉴了文学、精神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等领域注视内部世界的研究方法,在教师的课程解读中引入了自身对于这种解读的反思。教师要检视自己的经历、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社会地位等各种因子在课程解读中的作用。一系列围绕“教师自我”的反思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以我的教学为例:成长背景、中小学教育经历、生活环境等是否影响了我的教育教学方式;我在课堂上宣扬或者批判了什么、批判的时候有多少保留;从学生的反馈中感受到什么,我是否根据学生的反馈做了相应的调整等等。“日志”式的反思使我有机会不断触摸自己的教育理念与思想,对外部世界以及自我的认识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与此同时,部分反思也较为自然地嵌入课程内容拓展之中,从以前教师内部建构变成了课堂显性展示。
其二,学生内在自我的开放与流动。20世纪90年代后,格鲁米特、米勒和多尔等人开始倡导“存在体验课程”,将自传课程理论变为一种课堂教学方法。这种参与程度较深的教学方式要求每个学生仔细回顾与思考他们各自的体验,而教师则主要是阅读学生日记并且与他们展开讨论。在尝试自传式“中外教育史”课程解读与教学改革时,我首先向学生讲述了自己过去所遭遇的挫折以及关于历史价值的思索,一方面让学生熟悉并接纳这种教学方式,另一方面让学生认同历史也可以在适当范围和方向上“建构”的理念。行课期间要求学生在课程总体框架内,以教育制度、教育思想与教育事件为线索,进行思考与分析,沿着任何可能的方向进行联想与引申,并将思考结果带进课堂作为课程资源与师生分享、交流与讨论。通过初步的尝试,学生们逐渐打开了以前相对封闭的内部空间,由独自“咀嚼内心”状态转而与同学们分享自己的困惑、迷茫、希望、追求,对现实的观察、反思、探索,对教育的认识、判断、思考。教师与学生之间就这些话题展开深度交流与探讨,不仅促使学生更多地反思理论与实践、教育与生活、态度与价值观,还能加深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了解,形成人文情怀。
二、展示:基于后现代课程观的“中外教育史”自传式课程解读与教学片段
根据过去的观察和调查,很多学生觉得“中外教育史”的“实在价值”不明显。为消除学生对课程“空疏无用”的认知,我试图将教育史与广阔的社会生活与学生成长背景结合起来。
(一)自传式课程解读与教学片段
下面的课堂教学片断是我在讲授“教育起源学说”时,以“从教育的起源说到端午节之争”为题,对课程内容所作的个性化拓展,从中可一窥“基于后现代课程观的‘中外教育史’自传式课程解读与教学”的部分特点。
教师:同学们,关于教育的起源,分别有生物起源说、心理起源说、劳动起源说、需要起源说等。大家了解了教育的起源之后,你们觉得这样的知识有什么价值?或者说,你们觉得各种起源学说对现实生活有什么启示?
学生:什么价值都没有,就是知道了教育的起源而已,对生活没有任何启示……可以用来聊天,吹牛(笑声)。
教师:(微笑点头)我同意大家的观点。但如果我们这样学习历史,历史就会远离我们的世界。我们能不能赋予教育的起源学说一些深层次的意义呢?哪位同学能把教育的起源和我们的生活与教育联系起来?
学生:(面面相觑,开始议论)……
教师:(再次微笑)知道大家一下子可能无法展开,那么,请大家看看我怎么去诠释教育的起源学说。
学生:(立刻安静下来,保持倾听状态)
教师:2005年11月24日,韩国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消息传开后,引起我国民众一片哗然。无独有偶,据中国留学生的见闻,朝鲜教科书将人类起源追溯到朝鲜半岛。纵观世界,类似的“无聊”行为并不少见,为什么那么多国家,那么多人,对一些难以考证的“起源”情有独钟呢?请同学们回答。
学生:这和教育的起源有什么联系?
教师:这个,我需要稍作引申。追问起源与去向,是人类求知的一种倾向。范伟和赵本山的相声里有一句搞笑的对白:“我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我就想知道我是怎么没的”(学生开始发笑)。从某种程度上说,小到个体生活中的创意、灵感,大到影响人类思想进程的哲学体系,都可能起源于某种“诧异”,包括对“起源”与“去向”的诧异。当人们感到“诧异”时,思考与思辨就可能会产生。原初人类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也许就会追问宇宙的起源与宇宙的边界。这有点类似苏轼在《水调歌头》写的那样: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学生:(开始凝神思考)确实是这样!
教师:回顾源头或起源,也是人类回归精神家园的一种冲动。纳兰性德随军前行,深夜步出帐营,在风雪连天中远眺连绵灯火,不禁感从中来,思乡之情由然而生:“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起源或者源头在遭遇人类现实生活时,会变异演化为对“故乡”“童年”“过去”“经历”“历史”的某种眷恋。当人们感到迷茫、困惑、无根无据的时候,会去思念童年与故乡。在这种暂时性的回顾与回忆中,现实羁绊会瞬间终止,思绪会被转移,痛苦暂时消失。在这种对原处、原始、朴素阶段的回思中,现实中的某些虚无、牵挂、追求,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精神得到某种安慰,驿动的灵魂得到片刻安宁。我相信同学们会有这样的经历,对吗?
学生:是的,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状态。
教师:回顾源头或起源,也是在寻找某种证据来佐证我们的立场与观点。人们将当前的思想散布在追溯源头的行为中。我们知道某些教育活动确实缘起无意识模仿,因而揣测教育起源与心理有关;我们看到某些教育行为和本能与先天联系在一起,因而推断教育的源头根植于动物本能之中,故而有了生物起源说。在很多领域内,有关历史源头的观点,其实都是现实生活的镜像而已。
学生:也就是说,从起源中可以反思当前的教育方式?
教师:对,同学们理解了我说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引申。回顾源头或起源,也可能会被上升到很高的层面,与民族国家的自豪感与认同感密切相关。一些国家,不遗余力地将某些物种、节日、发明,经过所谓的考证之后,纳为己有,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东西可以提升民族自豪感,起着增强凝聚力的作用。在现代社会里,这种行为还掺杂着商业因素。
学生:(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
教师:同学们,现在回头看看,你们觉得没有价值的起源学说,经过这样的解读,有什么启示?
学生:(开始兴奋起来,激烈讨论)……
教师:我来总结一下同学们的观点:启示之一:教育起源说蕴藏着人们对教育的理解。有些教育活动需要模仿,例如中国书法艺术中的临摹与体育教育中的效仿;有些教育确实受制于与本能行为相近的先天素质;有些教育不能只依靠说教,而必须根植于劳动与实践。因此,教育的方式应该是多元的。启示之二: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当我们迷茫、无助、不知“去向”的时候,也可以“小资”一下,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沏一壶香茗,或抬头仰视,或低头冥想,在脑海里梳理一下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童年,我们的“来历”,浮躁的心灵或许就能安静、沉淀下来。
学生:(表情认真,有的点头,有的陷入沉思)
教师:同学们,学习中外教育史,不能像以前那样,死记硬背,不要认为记住了历史知识,就是学得好。要把过去的“记忆”与当前的生活联系起来,并能引导我们进行反思,历史才有价值。请同学们仿照我的方式,自己去阅读教材,在下一堂课上,大家一起分享与交流你们的思考、联想、引申的成果,让我们思想的火花在一起激烈地碰撞。好不好,同学们?
学生:(兴高采烈地表示同意)好!
(二)教学片断后的设计思想
前文提到,我第一次担任“中外教育史”教学时,教学效果不理想,学生评教结果强烈地刺激了我,为什么付出得不到回报。经过一段时间反省后开始意识到,历史本身的严肃性让我们在“历史”面前噤若寒蝉,失去了发言权,不敢多做引申,尽管我备课认真,对教材教案也熟悉,但所讲内容基本都可以在教材上找到,这样的历史教学有什么价值!经过理性反思之后,我开始用自己相对擅长的方式来改变课堂,将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思考融入课程之中,赋予教材中那些“实用价值”不大的内容以深度、广度、品味与灵韵。把教育起源中的“起源”与人类认知倾向、精神家园的冲动、现实社会的诉求、学生的迷茫等链接起来,是完全脱离教学大纲与教材内容的生成课程,在完成教学计划基础上也把自己对哲学、教育与人生的感悟导入课堂。之所以引入韩国的“端午节”一事,是担忧中华传统文化式微局面;之所以引入“人类认知倾向”,是希望学生能对事物保持好奇之心;之所以引入“教育”话题,是为了引导学生关注教育的多元性;之所以让学生“仰望夜空”,是期盼他们能“虚一而静”,保持淳朴、积极与充盈状态。通过教师的示范性展示引导学生以类似方式对课程进行个性化解读,在随后的教学中,学生参与课堂的深度与广度有了较大的拓展。
三、推广:基于后现代课程观的自传式高校人文社会学科课程解读与教学改革
人文学科是以人类精神世界以及精神文化为阐释对象的学科,而社会学科是以人类社会为阐释对象的学科。不可否认,高校人文社会学科课程解读与教学方法还存在太多问题,需要在新理念推动下大胆进行课程与教学范式改革。由于人文社会学科体系繁杂,不适合全面展开研究,比较现实的研究途径是从个案中探索共性问题。选择“中外教育史”进行探索,不仅因为这门课程本身具有人文与社会学科的双重特点,还在于这门课程能典型反映人文社会学科课程与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形而下”层面上尝试“中外教育史”课程与教学范式改革,便于从“形而上”层面上归纳出高校人文学科课程与教学范式改革的某些规律。
(一)自传式课程解读与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意义
从课程认知角度看,长期以来高等院校人文社会“学科”被当作“科学”加以学习,将教科书中的立场、观点、结论等当作“知识”进行传授。人文社会学科确实包含着历史积淀的精神文化与社会科学论断,但在这些精神文化与社会科学论断之外,一些内容仅仅是“观点”与“立场”而已。每一个领域都可以找到大量教材、专著或论文的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个体对人类精神文化与社会现象的理解与建构途径存在差异。人文社会学科应关注这种差异,赋予教师/学生自我建构与体验机会,允许教师/学生进行多元解读。但在实际教学中,受“科学知识”观影响,人文社会学科教学强调“知识点”的传授与学习,导致学科“知识”远离社会、人生、生活与工作。像自传式“中外教育史”那样提倡教师与学生对人文社会课程进行个性化建构,一方面可促进教师“内在自我的流动与开放”,[4]打开封闭的内部,避免固步自封与原地徘徊;另一方面为学生在内部与外部、理论与实践之间,学生与成人世界之间“穿梭”提供了机会。[5]从知识发生学角度看,人类宏大知识“叙事”蕴含着商业、工业、媒体、政治团体、宗教等领域中的权利运作者所希望传播的观点,旨在建立特定领域内的范式与秩序。对于学生来说,它不仅是无形的知识“规训”,也是知识的“霸权”。高校人文社会学科应能引导学生认识自身、认识社会、认识周围的世界,但不能强加给学生某种视角、立场与观点。以情境的、多角度的、质疑的、自传的方式对高校人文社会学科课程进行解读,可以改变“知识”之真理本位、科学本位与霸权本位倾向,拉近理论与实践的距离,促进个体思维水平的提升与“知识的解放”,从而推动人文社会学科的创新与繁荣。此外,在课程解读与教学中,以自传方式审视内在自我,在记忆、联想、预测中判断课程内容对于社会、事业与个体生活的价值,不仅具有成长的价值——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增强学生的洞察力、提升学生的思想,还具有生活的价值——可以通过课程观察周围世界、审视生活的价值与方式。对于教师来说意义也不可小觑。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教师教育研究转向了个人的、情境的、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与经验的研究。[6]这种研究模式将教师的自传或传记纳入了教师与课程研究之中,为教师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可促进教师自我认知与自我超越。教师与学生的自传式课程解读更高层面的意义是以日常渗透的方式推动学校教育实现深层次变革。
(二)自传式课程解读与教学模式的建构
目前,自传式课程解读主要用来研究课程与教师的关系问题,还没有在教学中探索出比较理想的模式。我们在初步探索基础上,认为“基于后现代课程观的自传式高校人文社会学科课程解读与教学”具有三个特征:其一,开放的知识观,认为人文社会学科的某些“知识”是相对的、历史的,可以受到质疑,可以进行引申;其二,课程内容解读是多元的、多维的、个性的,应该结合现实生活对其进行建构;其三,师生的自传式反思是课程内容拓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将其从“隐性反思”转向“显性呈现”。在上述三个理念基础上,我们开始创新课堂教学,初步摸索出教学效果比较理想的操作模式,如图1所示。

图1 自传式课程解读与教学模式框图
在这种教学“模式”中,人文社会学科课程将被视为意义建构的平台,教学(学习)思想从“我教(学)××课程”转向“我解读××课程”;教学内容会在师生双方的个性化解读下,向所有可能的领域延伸;教学过程强调师生的前期准备、课堂交流与课后反思;教学方法注重平等对话与探讨,注重思维与思想的开拓;教学资源由单一生成模式转向群体生成模式,师生与生生“互喻”现象受到尊重与强化。具体过程如下:教学之前,学生与教师以课程内容为载体,展开自我解读:教师将社会、自然、职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反思,与课程内容的某个部分连接起来,并记载自己的所思所想;学生也可以从自己的生活经历、生命感悟、学习生活、理想与梦想等各个角度进行类似思考。教学之中,学生在教师的组织下,分享自己的思考结果,讲述自己的故事,在此基础上进行师生与生生对话。教学之后,师生还可以借助网络教学平台、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工具等进行更多的交流。如此一来,源自教师与学生的或深刻、或鲜活、或新颖、或开阔、或感人的反思与感悟,就可以在课堂上激烈碰撞与交流,“坚硬”的计划课程转变为“柔软”的背景,传统“知识教学”那种直接、简单、单向、枯燥、粗暴的面貌被悄然改变。
[1] 时延辉.威廉·派纳的自传式课程理论研究[D].西南大学,2006(5):16-18.
[2] 胡春光,王坤庆.自传文本课程:历史背景、理论基础与课程诉求[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1(3):1-7.
[3] 杨晓峰.如何面对课程与教学中的创伤性叙事[J].现代大学教育,2010(5):84-88.
[4] 陈雨亭.以自传研究促进学校教育改革[J].当代教育科学,2012(2):12-14.
[5] 代琴.自传课程:穿越成人生活世界的教育之旅——基于后形式思维与生活事件模型[J].当代教师教育,2010(4):81-85.
[6] 陈雨亭.寻找自我的内部力量:自传研究方法、教师研究与我[J].当代教育科学,2009(20):3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