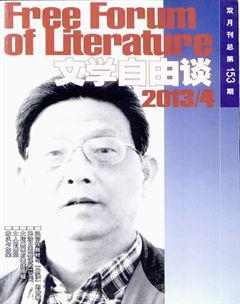三分人事七分天
王彬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纠结于椴树与菩提树。原因是2012年我与妻子去欧洲旅游,曾经在柏林的菩提树大街行走。几天之后到了巴黎,也是这样的树,碧绿的心一样形态叶片,发出悦耳的喧哗。导游告诉我这是巴黎著名的椴树。同样的树,怎么会有两种名称?而且在我的内心,始终有一个疑惑,菩提树是热带树种,怎么会在德国生长?后来明白了,这是中国人的错译而与德国人无关,在德国就叫椴树大街。在日耳曼人的心目之中,椴树具有神圣意味,犹如菩提树在佛土受到尊崇,是不可以亵慢的。
我之所以写下关于椴树与菩提树,这样一点辨析性的感想,是因为维也纳的方丽娜。2010年春,方丽娜到鲁迅文学院进修,准确地说,她是第一个到鲁迅文学院读书的海外华人。在我的印象里,小方是一个平静谦和的学生,踏实而不张扬,不像有些人叽叽喳喳。她听说我途径维也纳,执意前来看望,我劝她不要来了,因为我们到维也纳已经很晚,而且下榻的饭店在郊区,但她还是拉着她的先生老沃前来,坚持陪我们观览夜色里的维也纳,在皇宫附近的酒馆里喝啤酒,之后把我们送回饭店。小方说,她们所住的地方与我们的饭店位于城市的两个方向,我估计她与老沃回到家中,至少是次日凌晨,朝霞开始化淡妆的时候了。
在啤酒馆与小方交谈最多的是散文。谈到散文的本质、文学性与生活的关系以及游记在散文中的地位。回国以后,小方给我发来一些她的作品,从而对她的认知也就更为深刻。在我看来,小方的散文,视野纵横开阔,文笔瑰丽流畅,写情与写景,写人与写物,都浸淫着一种独特的魅力。在她的笔端,东方的树叶氤氲着神秘的芬芳,而异域的咖啡,则将杂乱的思绪收敛;丁点儿大的月亮悬挂于希腊宝蓝色的天空,一对海鸥悬在空中,“好似两朵迷途的云”而游移不定;印度女人是曼妙的,绽放敦煌飞天一般的气息,然而印度的女人又是不幸的,“香艳纱丽的背后,埋藏着多少”凄凉与悲哀;蒙巴萨的马赛人是天生的勇士,“仿佛烧焦的木炭,黑亮黑亮的。毫无例外地都裹在一块鲜艳夺目的花布里”,非洲之所以神秘,并不仅仅在于那块土地,而是源于那块土地上的人。“这些面无表情的肯尼亚土著,正是东非高原上最富有神秘色彩的游牧民族——马赛人。”马赛人以好战神勇和高傲闻名于世。那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傲慢与不羁,被西方殖民者冠以“高贵的野蛮人”。
在小方看来:“旅行是另一种阅读”。不仅有“轻音悠远,雪山映照,沙漠苍凉,万流归海”,重要的还在于,“经历了一场心灵的跋涉”。七十二年前的1941年,一群德国伞兵空降到希腊南部的克里特岛,其中有一家名叫“狼”的德国三兄弟,在同一天的黄昏均葬身于此。“站在这块刻有三兄弟名称的墓碑前,读着他们的简短生平”,小方“仿佛看到三张青春洋溢的笑脸,隔着泥土和花朵对我眨眼,微笑”。而在去俄罗斯的飞机上,小方邂逅了一个二战时被俄国人俘虏的德国士兵的后代塔拉斯。父亲死后,塔拉斯一心一意寻求与德国的关联。两年后,他在父亲的家乡汉堡码头上,找到一份小区管家的工作。塔拉斯拥有俄国与德国双重国籍,他“拿出两个护照给我看”。“照片上的塔拉斯很年轻,也很帅,不像眼下的他,臃肿而笨拙。他在“鄂木斯克有一个六口之家,他的俄罗斯妻子为他生两双儿女,他每隔两个月都要飞回西伯利亚来探亲”。关于二战,关于德国士兵,从来都是血腥与罪恶的形象,无论怎样痛斥都不为过。然而,声讨之外,是不是还可以有另外形式的批判呢?小方的《克里特之战启示录》与《西伯利亚的德国人》,其意义便在于此,在看似平实庸常而不露声色,却蕴潜着一种令人悸动的力量。李卓吾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追风逐电之足,决不在于牝牡骊黄之间”,而“风行水上之文”,也“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这是古今中外的为文规律,好文章是决不局促于“寻行数墨”的。
在我读到小方的散文里,当然不止游记一种,也有不少专题的笔墨。对这类散文,我最喜欢的是一篇描写乌鸦的文章:《冬季,从乌鸦开始》,当然这里的乌鸦不是中国的乌鸦,而是从西伯利亚飞来的乌鸦,轰轰烈烈地飞到奥地利过冬,直到“来年四月的复活节前后”,“再集结成群,浩浩荡荡,返回西伯利亚的家园”。“起初,我竟不知道它们是乌鸦,因为这里的鸽子”,“远远地望去,和壮硕的乌鸦并无区别。于是有一天,我问: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鸽子汇集在天空?老沃说:它们不是鸽子(Taube),是Rabe。是Rabe?原来是乌鸦!”
将这种乌鸦的故事,小方讲给她东北的一位朋友,朋友笑她“连乌鸦和鸽子都分不清”。分得清怎样,分不清又怎样?只要写出心曲里面的颤栗也便可以了吧。而我读到这样的文字,却难免心生感触而要啰嗦几句,啰嗦几句北京的乌鸦。如同到奥地利过冬的乌鸦,北京的乌鸦,也是在清晨,从长安街沿线,向北飞,飞到五环路以外觅食,而在黄昏的时候返回长安街,它们往返的路线是固定的,都是沿着北京的中轴线飞翔,在故宫金顶熠熠的上空飞来飞去而极少误差。这当然是现代的北京乌鸦,而在历史上,比如明清之际,那时的乌鸦是另有况味的。明人钱澄之客居京华时写过一首诗,题目是《到京寓增寿寺》:
一路风尘满鬓华,解鞍便宿老僧家。房留官坐监施饭,店与人开带卖茶。庭树午余时击马,钟楼日落乱棲鸦。五更不睡骡车过,铎响铃声枕畔哗。
钱澄之,字饮光,晚年自号田间老人,安徽桐城人,是一个重名节而爱护自己羽毛的人物。崇祯初年,有一个官员拜谒桐城孔庙,仪仗威赫,诸生列队出迎,钱澄之突然挡驾揭帷,斥其勾引奸党,贪赃枉法。明亡以后,钱澄之参加抗清的义军,妻女殉难,澄之与长子入闽继而辗转入桂,继续抗清,后因复明无望,遂归乡里结庐先人墓侧而闭门著书。
他所客居的增寿寺在北京的南横东街,今天已经拆掉。南横东街在长安街的南侧,也非畴昔旧貌。而钟楼在长安街的北侧,“钟楼日落乱栖鸦”,乌鸦们休息的时间没有变化,但是栖落的地点却不一样了。诗中颈联的首句“庭树午余时击马”,也有做“庭树午余时系马”,看似易解,其实是错误的。击马一典,出自“刖跪击马”,说是春秋时的齐景公,大白天的,疯疯癫癫,披头散发驾驶六马拉车,载着妃嫔从后宫出来,被刖跪挡住而击打景公的马,让它们返回去。刖跪对景公说:“你不是我的国君,国君没有你这样的!”听了刖跪的话,景公顿感惭愧,于是重赏刖跪,表示改正。刖跪的故事,后来被引喻为犯颜进谏。这样的典用在钱澄之的身上是妥帖的。
当然,这是中土故事,与奥地利无关,与那里的乌鸦更是毫无关联。那里的乌鸦是从西伯利亚飞来的,与中土有什么关系呢?所谓此乌鸦非彼乌鸦,而我之所以写下这些话,只是我读到小方的散文以后产生的一点随感,好文章是可以使人生发联想的。而写出好散文,一方面源于文学修养,另一方面源于生活开拓与经验的积淀,所谓“到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而在这一方面,小方自有优势。从中土到域外,出谷迁乔,既有中土经验,也有域外经验,如何将这两种经验捏合提纯升华,对小方而言是一个应该思忖的事情。如果一定要做个比喻,这样的经验,中土与域外,犹如结构主义中的互文,在两个文本之间相互移动,是复杂而艰辛的,但又是开放、变异、渗透、欢愉且多声部的,犹如马赛克拼贴,在闪烁的交流之中将题旨推进得更为深远。一座房子与一棵树不同,树自然生长自然存在,相对于树,房子的存在理由则要追溯到建筑师。建筑师伐树盖房子,散文家用语言盖房子,批评家则是对房子进行分析与研究。我不是批评家,只是作为读者,参观了小方的新房子,拉杂写下如上感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