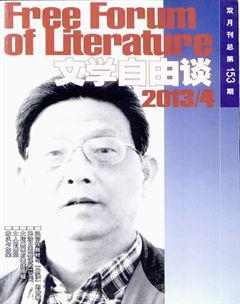激活内心的神圣
黄自华
一
李建纲先生将他跨越半个世纪,有声有色的文学创作,集结成六卷一百六十余万言的精彩文字——《李建纲文存》正式出版发行。文集收录了共六十年文学创作不同阶段的主要文学作品,有小说、散文、杂文、随笔、传记等多种文体。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起,建纲先生就开始了伴随自己漫长人生的文学创作之路,从业余作者,到著名作家。其创作之路都与他所经历的那个跌宕起伏的时代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从文品看人品,读《李建纲文存》,作者那种与生俱来的不依附、不苟且的独立的文学品质会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建纲先生满身正气的傲骨,也许让很多人感到尴尬和不快。尖刻辛辣的文字,曾经剌痛过不少庸官俗吏和主子奴才们的傲慢、自尊。然而,读者喜欢李建纲。喜欢李建纲,是从他幽默俏皮的文字和尖刻锐利的中、短篇小说开始的。当了解他的人品后,又更加喜欢他的文学作品。一个作家的文字固然可以成为个人化的精神舞蹈和个体灵魂的盛宴,但是任何作家都不能自私、残忍地疏远文学应有的精神品质。正是因为建纲先生具有现代精神的思维与精神素质,所以他才能以强有力的笔触、新鲜灵活的方式、丰沛的语言;平等、对视的姿态;独到而优雅的发现和表达方式,进行有别于其他人的文学写作。
建纲先生早年的文学理想,为的是实现与他生存的现实世界全然不同的正义与公平。当他将目光投向自己周遭的文化语境时,文学却作为一个面目狰狞的形象,戴着沉重的镣铐,失去了文学的灵魂。其实,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李建纲便以善于从工厂的现实生活中打捞潜沉的人性,获得优秀青年作家的盛名。在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多数小说作品中,工人是叙述的重要元素,工人的“主人翁精神”是他文学作品的歌颂主体。在他的笔下,工厂也有它自己的生命节律。机器、高炉、钢花、铁流、传送带和巨人般移动的吊车,既怪诞又神秘。虽然在当时由于文学美学层次贫乏,造成文学“审美性”的缺失,致使这种坚守也难免染上一层“文学国营化”即意识形态化的暧昧色彩。但就是在这个阴阳错乱的时代,鬼魅般的记忆,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常青植物,在他个人的经验里留下了一片片荫翳,但他也因此从中获得了感知人性最直接的方式。建纲先生虽然也曾经产生过虚渺的感觉,但他却始终不懈地,以自己微弱的力量,抵抗着那个时代的荒诞。他闯荡在文学江湖上,从微弱的孔隙里敏锐地寻找一些“人性”的碎片,渗透在自己的小说中。他拥有的是他自己的词语、句子,他用思想之刃,划开伪饰的言说,努力用细致准确的语言使其透露一点人性的亮色。
好的文学必定出现在王纲解钮的时代。一个被褫夺了历史话语权的作家,即使是天才也不可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只要他从事的是“良心写作”,那他必定是在对抗、拆解权力话语体系“分配”给他的历史观中,通过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自觉思考和文学实践,建立自己的独立精神人格,并以此直面现实。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满载“文革”残虐而新鲜的记忆,作者投入到了一个喜剧年代的话语狂欢。感谢那个宽松的年代,建纲先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接连发表了《三个李》、《打倒贾威》、《走运的左龟连》、《牌》、《儿子归来》等中短篇小说,揭露极“左”政治的荒诞和残酷。这些小说话语锐利,形象生动,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中,发表于1979年春的《三个李》,被誉为粉碎“四人帮”后描写知识分子的开山之作。《打倒贾威》被选入《新华文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送了一年之久。
建纲先生的小说以讽刺见长。在中篇小说《打倒贾威》中,细节、环境和人物性格的真实性,辛辣的讽刺手法,逼真的肖像描绘,个性化的语言等都取得了极为突出的成就。小说深刻揭露了在“文革”乱世中孳生的“五七干校”连队领导贾威的庸俗、猥琐和疯狂的恶行。贾威在“文革”中横行霸道,“文革”结束又用卑劣的伎俩“洗红”自己,重新掌权,身份的穿越与变幻几乎随心所欲。在小说中,作者虽然刻画的是贾威的丑陋,其实真正的批判指向是腐朽官场的制度性缺陷。这就是《打倒贾威》的文本价值,是小说艺术的核心魅力所在,也是文学的力量所在。在小说《走运的左龟连》和《三个李》中出现的几个“极左小官僚”角色,也让那个呆滞、古板的世界瞠目结舌。建纲先生将自己深思熟虑的东西,尖锐犀利,却又处处印着隐喻、嘲讽的语言,嵌入一个精致独特的话语框架里,寓意在自己的小说书写中,增添、渗透了自己努力探索的那个维度,让习以为常的生活景象和业已失声的记忆图景,变得郁郁葱葱,获得新的理解、新的生命。
建纲先生这一时期的小说,因其思想的前卫、对“文革”弊端的激烈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学理性的深刻性,让刚刚从“文革”噩梦中苏醒的中国读者受到了强烈的精神震撼。他的小说把那些丑陋的灵魂定格在了历史的镜像中,给后来者一种警世的提醒。建纲先生对“文革”历史的大胆逼进,为久别文学“阅读场”的受众,重新找回了一份特别亲切的感觉,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并被当时的媒体赞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学先觉。之后的岁月里建纲先生的小说“与时俱进”,在参悟的心境中,以半个世纪的个体经验,几十年来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变故,用幽默的语言解读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思考那个从病态的概念中寻找英雄与伟大,从阶级斗争火红的血色中获得美感享受的年代里发生的,深刻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历史命运的往事。盘算着如何将我们百年来路上的破碎经验整合与提升,让我们从一处处人性的冷硬荒漠中走出来,让我们互知冷暖而不是漠不关心;如何用文字说出一切需要的忏悔和反思,来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关爱;如何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搭建沟通的语言之桥,使人与人分离的力量重新凝聚。
二
建纲先生长期工作、生活在中部大都市武汉,他的散文也仿佛呼吸过江风吹拂的温润气息。纷乱的都市心灵,居然能够在他的笔下化解成为一种不期而遇的安顿感。故里情怀,蕴涵着直指心源的情感震荡。那种可借以倚傍终生的精神家园,不是笃笃的桨声,不是月也弯弯,水也浅浅,人也悠悠,乡情酽酽,乡风煦煦的田园牧歌式的乡间农舍,而是那深藏着许许多多童年稚趣的街道和老屋,是来自山西老母的谆谆嘱托。建纲先生的散文无论是叙事、抒情还是议论,都与创作主体心灵紧密相联。阅读他晚年散文,那些“性灵文字”给人突出的感受是宁静中弥漫着一种思想的深刻,这种深刻便是他深刻的生命体验的结果。他再也不像三十年前那样,在绚烂的文字里倾注昂扬与激越,而是追求一种随意、一种漫不经心、一种才智与情感的自然流溢。穿越时空的隧道,寻找古朴与深幽;透过弥漫的寂寥,捕捉美丽与情致;以历史、文化作背景,叙说身边的传闻与故事,摄掠凡人的俗事与唏嘘。虽然他的散文灵秀、轻盈、飘逸,但当我们看到作家在与天工造化的大自然作面对面的晤谈,以枯索的市井俚俗进入社会生活的核心,将生命还原于大自然美感瞬间的同时,似乎听到了泛黄的历史碎片,悠忽掀动的喘息之声。
建纲先生的瑞典旅游散文,几乎篇篇都是流淌着水一样的质感,承载着山一样的厚重,披盖着雪一样净洁;充满人道情怀,对一切美好事物充满敬意。由他心间流淌出的歌颂仁爱、赞美生命,发现、感悟自然,崇尚人性、人道、民主、正义,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字,能够净化心灵,启迪心智,是最能代表建纲先生晚年思想艺术日臻完美的散文佳作。他数次前往瑞典,并勾留日久,所以,他能以朴素而简洁的语言,将异国风情、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写得惟妙惟肖、超凡脱俗。作者始终保持叙述的安静状态,让情节、故事舒缓地展开,叙述在回忆与现实中愉快地穿插、轻松地合拢。瑞典美丽、民主、祥和的故事,作者如数家珍。无夸饰、无虚掩、无惊愕,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真情实录。于是,北欧半岛的民俗风情、市井民生以及瑞典人面对生活和世界的乐观、豁达、安逸、镇定与随性,全都通过他灵性的文字,给读者铺设出优雅的阅读语境。只要读者安静地将它读下去,一种缓缓的、柔柔的东西就会带着使命般的力量出现,细细地温润、慢慢地浸入读者的心灵,使阅读者无法拒绝这种感染。
建纲先生晚年的散文,更是高扬现代意识和精神理性,努力保持与社会和时代共进,以实现一个作家应有的文化担当;既有中国古典散文讲究含蓄,以淡为美的意境营造,又融合现代散文语言奔放,感情激越的阳刚瑰丽。他把技巧应用在无技巧之中,不露痕迹,不事雕琢,浑然天成,所以他笔下的人和事总是活灵活现并透出生命的饱满。
三
建纲先生的文学作品,铭刻着他记忆深处的那种浓郁的、难以化开的亲近现实的情怀,他始终让自己保持一种思想者的清醒。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当文学不再面对严峻的现实,丧失直面人生苦难和鞭挞灵魂丑恶的勇气时;当许多作家为了追求写作利益的最大化,制造作家的明星化效应,追求文学的表演性,向市场和受众庸俗趣味退让妥协,而放弃作家内心的挺进和文学对人类精神深度的庄严表现,消解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道义,以空前的速度生产出空前数量的文学产品时;当我们的文字追蝇逐臭般的紧贴着不断翻转的时髦,被俗世的功利扭曲,让灯红酒绿衬托生命的苍白,在狂歌劲舞中宣泄人性的丑恶时,建纲先生却依然孤独地坚守着自己一贯的文学品格和那种难以消解的人文关怀精神。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当代的知识分子,他始终怀着一份沉甸甸的历史使命感,深切关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命运,步步逼近芸芸众生的灵魂与生命本体;代表社会、代表正义对权势与邪恶进行毫不妥协的批判。其实,他又何尝不知道我们的历史与传统,赋予了作家太多的意义和责任,并且远远超出其承载能力呢。与后现代派作家不同的是,那些人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而建纲先生则在对作家身份深感困惑的同时,仍然怀着执著的社会责任感,直面坚硬冰冷的现实。
建纲先生晚年的文学创作完全摆脱了从概念、主题出发的拘泥,逐渐淡泊了那种强烈的社会功利、个人功利的理性工具意识,具有了一种多维的审美体验与感悟,蕴涵了更多的人文关怀意识。这一时期大量小说、散文、无不体现出作者对人生、对世界的精细观察和独到见解。在无拘无束的议论和兴之所至俏皮话中,凝固成了启人心智,风趣、轻松的话语符号,从而让读者与作家一道在恬淡的心境中,共同把玩哲理的碎片,一起分享思维的快感。作者侃侃而谈,大至社会、历史、文学、艺术,小至居家琐事、日常起居、街坊邻里,他都能用细腻、素淡的文笔,画出人情世态、风俗民情的生动图画。
建纲先生的写作风格和迂回环绕的灵魂节奏是一致的。在对心灵最细微处的解剖中,他也经常被意识颠簸的浪尖弄得遍体鳞伤;他善于将感人而丰富的画面并置,在混乱的现实中寻找源头,将人物心理的细腻变化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他希望文学是沉默中的声响,是悲戚时的诉说、是愤怒中的发泄、是麻木时的振奋、是困境中的慰藉、是冷落时的感动、是刺激中的快乐、是丧失时的疼痛;他认为文学天生就应该是一种为普通人群表达心声,激活内心神圣,呼唤渐渐远去的爱心的话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