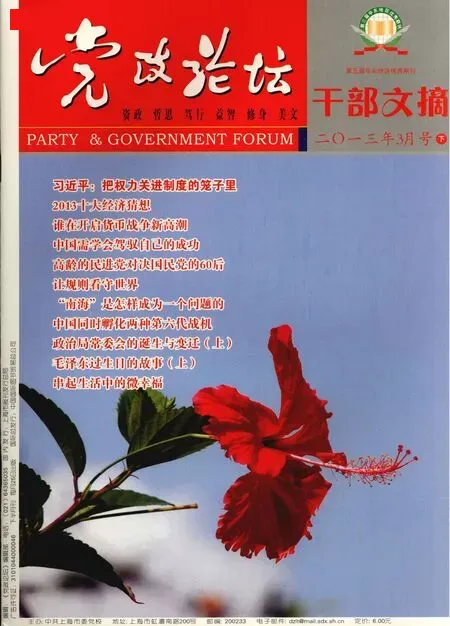《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法国政治
○甘正气
法国有两位伟大的作家,各自写了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伟大作品,他们就是雨果(1802-1885)和托克维尔(1805-1859),雨果的《九三年》、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均是作家生前最后一部有影响力的著作,和各自代表作(《悲惨世界》与《论美国的民主》)相比,篇幅和知名度都要小,但都是被低估的巨著。
读雨果的《九三年》可以感受大革命的暴风骤雨、血雨腥风,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则可认识法国革命前的政治,而这往往是被人所忽略或遗忘的。雨果说:“一件事使我看不见另外一件事”,托克维尔则说得更为明白:“我们离大革命已相当远,使我们只轻微地感受那种令革命参与者目眩的激情;同时我们离大革命仍相当近,使我们能够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加以理解。过不多久,人们就很难做到这点了;因为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便使产生革命的原因消失,革命由于本身的成功,反变得不可理解了。”
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说过:“历史学家恰恰是一批专职的要记住那些他们的公民同胞希望忘却的事物的人。”那我们就通过托克维尔的著作了解一下我们已经忘却的1789年前的法国政治吧。
可以说,1789年前的法国,已经具有较为厚实的宪政根基。
当时的法国司法较为独立。法官实行终身制,不求升迁,司法机关从不存在对政权的屈从,所以托克维尔说:“法国当时因其政治与行政制度已成为一个专制政府的国家,但是由于它的司法制度,法国人民仍然是自由的人民。”

在总体上,刑罚比较温和、轻省,“不愿使人受罪”,并且有“所有被告须在24小时内受审”的敕令,减少了超期羁押和对人身权的恣意侵犯。
有平民、教士、贵族等阶层,选举代表非常严格,履行职责也非常严肃。托克维尔就披露:“在三级会议召开前夕举行的选举中,原来要在第三等级中投票的著名化学家拉瓦锡,被从选举团中除名,理由是,他已购得有资格受封贵族的职位,因而丧失了与平民一起投票的权利。”并且教会较为独立,信仰自由较有保障,虽然路易十四亲自选定教会首脑,但是18世纪末,法国教士仍介入所有国家事务,特别是教会仍拥有财产,这样国家对教会的控制力就大大减弱,正如美国金融之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言:“人性就是如此:控制了一个人的衣食,就控制了他的意志。”
在这样的政治状况下,应该说人民的生活还谈不上“水深火热”,但为什么爆发了激烈的1789年革命呢?
托克维尔谈到了很多可能的原因。在人民性格方面,托克维尔认为法国人对自由具有强烈的热爱和渴求,“他们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他们什么物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
在政府治理方面,托克维尔提及了很多导致革命的原因。譬如官员的无能。“正是那些领导国家事务的人,大臣、行政官、总督,毫无先见之明。他们中间许多人对于本职工作的确都精明强干;他们洞悉当时政府的一切细微末节;但是,一涉及治国这门科学,这门教授如何理解社会普遍运动,如何判断群众精神动向并预见其后果的科学时,他们就和民众一样一窍不通。”
还有贵族和官员所享受的各种特权,托克维尔认为其中最危险的特权是金钱特权。“金钱特权比起权力特权来,危害更大。”因为金钱特权表现最明显,人们对金钱也最在意、最敏感:“金钱特权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这种特权的范围有多大,等看清楚时,便十分不快。金钱特权所产生的金额有多少,它所产生的仇恨就有多少。追求荣誉、渴望领导国家的人,为数不是太多,但是不想发财致富的人却少而又少。许多人对谁在统治他们可以不闻不问;但是对其私人财产的变化漠不关心的,却寥寥无几。”另外,政府还直接参与经营活动,与民争利:“政府变得更加活跃,发起过去连想都不曾想的各种事业,终于成为工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成为王国内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人。与政府有金钱关系、对政府借款颇感兴趣、靠政府薪金维生、在政府市场投机的人数惊人地增长。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
官员对人民利益的侵害,肆意征收百姓的财产缺乏合理的补偿,甚至巧取豪夺不予补偿。“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但是,不尊重私权的政府是人民的坏榜样,革命成功后,人民对旧政府组成人员的“专政”,譬如以革命的名义、国家的名义不经过正当程序剥夺原贵族和官员的财产权、生命权,其实就是下意识地模仿旧政府的作为。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路易十四以后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
但是,在托克维尔看来,上述这些都不是爆发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最主要原因。最主要原因是革命前的法国政府是全能型政府,妄图掌控一切、包揽一切、管理一切,职权过大,“将一切事务无论巨细,都系于一身”,“政府把全体法国人置于管理监督之下”,“政府实际上控制着城市一切事务,无论巨细。所有事务都须征询总督的意见,他对每件事都有坚定意见;他一直管到节日庆祝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公众的喜庆活动也由总督主持,由他下令点燃灯火,为房屋张灯结彩。有一位总督处罚资产者民团成员20里佛,因他们在唱《赞美诗》时缺席。”这就造成了职责繁重、艰巨,而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履行好这样全面的职责,揽一项权,负一项责,就是负一笔债,而履行不好,就会遭到抱怨甚至怨恨,所以全能型政府集中了最大的怨恨。
同时,全能型政府扮演了保护人的角色,这样政府治理下的人民,依赖思想也是最强的,不爱发挥主观能动性,遇到难事只是想到政府,而政府的能力毕竟有限,一旦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就又助长了人们的不满心理。“政府既然取代了上帝,每个人出于个人需要,自然就要祈求政府。农民要求赔偿他们的牲畜或房屋的损失;富裕的所有者要求帮助他们开发土地;工业家恳求给予特权,避免于己不利的竞争。最常见的是,制造商对总督诉说买卖不景气,并请他向总监申请救助或贷款。”
法国大革命前,希望政府能够帮助解决一切问题、处理一切事务的心理已经非常普遍,从中已经可以窥见大革命的端倪,因为一个政府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尤其是一个把自己当保护人和主人的政府,不可能提供足够的供给和完美的服务,当每个人都将自己生活不顺的原因指向政府,当每个人都将不满的矛头对准政府的时候,一个微小的事件都可能成为引爆火药桶的一个火星,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托克维尔写到:“连他们(种田的人)也竟然相信,如果农业得不到改进,应主要归咎于政府,因为政府既不提供足够的咨询,也不提供足够的帮助。一个种田人写信给总督,信的口气很气愤,已预示大革命的来临:‘为什么政府不任命巡视员,每年在各省巡视一遍农作物状况,教育种田人改进耕作方法,告诉他们必须怎样管牲畜、怎样把它们养肥、怎样饲养、怎样出售以及必须赶到哪里上市呢?’”
所以简政放权,不仅是发展的智慧,也是政府生存的智慧。《三国演义》里许褚迎战劲敌马超,就是“却了盔甲,赤体提刀”,我们也常说要抛弃压力和包袱,“轻装上阵”。权力可能是个好东西,但是包揽太多、运用不当,也可能成为烫手的山芋,不仅烫人而且粘人,想脱手都难。所以革命往往与暴力相连,英国偶尔来个非暴力的才弥足珍贵,称之为“光荣革命”。雨果在《九三年》中谈到对大革命中的“流血”的一种代表性观点:“革命要肢解身体,可是挽救了生命。革命在文明身上割开一道很深的伤口,人类的健康就要从这个伤口里生长出来!”
但是如何不“手术”,不“流血”,通过改革来促进改良,以革新代替革命,需要我们深长思之。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给我们指出了法国的病症,改革正在过大关的中国,或许也可以从中找到药方。
杜牧曰:“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王岐山同志向国人推荐这本书,原因可能就在于此吧。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