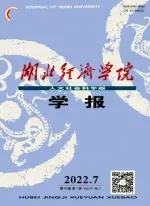语境与翻译实践研究——以语境缺失引起误解的错误分析为例
熊 潇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外语系,湖北 十堰 442000)
语境有着丰富的内涵。在翻译活动中,我们只有深刻理解上下文的语境、情景语境、文化语境的层层包围,经过对语境因素的过滤、筛选、限制、补充,才能真正理解原语文本的内容,才能用译语语言传递原语的信息。否则,仅凭文字字面含义,翻译将无从谈起。
一、源语语境的分析
语义理解离不开语境,成功的语义理解基于对源语语境的正确分析。影响语义的因素既有语篇内部语言方面的,也有语篇外部非语言方面的。在语义理解过程中,译者的文化背景、交际情景、相互关系、性别、年龄、性格、种族、修养、信仰以及他们的面部表情和身势语言都可成为非语言语境分析的范围。因此,分析源语的语境,应把自己放在源语读者的位置上,从自己潜在的认知语境中选择正确的相关语境假设,从源语的语音、句法、词义和语用层等各种线索中推断出源语作者试图传递的意图。译者正确理解源语作者的意图,是翻译交际成功的前提。译者在识别源语交际意图和语用用意后,如果发现按字面意义的直译达不到特定的交际目的和交际效果时,译者可转入语用层面的分析。在进行翻译时,不必拘泥于原文的羁绊,可用多种翻译策略对原文进行改写、替换、删除等等。
语音、语调的不同,营造了不同的语言环境,受话者可根据说话者营造的语境,以及语调所传达的情感和意图,猜测其说话的意图[1]。
如:When in Rome,do as the Romans do.
译文一:入乡随俗。
译文二:上/到什么山/见什么人,唱什么歌。
又如:An old dog like him never barks in vain.Whenever he barks,he always has some wise counsel worth listening to.
译文一:像他这样的老狗是从来不乱叫的。一叫他总有高见值得一听。
译文二:像他这样的行家里手是不会随便发表意见的,一旦发表,总有高见值得一听。
原句的语境是作者以赞赏的口吻谈“old dog=他”的老成持重,所以译文二是切近表达源语的语义的。
二、源语语境的缺失引起的错误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意义随文化的不同也会相应变化。人们需要顺应文化差异才能实现成功的交际。对于源语所提供语境的正确理解是翻译的关键。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文本所表达的意思,翻译就是一件易事。但是,翻译中所出现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因为缺乏对语境的正确理解造成的。理解是翻译的第一步,不仅要理解语篇中的每一个单词、语篇的结构,而且应该理解作者所在的时代背景、作者的语言环境、作者的文体风格以及文化特征。
杨秋娟,李何英,张德先的《背景语境与翻译》一文谈到:语言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小姐”过去指有钱人家的女儿,但现在统称所有年轻的女子,在有些场合还专指风尘女子。同样,“pen”在十九世纪不是指“钢笔”,而是指“鹅毛笔”;“cab”指“出租马车”,而不是“出租车”;“John built a house north of Ottawa.”一句写于十九世纪,意指“约翰亲自动手在渥太华北部盖房”而不是“约翰请人在渥太华北部盖房”[2]。
在翻译过程中,应该针对具体的语境进行翻译,不应是一蹴而就,不考虑各种语境因素进行的乱译和死译。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不分析语境因素也会引起翻译问题。由于两种语言隶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翻译时就会涉及到各自不同的语言特点、语法体系。这些不同之处可能会反映在双方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和句法上。翻译过程中,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不仅反映在词汇上,也体现在句法上,如:
西湖如明镜,千峰凝翠,洞壑幽深,风光奇丽。The West Lake is like a mirror,embellished all around with green hills and deep caves of enchanting beauty.[3]
英语语言中的句子结构重“形合”,而汉语则重“意合”。在翻译这类句子时,特别是句式讲究,句意优美的汉语句子,除了语言文化之外,译者应关注语言结构造成的句法差异,根据语境所提供的英汉语言的表达特点、表达习惯整合语句。
三、源语语境缺失引起错误的原因
(一)源语词汇理解的缺失
任何语篇都包含一系列的符号以及符号的组合来表达不同层面的意思。这一系列的符号以及符号的组合就是词汇。对源语理解的第一步就是是要对语篇中的词汇单位进行分析;词本无义,义随人生,词汇的意义是由生活在一定文化环境中的人赋予的。处于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由于生产、生活、交流信息等的需要给予了词汇不同的意义,而这些词汇的意义通常与他们生活的文化环境相联系,所以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可能会有不同的意义。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一定要注意文化语境对词汇意义的影响,选择最合适的词语。英语词汇与汉语词汇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这就给中英文翻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要想译出它在句中的确切含义,就必须根据上下文,仔细揣摩推敲。否则,就会引起误解。例如:“white”一词,“white coffee”、“white elephant”、“white lie”、“white hope”等等,均应该词与另一个词的约定俗成性,受着后面一词语域的限制而产生不同的含义。他们分别表示:“加牛奶的咖啡”、“无用而贵重的东西”、“无害或无关紧要的谎言”以及“可望给一个队伍或者集体带来成功的人”。再看下句:
1)Snakes are cold-blooded.
2)The cold-blooded murder shocked the town.
3)He gave a cold-blood account of the accident.
“cold-blooded”这个短语在这三个句子中分别受到“snake”、“murder”和“he,account”的制约,因此其意义从“冷血的”就逐渐变为“冷酷的,无情的”以及“冷静的”。不同的语言环境对词汇促使词汇意义发生变化。如果无视其具体的语境,这些句子将很难进行翻译。上面三句分别译为:
1)蛇是冷血动物。
2)残忍的谋杀案使全城震惊。
3)他冷静地叙述了这一事故。
无论是英语中还是汉语中,都有一词多义的现象,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现象,需要根据具体语境做出适当地选择。一个单词出现在一个新的上下文中可能会有不同的意思,逐词(Word-for-word)的翻译,字面上与原文统一起来了,而逻辑意义可能相差甚远。词汇语境的缺失主要是由于英汉语中的一词多义现象引起的,我们在翻译中必须根据源语句子所提供的语境进行分析,避免错误。
(二)源语语法结构的误解
语法是语言的一套规则。它决定一种语言中词汇、短语的组合方式以及一定信息的表现方式。我们知道英汉两种语言各属于不同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是一种以综合型为主要特征并逐渐向分析型发展过渡的语言;汉语则是一种以分析型为主的语言。综合型的语言,英语,通过词汇本身的形态变化来表达语法意义。而分析型的汉语,其语法关系主要不是通过词汇自身的形态变化来表达,而是通过虚词、词序等手段来完成的。这种不同语言的形态特点反映在英汉句子结构上,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英语重“形合(hypotaxis)”,汉语重“意合(parataxis)”。所谓形合就是主要靠语言本身语法手段。所谓意合主要靠句子内部逻辑联系。因此,英语句子结构紧凑严密;汉语句子结构简练明快。针对英汉语语法结构的不同,在翻译时就要根据各自的特点用目标语恰如其分地表达源语的信息。如果分析不够彻底,理解不够全面,那么可能因为源语与目标语语法结构的不同而导致信息量有一定程度的缺失。雅各布森曾经说过:“No lack of grammatical device in the language translation makes impossible a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entire conceptual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original(1996:35)”。这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如果对语法结构缺乏足够的分析理解,翻译时就不可能全部保留源语的信息。例如:
My point is that the frequent complaint of one generation about the one immediately following it is inevitable.我认为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抱怨是难免的。
The composer began his musical career as a violinist.作曲家是以拉小提琴开始他的音乐生涯的。
(三)源语修辞技巧的缺失
修辞是使用语言的一门艺术。人们表达思想时,在语言通顺的基础上,根据题旨和语境,选择最恰当的语言表达形式,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思想感情,并使之富于感染力,这就是修辞。修辞是同语言各要素密切相关的,对修辞技巧的翻译只有建立在对语言要素的综合把握之上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英汉语言中修辞手段的使用是我们从事翻译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从修辞学的角度看,翻译就是用译文语言形式对源语的语言内容进行对应性艺术转换,这种转换首先应保证正确而忠实地传达原文内容,同时还应调动各种技巧,灵活驾驭译语再现原文修辞的风采。使语言生动有力具有对等的修辞效果。英汉两种语言在常用的修辞手段上存在着许多相同相似之处,但又不是一一对应。由于历史发展不同,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的差异,甚至思维方式、美学观念的差别,往往使得我们在表达相同概念时,可能会使用大不相同的修辞手段。如果对源语中的修辞手段不甚明了,一知半解,就不能准确理解原文,更不能对源语的内容进行对应性地艺术转换,也达不到原文应有的修辞效果。a dizzy height(眼晕的高度)并不是a height that is dizzy而是a height that causes people to be dizzy;a sleepless bed=a bed on which the sleeper has no sleep(寝不安枕);a sweet voice(一个甜嗓子);a bottleneck of a crossroad(一个瓶颈般的路口)等属于移就修饰法,如果不了解此修辞格的含义和用法,就不能确切地传神达意。又如:
The silence was deafening.全场鸦雀无声,让人透不过气来。
(四)源语的文化背景的缺失
不同民族由于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文化传统,往往会形成其独特的文化意象。这些意象往往是某一民族所特有,而为其他民族所缺失或错位的。这种缺失或错位现象使得文化意象的翻译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语言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没有不受文化影响的语言,也没有不用语言传播的文化。无论是在英译汉还是汉译英的实践中,无论是在日常交往还是正式场合,由于缺乏对英美文化的了解而造成的误译比比皆是,常常会闹出笑话,甚至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和损失。如在meet one’s Waterloo(遭到惨败)翻译实践时,首先要了解Waterloo指的是什么,当然要了解它就得知道Battle of Waterloo(滑铁卢战役),爆发于 1815年6月 18日,是世界军事史上一次著名的战役,由以法国伟大的军事统帅拿破仑·波拿巴率领的法军对英普军在比利时小镇滑铁卢的决战。由于各种原因,英普军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拿破仑就被迫宣布退位,因此这次战役结束了拿破仑帝国。由此可知meet one’s Waterloo是遭到失败,一败涂地的意思。
看下面的两个句子:
Television has changed the importance of issues.It can be argued that since the 1960 presidential debates we have elected people,not platforms.电视已经改变了政治见解的重要性。可以证明,自从1960年以来的总统选举中,我们选择的是人,而不是政治纲领。
Suddenly,being wined and dined was considered insulting,part of the male conspiracy to keep us (female)in our places,so we got out our chequebooks and went Dutch.突然间,让男人请去饮酒进餐被认为是一种侮辱,认为这是男人们让我们安分守己的阴谋,所以我们拿出自己的支票簿,各付各的账。
所以,了解英美语言国家的文化,是一个英汉翻译者的必修课。对于任何人来说,出国体验这种文化是不现实的,但不能因此就因噎废食,相反,要从实际出发,利用各种现实途径,通过报纸、网络、书刊杂志来积极了解英美文化,切实提高自己的翻译、表达和跨文化交往的能力。
四、对错误结果的评估
翻译是一门技巧也是一门学问,对于翻译中语境因素的研究应该也是一门学问。翻译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离不开语境,语境也是依附于语言的存在而彰显语言的魅力。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将自己融入原文的语境,深刻领悟原文的语境含义、熟识作者的写作背景以及作者的写作特征,只有这样,译者才可以和作者产生强烈的内心共鸣,超越时空的界限,才可以与作者达到心灵的契合,因此译者才有可能将原作的形、意、神准确忠实地再现。译者的创造性劳动也就体现在他必须把原作由语境意义、语言意义和语法意义转化为译作,成为译作所要表达的语境意语言意义和语法意义。
五、结语
在翻译中,单靠词典义项很难将原文的意思传达到位,有时由于语法结构的限制、修辞技巧的运用、不同文化缺乏对等物等等原因,译者只能分析源语中的种种语境,才能恰如其分地选择词义、遣词造句,这样既有“信”也才能“达”。“词本无意,意随人生”,词之所以无定义是由于词的意义只存在于特定的语境当中,词义的确定取决于言语环境,语境的存在使看似简单的翻译变得复杂无比,使翻译从符号的转换上升到文化交流、文学比较、美学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活动。具体的语境决定了翻译过程中的一切细小问题,只有透彻地参悟语境,才有可能用译入语重现原文,达到翻译的最高境界。而翻译过程是理解和表达的有机体统一,正确的理解是准确传译原文内容的基本前提,而准确的表达是再现原文信息的关键。而无论是对原文的理解还是译文的表达都有赖于对语境的把握,尤其是对各种信息的解读。在某种意义上,翻译是理解与被理解的关系。翻译研究不仅要考虑信息的发出者,也要考虑信息的接受者。因此,充分且正确理解原文信息之后便是如何正确表达译文。
[1]Halliday,M.A.K.: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Baltimore:University Park Press,1978;London:Edward Arnold,1978.
[2]杨秋娟,李何英,张德先.背景语境与翻译[J].教学与科技,2003,(3).
[3]郭建中.人间天堂杭州[J].中国翻译,19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