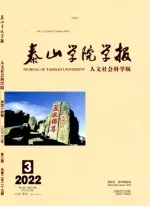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读陈瑞仪的《家在敦煌》有感
张立国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报告文学研究所,山东济宁 272037)
捧读陈瑞仪的《家在敦煌》,首先感到这是一部不错的、独具特色的报告文学作品,继而,引起我的诸多思考。该文发表在《中国作家》2012年第3期,《人民日报》作过简介,《北京日报》(2012年4月17日)进行了转载,现在《中华文化选刊》又全文选登,看来是大家公认的好作品,但一年过去了,为何至今未能引起评论界注意?是作品不值得一评,还是评论落后于创作?我想评论的倦怠或许会产生遗珠之恨,对报告文学的发展是不利的,因此,我想就自己的阅读所感说几句该说的话。在阅读《家在敦煌》的过程中,我产生了三个方面的思考:其一,该作好在何处?独到之处在哪里?一部好的作品,有引发一种文学现象的可能,该说的不能不说;其二,敦煌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我们对文化的思考仅停留在“赵忠祥的水平”上是不行的,伪文化、假文化和泡沫文化将毁掉中国文化这一现象至今无人重视;其三,我们常叹报告文学作家青黄不接,而行业报告文学作家正在兴起,我们对这一现象却缺少足够的重视。
一、独具特色的创作
就当下人们的阅读心理而言,大家对顺向求同的颂歌体报告文学一般都采取排斥态度,认为是宣传、是假大空、是有偿写作、是奉旨写作,而陈瑞仪自甘赔钱跑敦煌、跑北京去写樊锦诗,纯粹出于一种仰慕、一种佩服、一种责任和一种历史使命感。作为文物系统的作家,他觉得不写樊锦诗就对不起中国的文物工作,就对不起中国的文化。他写了,而且写成功了。樊锦诗是当代活着的雷锋、焦裕禄,是科技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的典范。一般写这样的先进人物往往会罗列其事迹,而陈瑞仪却淡化了她的事迹,更重视的是在大家熟视无睹的生活中,发现别人没发现的,感到别人没感到的生活悲喜剧。他从情感入手去写她多舛的命运,而命运多艰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几乎是他们的共性。共同的、共通的命运就使作品和传主吸引住了属于她们的独特的读者群,并影响着这一代知识分子周边的人和对敦煌感兴趣的人。作品的影响力也就自然生成了。
从徐迟的《祁连山下》至今,写敦煌的报告文学虽不能说有成百上千,但早已不是凤毛麟角。在人们快把敦煌写熟写烂的情况下,《家在敦煌》又能一炮打响,实属不易,这与作者的匠心独运是分不开的。
首先,是第一人称自述的角度。这在报告文学作品中虽有,但使用不多,昔日取得成功的是肖复兴的《海河边的小屋》,今日取得成功的是陈瑞仪的《家在敦煌》。一般作者会考虑“客观性”,采用第三人称或全知型第三人称,置身事外,以旁观者纯客观的姿态来写作,借此渲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而第一人称自述,难以摆脱主观之嫌,对于追求真实客观的报告文学写作来说,难度是相当大的。陈瑞仪敢于这样写,而且还写成功了,这与他把握的“度”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他拿捏准了分寸,让传主多说自己,少说别人,就连樊锦诗自己的丈夫、孩子“樊锦诗”也不多说,这就减少了许多争议性的东西,人家自己的事自己最清楚,别人也就难以质疑了。这种大胆的选择和尝试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因为只有这样报告文学创作的路子才会宽广起来。
其次,倒叙、插叙、追述、闪回、穿越的结构方式让人耳目一新。报告文学讲求新闻性,新闻在当下,回到过去总让人感到别扭,往往就与传记扯不清了。其实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不给活人立传的,因此,盖棺定论者应为传记,现实人的成长史、生活变迁史应归属于报告文学。倒叙、追述、闪回均属于忆旧。好的忆旧能引起读者相应的回忆,历史的底蕴、人生的哲理、文化的差异与真谛就在这回忆中产生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一定会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这样?作品的深度和力度也就显现出来。
另外,报告文学排斥虚构。樊锦诗的人生虽多舛,但还谈不上传奇人生,那么作品的吸引力来自何方?陈瑞仪确实动了心思,他用十几个设问制造悬念,调动起读者的好奇心、窥视欲,使人饶有兴趣地读下去。用悬念串联记忆碎片,构成自述性报告文学,这就是该文的最大特征。
当然,使报告文学鲜活起来、生动起来的最大功力还在细节描写上。《家在敦煌》的细节描写不同于一般的场景细节、事件细节、动作细节等的描写,它是着力于近乎琐屑的人物生活情感细节的描写上。如婚姻、旅途、母子等人性人情的细节描写。一般说,情感描写属二度创作,在这里二度创作消失,只有一度创作,这足以使人物还原成真实的、鲜活的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至情至性的感人的人。
我“民啊,民啊”地叫了好几遍,他才睁开眼,大梦初醒样的睁开眼,看着我……他的嘴唇,翕动了,吃力地翕动了,像在叫“妈”。翕动了几次,却都没能出声。一点声音,都没有……我的心,哆嗦了;鼻腔子,酸透了;泪水,更是不知不觉地涌了出来,簌簌落在民民的脸上。起初,他不由一激灵,想抬右手;针械的插拽,没能抬起来。又举起左手,给我擦抹眼泪。擦了这边抹那边。我一动不动,一任他的小手,在我的眼睑上擦来揉去,揉去抹来……我的心被抹软了,揉酥了……
正是这些描写使樊锦诗在读者面前丰满起来,鲜活起来,使作品在看似平淡的自述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二、值得反思的文化现象
我有一个观点:过去“反右”、“文革”等极左政治毁掉了一批人;现在经济大潮又毁掉了一批人;下一步文化也将会毁掉一批人。我不是故作警人之语,在人们看到文化软实力的力量,看到文化产业的巨大利润空间后,伪文化、假文化和泡沫文化开始兴盛起来,弄不好将毁掉中国文化,在毁掉中国文化的同时自然也就会毁掉一批人。
这使我记起赵忠祥在其《岁月随想》中说“在中国,不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是根本没有文化的人,尽管会写几个字,但他还是没有文化的人”。“在诸多要素中,最主要的是要有对本民族文化如醉如痴的一种感情。”我曾戏言,按照赵忠祥的标准鲁迅、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诸君皆是没文化的人,只有赵忠祥才是有文化的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之说,赵忠祥本不该当主持人、当记者跑遍全国周游世界,如此痴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孝子,只应在家门口摆个小摊以奉养老母亲。传统文化坚不可摧,不可动,历史还能发展吗?社会还能进步吗?略萨告诉我们说:“人们嘴里来来回回不离文化,然而他们的言论可能被那些无知的人用来掩饰其真实的意图:民族主义”。
我不是故意把话题扯远,文化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解决的问题。有时处理问题需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简单说,文化就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不断文明化的过程。由于生存条件、历史演进的不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产生了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的差异性。中国文化因其有大一统的形成过程就更复杂、更多元。从春秋无义战到秦统一六国,没有英雄性就无人能统一,而没有奴性你也统一不了。英雄性与奴性就并存于我们民族的文化中。汉朝统治者从“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中尝到了皇权的美好滋味,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儒家思想并不是进入哲学符号系统的哲学思想,只是一种社会伦理思想,但它造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因此,“大一统”和“超稳定”便成为中华民族的一条血脉,成为中国文化的政治核心。其它生活文化、民俗文化都是泛文化。随着历史变迁,每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核心臧否不断,聚讼纷纭。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我们就开始分新文化、旧文化,传统文化就是封建文化、旧文化,西方文化就是殖民文化。到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就又通过反思传统文化来拥抱现代文化。继而,随着“稳定压倒一切”和中国经济崛起,传统文化又成为我们引以骄傲的主体身份和文化认同。但我们的文化自觉在哪儿?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又在哪儿?
我之所以对《家在敦煌》感兴趣,是因为在前面我所说的伪文化、假文化和泡沫文化造成的文化混乱中,该作充分体现了樊锦诗与作者陈瑞仪的文化自觉。写敦煌,一不留心容易滑落进民族主义泥淖,樊锦诗、陈瑞仪没有陷入这一泥潭。在敦煌文化发掘、保护、研究、传承、创新中体现了一种不为世俗撼动,不为新潮左右,不被利益驱使的真正的文化自觉。在这种自觉中他们对敦煌文化的定位是准确的,均认同季羡林的观点:
“世界文化体系中,敦煌是一个极其独特的文化存在。它将(世界仅有的四大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希腊文化集于一身,并且以十分鲜明生动的形象,融会贯通地表达出来。这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是独一无二的。”
敦煌的意义在于古代文化的交流与依存,对敦煌文化的随意拔高和贬低,都是毁灭敦煌文化。
敦煌对于游人是可爱的,但却是祖国最需要的最艰苦可怕的地方。能在那儿安家成为“敦煌守护神”,“前有常书鸿,后有樊锦诗”,这绝不仅仅是两个响亮的名字,在光鲜的背后是苦难。没有对敦煌的酷爱,没有对文化的执着是办不到的。
“真的成了敦煌大家庭中一员,而不是再像实习的时候,被当作客人一样格外关照时,才着实领教了那种令人谈之色变的‘可怕’”。
风沙、鼠害、野兽、苦水、温差、荒凉……这就是现实的敦煌。而支撑他们的坚强信念,就是为了彻底改变“敦煌在中国,研究在海外”的怪谲;为了咱中国人,真正成为敦煌学的主人。
“在我们敦煌人的心中,敦煌就是佛爷,就是宗教,就是中国;而中国就是敦敦煌煌的敦煌!”
“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敦煌,也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不过,在对待洞窟上,两派却有不成文的默契:决不能招引外边串联的人来祸害。“还出现了恐怕是那个年代绝无仅有的一幕:两派合谋,怎么一致对外。真真应验了《诗经》的那句老话,‘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所以,自始至终,洞窟都未遭不测。”尽管江青发了话:“什么莫高窟,精神鸦片!敦煌那些人,都是鸦片贩子!”但敦煌还是在敦煌人的努力下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与曲阜三孔拉着孔子像游街,砸孔子塑像,挖孔子坟,烧三孔牌匾,就形成了鲜明对照。文化的自觉与守承并不是谁唱的调门高就是谁,文化深深刻在人们的一言一行中。
《莫高窟北朝石窟造像和南朝影响》、《莫高窟唐前期石窟形制及题材布局》、《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敦煌北魏248窟考古报告》、《敦煌莫高窟北区发掘报告》等学术论著是弘扬中国文化,而生物断沙、工程挡沙、化学固沙也是弘扬中国文化。不客气地说,“副研”以上专业人员住“四室”,院领导住“三室”的分房方案更是弘扬中国文化。这又使我想到现在不少单位在印春联、送春联,看起来是在弘扬中国文化,而实质上是在扼杀中国文化,如果没人印、没人送,势必大家要想法自己习练、自己写,或不得已求人写,无形中则弘扬了中国文化。说到底现在中国不是传统文化传扬,而是书吏文化弥漫,所以我说樊锦诗和作者是真正懂得文化,有着文化自觉与守承的令人尊敬的人物。在作品中,在她(他)们身上我们看不到书吏文化和书吏气。
我记得报告文学作家丰收说过,“我的孩子琴棋书画都必须会,但目的绝不是成为他们的职业选择,而只是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只要人文素养高了,将来干什么我不管”。我认为对于我们普通中国人,这才是至关重要的,这才是真正弘扬中国文化。因为文化的对象是人,文化的主体也是人。
三、不可忽视的创作现象
现在报告文学评论界有一种共识,认为报告文学创作队伍面临青黄不接,报告文学创作需要更多的生活积累,才能在众多现实遮蔽之中辨识真伪,这对年轻人是一种挑战。同时报告文学作者也需要一定的行政能力,才能便于去调查采访,因此,一般文学青年很难达到。而有偿写作、奉旨写作,人家权贵一方一般要找名流或准名流作家,谁也不会花钱去雇文学青年,这就使青年人很难在报告文学这块园地里有所作为,故而造成报告文学创作队伍的青黄不接。
读罢《家在敦煌》,看到陈瑞仪的成功,“行业报告文学作家”的概念突然闪现在脑海。行业报告文学作家的兴起,或许是解决报告文学创作队伍青黄不接的最佳路径。
仔细回忆报告文学文坛,李鸣生身为航天人,由写“航天四部曲”而成名;赵瑜是运动员出身,以“体育三部曲”称霸报告文学文坛,随后才有《寻找巴金的黛丽》;李青松是国家林业局森防总站的党委书记,他的报告文学基本都是在写与林业有关的题材;其实,理由的出道也与他的体育教练员身份不无关系,他的《扬眉剑出鞘》和《倾斜的足球场》都是写体育的;作为鲁西监狱办公室主任的姜良纲正是靠着《中国有座鲁西监狱》而一举成名;志愿军战俘张泽石写了《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六十年回忆》和《孤岛——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在台湾》,人们才记住了张泽石这个名字……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我们无须一一列举。纵观报告文学发展史,从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报告文学的创作队伍是记者、作家和广大工农兵,广大工农兵可能在《上海一日》、《陕北一日》、《冀中一日》中留下一两篇作品,但很难成为报告文学创作主体。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报告文学创作队伍基本是记者与作家,有意思的是“文革”中报告文学并未消失,反而大行其道,但作者都是“本报通讯员”和“某某写作组”,其成份难以考察。自“文革”后,特别是80年代报告文学轰动时期,一些行业的文学青年就开始从身边、从自身熟悉的东西入手,实事求是地去写,如一些知青去写知青的报告文学和通讯特写,从而进入作家队伍;一些军队通讯员去写军旅报告文学,而取得成功,各行各业均有在此显露头角者,他们的才华得以展现,报告文学作者的队伍得以扩展,行业作者、行业创作应是成就报告文学作家的一个重要途径。
首先,他熟悉情况,有一定的专业素养不会说外行话,因为是内行,他更容易抓到事物的关键,更能体现一种专业精神。陈瑞仪是泰安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对文物考古了然于心,因此对敦煌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怎么写,他心中有数。
其次,作为行业内人员,采访、调查总比外人方便些,即便是缺少一定的行政能力,往往也能在一定范围内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关照。例如国家文物总局的领导几次点名让陈瑞仪参加会议,这就为他的采访提供了方便。
另外,行业内作者一旦小有成就,或得到领导重视或面临压力,这二者都有可能成为其成才的条件。
因为行业写作,特别是某些狭窄领域的专业写作,很容易被大量的文化垃圾、文学垃圾所淹没,因此,我们应重视行业内作者的成长与发展,评论界应该更多关注他们的作品,为报告文学的发展,为报告文学作家队伍的发展尽一份自己应尽的义务。
——樊锦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