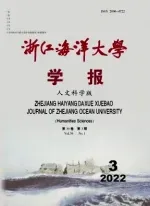“心为思官”:汉语“心”的思维隐喻哲学疏解及语料分析
方丽青 姜渭清
(1.浙江农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 临安 311300;2.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心为思官”是中国哲学中关于“心”的学说之核心观念之一。与西方文化的“心主情感,脑主思维”的二元观点截然不同,汉文化视“心”为认知的中心器官,不仅主性情,而且是能思能知之官。“心为思官”或“脑为思官”,业已成为了中西文化的一大分野。西方文化中由“人脑”承担的认知功能,中国文化赋予“心”来完成。中国的“心”,被概念化为认知中心,是思维和行为导向的器官。在中国哲学中“心”是重要的文化符号,超越了其器质意义,成为了一个概念隐喻。近年来,不少学者[1-6]围绕“心”的各种隐喻现象进行了研究。方丽青[7]以《红楼梦》原著及杨宪益、戴乃迭英文译著为语料,进行了汉英语料的分析、对比和求证,发现“心”的思维隐喻在英语译文中无一例使用对应词heart,进一步验证了思维之“心”的汉文化特质。我国有关“心为思官”隐喻的研究总体相对较少,而且缺乏语料的支持,本文拟对该隐喻的哲学成因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以古典小说《红楼梦》为研究语料,进行语料的归类、分析、验证,并讨论与之关联的隐喻性语言表达。
一、隐喻理论概述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们赖以思维和行动的概念系统,从本质上讲是隐喻性的。隐喻不仅是修辞手段,也是认知方式。[8]隐喻(metaphor)就是用彼事物来理解此事物,即把具体概念域作为源域(source domain),抽象的概念域作为靶域(target domain),借助于意象图式来实现始源域与靶域之间的结构映射(mapping),以达到理解的目的。隐喻的工作方式是映射,理解路径是通过源域理解靶域。
每一种语言都包含大量的隐喻体系。隐喻来源于我们的经验基础(experiential basis),所有隐喻,如果独立于经验基础外,不可能理解和表达。各类反复出现的身体经验会逐渐形成意象图式或认知格式塔(gestalt),并提供大量的约定性隐喻的认知、生理和神经学基础。[9]我们的经验基础既有普遍性,又有文化性。隐喻反映了深藏其背后的文化预设,同时隐喻的选择又为文化模式所限制。但是,不同文化的概念隐喻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在多大程度存在、以何种方式存在,则有待跨语言和跨文化的研究来发现。[10]
二、“心为思官”隐喻的哲学疏解
第一个注重“心”的,可以追溯到先秦哲学家孟子。他认为“心”与耳目等感官一样,是思维的器官。[11]孟子说:
(1)“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
孟子认为,耳目等感官不能思,与外物接触时容易被吸引而误入歧途;心能思,而且以思为职任,这是孟子心说的要旨。孟子对“心”的认识,实际上反映出先秦及秦以后哲学家对“心”的认知能力的认识。朱熹也将“心”分作“肝肺五脏之心”与“操舍存亡之心”,前者是“实有一物”,所指器官,后者是“神明不测”,所指思维,思想。二者之区分是物质与精神的一大分野。这说明思维、思想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系统,非器质之心所能管摄。[12]
(一)心为知官
“心”之所以能思,是因为它“有感而知”,心乃能知之官,知觉是心的特殊功能。心学大师王阳明认为:
(2)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之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王阳明《传习录》下,第322条)
(3)“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王阳明《传习录》上,第8条)
荀子、朱子等哲学家对“心”的知觉功能亦有表述:
(4)“人何以知道?曰心。”(荀子《解蔽》)
(5)“人之一身,知觉运动,莫非心之所为……”(朱熹《答张敬夫论中和》)
心之灵处,在于它的知觉能力。古人认为心能徵知,能察而知之,能缘耳知声,缘目知形。无心,虽有感觉亦不能有知识,徵知是心的特殊技能。[11]心不仅能感知现在,还能“藏往知来”,即具有记忆往事、预知未来的能力。
(6)“心官至灵,藏往知来。”(朱熹《朱子语类卷五》)。
心能知万物,能思虑无穷,察辨极微;耳目知视听,手足知痛痒,其知觉之源泉便是心。心是灵明,知觉是心的特质,这也是中国哲学家的共同观念。古人对心还有更为重要的理解,那就是道德知觉,即“知善知恶”之知觉。朱熹将心区分为“人心”和“道心”,指出心除感官认知能力外,还具内在的道德理性:
(7)“人自有人心、道心,一个生于血气,一个生于义理。饥寒疼痒,此人心也。恻隐、羞恶、是非、辞逊,此道心也。”(朱熹《朱子语类卷六二》)。
朱熹强调心的“虚灵知觉”,即不能“尘垢之蔽”,而要“本体自明,物来能照”:
(8)“心犹镜也,但无尘垢之蔽,则本体自明,物来能照。”(朱熹《朱子全书》第22册)
(9)“心之知觉,又是那气之虚灵底。聪明视听,作为运用,皆是有这知觉,方运用得这道理。”(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
王阳明亦有类似表述:
(10)“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王阳明《传习录》上,第122条)
此“能”字应作“良能”解,是指道德本性的“良能”,是一种道德能力或判断力。[13]
在他看来,心的道德知觉,才是阳明心学中的根本义。这个“心”也就是“汝之真己”,真己才是躯壳的主宰。
(二)心为主宰
古代哲学家强调,心作为思维器官具有两种功能性特征:心是“知觉”,心是“主宰”。心虽然依存于身,却是一身之主宰,支配着形体的行为。王阳明认为:
(11)“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动者心也。”(王阳明《传习录》下,第317条)
(12)“视听言动皆是汝心。汝心之视,发窍于目;汝心之听,发窍于耳;汝心之言,发窍于口;汝心之动,发窍于四肢。若无汝心,便无耳目口鼻。所谓汝心,亦不专是那一团血肉。”(王阳明《传习录》上,第122条)
朱熹也认为精神的“心”主宰着物质的形体,他说:
(13)“心,主宰之谓也。(朱熹《朱子语类卷五》)
(14)“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
心之特质为觉,而心之觉,实以感官为凭籍。[11]此能知觉之心,乃是身之主宰。有学生问:“形体之动,与心相关否?”朱熹答:“岂不相关!自是心使他动。”(朱熹《朱子语类卷五》)
关于“心”的主宰义,古人以“君臣”比喻“心与感官”的关系:
(15)“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有职,官之分也。”(管子《心术》)
(16)“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荀子《解蔽》)
(17)“一国之君,其犹一体之心也。……内有四辅,若心之有肝肺脾肾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体孔窍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地之行》)
“心”已被拟人化,如同君主统治国家与人民,心统率全身脏腑、经络、形体、官窍,主司意识、思维、情志等精神活动。故《素问.灵兰秘典论》说:
(18)“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
正因为“心”是人之主宰,是思维和行为的中枢,古人视它为修身的重要落点:
(19)“故欲修身在于体当自家心体,……主宰一正,则发窍于目,自无非礼之视;发窍于耳,自无非礼之听;发窍于口与四肢,自无非礼之言动。此便是修身在其正心。”(王阳明《传习录》下,第317条)
(20)“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见色,耳不闻声。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管子《心术》)
只有保持正常心,才能有条不紊地发挥九窍等各器官的作用;如果心里充满嗜欲杂念,违背了清静寡欲的基本规律,眼睛就看不见颜色,耳朵就听不见声音,各器官也就会失去应有的作用。因此,古人认为一个人的道德品行体现在心上。
(21)“心不可以不坚,君不可以不贤。”(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地之行》)
(22)“圣人之学,心学也。”(《王阳明全集》卷七)
追根溯源,“心为思官”隐喻的原始触发点源自“心主身”这一哲学本喻(root metaphor),“心主身”和“心为思官”是两个上下位隐喻,形成了套叠关系。古人“以君言心”,使人们透过源域“君”的概念图式来理解目标域“心”,“心”和“君”两者是对应关系。有关“心为身君”隐喻,NING Yu[14]做了甚为详尽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尤其就“心”和“君”的图式对应和隐喻映射关系做了清晰的图标分析。正因为心处“君主”之位,它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人的中央控制系统,操控思维,支配行为。
三、“心为思官”隐喻的语料分析
语言是文化的镜子。主心说可以从古代的造字法中找到依据。古人常把与人的精神现象有关的字加上“心”字和“忄”旁。许慎的《说文解字》中280个与精神现象有关的文字,都含有“心”(“忄”)部首。[15]小说《红楼梦》规模庞大,人物众多,描写细腻,尤其通过对人物内心活动的精妙刻画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成为该小说的一大亮点。小说前五十回与“心”有关的语言表述有1021处,其中有许多是“心主思维”的隐喻性语言现象。下面以《红楼梦》语料为例,围绕“心”作为思维器官或意识活动所具有的功能性特征,从知觉义(感官知觉、认知知觉)和主宰义两个层面作一分析归类。
(一)“心为知官”隐喻性语言现象
1.心能感知。心是身体知觉的源泉,其本身也具有感官知觉:
(23)薛姨妈又是心疼,又是发恨。
(24)薛蟠听这话,喜的心痒难挠。
(25)贾政听明,虽不理他,但是心里刀绞似的。
心的感官知觉不仅包括“知疼知痒”,还知“冷热酸甜苦辣”等:
(26)那黛玉此时心里竟是油儿酱儿糖儿醋儿倒在一处的一般,甜苦酸咸,竟说不上什么味儿来了。
(27)想到此际,脸红心热,拿着针不知戳到那里去了。
(28)宝玉慌了,只说“了不得了!”袭人见了,也就心凉了半截。
(29)贾母薛姨妈等都看的心酸落泪,也有叹的,也有骂的。
(30)宝钗笑道:“呆香菱之心苦,疯湘云之话多。”湘云香菱听了,都笑起来。
(31)月里出阁我原想过来吃杯喜酒的,不料我家闹出这样事来,我的心就象在热锅里熬的似的,那里能够再到你们家去。
2.心能认知。心除能感知外,还具有认知能力,能对感知的信息进行思考、加工,达到“察觉、领会(悟)、判断”等认知效果:
(32)宋嬷嬷听了,心下便知镯子事发。
(33)士隐本是有宿慧的,一闻此言,心悟。
(34)今见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觉察一半了。
(35)(贾琏)又怕贾珍吃醋,不敢轻动,只好二人心领神会而已。
根据心对信息的感知和领悟程度,有“心里也明白”或“心里糊涂”等表述。心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决定了其道德能力或判断力,因此,心能“知对,知错,知惭愧”,如
(36)凤姐开眼瞧着,只见贾母进来,满心惭愧。
(37)怎奈钱槐不得五儿,心中又气又愧,发恨定要弄取成配,方了此愿。
(二)“心为主宰”隐喻性语言现象
心可以主宰身体的各种感官运动和肢体运动,如视听言动。视和听是“心”接受信息的能力。LAKOFF等[8]认为,理解就是看见(Understanding is seeing),在汉语的概念里,作为思官的“心”是可视的,它带有眼睛,如“心眼”,
(38)刘姥姥笑道:“我的嫂子,我见了他,心眼儿里爱还爱不过来,那里还说的上话来呢。”
(39)这袭人亦有些痴处:伏侍贾母时,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如今服侍宝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
(40)今智能见了秦钟,心眼俱开,走去倒了茶来。
正因为“心”有眼睛,它能看见或看清事物:
(41)你这个丫头就不是个好货!想来你心里看上了,却拿我作筏子,是不是呢?
(42)凤姐儿说道:“老祖宗别管,我心里看准了他们两个是一对。”
“心”能视,也能听,如
(43)内中有一个人听在心里,掷了几骰,便说:“我输了几个钱,也不翻本儿了,睡去了。”
心能支配语言,用话语方式输出信息:
(44)(宝玉)定神一想,心里说道:“是了,我是死去过来的。
(45)见那一间配殿的门半掩半开,宝玉也不敢造次进去,心里正要问那和尚一声,回过头来,和尚早已不见了。
(46)那一天我瞧见厨房里柳家的女人他女孩儿,叫什么五儿,那丫头长的和晴雯脱了个影儿似的。我心里要叫他进来,后来我问他妈,他妈说是很愿意。
“心”还会实施“骂人、叫苦、笑”等信息输出行为:
(47)嘴里不好意思,心里不知怎么骂我呢。
(48)(宝钗)只是心里叫苦:我们家里姑娘们就算他是个尖儿,如今又要远嫁,眼看着这里的人一天少似一天。
(49)贾蓉起先听他捣鬼,心里忍不住要笑。
心能支配动作,下面各例均表示“心动”:
(50)宝玉听他提出“金玉”二字来,不觉心动疑猜。
(51)谁知狗儿利名心最重,听如此一说,心下便有些活动起来。
还有“心活、心死”等:
(52)一回夸奖,一回奉承,把老太太的心都说活了。
(53)袭人笑道:“他们两个都不愿意,我就和老太太说,叫老太太说把你已经许了宝玉了,大老爷也就死了心了。
“心”的活动方式五花八门,有“心中打算,心里有数儿、暗忖、沉思、品度、踌躇、疑惑、纳闷、烦闷、相信、打定主意、后悔”等,不胜枚举:
(54)门房签押等人心里盘算道:我们再挨半个月,衣服也要当完了。
(55)探春道:“可不是,外头老实,心里有数儿。”
(56)我心里却有一个算盘,还不至如此田地。
心能“视听言动”,反映出了古人“拟人”的隐喻性思维模式。LAKOFF&JOHNSON[8]认为,“拟人”现象,即用人类行为和特性来理解非人类实体,是一种很常见的实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
心能知,故能思。心所以能思能知,因为心统身,为身之主宰。“主心说”反映了汉文化一种特有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并在汉语言文字系统里留下了深深烙印,使“心为思官”隐喻成为了一种规约化的认知和语言现象。
[1]王文斌.论汉语“心”的空间隐喻的结构化[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24(1):57-60.
[2]张建理.汉语“心”的多义网络:转喻与隐喻[J].修辞学习,2005(1):40-43.
[3]张建理.英汉“心”的多义网络对比[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6(3):161-167.
[4]吴恩锋.论汉语“心”的隐喻认知系统[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6):49-55.
[5]齐振海.“心”隐喻词语的范畴化研究[J].外语研究,2004(6):24-28.
[6]齐振海.“心”词语的认知框架[J].外语学刊,2007(1):61-66.
[7]方丽青.基于《红楼梦》汉英语料的“心”的思维隐喻研究[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0(4):83-87.
[8]LAKOFF G,JOHNSON M.Ma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
[9]刘正光.隐喻的认知研究——理论与实践[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93.
[10]蓝纯.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129.
[1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12]汤一介.中国儒学文化大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23.
[13]吴震.《传习录》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65.
[14]Ning Yu.Heart and Cognition i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J].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Culture,2007(7):27-47.
[15]燕良轼.中国古代的主脑说与主心说[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26(5):3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