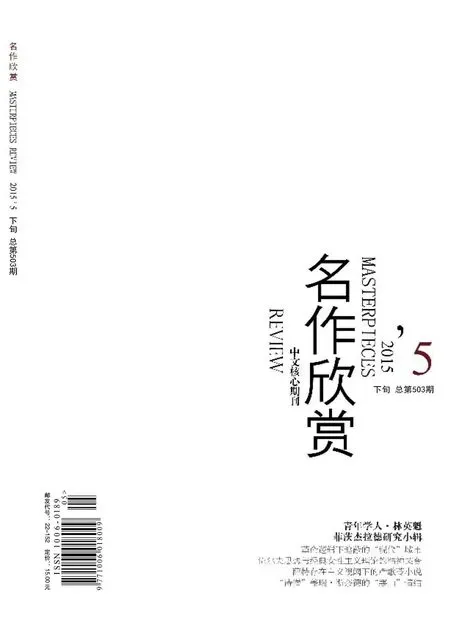流动现代性语境中的微博时尚现象
⊙陈志远[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南京 210097]
齐格蒙特·鲍曼是当代西方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最著名的社会理论家之一。他对现代性的分析和批判,以后现代性为参照系,以各种隐喻的修辞手法来分析和批判现代性。他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放弃了“后现代性”概念而代之以“流动的现代性”。
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齐格蒙特·鲍曼富有创造性地将“流动性”一词引入现代性的思想领域,他剖析了“流体”和“固体”的时空特性。他指出,“流体”易于连续地改变它的形状;对流体来讲,正是它时间上的流动(即时间之维)显示出其存在的重要性,而对于“固体”,其存在的空间(即空间之维)才是其存在的核心。他认为现代性是一个从起点就已经开始“液化”的进程,其主要的消遣方式和首要的成就是“溶解液体中的固形物”,换言之,现代性从它的萌芽时期起,就一直是“流动性的”。在他的流动的现代性社会理论中,对于时间/空间和个体性给予了新的阐释。
一、流动的现代性
1.对时空观念的新阐释
时间和空间作为哲学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无论是从古希腊巴门尼德所追求的“不变的一”到芝诺的“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飞矢不动”,还是到近代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圣人先哲从动态、静态的相互关系中去探寻时空的奥秘。时间和空间作为人存在的两个维度,在前现代,由于科学、技术和人的实践能力的局限,时间与空间多是固态的、凝固的。人们感受到的时空的流动和变换的频率是有限的。可是在流动的现代性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中的时空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语境中,现代社会产生于时间与空间的分离。时空的分离,让主体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感受到的是“时空结构已开始变化。由于通讯系统的改进,距离缩短了。由于城市生活的狂热节奏强加于社会的广阔领域,事件的发展更迅速了,整个生活的节奏也加快了”①。正是在这种时空分离的背景下,鲍曼把现代性划分为固态/沉重的现代性和流动/轻巧的现代性。在固态/沉重的现代性时代,“惯例化的时间将劳动和土地结合在一起,而工厂建筑物的宏大、机器的沉重和——最后但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持续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都和资本联系在一起了”②。正是在这种沉重的现代性语境下,人们感受到的是时空的彼此牵连。然而,“在以光速运动的宇宙中,空间简直可以在‘须臾’之间穿越;‘远在天边’和‘近在眼前’之间已经没有差别了。空间不再对行动和行动的绩效产生约束,空间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或者根本没有意义”③。在鲍曼的理论中,轻巧的现代性正是时间意识对空间观念的一种逃离。逃离,亦即一定程度的流动。
2.对个体化的重视
时间和空间是人存在的一个场域的两个维度,恰如马克思所言:“这两种存在形式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仅仅存在于我们头脑之中的空洞的观念、抽象。”面对现代社会“高速度、高效率”,现代社会时空置换的“高节奏”,人们会发出“叫停时间”的希冀。“‘山静如太古,日长似小年’。时间在隐沦之中停滞。如何叫停时间、欺骗感觉?这种静止感,是用近乎永恒的体验扼杀时光。……然而,悖论的是,‘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停滞的时间,竟换得飞驰而超速的历史。”④在这里是作者作为主体存在,期待的就是“叫停时间”,在时间停止的刹那间,体味个体瞬间的此在与永恒。
在前现代时期,尤其是中世纪,“时间在本质上是按照神学思想来理解的,它被看做人类生命短暂性的明证,是对于死亡和死后生活的一种永恒提示”⑤。在这一时期,人们感受到的是神学时间,生活在固定化的空间下,主体性意识尚未觉醒。随着文艺复兴的兴起、现代时期的到来、人的主体意识的加强,人作为自在自为的存在,开始亲身体验属于自我的时空。直到康德指出“人为自然立法”,人的主体性攀升到了最高点,现代性是随着现代主体的诞生而产生的。
在鲍曼看来,尊重社会个体成员和关注个体成员的生存境况的变迁是其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个体性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性和差异性。而在鲍曼看来,个体性、自由和尊严三者是紧密相连的一个整体,也就是说,个体的存在就必然具有这三种相互关联的价值。”⑥个体的自由和尊严离不开社会的“共同体”。那么,当个体在面对社会“共同体”的时候,如何存在呢?“占有”和“存在”作为两种对立的生活模型,在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视域下,它们的对立性被消解了。他指出,“占有”关注个人与事物的共处,而“存在”关注的是个人与之共处的人性。其实,无论是占有还是存在,都有一定的依附关系,前者依附的是财富,后者依附的是他人。可是,面对流动的现代社会出现的“立即的变化、突然的变化”,个体要求摆脱对他者的依附。只有这样,个体才能够用亲身的体验来感受自我与生活的联系。
二、微博时尚的“流动性”特征
时尚作为一个舶来品,英文“fashion”在朗文词典中词目是“thepopular styleof clothes,hair,behaviour etc at a particular time,thatislikelytochange”译为“在一段时期内,衣服、头发和行为等流行式样,并且容易发生改变”。在理论领域,伊曼努尔·康德、恩特威斯特尔和齐美尔等都对时尚做过解说,但是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见解。挪威哲学系教授拉斯·史文德森在《时尚的哲学》中提出:“一般说来,可以将我们所理解的‘时尚’区分为两大类:一类认为时尚就是服饰,另一类则认为时尚是一种总体性机制、逻辑或者意识形态作用于众多领域,而服饰领域只是其中之一。”⑦诸位理论家虽然没有对时尚的界说形成统一认识,但是,时尚的新颖性和流动性特征获得了一致的认同。康德指出“所有的时尚,就其本质而言,就是生活之多变的方式”⑧。“多变”指出了时尚的追新和流动的特质。时尚是“在对转瞬即逝、昙花一现、过眼烟云之物的抬升,对动态主义的欢庆中,同时表现出一种对纯洁而驻留的现在的渴望”⑨。“转瞬即逝”“昙花一现”“过眼烟云”精准地剖析了时尚的流动和求新的特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电脑、手机的快速普及,近年来在中国的传播界,“微博”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微博”,即“微博客的简称,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的平台,用户可以通过WEB、WAP以及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以一百四十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⑩。“微博”融入了流动性、个人性、即时性、互动性,将自己打造为一个开放式的信息分享平台。近年来,微博首先在社会年轻人群体中广泛传播,他们生活在“流动的”现代社会,通过微博表达瞬间的自我,这种表达方式不再受到时空的限制、表达模式多是碎片式的。随着微博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传播,人们在追新的心理作用下,通过微博展示自我成为一种时尚。随着微博自下而上的流动,各类有影响力的媒体相继开通微博,如:人民日报微博、新华网微博、凤凰微博等等。它们这些媒体希望通过微博的即时性,来向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及时传递信息。各个政府的官方微博的也相继开通,如:上海发布是上海市新闻办的官方微博、外交小灵通是中国外交部的官方微博、微言大义话教育是教育部的微博等等。它们希望通过微博的个人性与互动性,及时了解民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流动的现代性”社会生活中,微博时尚对人们的生活、生产和生存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微博时尚成为社会生活的常规后,它存在方式的流动性和思维方式的碎片化成为其典型特征。
1.存在方式的流动性
流动的现代性社会,时间和空间不再合二为一而是时空分离,空间被时间所控制。时空分离,是现代性的前提。鲍曼提出的“流动性”不仅是对现代社会状态的一种独特描述,同时也是对处在该社会中个体生存境遇的一种概括。社会个体存在的流动性是指生活在现代性社会之中的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人际交往互动模式发生的流动与液化的转变。现代人,正如鲍曼所言:“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移动着。”⑪这里的“移动着”就是指生活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时空置换的快节奏。在这种“移动着”的现代社会中,随着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迅猛发展,人际交往克服了前现代社会的那种时空局限,变得更加便捷。“流动的现代”社会下的个体,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发出个体自我的思考。
2.思维方式的碎片化
鲍曼指出:“在‘流动的现代性’时代的所有烦恼中,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不可靠性(insecurity)和不安全性(unsafety)是最险恶且最令人痛心者。”⑫面对这种不确定的现代社会,个体展现出自我的焦虑。个体为了确认自我的存在,试图寻求一种身份确认的方式。于是他们通过发“微博”,获取一定程度的关注,来让自己获得一定的存在感。这就像恩特威斯特尔所说:“在像现代社会的这样一个世界里,时尚获得了一种新的含义:它是现代人用来确认其身份认同的一种工具,人们借助时尚与衣着可以隐秘地漫游于城市(或者相反,借助时尚的魅力而引人注目),由此,时尚与服装成了保护个人生存的一道必要的‘屏障’。人们可以用时尚来为自己获得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个体的’身体特征,但与此同时它也可能凸显出一致性,因为时尚本来就是对某种清一色的东西的强化。”⑬
碎片化是与整体性相对的,整体性就是指个体在“固态的”时空下做出的系统完整的思索。碎片化是指,在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中,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呈现出破碎的状态,不再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伦理、文化传统或宗教信仰基础上的集合体。个体生活在“碎片化”社会中,感受到的是时空的分离,逻各斯中心的消解,内聚力的消散。因而,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体,通过对时尚的不断追逐,去获得个体存在的确认。在现代社会,个体就是通过“微博”这一新的时尚,不断地更新自我的心情,发出“碎片化”的思考,凸显个体的存在。
三、微博时尚的意义
在流动的现代性语境下,微博时尚以其发布方式简单、快捷,赢得了众多人的青睐。一方面可以让社会的个体感受到自我的存在;另一方面,微博时尚中的碎片化信息,已经汇聚成一股新型的话语形态。
微博碎片化的表述,更加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习惯。生活在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中的个体,面对着“时空压缩”的压迫感和个体流动的不确定性,他们会对自我的存在产生质疑和惶恐。在这样的情境中,个体会因为无限大的世界(时空)而产生恐惧。为了消解对无限大的世界的恐惧,无限小的内心世界,会发出呼唤。这呼唤就是感性主体抑或理性主体通过微博发布的心情状态。社会存在的个体因微博的“即时性”特征,刹那间无法经过理性的思维,只能作出感性的判断。个体瞬间的感性认知,能够让无限小的内心世界获得了一种释然,进而使其摆脱对无限大的外在世界的恐惧。在这种感性认知中,个体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
微博的碎片化,让信息瞬间爆发。在大量信息中,虽然不乏于事无补的琐碎消息。但是,微博因其强烈的“互动性”,使得很多事情回到了事实本身。在流动的现代社会语境中,个体化不得不面临“共同体”的遮蔽。在发布的微博中,当众多人参与到同一“事件流”时,他们可以发挥个体的优势,集思广益,让信息、观点和知识聚合,还原事实的真相。逐渐的,这些碎片化的话语,形成了一种具有平等性、互动性和互补性的新型话语形态。在新型话语形态中,消解了“共同体”话语。正是这种新型话语形态的形成,使得流动的现代型社会不断走向完善。
齐格蒙特·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理论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个体来说,使得他们增添了理解现代世界的一个新视域。伴随着微博时尚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的不断进步,个体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① [英]麦克法兰:《现代主义思想》,马·布雷德伯里、詹·麦克法兰《现代主义》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
②③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2页,第184页。
④ 骆冬青:《毒蛇》,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
⑤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4页。
⑥ 周栋栋:《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研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45页。
⑦⑧ [挪威]拉斯·史文德森:《时尚的哲学》,李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第5页。
⑨ 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⑩ 郑燕:《民意与公共性——“微博”中的公民话语权及其反思》文艺研究,2012年第4期。
⑪ [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7页。
⑫ [英]齐格蒙特·鲍曼:《寻找政治》,洪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⑬ [英]乔安妮·恩特威斯特尔:《时髦的身体》,郜元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