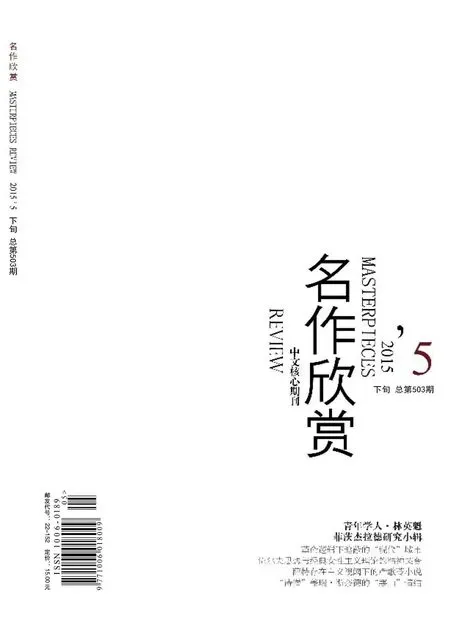错位叙事与时空留白——评雷蒙德·卡佛的《平静》
⊙游 澜[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州 350007]
作 者:游 澜,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2011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小说美学理论。
雷蒙德·卡佛是美国20世纪下半叶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要作家。卡佛的作品上个世纪80年代就介绍到中国,曾在作家圈内引起兴趣。之后,卡佛作品在中国国内沉寂了近二十年。近几年,卡佛的作品集陆续译介到国内,进入工业化阶段的中国读者似乎毫无障碍地接受了卡佛笔下现代生活环境中小人物的孤独、无奈、错愕、恐惧、愤怒、绝望或超脱。
卡佛不尖锐,他不会引导读者那样去做终极追问,他缺乏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拷问心灵的追问力,也不会如托尔斯泰那样敞开悲悯的心胸。这不奇怪,卡佛不会很刻意地提升日常生活的深义,但他叙述的现代人的微末生活却处处引发人的沉思:“有可能用一段似乎平淡无奇的对话,让读者读得脊背发凉。”①中产阶级和底层人士是卡佛笔下的常客,但这些底层人不似美国作家中写小人物的先驱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那些怪里怪状的小镇人那样以外部动作的“怪”反射其内心的不满和渴望。卡佛笔下的人物多抑郁,他们多不太愿意声张,言词直接简短,不善修饰,但卡佛的叙事本领就在于他能够透视这些外表粗粝的普通人的内心,通过极具表现力的外在细节勾勒显露出他们内在的脆弱、敏感、自尊和对爱的渴求。这一叙事艺术手法,与海明威有些类似,但又有所区别。其不同在于:海明威的简洁叙事法与其笔下的失败英雄“我不必多说”之无所畏惧气质相呼应,而卡佛式的“极简主义”则与他的诸多小人物“我不知该说什么”的内敛而敏感的性格有密切关系。
事实上,现代社会人与人沟通的困境是卡佛一再表现的主题。卡佛对现代人的脆弱性、易变性和隔膜感的艺术处理之创造性在于,他不仅仅将笔端停留在孤独和隔膜的书写上,他还善于从隐蔽的细节中发现这些孤独者、执拗者对理解的渴望和对自我尊严的维护。粗糙的言辞与敏感的内心,波折不断的对话与不期而至的和解,构成了卡佛短篇小说的重要的“看点”。由此,心口错位的叙事法营造了卡佛式的戏剧冲突,言外之意的留白法生成了卡佛小说文本的多层意味。
《平静》便是一篇能很好诠释卡佛简约而不乏深义的叙事风格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通过对五位小人物的言行,简约勾勒出一个有限空间内部人与人沟通的尴尬,每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以及陌生人间相互理解的可能。小说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却在平淡的叙事中传达出意味隽永的关于生命、尊严与理解的主题。这应归功于卡佛独特的叙事手法——错位叙事与时空留白。
一
《平静》说的是发生在理发店里的故事。篇中出现了五个人物:“我”——正在理发的顾客、理发师以及三位等待中的顾客。“我”刚搬到新月市不久,到一家理发店理发,理发师与其中的一位叫查尔斯的熟客攀谈,请他讲讲打猎的事。从警卫查尔斯的口中,我们知道他打中了一只老公鹿,却让它带伤逃走了。查尔斯大肆渲染暴力的打猎故事,不经意间冒犯了其中一位老年顾客艾尔伯特,两人起了龃龉。第三位顾客(根据卡佛的暗示,应该是一位伐木工人)撺掇两人到店外解决。理发师竭力调停,众人仍不欢而散。而“我”在目睹了这一幕后,做出了离开这个城市的决定。
小说的开头,理发师请警卫讲述“打猎故事”,大约是为了活跃店里的气氛,给等待中的顾客以消遣,不想却让顾客间起了争端。理发师想要平息争端,却按住了最不该按住的人(“我”),指责了最不该指责的人(其实“我”仅仅是一个一言不发的旁观者);查尔斯刻意渲染暴力氛围,夸大自我野蛮粗俗的气概,实际上是为了获得男性顾客间的认同,不料却冒犯了艾尔伯特;伐木工人的工作环境远离人群,生活空虚寂寞,因而特别渴望与人交流,参与到事件当中。所以他才会不断地打断查尔斯的叙述,并撺掇查尔斯和艾尔伯特武斗。
这些人物的内心想法与外在言行的实际表达总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位,而这些错位导致的人际隔阂与沟通无能构成了小说戏剧冲突的第一层次。在第一层次中,这三个人物代表的错位冲突是场景化的、当下性的,尽管携带有过去生活的印迹,但其仅仅作为性格影响下的言行方式进入到文本当中。
而第二层次的错位冲突则是由过去生活与当下生活的境遇落差构成的,它所涵括的时间跨度与内心深度远超过第一层次,而这些意义的生成集中体现在艾尔伯特身上。
艾尔伯特,根据理发师事后叙述,曾经是一位富于魅力的人物:“他教了我所有和三文鱼有关的东西。还有女人。她们曾缠着这个老小子不放。”②而现在,他“得了肺气肿,剩下的日子不多了”。衰老造成的这种前后境遇的巨大反差使得艾尔伯特对某些词汇极为敏感。警卫查尔斯“打猎故事”中夹杂着大量诸如“又老又大的婊子养的”“倒霉蛋”的词汇,这已经让艾尔伯特十分不快了,而当他听到查尔斯不肯放过中枪垂死的老公鹿,还对其惨状进行肆意的调谑时,他更是“于我心有戚戚焉”:老公鹿希望“找个不容易发现的地方去死”,就像艾尔伯特渴望葆有尊严的死亡,而查尔斯的追踪和嘲弄之于老公鹿就像疾病与衰老之于艾尔伯特那样,使生命最后的尊严都面临威胁。无怪乎艾尔伯特对查尔斯的言词极度反感,直言想要给查尔斯几个耳光了。
艾尔伯特内心的冲突来自于时间造就的境遇落差,生命衰老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抗拒又令人错愕的裂变,艾尔伯特现在的自我与过去的自我之间显现出一道不可弥合的鸿沟,在这里,生命境遇的错位带来的内心冲突似是不可和解的,因为艾尔伯特已经临近自己生命时间的终点了。艾尔伯特的“火气”与其说是面对查尔斯,不如说是过去之我与现在之我的不可调和:他不服老,不愿老,畏惧老。艾尔伯特现在之我与过去之我的错位关系,构成了时间向度上人之自我的内在矛盾。
第三层次的错位冲突则体现在叙述者“我”的身上。在“我”身上,错位冲突来自于“我”对生活的希望与失望的永恒循环。在小说的前三分之二篇幅中,“我”始终作为旁观者见证了这场争端的起因、发展和结果。直到最后一个部分,“我”本人的内心世界才开始向读者打开:“我”来到此地“尝试过一种新生活”。然而,在目睹了这场争端,听闻了艾尔伯特令人唏嘘的经历后,生命的暗面开始向“我”展露它神秘而冷峻的笑脸,阴影悄悄地潜入“我”的心底。
人去店空,在巨大的沉默中,“我”和理发师开始了无声的沟通:“我们一起看着镜子,他的手还框住我的头。我看着我自己,他也看着我。但如果他看出了什么,他并没有说出来。”这一刻,两人的内心达成了某种理解和认同,在两人共通的体验里包含了一种对命运无常的慨叹。这慨叹是如此的沉重,以至于无法言说,然而两人之间自有一种默契在传递着。于是第一层次中人们通过语言所渴望达到却未能达到的交流境界,在理发师与“我”的无声的动作和眼神中获得了,而第一层次中人际沟通的错位冲突也在这里也得到了象征性的和解。
理发师“用手指捋着我的头发,动作很慢,像在思考着什么。他用手指捋着我的头发,动作很温柔,像一个恋人”,这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安抚,充满怜爱的关注,好像生怕碰坏了什么似的虔敬,那么,究竟是什么值得他这样悉心地存护呢?是他们共同感觉到的生命的可贵和生命的无常吗?是他们对另一个人命运的同情和怜悯?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故事发展到这儿,人际间的冲突终于拐了一个弯,转化为理解和同情。虽然冲突制造者与被同情者都已经不在场了。
篇末,“我”叙述这段往事时回想起:“当我闭上眼睛,让理发师的手指在发间移动时感到的平静,那些亲切温柔的手指,那些已经开始生长的头发。”原来,理发师悉心存护的是“那些已经开始生长的头发”。头发是生命力的象征,查尔斯的鬈发代表其旺盛的生命力,艾尔伯特灰白的鬈发是“烈士暮年”的哀叹,伐木工全谢的头顶和过耳的鬓发代表了生命力的早衰或是生长的异位,而叙述者“我”的“那些已经开始生长的头发”则代表了“新生”。
命运的变化尽管不可控制,失望与灰心常常不可避免,然而新生的头发象征的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中仅存的“希望”一样,给予生命不断前行的动力。这“希望”就是人类在面对不可知的命运以及难以调解的错位冲突时唯一可能获得平静感的来源。
二
以上就是《平静》中三个层面的错位冲突,与其相对应的是文本中的三层叙事:第一层叙事是“理发店事件”,即查尔斯与艾尔伯特的冲突矛盾,其中嵌套了“老公鹿事件”;第二层叙事是艾尔伯特的故事,即他辉煌的过去与病苦的现状;第三层叙事是“我”的故事,即“我”是如何带着希望来到新月镇,又是如何决定离开此地重新开始生活的。这三层叙事各个存在于不同的时空维度,又相互嵌套于同一文本中。但是,除了“理发店事件”具有相对完整的空间展示性与时间延续性以外,其余两层叙事都是以碎片化的形式零散地分布在文本中。这些碎片与碎片之间的空白距离,正是叙事意义生成的空间。
卡佛运用富有暗示性的语言和点到为止的细节展示,引导读者积极思考,铺展想象,从而完成细节的联结和意义的建构。这种高参与度的阅读方式给予读者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地位和智识性的刺激。然而,这些意义的生成看似读者的功绩,实际上是作者运筹帷幄的结果。只不过卡佛式的作者是隐居幕后的,他高度发达的叙述克制力与信息交流能力使其可以通过留白和暗示的方式控制意义的传达,以达到无言而言以及不控制之控制的艺术效果。下面逐层分析卡佛的留白叙事策略。
在第一层叙事,即“理发店事件”中,叙述者“我”没有带上历数往事式的视角叙述故事,而是和读者一样处于无知的状态,重新经历了事件的发生过程。第一层叙事是有关人际沟通的错位冲突,人物身份以及性格理应成为作者刻画的重点,然而卡佛对此并没有给予直接描写,而是用简洁且富有暗示性的语言启发读者自行想象并勾勒出人物形象。
“我不喜欢那个人的嗓音,那嗓音与一个警卫不相符。它不是你期望的那种嗓音。”卡佛并没有说,一般人所期待的警卫的嗓音应当是怎么样,但联系日常生活经验,我们可以知道,警卫的职业身份应给人一种稳定感与安全感,然而查尔斯却是一个喜欢炫耀和浮夸的人,这些可以从他叼牙签的动作以及极富暴力炫耀性的言语中体现出来。然而,他富有侵略性的言行并不是恶意的。他在离开理发店时,不无失落地说道:“我想我待会儿再来剃。现在这里的人没什么劲。”可见,他用这样的方式说话仅仅是想要获得其他男性的认可,希望自己成为理发店里的一个中心人物而已。
对第三位顾客的形象刻画亦是如此。卡佛用“伐木靴”“机油”及其在谈话中所显示出的对山林生活的熟悉程度来暗示第三位顾客的职业身份——伐木工。又用“全谢的头顶”和“过耳的鬓发”来暗示远离人群的边缘生活导致的生命力的空虚和异位。他对生活并非没有热情,只是长期的孤独状态使他对生活的热情转移到了不正常的位置。不同于查尔斯,伐木工并不渴望成为事件的主角,他只是“希望发生点什么”,好让他得以观察和“享受”别人的生活,就像他住在荒远的深林里看着热闹的市镇一样。
这些细节碎片散置在叙事的过程中,看似毫无意义,然而每一处都可能打开一个新的想象时空,每一处都有可能在与另一处的关联中勾勒出人物的形象,并建构起叙事的意义。
第二层叙事,即艾尔伯特故事,涵括于理发师简短的百字叙述中。过去的艾尔伯特是个充满魅力的花花公子,如今的艾尔伯特则重疾缠身,时日无多。死亡是其唯一的结局。艾尔伯特的故事是令人感伤的故事,但卡佛没有直接写出这个故事。只是在篇末由理发师向“我”做非常简短的透露。然而,卡佛的小说叙事妙处也就在这儿:一篇看似两个男人“斗气”的故事,通过小说家笔端的轻轻腾挪,变幻为写一个男人如何对待自己的命运的故事。通过理发师对艾尔伯特身患重病这一消息的透露,艾尔伯特看似有点过头的“愤怒”被破译了。无聊的斗气故事背后原来藏着一个如此令人感伤的命运故事。因此,第一层叙事中,艾尔伯特听闻“老公鹿事件”时的种种言行,以及他对警卫有点夸夸其谈的打猎故事的“过度反应”,都可能与“艾尔伯特患上重病”发生关联,而产生新的意义。他对打猎故事的敏感,他对充满暴力和征服意味的言词的反感,都可以与第二层次“烈士暮年”的故事发生密切的联系。这两者虽互为诠释,但第二层次叙事几乎未有任何展开,仅仅通过第一层面的故事若有若无的细节就获得了一个非常开阔的叙事想象空间:艾尔伯特是有着怎样性格的男人?他与诸多女子的故事有着怎样的传奇?他对自己绝症是接受还是不甘?他是不是曾经也有拥有过非凡的英雄气质,而病痛又会让他发生怎样的心态改变?卡佛都未写出,但卡佛仅仅通过一场“斗气”的场景展示,就足以向读者敞开一个想象通道,引导读者去“摸索”一个不幸的老年男人的内心世界。正如卡佛所言:“每个故事都有神秘之处,表面下别的事情正在发生。”③
为此,我们可以细察第一层故事中艾尔伯特的反应。他之前一直十分安静地听查尔斯讲述“老公鹿事件”,没有插话,直到查尔斯开始讲述他们是如何追踪垂死的老公鹿时,他才冒出一句“不太像是个问题”的问话:“你们追踪它了?”艾尔伯特确实不是在表达疑惑,而是在表示惊讶,他惊讶于人何以对于垂死者(人/动物)表现得如此残忍,缺乏怜悯之心。当他“在椅子里转过身,注视着窗外”时,一定是由老公鹿的命运联想到了自身的遭遇。于是,查尔斯对垂死的老公鹿的攻击就成了对艾尔伯特间接性的攻击了,无怪乎艾尔伯特想给查尔斯几个耳光了。这里,第一层叙事中内嵌的“老公鹿事件”促发了艾尔伯特心理和言行的异常化。“老公鹿事件”发生地点在郊区,发生时间在“理发店事件”之前,而“艾尔伯特故事”是一个具有空间变动性和时间延续性的叙事,但两者却是并置的。因为前者的讲述促发了艾尔伯特言行的异常化,进而促发了后者的讲述,而后者的讲述也解释了前者讲述过程中的细节盲点。于是不同时空之间建立起了意义的联结,不同叙事层次间的空白也被弥合。
第三层叙事,一直作为一股潜流深藏在第一、二个叙事层面下。直到小说的结尾,卡佛才使之浮出表面:“那是在加州的新月市,靠近俄勒冈州边界。我不久就离开了那里。但如今我在回想那个地方,回想新月市,回想我和妻子怎样在那里尝试过一种新的生活,以及那天早晨我怎样坐在理发师的椅子里,做出离开那里的决定。”这段叙述,使得第一、二层叙事的时间形态都向后退了一“格”:“过去”变成了“过去的过去”。一切事件都重新与读者先前的阅读经验拉开了一段距离。
理发店里发生的事,在当时的情境下不免使人疑惑,而一旦拉开了适度的时空距离,作家便得以通过叙述者的回忆对其进行“二度”观察和思考。而这一段距离,便可以引领读者对之前叙述的故事涂抹上别样的想象和感受。使得之前叙述的理发店故事的内在意义再次被打量和思考。第一、二层叙事是第三层叙事的基础,而第三层故事却以“回忆”统合了第一、二层叙事。“回忆”就是回味,我在另一个时空中对之前“我”所看到和听到的故事再次进行过滤,使之成为“净化”“我”的情感世界的一个中介,溶解在“我”的灵魂深处的生活体验,以及能够反复引发“我”对命运和人生不断思考的一个窗口。这样,一件日常性的“杯水风波”,因为叙述者含蓄而诗意的沉思,成为一个能感动他人、引发他人思考的情感故事。这种写法,就是土耳其著名小说家帕慕克所倡导的让“故事里的宇宙”进入人物内心的写法:“小说艺术的根本问题不是主人公的人格或性格,而是故事里的宇宙如何呈现给他们。如果我们要理解某人,对其人格作道德观察,我们必须理解世界是如何在那个人的视野里呈现的。”④
那么,是因为什么“我”离开了原本生活的地方,来到新月镇“尝试过一种新生活”呢?卡佛没有交待。现在的“我”为何回想起这段往事,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之间的时空空白里又发生了哪些事件,卡佛也没有交待。但是,我们可以揣测,来到新月镇之前的“我”可能遭遇了生活挫折,才会迁居此地以求重新开始。不想来到新月镇以后,“我”再度对生活“失望”了。而现在的“我”之所以要在回忆里重新体验曾有过的那种“平静”,很可能是因为现在的“我”同样遭遇了不可调解的冲突和令人失望的现实。这些细节和空白暗示出一个不断变动的历程,灰心丧气与重整旗鼓的悲喜剧在其中不断重演。希望与失望的交替冲突已经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变成了令人绝望的永恒的循环。
这种循环的暗示,使“我”的故事有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它的时间没有终结,而是不断地向前延伸。这是一个留白式的结尾,没有人知道结局是什么,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样的重复交替不会停止,每一次结束都是一个开始,每一个开始也都预示着结束,每一次都带着过去经历所馈赠记忆和经验,充满希望地重新踏上生活的旅程。
生活的荒谬性正在于此,而生活的幸福感也来源于此。“我”不断重复着希望与失望的交替运动,就如西西弗斯不断地将滚下的巨石推向山顶一样,明知那石块终究会落下,却选择了一再将其推向山顶。“我”明知失望在所难免,现实与理想终会发生错位,却不断地选择相信“希望”一样,因为只有这能让“我”“平静”。
① [美国]雷蒙德·卡佛:《关于写作》,见雷蒙德·卡佛《火》,孙仲旭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② [美]雷蒙德·卡佛:《平静》,小二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下文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③ 转引自唐胜伟:《体验终结:雷蒙·卡佛短篇小说结尾研究》,上海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2011年版,第59页。
④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彭发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
[1][美国]雷蒙德·卡佛.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M].小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2][美国]卡萝尔·斯克莱尼卡.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M].戴大洪,李兴中译.北京:龙门书局,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