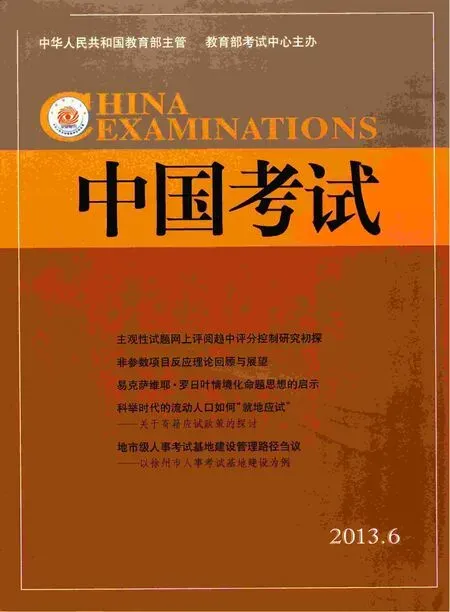清代书院“课试”的现代启示
林上洪
书院与科举是一对难兄难弟[1],几乎在同一时期兴起,又在同一时期被停废。如今,科举制度在名义上已经不复存在,而古色古香、带着浓郁文化气息的书院,却成了时髦的名词,且有方兴未艾之势。除沿袭“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慨叹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外,从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亚书院开始,复旦大学有志德书院、腾飞书院、克卿书院、任重书院、希德书院,西安交通大学有励志书院,汕头大学有至诚书院,等等。但是,今天中国大学的书院显然是取书院之名而学西方寄宿学院之实,因为古代书院、现代书院与西方寄宿学院在理念上的交集是师生亲密相处,这是诸多现代学者总结书院精神时特别强调的。人们有所忽略的是,除了“师生亲密相处”,“课试”也是古代书院的一个重要特色,清代书院尤甚。
1 书院“课试”概述
在现代学校,“课”是按规定的内容和分量进行讲授或学习的教学时间单位,如:上午有四节课。“课”也用做名词,指教学科目,如:必修课,选修课,专业课,语文课,物理课等。但是,“课”的本义是“考核”,在许慎《说文》中,“课,试也”。“课”常用指对官员政绩或学生成绩的考核,如考课;又引申为督促完成指定的工作或学习任务,如课子、课读。课试是书院学业考查的主要形式,也是书院教学的重要特点。书院学习的“功课”是考试,考试是书院学习的“功课”。书院“课试”的内容多以“举子业”为主,兼有诂经与诗文。书院教师以考课为职责,常被称为“课师”。
不同层次书院的课试侧重点有所差异。以总数为历代之最的清代书院为例,就整体而言,最底层的是私立的家族书院和民办的乡村书院,数量大、分布广,扎根乡村社会,构成中国书院等级之塔的底座,这类初级水平的书院,包括族学和义学性质的私立书院,有些仅借书院之名称,性质与私塾无异①书院区别于私塾的特征有四:其一,书院非启蒙之学,教学程度相对较高;其二,书院有公益特征,经费来源多元,由集体公办或官方主办;其三,书院有制度规章,教学和管理各有人员分工;其四,书院规模较大,有固定建筑或专门场所,设施完备,一般会有藏书。;中间层是县立书院,承担传播文化知识和将儒家理念政治化的任务,是书院等级之塔的塔身,主要针对优秀童生和生员而设;高层则是州、府、道、省、联省各级书院,有研究学术、养育学派之责,可以视作“书院之塔的宝顶部分”[2],主要针对举人、贡生和优秀生员。底层和中间层的书院,以应对科举考试为直接目的;高层书院名义上以治学为宗旨,但多数仍以应对科举考试为其终极目标。除了少数书院间或有讲学、讲会、研究等活动,以考课为主要活动的书院数量最多,“课试”是各级书院最重要的教学方式。
书院“课试”,多以训练作八股文、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为主要目的,或开卷考试,限定时间缴卷,或以闭卷形式模拟科举考试。根据经费状况差异,书院肄业生徒的名额各有不同,一般在每年年初举行甄别考试,也就是书院肄业生童的入学考试。被录取者一般分三种,第一种为正课生(也有称内课生),待遇最好;第二种为副课生(也称外课,童生则称附课),待遇较差;第三种为随课生(也有称附课生),没有膏火补助。书院肄业生的分类等次和地方官学的廪生、增生和附生有些相似,也和国子监分内外班有些相像,不同类型学生由考试决定等级升降。因为正课生和副课生有膏火补贴,各书院对这类生徒的名额有相当严格的限制,陈寿祺主鳌峰书院时曾在《拟定鳌峰书院事宜》中定肄业生徒之名额:
向来书院肄业生监内课、外课各六十名,附课无定额,大率多不过百人,少不过数十。盖当事遴才举贤,其道贵精而不贵多,诸生取友乐群,其道亦宜纯而不宜杂,多而杂则浮滥混淆,势难周防,且浇薄顽鄙之徒,幸厕其中,转足为有志者累。今请自后录取生监,仍旧内外课各六十名,附课准之,童生仍旧内课六十名,附课四十名,沙汰精严,毋庸逾额。[3]
从书院肄业生徒之“课生”之名,可以看出“课试”是书院的常态教学活动。从时间上看,有日常的小课、堂课,有每月进行的月课,还有每年进行的大课。书院学规常常有日常“课试”的要求,如嘉庆十六年(1811),知县杨桂森为福建台湾府彰化县(今台湾省彰化县)白沙书院订立《白沙书院条规》,其中有:
上灯时,读名家新文半篇、旧文一篇、汉文十行、律赋二韵、五排诗一首。读熟毕,再将次早所应佩背之《四书》、经书本本读熟,登于书程簿内,方可睡去。次早,将昨晚所读之文章、诗赋、四书、经书朗诵熟咏,务须读得极熟始去。在先生讲案,逐本背诵。……既背后,请先生命题,须将题义细求其所以然,寻其层次,寻其虚实,然后布一篇之局,分前后、浅深、开合而成篇,务须即日交卷。交卷后散学,仍夜读如前功。凡单日讲书,凡双日作文,此方有效。[4]
月课、大课的内容也是参照科举考试设定,有的书院甚至还按照科举考试的要求制定考课关防制度,防止考生舞弊。如桐乡书院规定:“生童大课,四书文一首、律赋一首、经解一首,律赋、经解不能者听。”[5]兰山书院规定,“月课宜认真扃试也。书院应课诸生多至三四百人,其中良莠不齐,抄袭枪替之弊势所不免。……本年正月甄别,宪台认真扃试,终日监临,诸弊皆除。”[6]
书院因科举而生,“科举制度是书院发展的政治基础”[7],书院“课试”之目的是训练并提高生徒应对科举的能力。有清一代,包括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在内,没有不应科举的书院,只不过应科举的主旨和层次不同而已。书院培养人才与科举选拔人才,本不是一件矛盾的事情,书院教学主旨之区别在于是以真才实学应科举,还是以投机取巧应科举。到书院求学的士子,除了少数绝意科举、潜心学问者,绝大多数抱有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出世理想,研究学问的深层目的是参加科举考试;书院举办者也希望培养的人才有济世安民之用,科举考试是检验教学成果的根本途径,故而应科举是书院存在的本来意义,“课试”必然成为书院的主要教学活动。
2 书院的“官课”和“师课”
书院与科举关系密切,书院与地方官府的关系亦非常密切,这是由书院补充甚至替代官学的办学性质决定。清代书院与官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钱维城在《中山书院记》写道:
古者国有学、术有序、党有庠、家有塾,皆学也。今郡县各有学,京师有太学,皆官为,给食或赐田。太学则有膏火,郡县学则有廪粮,有学租以赡贫乏,国家养士之厚如此,而贤有司之留心教化者,往往择高等弟子员与民之俊秀,别立舍以教之,名曰书院。书院与郡县学,其教一也,所谓名异而实同者也。[8]
书院与官学“名异而实同”,所同者仍养士之目的;“择高等弟子员与民之俊秀,别立舍以教之”,所不同者则是教化之功能。“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才、广学校所不及。”[9]清代地方官学大多没有教学活动,也没有住宿条件,书院学习条件和学习氛围比官学更好,士子在书院求学,能得到频繁的“课试”训练机会,提升应对科举考试的能力。如果说官学是学籍管理和初级考试管理机构,功能相当于今天的教育管理部门,那么书院则是教学和肄业场所,也是学业督查之所,功能相当于今天的学校。
清代书院受官方严格控制,官方在书院筹办中有主导作用,“或由地方官奏准,或由士绅筹设;或用公款,或由私人出资,置产买田,惟概须受地方官查复。”[10]虽然从经费多元来源来看,除了省城书院,府州县一级的书院并没有纯粹的官办,只能说是公立,书院的基金由地方筹募,“大都是多数绅士努力”[11],但地方长官担任了主导者的角色,故而这类书院依然可称为官办。据陈谷嘉、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统计数据,清代新创建的书院可考者有3 868所,其中官办书院2 190所,民办书院935所,情况不明及其他743所[12],可见官办书院是清代书院的主体。书院官学化,加强了书院与地方官学的联系,“一些大中型书院成为高于地方官学、吸收官学高才生深造的学校,书院的地位因而有所提高”[13]。
官办书院,控制学生录取、掌教聘用、教育内容等多方面,而“官课制度”则是清代书院的最大特色。官课,是指地方官员对书院学生进行常规考试,从出题、阅卷到奖励,都由官府主持。因此,清代书院“课试”同时存在“官课”和“师课”两种类型,特别是在中高层次的书院,形成了地方官府和书院轮流考课的制度。“官课”常常由地方官吏轮流主持,府、州、县书院由道台、知府、知州、知县或教谕、训导轮流主持,省会书院则由总督、巡抚、学政或布政使、按察使、转运使、道台等轮流主持;“师课”则由山长或掌教主持。
由官吏出题的“官课”,一般是一月一次,“师课”的次数更多。如广东粤秀书院“官课”、“师课”的日期规定为:“初三定为官课,十三、二十三定为馆课。两院于四季孟月轮课,司道仲季两月轮课,院长每月两课。”[14]河北的龙冈书院章程规定:“每月初二日官课一次,十七日馆课一次,作为正课,在院扃试,专试制艺试帖。初九日、二十四日两日散课,一由本县出题,一由山长出题,一文外,或论辨经解策赋,不拘一体。”[15]陈寿祺在鳌峰书院规定,“书院每月三课,官课居其一,师课居其二,请以十六日一课时艺,排律,外兼课经解史论及古文词,以期兴倡实学,搜获异才”[16]。
我们在清代科举人物硃卷履历的师承记录中,可以找到书院“官课”和“师课”的记录。在书院进行“课试”的官员、山长或掌教,常被卷主在履历师承项中记录为“业师”、“书院肄业师”或“书院受知师”。图1为记录为书院肄业师的“官课”官员;图2为书院肄业师的“师课”掌教;图3为记录为书院受知师的“官课”官员;图4所示,为书院受知师的“师课”掌教。如果说在履历中记录为“业师”或“肄业师”者,除了“课试”可能还有一些讲授活动,那么记录为“书院受知师”者,他们的主要活动就是“课试”,因为“受知”和考试直接相关,是指在“课试”活动中被赏识。

图1 硃卷履历“书院肄业师”中的官员记录示例[17]

图2 硃卷履历“书院肄业师”中的书院掌教记录示例[18]
例如,光绪六年(1880)庚辰科贡士王丕釐,湖北黄冈县人,其硃卷履历“业师”项中有这样的记载:“孝达张夫子,印之洞,直隶南皮人,癸亥探花,现官侍读,前任湖北学政,创立经义治事学舍,丕釐暨弟会釐肄业两载,受益最深”[19]。张之洞创立经义治事学舍,王丕釐就把他记录为“业师”,可能有些牵强附会,但担任湖北学政的张之洞,肯定会定期对他所创立的经义治事学舍的生徒进行考课,被王丕釐认作教师亦是理所当然。又如,同治十年(1871)辛未科贡士朱鑑章,其履历“肄业师”项记录多名考课知县,如“郭愚溪夫子,讳映奎,前无锡县、金匮县知县,课取第一;吴春舫夫子,印政祥,戊午举人,前无锡县、金匮县知县,课取第一”等,虽无书院名称说明,但“课取第一”应该是知县在当地书院进行的官课成绩记录。[20]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贡士袁嘉谷,云南临安府石屏州人,其“受业知师”中有书院考课官员15人,例举其一,“张季端夫子,印建勋,己丑状元,国史馆协修,功臣馆纂修,武英殿协修,编书处协修,教习庶吉士,甲午科云南大主考,提督云南学政,五华、经正两书院经正课、时务课、诗文课、卷折课屡蒙取第一”[21]。
从书院章程和清代科举人物的硃卷履历记录可以看出,“课试”是在书院肄业的士子之日常活动,是训练应科举能力的主要手段。书院“官课”数量上不及“师课”,但与“师课”同等重要,书院入学资格和膏火发放都由官课成绩决定,官课是书院教学质量的外部衡鉴,是官方控制书院的表现。通过“官课”,士子以能结识地方官员为荣,地方官员也乐意广收门生、提携后进。“师课”是书院“课试”的常态形式,是清代书院的主要教学方式,也是书院教学质量的过程化评价方式。

图3 硃卷履历中的书院“官课”受知师示例[22]

图4 硃卷履历中的书院“师课”受知师示例[23]
3 书院“课试”对现代大学的启示
中国古代的书院教育,相当于今天的高等教育,那么书院“课试”就相当于现代大学的学业考试,就二者的特点进行比较,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以下从书院“课试”的应试目标、书院“课试”的过程性、书院“课试”的促学作用、书院“课试”的官方特征、书院“课试”的开放性几方面做若干分析。
其一,书院“课试”的应试目标,反映了书院教育与考试的矛盾。今天人们对清代书院教育的批评,缘于官学化书院的应科举特征,书院以应科举的“课试”为常务,这种天天考、月月考的“课试”活动,目的在于训练读书人的应试能力。清代书院多以八股文写作及其相关知识为教学内容,因为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专用文体,虽然没有实际用途,但八股文是士人博取功名的“敲门砖”。书院“课试”的核心内容便是写八股文,参加书院“课试”者,除了童生、生员,还有举人,“专课举人和兼课举人的书院成为所在地科举应试教育的重要机构,为举人在竞争激烈的会试、殿试中脱颖而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24]。
现代大学也存在教育与考试的矛盾,这种矛盾没有高中阶段尖锐,但也在大学校园中随处可见。对大学教育产生冲击的考试有高等教育系统内的考试,也有高等教育系统外的考试。高等教育系统内的考试,主要有英语等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高等教育系统外的考试,主要有各类职业技能考试、执业资格考试、公务员考试等。因为应试的需要,大学校园出现了一浪又一浪的培训热潮,法学课不如司法考试培训班受欢迎,英语课没有英语辅导班人气旺,政治课赶不上考研政治辅导班火爆,考级考证考研考公务员,俨然成了大学教育的指挥棒。如果说书院应科举坏了书院精神,那现代大学的应试现象当作何解?
其二,书院“课试”具有过程性评价特点,是教学目标明确的表现。总体上书院“课试”本身就是应试导向的,书院日常教学的目标是明确的,“课”是教学内容,也是教学时间单位,是教学目标的具体化,也是教学效果的评价手段。比较而言,现代大学对学生进行学习评价不太重视诊断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一般只是以期末考试成绩进行终结性评价。虽然大学的课程成绩一般都要求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两部分组成,但是许多教师的平时成绩仅仅是以出勤为依据,更进一步的是以课堂提问发言为参考。把作业作为平时成绩依据的教师较少,进行课堂小测验的则更少,而国外大学教师则往往把课堂测验作为记录平时成绩的依据。可以说,大陆高校的课堂教学已经失去了传统书院有“课”即有“试”的做法,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难以有机结合,教学目标没有成为学生学习目标,不能形成有效教学。
其三,书院“课试”具有促学作用,发放膏火是激励手段。与过程性评价的日常“课试”不同,发放膏火一般依据较为正式的每月课试成绩,如河北龙冈书院章程规定:“生监取在前十二名,每名月给膏火大钱五百文。每月膏火,以初二日官课为定。”[25]因为膏火银两往往来自官方资助,所以官员主持的“官课”成绩最为重要。相比而言,现代大学的考试促学的作用大为下降,从图书馆和自习室的学生人数周期性变化可以看出这一点,期末考试前的一个星期,是学生临阵磨枪的时间,而在平时,大学生上课不认真现象比比皆是,无故“翘课”不在少数。大学生“翘课”固然有教师教学品质优劣差异的原因,没有平时阶段性考试压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国内有一些大学仍然坚持实行期中考试制度,是否能有效提升大学人才培养质量,有待进一步研究考证。评价驱动可以提高学习效果,但不能保证学习的效用;可能造成学生与兴趣背离的被动学习现象,学习无用的知识,不能培养思维能力。但是,学生的学习投入是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就兴趣驱动和评价驱动两种方式的现实操作可行性来看,学业考试的评价驱动是现阶段中国大学教学质量提高的主要增长点。
其四,书院“课试”的官方色彩,是书院办学质量的重要保证。书院“官课”制度,是官方控制书院办学方向的表现,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官方重视书院办学的体现,如果没有官方支持和资助,清代书院数量不可能超过历代书院数量之总和。主持“官课”的官员大多也是经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进士或举人,他们有深厚的儒家文化修养,也有丰富的科场考试经验,对于期待科举成功的书院肄业生徒而言,官员就是他们应该学习的楷模。官员的“课试”能够保证书院办学质量,既是衡鉴,也是助力。比较而言,现代大学难以在办学质量上获得官方的直接支援,对大学内部的学业考试没有进行有效监督。虽然各学科成立了教学指导委员会,但是并没有制定有效的大学教学质量标准。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政府曾在1927年公布《专门以上学生毕业资格试验委员会规则》,将高校毕业考试的权力收归教育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毕业生质量[26]。需要思考,现代大学是否需要高校外部的衡鉴?
其五,书院“课试”的开放性,是书院办学社会化的表现。书院肄业生徒有正课生与附课生之区别,附课生名额不定,一般没有膏火,是书院“课试”开放性的一种形式。此外,有些书院设定奖励吸引士子写文章课试评比,士子称参加这种书院定期公开举办的考课活动为“考书院”。商衍鎏肄业期间“每月必向各书院应考,到课期晨兴往书院看题目,回家写作,傍晚到书院交卷;古学的学海堂、菊坡精舍,则限三日或五日交卷。”[27]黄炎培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过这种书院写作考课活动,童生也可以参加,优等者有奖金。[28]这种书院“课试”活动可以自由投考,充分显示了书院办学社会化的开放特征。相比之下,现代大学的学业考试并没有这种开放性,特别是很多大学实行按学分收费制度,勤学多学不但没有奖励,反而变成一种奢侈的消费,进步还是倒退?
综上,清代书院“课试”固然有其极端应试教育的不足,但是“课试”形式及其意义亦有其合理之处,对改进现代大学的学业考试制度有启示价值,值得研究、学习、借鉴。
[1] 刘海峰.纪念中国书院改制110周年(专题讨论)——书院与科举是一对难兄难弟[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100-102.
[2]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438.
[3] (清)陈寿祺.左海文集(卷十).清刻本.
[4] 杨学为.中国考试通史(卷三)[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87.
[5] (道光)桐乡书院志(卷三,桐乡书院章程).转引自: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507.
[6] (宣统)甘肃新通志(卷三五,兰山书院条规).转引自: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507.
[7] 胡青.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50.
[8] (清)钱维城.钱文敏公全集.茶山文钞卷五记,清乾隆四十一年眉寿堂刻本.
[9] (清)素尔讷.学政全书(卷七十二).清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刻本.
[10]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4:103.
[11] 齐如山.中国的科名[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207.
[12] 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353.
[13] 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五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209.
[14] (道光)粤秀书院志(卷二,粤秀书院条规十八则).转引自: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506.
[15] (道光)栾城县志(卷三,龙冈书院章程).转引自: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507.
[16] (清)陈寿祺.左海文集(卷十).清刻本.
[17] 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第54册)[M].光绪九年(1883)癸未科贡士王祖畲硃卷履历.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35.
[18] 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第86册)[M].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贡士蒋玉泉硃卷履历.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420.
[19] 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第48册)[M].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233.
[20] 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第32册)[M].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197.
[21] 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第89册)[M].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179.
[22] 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第36册)[M].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科贡士庞庆麟履历.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174.
[23] 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第82册)[M].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贡士孙荣枝履历.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362.
[24] 李兵.清代书院的举人应试教育初探[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30-33.
[25] (道光)栾城县志(卷三).见:龙冈书院章程.转引自: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507.
[26] 杨学为.中国考试通史(卷四)[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75.
[27]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423.
[28] 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