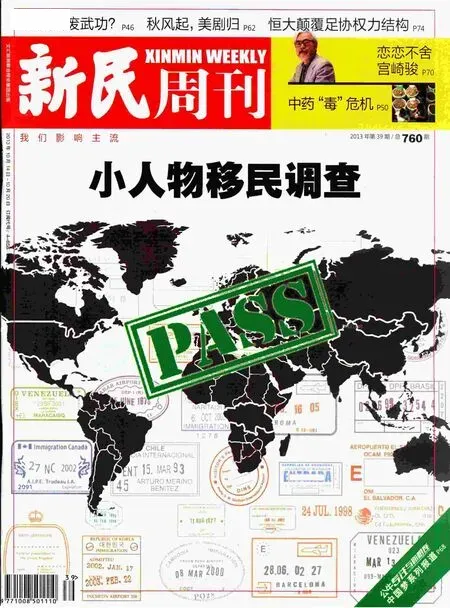喧嚣时代的冷音
顾文豪
宇文所安在析解张岱《陶庵梦忆》的长文《为了被回忆》中说道:“回忆是不落窠臼的,是别具一格的,它不是那种一成不变的东西。除非我们把复现的事件同某一具体事件、具体地点和我们生活中的某一具体时刻连在一起,否则,我们不会回忆起潺潺流水和盛开的花朵。”张岱捕捉和试图穷力复现的就是这些倏然现身倏然泯灭的时光之花。即如日后的战事、亡国、家破、友散使他的人生密布创痛,也丝毫不妨碍他以多姿有味的笔触为我们重现西湖香市的闹猛,葑门荷花荡的摇飏,绍兴灯景的鲜妍飘洒。
我不知道,早年研究晚明文学的台湾学者周志文先生在书写他的回忆散文系列时,是否会想及张岱。在我眼里,周先生多少有些像归隐的张岱,通身有幽人气质,可他的书写却并不完全类似张岱。如果说张岱的书写是有意为自己记录过往生活的璀璨光影,由此在逼仄的现实世界中闭门反刍记忆而活,那周志文并未如此拣择一己记忆,事实上,他笔下的过往常常是灰色的、幽暗的、并不愉快的。也丝毫不见别的作家写起回忆文章来的津津自喜,对他们而言,回忆不是目的,他们需要的只是不停经由选择性记忆而让自己致幻着迷,他们只欣赏特定时段的自己。而周志文的回忆却单纯得多,很少在回忆中代入自己,一树一花一人一物,之所以被书写,是因为它们值得被书写,不妄图从中兑换声名,妆扮形象,虽然这些临流而观的文字其实不乏介怀、悲喜、穷窘、欢愉之情。
而在新近出版的《记忆之塔》中,这些介怀、悲喜、穷窘、欢愉之情倒是出乎意料地表达得更为朗亮。比起《同学少年》里的少年青涩,《塔》叙写的是初进大学的憧憬与憧憬破灭后的漫长寂寞;比起《时光倒影》里的谈文论艺的余裕从容,《塔》坦露的是对文学之为文学的究诘追问,是对知识人之为知识人的批判狐疑;比起《第一次寒流》里下笔的疏冷自制,《塔》却信马由缰,愤怒处笔挟风雷,诘问时剔肉见骨。
这份朗亮乃至热烈,一开始就有。在开篇《第三号交响曲》中,刚考上东吴大学中文系的周志文,一个宜兰乡下少年,“对未来充满了意志与憧憬,前景将无止境地在眼前一幕幕地展开,英雄可能是别人,也可能是自己”。一如贝多芬的音乐,即便照旧有山风海雨、猛虎恶豹、电闪雷鸣,但“理想如日,就在不远处”。甚或在彼时周志文的心中,理想定要有风雨波浪相伴随,才当得起理想的美名。但现实的糟糕恰恰在于连糟糕自身都欠缺品质,不会有山风海雨的壮阔美学,总是来得猥琐卑浅,如胭脂化水般溶尽一个人所有的志愿与抱负。
乌七八糟的老师。到处都是“有些小聪明,但没有真学问,教得稍好的,其实也只是在逞口舌之巧而已”的所谓教授。放眼校外,报业的旋起旋灭仅匆匆十余年,好不容易争取到的言论自由的结果只是“让贝多芬都换成了李宗盛,把张大千都换成了几米”,而且问题在“这世界选了通俗就不许典雅存在”;教育则总是踌躇难前,“正面的力量常敌不过反面的力量”,因为数十年来都只是“把教养一个人成为‘人当成一个次要、不重要甚至迂阔的问题。”
林林总总的丧气事、卑琐事、不平事、好景成梦事、勾心斗角事、徒唤奈何事,层层垒砌成一座“记忆之塔”,但这不意味着这是一本旨在抖落儒林八卦的外史轶事集,也不代表边缘人周志文要借此一抒块垒,相反作者是要借这满眼的无趣人事,唤起知识人的时代担当。
是的,知识人理当渴求自由,但缺乏高贵道德视野的自由,“顶多只是各行其是的散漫罢了”;文化也不该是一种做学问的、讨论会上的“材料”,重建文化更不该流于“材料”的工作,所以就整体而言,“不论大陆或台湾,在文化价值上,华人仍处在一片虚无的世界之中”;而在信任与背离,荣耀与嘲讽,幸与不幸皆如硬币两面的“我们的时代”,所谓真正的文化人,“必须认真的选择自己的价值,选定后就朝着这个方向走……少说话,最好是默默无言”。
这并非什么惊听回视之论,但一如周志文冷静自持的笔调,是一种喧嚷时代的冷音,也是一个边缘人对时代的热响。边缘,不仅是位置,更是立场。但边缘却并非是文化人逃避担当的理由。就某种意义来说,《记忆之塔》是一部冷热书,只不过我们所谓热,在他这里全属避之不及的虚热,我们鄙夷的僻冷荒寒,在他这里则是需贯注一生的热诚。
——领悟张岱的“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