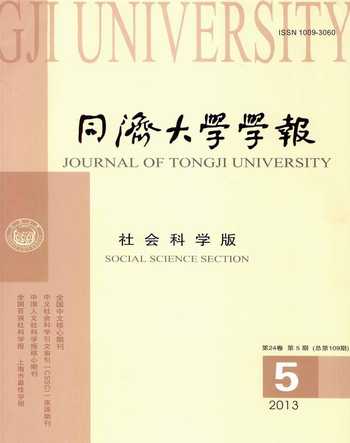道德·制度伦理·政治哲学
陈家琪
摘要:文章讨论了道德、制度伦理、政治哲学的概念,并依照康德、黑格尔、拉康、阿伦特以及国内学者王海明、高兆明等人的有关论述,讨论了现代性的突出特征即政治参与的公共领域的衰落,并在此基础上重提人格尊严以及在中国历史上几乎从未有过的公共领域和共同世界如何重建的问题。
关键词:道德;制度伦理;政治哲学;人格尊严
中图分类号:D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5—0073—07
康德在道德哲学中讲德行,认为德行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力量;所以人的理性的固有使命不是为了幸福,而是为了更高、更纯粹的理想,这就是道德的自主与自律。德行与幸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不能用幸福定义德行,从直觉上说,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康德的目的是要克服一切从非理性的冲动而来的动机,让德行本身发号施令。而幸福作为一种感受性经验,只是对德行的意识,或者说,德行是幸福的条件,对其本身的意识就是幸福。
当然,这里存在着一种矛盾:那种道德的自主与自律一定是能够实现的,否则无法成为人们的道德要求;但它又一定是一个几乎无法实现的道德理想。这也是一切坚定的道德理想主义者所面I临的困难。也许有人会说,正因为道德完美只能是理想,才会成为自主与自律的方向;当然也可能有人会说,那它就不应也无法成为人们的道德义务。
在康德之后,最先对康德的道德理想提出质疑的就是黑格尔。在黑格尔看来,我们不应把个人的德行抬得过高,制约人的道德行为的,也许更多地应归因于家庭(亲情)、市民社会(友情)和国家(团结)中所体现出来的传统、法治以及可以通称为伦理意志的客观精神。
到了20世纪,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现实就是这种德行理论的崩溃。塞瑞娜·潘琳(SerenaParekh)在《阿伦特与现代性的挑战》中讲到阿伦特的20世纪道德经验时告诉我们,欧洲人原先所认为的那种普遍永恒的东西,比如理性,即那种识别对与错的能力,其实是可以毁于一旦的。于是道德就似乎又回到了其原初的含义——“习惯”(mores),就是说,道德已经成为了一套没有坚实基础的习俗,就如餐桌上的礼仪一样。
作为背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20世纪是一个杀人不眨眼和死人超过任何一个世纪的世纪。
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现实。阿伦特说,当“你不应该杀人”转变为“你应该杀人或杀坏人”,而“坏人,,又是一个可以随时更换的概念时,已经不会有任何人表示抗议了。
于是,我们就发现以后的道德哲学至少沿着两个方向艰难前行,一是幸福问题,或者更具体地说,也就是追求幸福这种欲望的正当性问题;再就是用人权取代传统的德行或良知,为道德规范重新提供一个主要的基础。讲人权,主要是针对强权而言的,因为20世纪给我们的一个基本教训就是必须抑制权力的为所欲为。所谓的“杀人不眨眼”大都与权力的运作有关,甚至自然灾害或贫富差异也蕴含着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于是追求权力的欲望(当然权力本身不会是空洞的东西)也就压倒了所有其他一切的欲望。拉康的“欲望伦理学”就是要让主体把自己的无意识(那里一定积压着诸多的欲望)清理出来,好好地说出来。这既有临床的意义,要解决人类文明中的症状,也通过把外在的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命名为“大他者”,而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无意识正是“大他者”的语言效果,而我们只不过是这种语言的傀儡而已。传统的德行与良知学说在理论上总与某种神圣的或者具有超验之源的内在经验有关;这种内在经验所依赖的,就是西方自中世纪以来漫长悠久的自然法或自然权利学说。那时候,外在的规范与强制性戒律(自然法)、内在的反省(良知或德行)是完全一致的。今天,外在的规范与强制性戒律(自然法)崩溃了,剩下的就只有内省的主观经验。也就是说,一方面,这种内省的主观经验丧失了其神圣而超越的外在依据,另一方面,它又同时告诉我们,所谓的道德,必须完全与外在的服从相分离。道德一旦变成了对外在力量的屈从,便不再有道德可言;这种屈从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伪善。伪善几乎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无法解脱的道德之困,此即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所谓的“乡愿,德之贼也”。“无论是上帝之法,还是国家之法,我们必须在法律与道德之间进行区分。”分离后的道德也不全靠内省,而是被置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阿伦特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三个道德箴言均与他人相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己之所欲,当施于人”;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人;康德的道德绝对命令: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为所有人认可从而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去行动,这就是自己必须与自己相一致(不矛盾律),因为自己同时在为某种具有普遍性的东西立则。
于是,道德的根基不再源于某种神圣的或者具有超验之源的内在经验,它事实上来源于语言在沉积中构建而成的“自我”,来源于那种人所固有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他人的现实关系之中。
如果要讲内在经验或者讲德行与良知的话,它也就应该在与“自我”(拉康命名为“小他者”,即另一个与“我”相似的“我”)的内在关系以及与他人的外在关系这一前提下更内在化、主观化为一种对尊严的意识。
康德说:“目的王国中的一切,或者有价值,或者有尊严。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能被其他东西所代替,这是等价;与此相反,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代替的,才是尊严。”
康德进一步区分了市场价值(与人们的普遍需要有关)、欣赏价值(与人们的无目的情趣相适应)与尊严。前二者都是相对价值,只有尊严才是“构成事物作为自在目的而存在的条件的东西”,这里显然就指的是生命;或者说生命本身就应该有它自身的尊严。
只有生命的存在才是绝对的,它不似人权或权利学说那样在与义务的相对性中讨论问题,而是把某种具有绝对性的自在目的作为了一切权利的前提或条件。
在阿伦特的书中,多处地方谈到了生命或某些人的生命,某一种族、某一阶层、某一群体的生命为什么在某种情况下会被视为了多余。
那些被视为了多余的生命首先丧失的就是尊严;而他们在万般无奈的境况下唯一可维护的,其实也只有自己的尊严。徐贲先生在为意大利最重要的作家、化学家和奥斯维辛174517号囚犯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所著的《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所写的“导读”《幸存者的记忆与见证》中说,在莱维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平凡美德”,一种“弱势美德”;这种美德就是在经历了地狱之火,已经变得十足的谦卑而现实的同时,却依旧怀有羞耻心,怀有自尊感,拒绝就此堕落下去。所谓“弱势美德”,是相对于“强势美德”而言的。“强势美德”常与历史进步和公民政治联系在一起;而“弱势美德”则总是伴随着被侮辱、被损害、被践踏的弱者经历,它不能使人成为英雄,也无法让人充分高尚,至少不是康德意义上的道德高尚,而是在人性道德的灰色地带保持那种人之为人的最起码的尊严,不至于完全绝望或彻底堕落。
当我们今天谈到道德、制度伦理和政治哲学时,都应该首先确立自己作为一个“平凡美德”或“弱势美德”的立场;这等于先要承认自己其实无法认识或掌控历史的进步,甚至至少在眼下还无法实现公民政治的宪政,剩下的就只有了个人的尊严和彼此间在尊严问题上的相互沟通与彼此维护。于是从这里就可以引申出制度伦理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
康德其实也已经意识到了尽管德行是唯一内在的善(德行完全依赖于自身,无论条件是如何的不利,德行总是能够实现的),但却不是至善;“至善由拥有相应数量的幸福的德行构成。”这里的“相应数量就说的不是个人,而是“共同体中的总体善”。从逻辑上讲,“至善”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既包含了完美德行同时也实现了最高幸福的概念。布劳德(Charlie Dunbar Broad)在他的书中区分了“共同体中的总体善”与“共同体的总体善”这两个概念,这比较有意思。前者说的是共同体中所有人的善(或理解为利益、幸福)的总和,后者说的是共同体(富国强兵之类的愿景)自身的善。如此看来,康德所讲的“相应数量的幸福的德行”就指的是“共同体中的总体善”,而不是“共同体的总体善”。在布劳德看来,“共同体的总体善”依赖于“共同体中的总体善”;这种依赖部分指的是“如何分配共同体中的总体善的方式”(罗尔斯就是想回答这一问题),部分指的是共同体中成员间的相互关系(沿着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与“主体间性”一脉相承下来的所有问题)。
在拉康看来,如果说“善”与个人“道德”有关的话,“至善”就指的是“伦理”意义上的“善”;也就是说,如果说“善”是个人的自我约束的话,“至善”则是自我约束的参照,也就是说,约束个人的东西其实来自于某种普遍性的、约束着所有人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什么呢?一是决定着个人习惯养成的习俗、传统、文化;二是社会性规范(最具有强制性的无疑就是体现国家意志的制度、法律),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某种具有普遍性品格的文明秩序,它与制度文明、政治文明当然也有着更多的关联;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至善”这一概念所要告诉给我们的那种道德理想。在康德这里所讲的“道德”之所以在黑格尔那里会变成“伦理”,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康德的个人意义上的道德理想其实不得不参照或不得不来源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意义上的普遍伦理;国家不过是这一普遍伦理得以实现的载体而已。在拉康看来,“至善”其实也就是传统形而上学所讲的“实在”,它无法触及,但又具有无比的吸引力,“因为善的领域正是围绕着这个完全不能触及而又具有吸引力的中心组织起来的。”拉康接着说,“问题在于,要将实在作为‘空来认识理解,并通过欲望和时间的辩证法来思考实在。”
伦理意义上的“至善”其实不过就是一个“空”。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经常将上帝、关于法律和伦理的原则相提并论,并告诉我们人类开始思维时,只能从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有”(纯有)开始,而这样的“有”其实也就是“无”,因为它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定性。王海明教授在他的《(国家学>自序》中专门提到了文化大革命时的“公字化”与“忠字化”运动,全民性地大立“公”字、“忠”字,大破“私”字、“我”字,人人都要做到“三忠于、四无限”。但这里的“公字化”、“忠字化”运动中的“公”与“忠”,不过就只是两个空洞无物的“字”而已,谁都无法做到,但又具有无限的吸引力,致使全国人民都处于某种癫狂状态之中。除了不得不的外在使然,也与“主体对自己的欲望一无所知”有关,于是欲望(完全做到“三忠于、四无限”)就在一条长长的能指链上奔跑,“并且通过一个阻止固着的无可救药的不满意,被一个根本性t不是这个所标记,于是乎,不再有欲望的自然性。”由于没有人能做到,所以也就没有人(包括自己)满意,它的唯一作用就是“不再有欲望的自然性”。
我们每个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应该仔细想想,“不再有欲望的自然性”,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对我们来说又是多么的真切。
于是,我们也就更理解了我们的世界其实是用语言建构起来的,特别是伦理意义上的“至善”,比如“公”、“忠”,比如“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它超越了所有具体的、个人道德意义上的“善”,成为了具有“至善”意味的外在强制。统治者是一定会通过一整套的制度和实际的军队、法庭来维护这种有利于自己统治的“至善”理念的。在现实生活中,它导致的也一定就是伪善。从理论上说,离开了“至善”,我们无法规定具体的、有形的“善”;但离开了这些体现在具有个人自主精神的人身上的具体的、有形的“善”,所谓的“至善”不过就是一个“空”。“至善”作为“空”,否定着所有具体的、有形的“善”(“不是这个”);而所有具体的、有形的、不是这个或那个的“善”的总和又在实际上实现着一开始必定是空洞无物的“至善”,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拉康说要“通过欲望和时间的辩证法来思考实在”,其实也就是要遵循着黑格尔的思路来理解作为“空”的“实在”是如何成为了“实”的“实在”的。这当然也是一个漫长到几乎看不到尽头的过程(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过程哲学”)。如果我们能从主奴关系的角度理解无限的“空”(主人)与有形的“实”(奴隶)的关系,也许会使问题变得更为清晰。纳塔莉·沙鸥在讲到拉康的学说时,专门提到1933年至1939年间,拉康曾专门跟随亚历山大·科耶夫阅读黑格尔,阅读的线索就是欲望问题;人的欲望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价值的追求,“如果价值没有被他人认可,那么欲望也就迷失了方向”。所以,首先,欲望完全是被认可的欲望,欲望本身需要如此被承认;其次,主人的位置一定会在奴隶们“为承认而斗争”的过程中受到严重动摇。当然,动摇或改变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奴隶变成主人,而原来的主人则沦为奴隶。在霍布斯看来,最初之人是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人;尼采认为,最后之人则是最终获得了胜利的“奴隶”。
于是,主人们为了不致使自己沦为奴隶,有两条路可循:一是强化暴力镇压的力度,二是必须“对于制度进行价值审视,以制度的‘善为核心,分析与揭示制度的道德价值属性及其具体内容”。设法对制度本身进行价值审视,以从根本上灭除主奴之别,这种制度化的保证就是高兆明教授所理解的“制度伦理”,亦即他所理解的“宪政正义”。当然,它的前提必须是:第一,任何正式的国家制度本身就具有伦理属性;其次,制度作为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一定离不了人的“自由”与“实践”。纳塔莉·沙鸥认为拉康更强调的是人的“意识”,因为人总是要有意识的,而“意识”(conscience),无论在英文还是在法文中,本身就具有道德层面(好的意识即良知)与认识层面(正确的认识即真理)双重意思。“有意识”,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就指的是“故意”或“有价值取向”。这也就是说,“理论”(求真)与“实践”(求善)并不是两张皮,而是人的意识活动本身的两种属性;而人的意识活动本身就是自由的,这似乎本来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什么东西都无法限制也限制不了的简单事实。所以自由应该是讨论自尊、道德、制度伦理、主体间沟通与交流等所有问题的最底层的要求或前提。
“有意识”,到底其意何在?现在大多讲“承认”,这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但承认,用《(世界人权宣言>前言》中的话来说,就是追求“大家庭中所有成员的内在尊严以及平等与不可让渡之权利”,并认为这才是自由、正义与世界和平的基础。“人格尊严”(human dignity)这个概念虽说来自西方,但也是中国古代的先贤们反复强调的一种“君子风范”,如“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孔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等等。
现在的问题只是要讨论:为什么主奴关系的制度本身并不是善,以及如何才能使要求承认的欲望(要有人格尊严的欲望)在制度上受到保护的问题;当然,它也不可能只限于“君子”,而是指“大家庭中所有成员”。
到底什么是政治哲学所要研究的问题?早已众说不一;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这就是政治事关众人,事关共同体的存在、运作方式,所以也就与共同体中的每个人都有着切身的关系;它所要保护或维护的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具有相同的自由的机会与能力。但现实生活中却并非每个人(或因种种外在因素的限制或不愿意、不允许)在机会与能力上都是均等的,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参与到政治的活动之中。政治活动需要作出判断,所以阿伦特才认为《判断力批判》包含着康德政治哲学最伟大与最原创的部分。①她认为政治与审美归根结底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都源于“主体间性”这一概念,也就是自胡塞尔以来的现象学一脉。塞瑞娜·潘琳解释说,《实践理性批判》之所以与《判断力批判》(尽管康德或其他更多的人均想从道德学说发展出政治学说)不同,就在于前者的“绝对命令建立在一个人不应与其自身相冲突的观念之上;而后者所讲的“判断”则涉及到共识的达成,所以它不是个人的思考,而是“必须将自己从主观的、私人的状况与特质中解放出来,就是说,一个人必须超越其个体局限性,以便考虑其他人的立场”。政治与审美都需要通过对判断的分析来理解一个对共同世界的共通感是如何形成的。政治判断与审美判断的主观普遍性相似,既非完全主观,也非完全客观;“这个双重性有助于我们通过表现这个‘主观普遍性空间的重要性来理解共同体的世界。”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全部努力就是要重建一个与现代性相适应的公共领域的本体论意义;这个公共领域的重建又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感。共通感不同于私人感觉,而所谓的“私人感觉”事实上又只能求助于共通感。鉴赏判断中的“这使我愉快”就扎根于共同体的经验之中,并因此走向一种开放沟通的心态。可沟通性依赖于一个开放的心态,共通感是重建一个共同世界的条件与结果。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告诉我们,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恐怖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使人孤立,当所有的劳动都只是为了活下去时,孤立就变成了孤独;而孤独是一种根本不属于世界的感觉,“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最绝望的一种经验”。塞瑞娜·潘琳说,“无根”意味着“在世界中没有立足之地,不受他人的认可与保护”,“多余”意味着“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无世界性”则可以界定为共通感的丧失。许多人走上犯罪道路都是因为他们成为了事实上的“孤独个人”,于是也就丧失了本属于阶层或共同体才有的尊严。而那些故意炫耀权力与财富的人,也是因为他们把自己视为“孤独个人”,于是只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他人的承认。对每个人来说,共通感都是这样一种感觉,它“规范并控制其他所有感觉,如果没有它,我们每个人都会被封闭在自己特殊的、不可靠的感觉材料之中”。如果人权的本体论基础是其所呈现的多样性,以及它只有通过我们的判断而持续存在的话,那么在现代性中,公共领域的衰落对于人权来说就具有了如此的毁灭性。
其实政治哲学的根本意向就涉及到一个公共领域的重建。从理论上讲,这里面又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公共领域是如何丧失的,再一个就是主体间性、他人、承认、尊严,即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道德与制度伦理,对于公共领域的重建为什么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在古希腊的城邦,世界被明确划分为公共与私人两个领域:家庭属于私人领域,家庭也提供了欲望的基本需要与满足,劳动与制作的地点就在家庭的领域之内;而广场则是公共活动的领域,它是在与他人一起言说与行动中展现出来的。前者受着必然性(或理解为生活必需品)的驱使,后者则是一个自由的领域;受必然性驱使是前政治的,因为它只能以暴力的形式获得解脱;所谓的“自由”,就指的是不再为谋生或维持生命而奔波,自然,在古希腊的城邦,那些衣食无忧的人都是一些具有公民身份的人,也可以理解为后来的贵族。而政治从来不仅仅是为了生存,它是为了生活,或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从前政治的必然性的驱使中解脱出来。这也是革命不得不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这种解脱的一个结果就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在界限上的消失,因为“社会”的出现同时取代了家庭和广场;原本属于私人的事情变成了公共的事情,而所有人的平等(同质化的同一)则取代了原本属于贵族们只有通过政治参与才能获取的平等,同情取代了尊重,人民取代了公民。这里面重要的地方在于对“同质化的同一”的理解,因为这种“同质化”在消灭了多样性的同时,也毁掉了个性、特征这些努力要使自己表现得卓越的“客观联系”,因为随便“你做什么对其他人来说都没有影响,或者从字面上来说,没有兴趣”。这当然也就意味着一个可政治参与的公共领域的消失。政治成了一个单纯地想达到什么目的,于是只能在手段与目的框架内,以成王败寇为价值取向的少数人最后化简为一个人的活动。所以西方的政治哲学史家大都认为在希腊化、古罗马时代是无政治可言的,因为没有了众人的参与。但这并不等于就没有了个人的尊严。尊严来自于基督教的世界观,基督教的一个核心信念就是普遍的人类尊严。这同时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基督教是站在被侮辱、被损害与被践踏的弱者一边的;他们没有权利可言,也几乎没有人权的概念与意识,有的就只是尊严。这同时说明了,为什么在阿伦特眼中,并不存在天赋人权、自然权利之类的东西。塞瑞娜·潘琳补充说:“只有当人类尊严向现代性挑战的时候,人权才会表现为捍卫尊严的一种方式。在这一意义上,人权是对人类尊严的特别堕落的一种反应。”国家当然是人类需要的产物,当维持并压制住社会的同质化同一并继续垄断政治领域的公共空间时,那即是阿伦特所理解的极权主义了。
这里面可能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在现代性危机的总体背景下,人们是否又表现出某种渴望回到古代社会的精英主义立场?二是在中国式的、古代传统的家国体制下,家庭这一必然的、暴力的、前政治的欲望满足方式是如何演化为现代性中的中国政治模式的?我们是否能按照欲望的满足(比如承认问题,比如尊严问题)从“是”中推论出价值的“优劣”?按照王海明教授在《国家学》中的分析,国家本来不过是社会的下位概念,即国家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但由于国家又是拥有最高权力的社会,所以便具有了可怕的强制性力量。这种力量作为一种欲望,也需要获得承认。获得谁的承认?自然是该社会成员的承认。与此同时,王海明教授再引用邓初民的话说:“政府不过是执行政治任务、运用国家权力的一种机关罢了。”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最习以为常的,恰恰是政府代表着国家,国家代表着社会:也就是执行机关(政府)取代了它的主权(国家),而主权又取代了它的委托者(社会)。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事实上,这里都存在着一种颠倒。在此颠倒下,承认就发生了颠倒,个人的尊严也就变成了不得不让别人臣服的尊贵。
既然社会的兴起以及公私两领域的衰落是现代性的突出特征,那么如何重建我们的公共世界也就成为了一个现时代的重要议题。阿伦特作为一位现象学家,也就把对政治现象的关注贯穿于她的所有作品之中,而且时时处处不忘“回到事物本身”的原始意图。于是,按照胡塞尔关于“他人就是现象学的自我变体(modification)”(这几乎与拉康对于“小他者”的定义一模一样)的说法,就从“我”与“自我”的关系(内省)扩延为生活世界与主体间的关系,并把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感与作为前提和结果的公共领域联系在了一起;而其间的不同于劳动与制作的“活动”、能把人类活动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靠性如其所是地保存下来的“承诺”、不同于自我相统一的“判断”就使得共通感、共同领域与公共世界的重建在理论上成为了可能。它同时也构成为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基本架构。
最后让我们引用《极权主义的起源》第458节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因为尊重人的尊严意味着承认我们的同伴或者同胞(fellow nationals)都是主体,是世界的建造者,或者共同世界的共同建造者。”
对我们来说,要如康德当年一样追问的,其实就是:在现有条件下,一种有意义、有尊严的生活到底县如何可能的?
(责任编辑:谢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