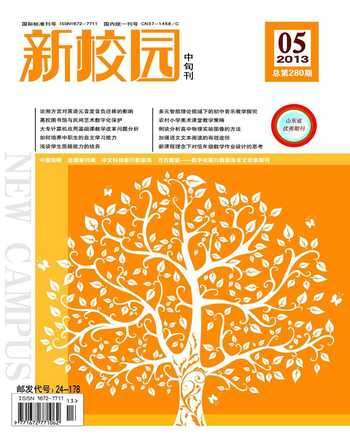上海通社成立缘由及其与上海市通志馆的关系
陈鸿 俞秋玥
摘 要:上海通社,是研究上海史的一个民间学艺团体,成立于1934年2月。该团体的主要成员即为当时上海市通志馆1编辑部的同人,按照柳亚子的说法,“上海通社和市通志馆的关系,正是孪生的姊妹呢”。2上海通社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上海的掌故历史及搜集、保存关于上海史的资料,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影响颇大。
关键词:上海通社;上海市通志馆;缘由;关系
上海通社活跃在1934年至1938年这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是当时上海市通志馆编辑部的同人们在馆长柳亚子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成立的一个立志于研究上海掌故历史的民间学艺团体。
今日,也许不会有许多人还记得这个团体,而且有的人还误会其为上海市通志馆下属的一个机构。其实,上海市通志馆是当时南京中央政府下辖的机构,是官方的组织;而上海通社则是个民间团体。两者虽不是从属关系,但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上海通社的成员,主要是来自于上海市通志馆编辑部,通志馆馆长柳亚子在《上海研究资料叙》中如此说道:“上海通社是徐蔚南、吴静山几位先生所发起的,通志馆编辑部的同事们差不多完全加入。”3
可以说,两者的成员是重叠的,其工作及研究的范围和方向也是相近的。用柳亚子的话来说,“上海通社和市通志馆的关系,正是孪生的姊妹呢”。4
然而,通志馆的同人们既为通志馆工作,为什么还要另外重新成立了上海通社这样一个团体呢?
通志馆和上海通社可以说是有着血缘上的亲密关系,但前者为公,后者为私,两者在体制上的区别还是显而易见的。这里,我想有必要先说明下通志馆成立及运作过程中的情况,可以有助于说明通志馆与上海通社的关系。
1932年成立的上海市通志馆,其编辑部主要有徐蔚南、吴静山、胡怀琛、蒯世勋、席涤尘、蒋慎吾、李纯康、顾南农、郭孝先、胡道静及后来加入的徐蘧轩等人。而上海通社的成员除与之基本相同外,还有少数几位非通志馆的人员。5
上海市通志馆的成立,经历了一段波折,其间的种种,也是促使上海通社成立的原因之一。6柳亚子被聘为馆长时,通过其好友邵力子对市政府提出多项要求,由此才肯担任馆长一职。
通志馆编辑部的编纂们,立志于探索和研究上海史,而作为“公”的通志馆,往往要受到政府的制约。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以修志为目的而成立的通志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特别是经费的问题,如果是修好通志的话,通志馆也难逃被撤消的命运。据当时的编辑胡道静回忆,普通编辑或以下的人员如果没额外收入的话,生活并不宽裕。7因此,编辑们便想出了一条后路:“准备将来不依靠政府拨款,自己搞一个研究上海历史的民间机构,而这个机构的培育就从现在开始,这就是组织上海通社。”8此即为: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1934年2月,上海通社白手起家,通过徐蔚南与《大晚报》总编辑曾虚白洽谈之后,在《大晚报》上开辟了一个周刊,以《上海通》9为名。主编具名为“上海通社”,所得稿费都统一存在银行里,当作上海通社的公积金。在这一天,上海通社便以出版《上海通》周刊的形式,宣告团体的正式成立。
上海通社是个松散的组织,没有任何形式上的规定和约束,原则上,志愿以“上海通社”名义发表文章的即为社员,从来没有过社员的名单表。上海通社虽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它利用的却是上海市通志馆的资源,包括人力以及资料、工作地方等。《上海通》周刊问世之后,主要是刊登关于上海掌故历史的文章,也有关于社会政治、自然地理和人物传记等,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于是,在1936年5月及1939年8月,由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上海研究资料》及其《续集》,前者16门共48篇,后者14门共73篇。
而在1936年,为了保存一些珍贵和罕见的史料,上海通社根据上海市通志馆几年以来所积累和搜集的图书资料,用上海通社一年多以来积存起的公积金,由胡朴安主编,以上海通社的名义出版印行了《上海掌故丛书》第一集,共十册十四种三十一卷,包括有(元)陈椿辑《熬波图》等。
通志馆搜集的上海史料的珍本秘籍,远不止这些,所以上海通社在完成首集的编校工作之后,又计划部署了第二集共七种的工作,拟定了(清)徐璋募刊《云间邦彦画像》不分卷等目录。10但由于经济原因以及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导致第二集无法出版。
没有上海市通志馆这个机构的成立,也就不会聚集起这样一批致力于上海史志研究的编辑们,更不可能“诞生”出这样充满活力的民间团体——上海通社。
注释:
[1]上海市通志馆,成立于1932年8月,是当时上海市政府为编纂《上海市通志》而成立的一个机构,柳亚子和朱少屏分任正副馆长。
[2][3][4]柳亚子:《上海研究资料叙》《上海研究资料》,上海通社编著,上海书店1984年1月影印本。
[5]据《上海研究资料》正续两集的作者目录来看,有撰写《申曲研究》的吴企云,撰写《明褚东汀铜墓志书后》的孙鉴以及撰写《读华泾访古记后》的金世德。
[6]可参见袁燮铭:《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始末》《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6期。
[7][8]胡道静口述,袁燮铭整理注释:《关于上海通志馆的回忆》《史林》,2001年第4期。
[9](一)通者,通晓也。这是说,我们这个周刊是通晓、精通上海的凡百事务的。(二)“上海通”这三个字是从“上海市通志馆”这个馆名中取出来的,暗示二者两位一体。
[10]胡道静:《上海通社纪事本末》《档案与历史》,1989年第4期。